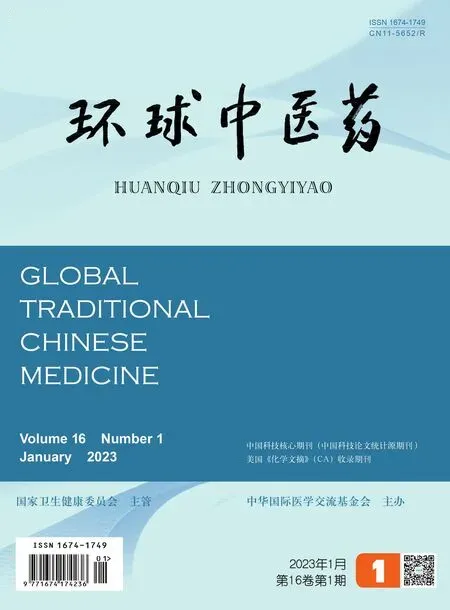中醫疫病經典防治理論研究現狀述評
周凱男 孫帥玲 馬曉北
中華民族歷史上每當發生重大瘟疫流行,中醫藥都在其防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歷代醫家面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時,都是在繼承前人防治疫病經驗的基礎上,針對當時疫病特點,不斷地創新與發展中醫藥防治疫病的理論與手段,產生防治疫病的新理論和新方法,最終以著作的形式流傳至今。《傷寒雜病論》即為張仲景在東漢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時,根據其診治過程與施治方藥整理而成,提出以六經辨證治療傷寒。《溫疫論》則是吳又可在明末崇禎年間疫病流行時,在以傷寒之法治療無效的情況下,根據臨床觀察病證表現大膽創新而成,提出“異氣”“戾氣”病因說、“邪氣初在膜原”病位說以及“表里九傳”辨證方法。清代“溫病四大家”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提出溫病辨病、辨證方法,如葉天士《溫熱論》“衛氣營血辨證”和吳鞠通《溫病條辨》“三焦辨證”等,豐富發展了疫病理論與實踐。
2002年至今,不斷有新發突發傳染病小范圍或是全球范圍內的流行,如非典型性肺炎、甲型H1N1流感、H7N9型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等,中醫藥均積極參與其中并有效降低了病死率。2020年起在全球范圍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至今已持續三年。目前為止,針對新冠肺炎尚沒有確認有效的抗病毒治療方法,疫苗也還不能完全阻斷疫情的傳播。新冠肺炎出現以來,中國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顯著地低于國外[1],中醫藥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近二十年有關中醫藥防治疫病的臨床、實驗及理論研究繁多,其中有關疫病經典防治理論進行研究主要圍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本文就此做簡要評述。
1 古今融合,拓展疫病文獻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中醫疫病古籍文獻是數千年中醫疫病理論和實踐精華的載體,是中醫臨床證據的主要來源,是中醫學術傳承發展的重要依據。收集和整理中醫古籍疫病文獻,挖掘現代疫病的共性認識及特點,探索古今疫病理、法、方、藥之間的內在聯系,能為現代疫病的臨床防治提供理論依據,從而為現代急性傳染病的診療、防治拓寬思路。張萌等[2]提出基于中醫文獻多樣性、復雜性的特點,古今疫病文獻研究應采取傳統文獻研究與現代數據挖掘技術相結合的方法。
1.1 應用傳統文獻研究方法進行疫病文獻研究
有學者從歷史文獻的角度進行研究,如陳仁壽等[3]通過對古代有關疫病的非醫藥文獻和醫藥文獻進行了研究,發現古代防治疫病方法多種多樣、用藥靈活、針對性強。他通過對中醫藥辨治疫病的歷史回顧發現,傷寒與溫病中包括疫病的內容,疫病有寒疫、溫疫與雜疫之分;疫病成因有多種學說,如非時說、運氣說、乖戾說、六淫說、邪毒說、正虛說[4]。楊榮源等[5]以中醫歷代文獻為依據,采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對中醫防治肺系疫病的學術內涵和理論展開探討。
有學者基于中醫古籍文獻對疫病的病名進行了分類考證,如劉珍等[6]認為,歷代疫病種類繁多,其病名及內涵不斷演變和發展,在各個時代有所不同,存在病名概念模糊、病名不統一的問題。他們基于中醫古籍疫病理論,從疫病名稱的古籍出處、古籍內容等方面對疫病、疫癘、瘟疫、溫疫和肺癆、大頭瘟等肺系疫病,痢疾、黃疸等消化系疫病,天花、麻風、鼠疫及動物傳染性疫病等疫病名稱進行了考證辨析。
1.2 結合數據挖掘等新技術進行疫病相關中醫文獻研究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研究者需要將傳統的文獻整理研究方法與現代數據挖掘方法、互聯網技術等結合起來進行中醫疫病文獻數據的深度挖掘與開發。如彭麗坤等[7]收集明清兩代部分醫籍、醫案、醫話總共8本559例治疫處方,將其中關于疫病癥狀、用藥方面的資料進行整理、歸納及規范,運用因子分析的數據挖掘方法對收集的資料進行挖掘,得出疫病與人體體質密切相關,疫病總屬熱邪為患,最易傷及營血,疫病多屬危急重癥、病情復雜變化多端等規律。鄧雪儀等[8]系統建立了古代肺系疫病文獻數據庫,發現古代肺系疫病與本次新冠肺炎診療方案辨證分型雖不盡相同,但高頻用藥多為清熱藥、解表藥,處方規律則將瀉火解毒改為辛涼宣肺,注重顧護胃氣。
2 研究疫病之中醫病名,病證結合確定中醫疫病研究之基本路徑
中醫理論中的每一個概念,都不是一個簡單的符號,而是對某個理論的高度概括從而形成其代稱,因此具有豐富的內涵。中醫疫病病名也不例外,它不是簡單地作為疾病辨識符號來加以使用。中醫疫病病名的確定與使用,實際上與具體的中醫疫病理論相聯系。換言之,某個具體中醫疫病病名就是某個具體中醫疫病理論的映照,這就是疫病研究中要首先研究疫病病名的意義所在。
中醫學在面對新發、突發傳染病時,在提出具體的診療方案之前,首先必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即目前所發生的這一傳染病在中醫學中屬于哪一類疾病中的哪一種疾病?這需要醫者基于這一傳染病的當下臨床表現和發病特點,與中醫古代疫病經典著作中的疫病命名原則和相關具體疫病的概念、臨床表現等進行比照分析,確定其病名,并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分析病因病機,確定治則治法,從而提出治療方案。因此,正如《傷寒論》中“辨某某病脈證并治”一樣,醫者在確定針對某一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診治方案時,都必須先辨病、再辨證、辨病與辨證相結合。
陳仁壽[4]通過對中醫藥辨治疫病的歷史回顧發現,古代疫病的名稱較為復雜,又稱癘病、天行、時行。劉鐵鋼等[9]指出,新冠肺炎的中醫命名目前有疫病、瘟疫、寒疫、寒濕疫、寒濕肺疫、濕瘟、濕疫、濕毒疫、溫疫、濕熱疫、肺瘟、風瘟、冬溫、風溫夾濕之疫癘、木疫等。經分析,該病的中醫命名可統稱為疫病、瘟疫;根據病證性質和病機特點可命名為“濕毒疫”,能夠反映濕性病證貫穿始終、瘀毒阻滯的疾病特點。楊薇等[10]提出了基于吳又可“雜氣說”命名新冠肺炎的建議。范逸品等[11]認為本次新冠肺炎更符合寒疫特征,同時提出本病可分為兩個階段,2019年11~12月屬于寒燥疫,2020年1月及以后屬于寒濕疫。
對中醫經典著作中疫病病名進行考證,梳理中醫疫病辨病的原則與方法,結合現代疫病防治研究規范中醫疫病病名,可以為辨病與辨證相結合診治疫病確定基本路徑。
3 研究傳統中醫疫病辨治理論,提出現代中醫疫病防治新方案
3.1 研究古代名家名作經典辨治理論,總結古代中醫疫病防治相關理論
當代學者通過對于中醫經典著作和代表性醫家防疫思想、理論和臨床經驗的深入研究,豐富和完善了中醫疫病經典理論方法與實踐,凝練出中醫疫病防治理論優勢與特色所在。
有學者研究了《黃帝內經》中的防治疫病思想。岳冬輝等[12]發現,《內經》中闡述了運氣變化與疫病發生的相關性、疫病的病因病機、疫病的發病規律及疫病的防治等內容。黃玉燕等[13]提出,《內經》認為疫病發病與天、人、邪三方面因素有關,人的正氣虛又逢氣候、運氣失常時則易感邪而發病。對疫病的病因病機應根據臨床表現分析,也可結合運氣學說根據發病時間分析。
有學者對張仲景疫病理論進行了研究。王東軍等[14]認為張仲景疫病理論寒溫同具,其疫病理論可見于《傷寒論·傷寒例》《傷寒論·辨脈法》及《溫熱經緯·仲景疫病篇》。有研究者認為,郭雍《仲景傷寒補亡論》在疫病發病理論方面與前人相較多有創新[15],是書將疫病稱為時行,將流行性和氣候失和作為判斷疫病的標準,論及寒溫兩類疫病,并強調寒溫分治。
李董男[16]研究發現,金元四大家認為疫病因正虛邪實而發病,提出疫邪秉天地而成、趁體虛而入、因情志而甚,以扶正祛邪為基本治疫原則。劉完素倡導施用寒涼祛邪,李東垣則強調顧護脾胃、扶助正氣、甘溫除熱,朱丹溪寒溫同用。疫病全程需顧護脾胃,謹慎使用寒涼藥物,堅持中醫“治未病”理念,增強人體正氣,調暢情志。
有學者研究了《溫疫論》疫病防治思想。趙克勤等[17]認為吳又可明辨傷寒時疫與溫疫不同,使溫熱病從傷寒體系中脫離出來,許多理論和觀點對清代溫病學家影響極大。張獻忠等[18]認為,《溫疫論》破除了將瘟疫混同于傷寒的傳統理論,極大推進了對于瘟疫的科學認識。
黃玉燕[19]總結了傳統的疫病傳變理論,提出疫病有多種獨特的傳變規律,可概以六經傳變、表里傳變、三焦傳變、十二經傳變、衛氣營血傳變等。
3.2 結合新冠肺炎等新發疫病之臨床實踐,總結中醫疫病防治經驗與方法
有學者針對新冠肺炎的辨治進行了分析研究。劉淑真等[20]運用傷寒和溫病經典理論,分析了新冠肺炎的中醫病因,并應用兩大理論體系的六經及衛氣營血辨證闡述其病機及傳變規律,選取有效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方藥,結合臨床實際效果,分析總結應用于各證型的方劑。趙鋼等[21]認為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機為疫癘之邪犯肺,正邪相爭,阻遏衛氣,由表入里,發病因素主要包括正氣因素、自然因素以及社會因素。中醫治療以祛邪扶正為大法,分輕型、普通型、重型及危重型,采取辨證論治。李明陽等[22]分析發現,此次新冠肺炎主要以濕毒為主,濕邪影響肺,處方基本以麻杏甘石湯加葶藶子、蒼術、藿香貫穿始終,以提高肺宣降功能、祛濕為主。本病各期主要定位均以肺、脾胃為主,通過各期臨床癥狀,進行肺、脾胃補瀉,配合相應藥物進行辨證論治,并遵循“衛、氣、營、血”傳變規律進行防治。賈振華等[23]提出新冠肺炎病位在肺,病因為感受“冬溫之毒”,從口鼻而入,侵襲肺絡;指出疫毒襲肺、邪熱壅肺、毒熱閉肺為其核心病機。
有學者針對肺系疫病診治展開了研究。王永炎等[24]認為,中醫學認識肺系疫病應有一定的時間、空間觀念,不能被病原體所困擾,而應著眼于病因的產生、病因與機體的相互作用,從病因作用于機體后出現的證候來把握病因、尋求治法。吳兆利[25]認為,應在繼承中醫經典理論基礎上,循于經典,不囿于經典,探析肺系疫病的發病規律,要根據具體疫病的本身演變規律來認識疫病的本質。鄭齊等[26]提出,中醫肺系疫病診療理論經歷了在傷寒理論范疇內的孕育、從傷寒理論體系逐漸分化、病機治法理論在宋金元時期的進一步發展、伴隨明清溫病理論體系的發展以及西學東漸至新中國成立后的發展五個階段。
3.3 基于中醫疫病防治的經典理論和現代臨床實踐,發展疫病防治理論
周仲瑛提出以“疫毒”為病機辨證核心,確立疫病的辨治方法,認為疫毒是外感而來,兼夾六淫之邪侵犯人體后引動內伏之邪,可在體內化濕、生痰、致瘀、傷陰,與濕、熱、寒、痰、瘀等病理因素相互膠結,構成疫病的復合病機[27]。楊映映等[28]基于仝小林院士診療疾病的指導性思想“態靶辨證”,從“態靶”的角度去審視疫病之因,并探討“疫邪”(對疫病病因的綜合性稱謂)的致病特征。方邦江等[29]率先提出了新冠肺炎“急性虛證”病機理論,倡導“全程補虛”的新冠肺炎中醫防治策略,制定了“急性虛證”病因病機、治療原則、代表方藥等。在中醫危急重癥領域內有關“全程補虛”的闡述,不僅是疫病治法上的突破,也是對中醫外感熱病內容的豐富和充實,是中醫外感熱病理論的新發展。
4 緊扣中醫疫病研究的關鍵問題,實現中醫疫病研究的新突破
4.1 發現中醫藥防治疫病研究的關鍵問題,明確未來疫病研究重點領域
當代中醫在疫情防控中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和醫療環境不同于古代。目前,中西醫兩套醫療體系為人民健康保駕護航。此次新冠肺炎的防治就是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并且取得了較好的防疫效果,中醫藥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更好地發揮中醫藥防疫的特色與優勢,需要中醫臨床者認真總結此次防疫中的經驗,更重要的是發現中醫藥防治疫病中還存在哪些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在今后的中醫藥防治疫病的研究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中醫臨床者需要抓住關鍵問題深入研究,進一步優化中醫疫病防治的理論和方法。
杜宏波等[30]認為目前傳染病的中醫預防理論缺乏完整體系,其方法眾多但基礎研究及系統評價不足。劉辰昊等[31]提出中醫藥臨床證據和中醫藥療效的科學評價體系不足,中醫藥第一時間防治疫病的機制亟待完善,優勢資源整合不足,信息化體系建設不夠,中醫藥防治疫病基礎保障體系建設亟待加快,中醫藥疫病防治人才培養不足。何偉等[32]提出,未來中醫疫病研究的重點領域及關鍵問題是堅持中西醫協作救治的疫病聯防機制、全面規范開展中醫藥防治疫病臨床研究、建立系統的中醫疫病學理論體系、探索中醫疫病發病風險預警方法等四個方面。
4.2 整合現代科學研究新方法,實現中醫疫病理論研究的新突破
古代醫家在預防和治療疫病的實踐中形成了許多有效的防治經驗,如何將這些經驗總結提煉上升到理論上的突破,并在醫學界形成共識,就需要高質量的臨床研究證據,需要引入交叉學科的研究方法,借鑒現代傳染病研究方法與多學科協同交叉研究方法,加強中醫疫病理論內涵研究,力求實現中醫疫病理論研究的新突破。
董斐等[33]提出,今后研究應著眼于將循證醫學的理念和方法整合到中醫疫病研究中,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產出高質量臨床研究證據,探索中醫與西醫的有機協同,實現最佳的疫病診療效果,提出循證中醫疫病學建設思考。谷曉紅[34]認為,應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思路,通過加強跨學科和跨部門研究合作,實現知識的匯通和整合,發揮中醫疫病學在應對新發、突發疫病方面的作用;采用多學科技術和手段研究和解決中醫藥防治疫病的關鍵科學問題,揭示中醫藥治疫療效的關鍵科學內涵,實現中醫特色防治疫病新設備、新工具的應用,提出中國特色的疫病防治康方案。杜宏波等[30]認為,以現代傳染病規律為基礎,多學科協作,做好基礎貯備,可提升中醫疫病精準預防及治療能力,而加強中醫疫病理論內涵研究與多學科基礎研究儲備是中醫疫病事業未來發展的方向。鄧凱文等[35]認為,通過對隱藏在中醫藥疫病防治理法方藥的超分子作用規律進行分析,探討其現代化關鍵科學問題并提出解決策略,有望闡明中醫藥疫病防治的科學原理,研制出組分中藥,加速疫情控制。
5 以中醫經典理論為基礎,構建現代中醫疫病防治理論新體系
中醫學歷史上,疫病經典防治理論有傷寒和溫病兩個體系,溫病防治理論體系中又包含兩類,即以是否具有傳染性和流行性而分為溫病與溫疫兩個亞體系。因此在當代中醫面對新發突發傳染病時就有著多個防治理論體系的選擇與實踐的問題,迫切地需要新的統一的防治理論體系的構建,尤其是在本次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時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本文認為應該是以臨床療效為唯一標準,探索將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表里九傳辨證等融合統一后構建現代中醫疫病防治理論新體系。
郭玉琴等[36]提出,傳統溫疫學派學術思想駁雜而有失系統化。從辨癥論治急治標、辨證論治重病位、辨病論治鑒寒溫、辨舌論治知應下、辨體論治明常變、審因論治搗病源六個方面,總結溫疫學派代表醫家的多元辨治思維,嘗試建立“癥-證-病-舌-體-因”一體化的溫疫綜合辨治模式。孫伯欣等[37]提出瘟疫辨治理論創新應繼承和發揚中醫瘟疫理論辨證與辨病施治的優勢,貫徹中醫“治未病”思想,重視藥物配伍規律的研究,以及中藥劑型的改革,積極開展對各種傳染性疾病的防治研究。結合現代醫藥技術,充分發揮中西醫結合防治疫病的優勢。谷曉紅[34]提出要加強中醫藥核心理論引領,系統整理挖掘寶貴的疫病學術思想及經驗,構建中國特色疫病防治理論體系。杜宏波[30]認為中醫疫病理論體系是一個比對數據庫,其以經典理論為依托,以現場調研為基礎,圍繞核心病機配合個體化辨證的防治體系,對于新發傳染病的防控是一種成功模式。
6 結語
在中醫防治疫病的歷史上,如果說東漢時期《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和明清時期《溫疫論》的表里九傳辨證、《溫熱論》的衛氣營血辨證和《溫病條辨》的三焦辨證分別是中醫疫病防治理論的兩次重大突破的話,此次新冠肺炎的中醫藥防治實踐,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下,中醫藥人防治疫病的一次成功的生動實踐。基于已有的中醫防治疫病的經典理論,全國的中醫藥工作者在臨床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諸多新理論與新方藥,這就對傳統的中醫疫病經典防治理論提出了新挑戰,需要我們加強中醫疫病防治理論的研究。中醫疫病防治理論研究應該是在挖掘整理研究中醫經典防治理論為核心的基礎上,結合現代傳染病防治認識與研究方法,構建中醫疫病防治新體系,從而形成中西醫有機融合的傳染病防治體系,服務于現代傳染病衛生防疫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