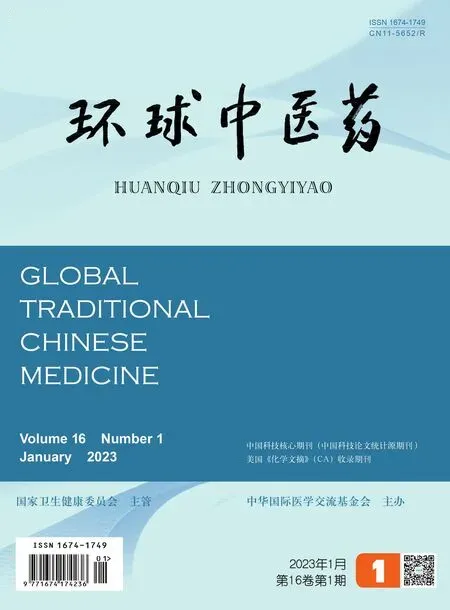從葉天士辛潤通絡法論治類風濕關節炎
陳霞 何曉芳 鄭新璐 陳自佳 韋尼
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種原因不明的全身性自身免疫病,可發生于任何年齡,中國發病率約為0.42%[1]。RA屬于中醫“痹病”范疇,目前認為RA的病機以本虛標實、虛實夾雜為要點,其中氣血虧虛為發病之本,風寒濕邪、痰濁、瘀血痹阻絡脈是發病之標,而絡脈不通是病機關鍵[2]。RA病程遷延日久,可導致關節疼痛纏綿反復,并耗傷臟腑氣血,符合“久病入絡”“久痛入絡” 的絡病發展規律,故不少學者主張RA當從絡論治。“辛潤通絡法”由清代名醫葉天士創立,首見于《臨證指南醫案》,是其為“絡病”所制定的治療大法,目前廣泛地運用于多種內傷雜病的治療中。筆者認為從葉天士辛潤通絡法論治RA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不僅能為RA的辨證論治帶來了新的思路與方法,提高中醫藥治療RA的療效,而且還有助于擴大辛潤通絡法的運用范圍,更好地繼承及發展葉天士的學術思想。
1 辛潤通絡法的發展源流
1.1 “辛潤”的定義
“辛潤”,即“辛以潤之”,其理論源自《素問·臟氣法時論篇》“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曰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后世歷代醫家對此進一步闡發,唐代醫家王冰有“辛性津潤”“辛亦能潤能散”之言,金代醫家張從正也有“辛能走氣化液”之說。明代醫家繆希雍在《本草經疏》中云“桂枝、桂心、肉桂,夫五味辛甘發散為陽,四氣熱亦陽……辛以散之,熱以行之,甘以和之,故能入血行血,潤腎燥”;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亦言“肉桂下行,益火歸源,此東垣所謂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其氣者也”。張景岳則在《類經》中進一步總結道:“腎為水臟,藏精者也,陰病者苦燥,故宜食辛以潤之。蓋其能開腠理致津液者,以辛能通氣也。”目前認為,“腎苦燥”是由于腎病導致陽氣不能蒸化、敷布水液,而發生“干燥”癥狀。“辛潤”理論是指運用辛味藥物“潤燥”,其核心在于通過辛味藥物的溫通、發散、開腠、通絡等作用使人體陽氣充沛流暢,水液得以正常輸送布散,從而達到“燥者潤之”的治療目的[3]。
1.2 辛潤通絡法的來源
葉天士深受《黃帝內經》與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學術思想的影響,對雜病的辨證論治以臟腑經絡氣血陰陽為綱,以“臟腑陰陽升降—在經(氣)入絡(血)—奇經”為軸,形成了極具特色的絡病學說[4]。葉天士認為絡病的病理實質為“不通”,應以“通絡”為治療原則。但絡脈系統支橫別出、絡體細窄,呈網狀逐級細分,且氣血流緩、易滯易瘀,當各種內外病因損及絡脈導致“不通”時,具體又可表現為“不得通利”與“不得榮養”兩種病理特征。葉天士繼承了歷代醫家對“辛潤”的定義,主張“絡以辛為治”“絡以辛為泄”,旨在借助辛味藥辛香走竄、橫行入絡、散結潤燥的特性以達到“通絡”的目的。但葉天士對“辛潤”認識并不拘泥于此,他還強調“凡久恙必入絡,絡主血,藥不宜剛”,在絡病的治療中不能一味使用辛燥耗氣傷陰之品,當與體潤之藥配伍,既可既通絡又能避免傷及氣血。由此可見,葉天士辛潤通絡法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通過辛味藥“能散能潤能橫行”的特點治療絡病,二是將辛散之品與柔潤藥物相配伍治療絡病,而以上兩方面的最終目的都在于確保通絡而不傷正[5]。
1.3 辛潤通絡法是絡病的治療大法
絡脈是氣、血、津液運行的通道,邪氣侵襲人體,首先侵及絡脈,并通過絡脈由表及里,傳入臟腑。葉天士認為治療絡病當宗《黃帝內經》“疏其氣血令其條達”之旨,以“絡以通為用”指導原則,但絡病病位狹細幽深,非辛味不能達病所,同時絡脈細微易損易傷,非滋潤之品不能濡養,故主張以通絡辛潤通絡法為絡病的治療大法。《臨證指南醫案》中收錄了葉天士運用辛潤通絡法治療的20多例病案,其中大多為痛癥或以疼痛為主要癥狀的疾病,如脅痛、胃痛、痹征、積聚、郁證等。葉天士臨證多以仲景旋覆花湯為主方,以旋覆花、蔥白等辛味藥配伍當歸須、桃仁、柏子仁、紅花、赤芍、牡丹皮、茜草、澤蘭、延胡索、小茴香、肉桂、鹿角霜等,強調“用辛理氣而不破氣,用滑潤燥而不滋膩氣機,用宣通而不拔苗助長”。華玉堂在《臨證指南醫案·諸痛篇》的按語對“辛潤通絡法”評價說:“癥之虛者氣餒不能充運,血衰不能滋榮,治當養氣補血而兼寓通于補……若撮其大旨,則補瀉寒溫,唯用辛潤宣通,不用酸寒斂墻以留邪。此已切中病情,然其獨得之奇,尤在乎治絡一法。蓋久痛必人于絡……此乃古人所未及詳言,而先生獨能剖析明辨。”名老中醫俞岳真先生也評價道:“絡為血絡,血為濡潤之質,故藥取辛潤,辛則能通,潤則入絡。”
RA屬于中醫痹病范疇,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指出“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痹,然經年累月,外邪留著,氣血皆傷,化為敗瘀凝痰,混處經絡,蓋有諸矣”,可見本虛標實、虛實夾雜為RA的病機要點,絡脈不通則是病機關鍵。其中不僅包括因氣血不足而致絡脈不通,也包括因外邪、痰濁、瘀血阻遏而致絡脈不通。因此,從辛潤通絡法論治RA可達標本兼治、祛邪而不傷正的目的。
2 辛潤通補絡脈
2.1 陽氣不足、氣血虧虛是RA的發病內因
陽氣不足、氣血虧虛是RA的發病基礎,現有研究顯示[6],RA患者屬虛性體質者居多,尤其以陰虛質、陽虛質和氣虛質為主。國醫大師朱良春認為RA發病過程多為陽氣先虛、腠理不密,外感風寒濕諸邪,盤踞經髓,深入骨節,阻遏脈絡氣血運行,尤其責之脾腎陽虛,治療上當以溫扶陽氣為首要[7]。婁多峰教授則認為在RA病情發展的不同時期,“虛”也各有偏重,如RA早期以陽氣受損失于溫煦、溫通為主,中期則逐漸由表入里,由氣及血,晚期多氣血俱虛,損及臟腑[8]。李露等[9]認為RA的核心病機責之于脾腎不足,應從“脾腎靶效應”論治RA,以運脾祛濕解毒通絡和補腎強骨活血通絡為主要治療原則。《醫法圓通》云:“陽者,陰之主也,陽氣流通,陰氣無滯。陽者,陰之根也,陽氣充足,則陰氣全消,百病不作,陽氣散漫,則陰邪立起。”由此可見,RA起病多因先后天因素導致陽氣受損,外邪侵襲,痹阻絡脈,此后逐漸傷及臟腑氣血,最終導致機體陰陽俱虛。
2.2 辛潤兼顧溫通與溫補
RA是一種異質性很強的疾病,可發生于任何年齡段,且不同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癥狀體征、疾病轉歸等均存在較大差異,這就決定了RA患者既有整體陽氣虧虛的陽氣絕對不足者,也存在因局部陽氣流通不暢導致的陽氣相對不足者。因此,在RA治療中當溫補陽氣與溫通陽氣并重,不可偏廢,而辛潤通絡法可通補絡脈,兼顧溫補與溫通。辛味藥大多性溫熱善走竄,補中有行,行中有補,如附子、桂枝、續斷、巴戟天、補骨脂、淫羊藿、菟絲子等。一方面,此類辛味藥通過溫補陽氣強壯先后天之本,也為陰精源源不斷的產生提供了物質基礎,即“善補陰者,必于陽中求陰,則陰得陽升而泉源不竭”,機體氣血充沛、陰陽調和則可既病防變,避免RA病情進展;另一方面,此類辛味藥通過溫通陽氣可避免風、寒、濕等邪氣進一步循經入里,變生痰濁、瘀血等有形之邪,正如近代醫家丁甘仁所言“陽氣不到之處,即濁陰凝聚之所”。此外,對于已經表現出營血不足、不榮絡脈的RA患者,則需要聯合質潤之品,臨證可根據辨證類型選擇甘寒質潤之品,如生地黃、知母、麥冬等;或溫潤之品,如熟地黃、枸杞子、山茱萸、黃精、桑葚、肉蓯蓉、炙百合等;或選擇血肉有情之品,如鹿茸、鹿角膠、龜板膠等。這也與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反復強調的“大凡絡虛,通補為宜”原則相一致。
筆者在臨證治療多以桂枝配伍鹿茸或鹿角膠溫通、溫補絡脈。中醫大家曹穎甫曾言“蓋孫絡布滿腠理,寒郁于肌,孫絡為之不通,非得陽氣以通之,營分中余液必不能蒸化而成汗,桂枝之開發脾陽其本能也……皆宜桂枝”,而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多用桂枝治療痹病,取其“溫通脈絡”之意,現代著名中醫風濕病學者周乃玉教授臨證治療RA,主張“通陽主用桂枝”“扶陽首選附子”[10]。鹿角形似樹枝,如絡脈支橫別出,葉天士也有“鹿茸壯督脈之陽”“鹿霜通督脈之氣”“鹿膠補腎脈之血”之說。由此可見,鹿茸、鹿角膠為通補絡脈之佳品。桂枝配伍鹿茸或鹿角膠是辛潤通絡法的重要體現,一方面,辛甘合用可扶陽,氣旺則營血自生;另一方面,質潤之品可防止辛味藥溫燥耗氣傷陰,而辛味藥也可避免質潤之品滋膩礙胃,阻遏氣機。
3 辛潤祛邪通絡
3.1 風寒濕外邪侵襲是RA發病的外因
《類證治裁·痹證》云“諸痹……良由營衛先虛,腠理不密,風寒濕乘虛內襲,正氣為邪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滯,氣血凝澀,久而成痹”;《儒門事親·痹論篇》亦云“此疾之作……太陰濕土用事之月,或凝水之地,勞力之人,辛苦過度,觸冒風雨,寢處浸濕,痹從外入”。由此可見,風寒濕等外邪是導致RA發病的重要外在因素。馮興華教授[11]認為祛邪是RA的基本治法,其中祛除風寒濕等外邪最為基礎,也最為關鍵。
3.2 辛潤祛邪而不傷正
辛味藥多入肺經,能行能散,具有較好的發汗解表祛邪的功效,如麻黃、桂枝、荊芥、防風、羌活、細辛、白芷、紫蘇、生姜、辛夷等,使風寒濕等外邪隨汗而解,是RA治療中的常用藥。辛味藥雖能解表祛邪,但其性“走散”,在祛邪的同時也易于耗散正氣而影響整體療效。《內經》云“辛甘發散為陽”,張仲景創立桂枝湯為此代表方劑,葉天士在張仲景學術思想的影響下,進一步將辛味藥與質潤味甘之品相配伍,可在解表祛邪的同時充分發揮甘緩益氣養營之功效,使發汗之力緩和而持久,解表祛邪而不傷正,如麻黃、桂枝、生姜、附子與人參、甘草、大棗、杏仁等合用。王欣妍等[12]分析了近10年以來治療RA活動期的處方用藥,結果發現桂枝+白芍、青風藤+白芍、蒼術+薏苡仁、蒼術+當歸等具有開腠解表的辛甘配伍藥對出現頻率位居前十位。中藥藥理學研究則表明,桂枝、荊芥等辛味藥的解表祛邪作用主要表現在抗病毒、抗菌、解熱以及協助發汗等方面[13],而附子與甘草、人參合用[14]、麻黃與杏仁合用具有減毒增效的作用[15]。
4 辛潤行津通絡
4.1 痰濕是影響RA病情進展的重要因素
痰濕是RA發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致病因素。在病情初期,風寒濕邪侵襲肌表,其中濕為陰邪且性黏滯,若不能及時由表而解,外濕最易傷脾,脾傷則健運失常,水濕內停,日久必成痰濕。范永升教授認為痰濕是RA病情進展的重要因素,濕邪阻絡為病機發展過程的重要環節[16]。肖紅等[17]則認為RA發病多因外邪乘虛而入,客于經絡骨節留而不去而化生痰濕,痰濕進一步痹阻經脈氣血,導致瘀毒內生,凝聚經隧。正如《臨證指南醫案》所云:“云痹者,閉而不通之謂也,正氣為邪所阻,臟腑經絡不能暢達,皆由氣血虧損,腠理疏豁,風寒濕三氣得以乘虛外襲,留滯于內,致濕痰濁血流注凝澀而得之。”陳士鐸也有“風寒濕之邪,每籍痰為奧援,故治痹者必治痰”之說。
4.2 辛潤化痰祛濕而不阻遏氣機
“諸濕腫滿,皆屬于脾”,痰濕的產生主要責之于脾,腎、肺、肝等臟也參與其中。首先,《素問玄機原病式》云:“辛熱之藥能開發腸胃郁結,使氣液宣通,流濕潤燥。”肺為水之上源主通調水道,肺的宣發肅降作用有助于水液向上下內外輸送;腎主水,水液的輸布代謝需賴以腎陽的蒸騰氣化作用,而中焦為水液代謝的樞紐,辛潤通絡法可開發腸胃郁結,打開通路,進而消除痰濕等病理產物,如蒼術、藿香、佩蘭、半夏、生姜、陳皮、厚樸、木香、烏藥、杏仁、砂仁等。此類辛味藥氣味芳香,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也有“久病在絡,氣血皆窒,當辛香緩通”“攻堅壘,佐以辛香,是絡病大旨”以及“欲宣內閉,須得芳香”之說。中藥藥理學研究發現芳香類中藥富含揮發油成分,能促進消化道黏膜血液循環,增加血流量,增強胃腸道蠕動功能[18]。還有研究顯示[19],芳香類中藥可通過芳香烴受體調節腸道免疫功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療的潛在通路;其次,肝主疏泄,調暢氣機,氣機充沛流暢是維護水液的正常輸布的關鍵,正如清代醫家周學海在《讀醫隨筆》中言“郁則津液不得流通,而有所聚,聚則見濕矣”。在RA治療中,若想有效祛除痰濕應重視多臟同調,確保氣機順暢。《儒門事親·卷一》云“《內經》云辛以潤之,蓋辛能走氣,能化液故”,辛潤通絡法可疏肝氣、調肝血,如柴胡、香附、郁金、佛手、香櫞、當歸、柏子仁、桃仁等。仇湘中教授[20]認為肝虛、絡痹、痰滯是RA病機關鍵,主張從肝論治,臨證多用柴胡、香附、佛手等辛味藥。李秦等[21]認為對處于更年期的女性RA患者,治療中運用具有疏肝理氣功效的辛味藥不僅可以改善關節癥狀,還能調暢情志,避免出現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
5 辛潤化瘀通絡
5.1 瘀血是導致RA病情加重的關鍵
《類證治裁》曰“痹久必有濁痰敗血,瘀滯經絡”,《醫林改錯》也有“瘀血致痹”說,在RA發生發展過程中瘀血既是一種病理產物,又一種致病因素。姜泉教授認為“瘀”為RA之終,是RA后期的病機關鍵,瘀血不去則新血難生,從而導致關節腫痛綿綿不絕,甚至骨損致殘[22]。路志正教授也認為痹證多夾瘀,瘀亦可致痹,一旦瘀血與痰濕結合,可化生毒邪,痹阻絡脈,傷筋損骨,耗傷氣血,治療上需加強化瘀通絡[23]。
5.2 辛潤祛瘀而生新
葉天士認為“絡主血”“血結必入于絡”,RA病情后期關節腫痛雖尚可忍耐,但持續存在,綿綿不休,且伴有關節強直畸形,此時病機以“虛—瘀”為特點。一方面表現為血絡瘀閉,不通則痛;另一方面則表現為舊血不去,新血不生,不榮則痛。此時治療以化瘀通絡為主,但也要意養血扶正。辛潤通絡法既可祛瘀通絡,又可滋潤養血,尤其適用于年老體弱、病史長久,或伴有氣血不足證候的RA患者。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常用青風藤、海風藤、雞血藤、忍冬藤、絡石藤、夜交藤等藤類辛味藥配伍當歸尾、阿膠、柏子仁、桃仁等質潤之品,他認為藤類辛味藥其形態特征與支橫別出、網狀分布的絡脈相似,因而可以入絡。正如《本草便讀》云“凡藤蔓之屬,皆可通經入絡,蓋藤者纏繞蔓延,猶如網絡,縱橫交錯,無所不至,其形如絡脈”;清代醫家吳鞠通也有“凡枝皆走絡,須勝于枝”之說。當歸性辛溫質潤,為補血活血要藥,其中當歸尾、當歸須活血之力尤強,《湯液本草》謂“尾能行血”,李杲也有“梢破血而下流”之說,且當歸尾、當歸須更易入絡,即葉天士強調治絡病用藥當選“有根有須者”。現有研究顯示當歸尾中揮發油、阿魏酸含量顯著高于其他部位[24]。對于瘀血較重者,還可使用蜂房、僵蠶、全蝎、蜈蚣、地龍等蟲類辛咸通絡藥,取“藉蟲蟻血中搜逐,以攻通邪結”之說,深入病所,搜剔絡中之敗瘀凝痰。筆者在臨床中發現,對于以上肢關節病變為主的RA患者,可選擇蜂房、僵蠶、蟬蛻等性升善飛而上行者;對于以下肢關節病變為主的RA患者,可選擇地龍、全蝎、蜈蚣等性降善爬而下走者。這正如葉天士所言:“其通絡方法,每取蟲蟻迅速飛走之諸靈,俾飛者升、走者降,血無凝著,氣可宣通,與攻積除堅,徒入臟腑者有間。”
6 結語
RA病機復雜,病情纏綿反復,可造成多系統損害,危害性大。RA久病久痛、病久內舍于臟的病情發展特點符合絡病久病入絡、久痛入絡的發展,因而可從絡病論治。辛潤通絡法是葉天士為絡病所制定的治療大法,從辛潤通絡法論治RA不但能借助辛味藥溫通、發散、開腠等功效達到祛邪通絡的目的,而且通過合理配伍質潤之品還可益氣養血通絡,使標本兼治、祛邪而不傷正。但需要注意的是,辛潤通絡法并非RA的唯一治療方法,因此要正確看待辛潤通絡法的適用范圍。辛味藥是辛潤通絡法的核心,起主要治療作用,而質潤之品處于從屬地位,這也就決定了辛潤通絡法更多地適用于辨證屬虛實夾雜且實多虛少的RA患者。對于病性以虛為主的RA患者,還是應當具體氣血陰陽的虛損不同以針對性地補養通絡為主,臨證中可以少佐辛味藥,避免補益之品過于滋膩阻遏氣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