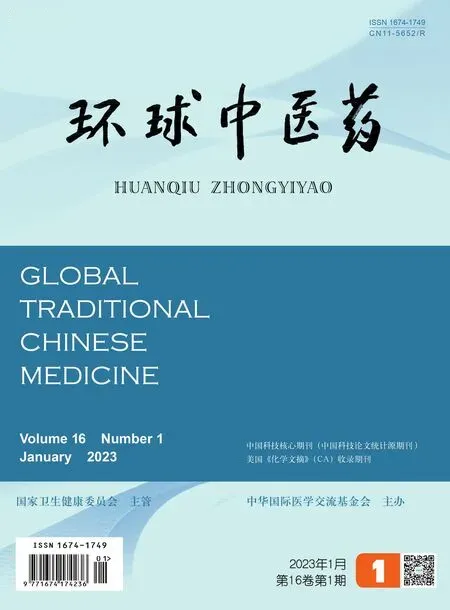“肝為主體,脾腎為側翼,疏調人體氣機”論治肺結節經驗
王英 何榮平 朱建平 郭利華
肺結節(pulmonary nodule, PN)可分為實性結節、部分實性結節和磨玻璃密度結節。其中部分實性結節的惡性概率最高[1]。在中醫學中,肺結節歸于輕癥的積聚范疇,古代醫家多認為機體正虛邪實,氣不通,為痰、為血,流滯不去等為積聚。《素問·至真要大論篇》云“結者散之”,靈活選用化痰散結、化瘀散結、行氣散結、解毒散結等法以祛邪。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云“凡人身上中下有塊者多是痰”,認為痰濕凝聚是肺結節形成過程中不可忽視的病理產物。劉偉等[2]認為肺結節發病總因正虛邪實,治療上以補益肺脾扶其正,祛痰化瘀攻其邪。宮曉燕教授認為肺結節的病因為疏肝不疏,治療上應以開郁為先[3]。姜良鐸教授認為認為正氣虧虛、氣滯濕阻、痰瘀積聚不通為肺結節基本病機,治療上需“從通從毒”入手[4]。總結可知,肺結節發病總屬在肝,責之脾、肺等臟。
1 淺析“一體兩翼”疏調氣機學說
氣機,為氣的出入、升降、變化,其核心為氣的動態運動形式。中醫學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其生理活動功能、病理變化均與臟腑氣機運動變化密切相關。
“一體兩翼”疏調氣機學說是國醫大師張震研究員根據多年臨床行醫經驗提出的一種疏調人體氣機新思想,即以疏肝為主體,健脾補腎為兩翼的架構辨治疾病,其治療理念涉及范圍甚廣。肝作為人體氣之大臟,為氣之中軸核心,司疏泄,總調人體氣機,但總調人體氣機不是肝的專屬名詞,也非僅肝一臟工作運行,需脾、腎兩臟共同營養溫煦、溝通氣化,相互配合、生生不息。脾作為后天之本,運化人體水谷精微,化生氣血,運化中焦氣機,時刻為人體各臟腑機能維持、以及精、氣、血、津液的輸布、運轉提供動力支持;腎為先天之本,主溫煦、封藏,為下焦氣化、與中上焦交互提供原動力,先后天交相呼映運轉,泛如車之雙輪。肝與脾、腎相互為用,三臟共同運作,在氣機、機能運行方面相互協調形成動態關系,猶如動態馬車,以中軸為核心,車輪帶動,馬車滾滾向前,氣機循環往復,此為人體氣機運動之臟腑功能的表現形式。
張震研究員認為氣機失調是人體諸多病疾發病的重要內在因素,強調疏調人體氣機并不是單純的疏肝理氣,必須以疏理肝氣與調護脾腎相結合的治療原則為基礎,既可促進肝之疏泄條達的生理功能,又能固護先后天之本的脾腎機能;從五臟出發,整體調達人體氣機的同時,顧護肝、脾、腎之特性而通調之[5]。再兼顧其他有關證候統籌處理,有所側重地靈活施治,增強治療的針對性,即為根據氣機失常的具體情況“矯枉偏糾”“撥亂反正”“削其有余,補其不足”,助歸其原[6],臨床運用廣泛且收效甚可。
2 “一體兩翼”之肺結節具體辨析
對于氣機的運動,總體而言,首與肝肺相關。肝色青,應春之令,位歸東方以為木,乃萬物生發生長之首,故生機之氣始于左;肺,屬金色白,與秋季相呼應,位歸西方,主沉降收斂之性,氣降于右。肝、肺兩臟生、肅春秋,春秋交替輪回,故肝氣左升而肺氣右降,肝氣疏泄,升發條達,有利于肺氣的肅降,肺氣肅降正常,又有利于肝氣的升發,既相互制約又相互為用,構成“龍虎回環”運動,“龍虎”之勢即人體氣機升降運動之總表現。肝、脾、腎又相互作用影響,為一個整體,即以“肝為主體、脾腎為兩翼”的“動態馬車”與肺共同形成人體氣機動態循環之總圓環,而非單純、單向的各自運動。人秉五行臟腑,總屬五行臟腑之病,皆運動不圓,作用分離,不能融合所致,以下為分段具體論述。
2.1 “肝為主體”—肝氣不疏是肺結節發病的首因
肝司疏泄,《禮記·樂記》記載:“感條暢之氣,具有疏調、暢達全身氣機之功。為剛臟,其性急而動,將軍之官,五行之首位,主生主升,通過啟迪他臟、帶動全身機能,進而調暢全身精氣血津液的輸布,人體諸氣血運皆需借助肝膽之氣而升發。”在五行相互制約關系上,肝木克脾土,肺金克肝木,時刻保持著平衡態勢。然,萬事萬物頗俱雙面之性,肝氣升發之力過于旺盛可為抑、為逆,恐生他變。一則肝郁氣滯而氣機不通引發氣機郁滯;二則本其過旺則傷及他臟,即厥陰肝一身上下,其氣無所不乘[7]。黃元御言:及其傳化乘除,千變不窮。故風木者,五臟之賊,百病之長,凡病起,無不因于木氣之郁。以肝木主生,而人之生氣不足者,十常八九,木氣抑郁而不生,是以病也[8]。當木氣升發旺盛,肺金肅降不及失于斂降而至肝氣郁滯,氣機不達,致金不克木,木反伐肺金,形成肝氣過犯于肺,氣停則血停,肺氣郁滯引發血液局部運行障礙,精微不達,濁氣、痰飲無以向上布散排除體外,團積于肺,產生微小病灶,久之即為炎癥,為肺結節發病之隱患。故肝郁氣滯、氣機不調為肺結節發病之首因。
2.2 “脾腎為兩翼”—脾、腎失護是肺結節發病的助推器
脾者,五行己土,色金,主稼穡,治以中央,醞釀化生。其氣以太陰而主升,水谷的運行與精微的布散均賴于脾氣的推動與激發,脾臟是水谷精微轉化的直接臟器,故脾(胃)是生氣之源。五行中土,脾土生肺金,脾氣轉輸的精微可上供心肺,通過心肺布散全身。《黃帝內經·素問》言:“中央以灌四傍。”飲食游入于胃,化水谷輸送至小腸,期間,脾氣將食糜化生精微、霧露,向四布周散、上輸于肺,充養臟腑百骸,為氣機升降、物質代謝等提供動力源泉。故人體氣機功能正常與否,與脾氣的功能是否正常密切相關,脾是人體氣機的動力源泉。
腎者,為先天之本充養,主臟腑氣化,推動和調控機體津液代謝。屬冬,接秋肅之斂藏,腎精(氣)充足能為人體之氣的化生、轉化提供營養基礎,也是氣機正常升降出入的動力與源泉保障;肝之疏泄與腎之封藏制約互用,肝氣疏泄可使腎氣開合有度,腎氣閉藏可防止肝氣疏泄太過,相反相成。又因腎陽為諸陽之本,能資助肺陽,推動津液輸布,其用在于升騰,司氣化,將本陽輸送于上,上下互助,痰飲不生,咳喘不做。同時,肺的呼吸升降與腎氣的納攝緊密相關,腎氣納攝,將吸入的清氣下納于腎,以維持呼吸深度。吐故納新、表里交換、溫煦納攝是肺腎生理功能的直接表現。
脾腎是聯通人體上下氣機的紐帶。脾腎先后天互資,是脾氣與脾陰陽相互作用的結果,同時也依賴于腎氣及腎陰、腎陽的資助和協調,脾運化水飲的機能,必須依賴腎氣的蒸騰、溫煦推動,腎主水,又賴于脾氣以及脾陽的協助,所謂“土能治水”。先后天相互滋生、激發、充養、培補,相互促進,維持氣機的生理機能。脾腎二者密不可分,在生理機能上相互補充、相互為用,馬之車輪兩兩不可互分。
然,“木以發達為性,己土濕陷,抑遏乙木發達之氣,生意不遂,故郁怒而克脾土”[9]。肝木失于疏泄,最易犯脾土,當“脾氣散精”的生理功能受到破壞時,脾失健運,脾土虛弱,脾陽不升,脾氣虛使得水谷精微無以生化,津液無以輸布[10];轉化失常,成為內生之邪氣,脾虛濕困郁而發為痰濁、水飲等病理產物,成為生痰之源;肝旺腎虛,則見藏泄失用,氣失溝通,下不可藏,上不可瀉,當屬氣機逆亂。腎水下寒而病,腎失納攝、溫煦,津液、水飲無以布散蒸發,聚集于肺,如《黃帝內經·素問》所言:“誠本在腎,末在肺,皆積水也。”肺主氣,司呼吸,而通調水道,肺與機體所需精微、氣血、津液的充養、化生、轉化皆賴于脾腎二臟。痰、濕、瘀、濁停聚于肺,阻礙臟腑氣機的正常運行,故脾腎失護是肺結節發生的助推器。
2.3 肝、脾、腎、肺諸臟失調終致肺結節發生
肺為華蓋,位居至高,主持諸氣,主呼吸,氣體內外之交換,體之至清至輕者也。肺主一身之氣的運行,體現在對全身氣機的調節,以及全身的血的運行、津液的輸送,氣行則水行,其溫養布散有如霧露之灌溉。肺的生理機能正常運行多由肝之疏泄升發、脾輸送供養激發、腎之命門溫煦推動協同。
當肝氣郁滯不舒,氣機阻滯,肝木反伐肺金,肺氣閉塞失于布散,即肝升太過,肺降不及,以致肺氣升降出入失常,肺氣郁亂不通合并肝氣壓制,久則導致肺氣郁滯,失于宣發布散,致呼吸內外不能溝通。氣為血之帥,肺朝百脈,全身血脈皆過往于肺流通全身,氣機不暢則血液難行,血停于脈,形成瘀血。同時,瘀血內停阻礙氣機運行,氣血互結膠著聚集日久儲肺;另一方面,升降金木之權,總在于土,脾土虛弱,土不生金,又使肺氣虧虛,氣不行津,聚津成痰;痰濁質稠黏膩,流動性極差,易附難除,痰濁長期內停凝聚,阻傷肺絡,絡網失約,化為頑痰、痰核。痰濁阻肺加劇氣機失行,致病理產物凝聚不散、停滯于肺,為結節的發展提供可復制條件,以致內毒泛濫滋生;腎失溫煦以致濁陰、水飲等郁積無以運化,機體上下吐納不交,無以氣化升散,上下失于聯動,肺失動力;蓋因傷郁于肝氣、動于脾濕,失于固腎溫煦,終傷于肺氣,形成有形的病理產物,其病理物質加速濁毒痹阻肺絡,肺絡不通。主軸之郁,車輪兩翼失轉,左右升降循環受阻,諸臟錯節盤亂。是多個臟腑長期功能失調,總致人體氣機阻滯、氣血津液運行失常,產生痰濁、瘀血等病理產物膠著與肺,惡性循環,終發為結節。
3 “一體兩翼”,疏調氣機辨治肺結節
基于上述認識,肺結節發病在肺,病性虛實夾雜,形成肝郁、脾腎兩虛,氣機閉阻,氣滯血瘀的證候類型。在臨床癥狀表現上患者可表現:肝區、兩脅脹痛,生氣后尤甚,情緒緊張,易抑郁,偶有咳嗽、咳痰,初期時無胸悶、氣短、乏力,口苦,脘腹脹痛,腰部寒涼不適,酸軟,納眠可,大便溏,或大便次數增多,便前腹痛,或如廁時便質先干后稀,小便大致正常,舌質黯淡,舌底靜脈略青,苔薄白,脈弦細。故治療應以疏肝、健脾、補腎為主,佐行氣活血、軟堅散結為思路,主治肝失疏泄、脾腎不足、氣機失常、血行不暢等證。
3.1 調“一體”之疏肝,為治療肺結節之總則
對于肺結節的治療,應以調“一體”為總則,即以疏肝為主。《醫方論·卷二》費伯雄云:“肝具有生發長養之機。”肝氣疏解可助人體氣機之舒展暢行;故疏肝行氣解郁之品乃治療肺結節之首藥。鑒于肺結節之發病與氣滯血瘀相關,然氣為血之帥,肝體柔而用剛,體陰而用陽,其陰與血關系縝密,故疏肝解郁的同時需與活血、酸甘柔肝養陰之藥相配,一則增強行氣活血之功,氣行則血行,鞏固氣的推動之力,暢調氣機;二則防止疏肝、升發之品過于香燥,辛溫,導致肝之體陰耗傷,引發疼痛等不適。即加強以肝為主體的“一體”疏調之力,此乃調“一體”為主。
3.2 補“兩翼”之脾腎,為治療肺結節之要點
肝氣過旺恐致脾氣虛衰而脾運不及,故需輔以健脾之品,防止因脾氣虛弱,痰飲、水濕無以布散,成為生痰之源,脾病日久,化生不足,無以滋養先天;脾氣生化,布散、灌溉水谷精于肺、心等,充養四肢、百骸、臟腑。腎做為先天之本始,與脾相互參用,與肺封藏納攝。溫補腎陽,乃固護、溫煦先天,先天充足,與后天之脾相互作用,聯通上下,于肺納攝呼吸,培補互資,加強固護脾腎之力,即“兩翼”之機互參,肝脾腎共調,初見疏調之雛形;治療理念總體散中有收,速中有緩,有升有降[11],肝脾腎同調,總作用于肺,氣之臟腑通而不滯,盡顯疏調之意。(具體選方配伍可參照國醫大師張震的疏調湯。)
3.3 觀其微,同配抗腫瘤、護胃之品
疾病有輕重緩急,肺結節一定程度上為肺癌的前身,針對久積難化之結節,筆者認為在辨證的基礎上,覽其宏,疏調之余,觀其微,應適當加入解毒散結、軟堅消癥等廣譜祛邪之品,促進癌細胞凋亡、調節人體免疫力;對于久積難化之頑疾,祛邪藥物可直達病所,攻其巢穴。雖屬氣滯血瘀,但立方選藥時可無需考慮額外添加散瘀之品,本著過用血藥恐耗散傷正的原則,故以行氣藥為主,旨在氣行則血行。若考慮患者服用抗腫瘤之品寒涼,藥性過強而格拒,敗壞脾胃,傷及中焦,影響脾胃功能以及消化,則配以通行溫中、固本護力、促消化之品。
總以審證求因疏調氣機為本,兼顧整體為綱,緊密圍繞“一體兩翼”的疏調思想,以疏調為圓心,肝脾腎臟腑辨治為主線,疏肝、健脾、補腎,活化氣機運動。人體氣機順調,主軸旋轉,車輪兩翼互參,氣機左右升降循環,有序往復,諸臟協同配合,從根本上阻斷結節的發生與發展,結節難復。肺結節雖在某種程度上與肺癌相似,但仍有諸多不同,故在治療上不可一味攻伐、急功近利,用藥不可過猛,過猛恐傷正氣,引邪深聚,應緩而圖之,使人體氣機調達,則結節可散,正所謂“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也。
4 小結
肺結節因發病隱匿,且多數患者無明顯臨床癥狀,現代醫學處理肺結節多以隨訪為主。中醫認為,人是一個有機整體,肺結節發病雖在肺,但與肝、脾、腎生理病理關系縝密,以國醫大師張震研究員“一體兩翼”疏調學術思想為核心,發散分析肝、脾、腎與肺臟的生理病理關系與相互作用因素,通過疏肝、健脾、補腎合并解毒散結、軟堅消癥等祛邪之法,加以護胃,探討肺結節臨床經驗,擴大肺結節中醫臨床診治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