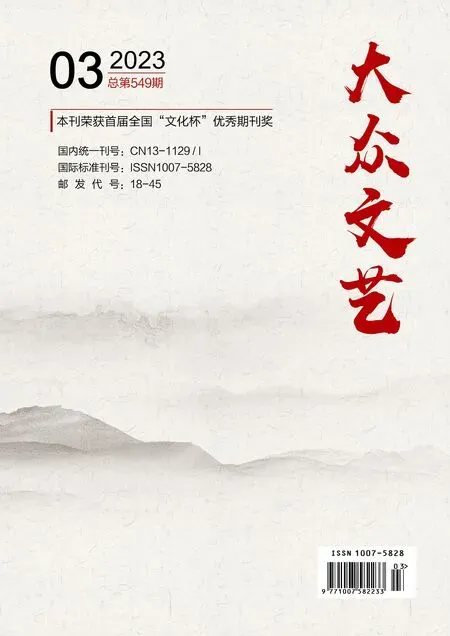勞動、入社與農業合作社的運行
——論《三里灣》《創業史》的敘事策略
蔣賀麗
(長春理工大學,吉林長春 130022)
1951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制定,明確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基本方針、政策和指導原則。[1]1952年,趙樹理再赴山西平順縣川底村,參加農業社的生產、分配工作,1955年,發表作品《三里灣》。趙樹理在《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1966年)這篇文章中表示,他的很多小說是配合著方針政策宣傳寫作的。《三里灣》包含宣傳入社、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爭取婚姻自由等內容,“是第一部參與了農業合作化權力資源運作的長篇小說”[2]。1952年,柳青返回陜西,并在皇甫村扎根14年。1959年,《創業史》(第一部)發表。小說講述老一代農民創業的勞苦史、饑餓史、恥辱史,與新中國成立后農民進行對比,展現了黨的帶領下走向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正確道路。《創業史》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3]趙樹理和柳青作為現實主義作家,觀察并記錄了這場變革在農民中引起的巨大反響。論文以《三里灣》和《創業史》為主要分析文本,結合《山鄉巨變》(周立波,1958年發表),《艷陽天》(浩然,1964年第一卷出版)舉例類比,論述作者進行農業合作化的宏大敘事時,采用的敘事策略,以及采取這種策略的原因。
一、集體勞動形象的塑造與被規訓的個體勞動
新中國成立以前,農民作為封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礙于生產資料的制度性隔絕,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土改的創舉,改變了農村的生產結構關系,解放了生產力,同時改變了鄉村的權力格局,使得新政權能夠在鄉土中扎根。
十七年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帶有政治宣傳性,并形成了一定的敘事模式。隨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發展,敘事模式更加固化。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特點是統一經營,并實行集體勞動。大量合作化題材小說通過鋪敘集體勞動的熱情,確指國家選擇合作化道路的正確性。《創業史》中高增福想起“施追肥、修建飼養室和平整土地的集體勞動中,這些男女老少勞動熱情高漲的情景……”[4]集體勞動的熱情,代表著人們對農業實行合作化的積極心態。《艷陽天》中“刨土的,開石的,推車的,挑筐的,還有背石頭的;你來我往,你呼我叫……”[5]集體勞動劈山引水的熱烈場面,帶著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強大意志,樹立積極建設新中國的正面形象。正是在這樣的書寫中,作者完成了集體勞動形象的塑造。集體勞動與農業合作化緊密連接,是新中國建立初期,黨和領導人篳路藍縷帶領人民走向新生活的合法性敘事。
當集體勞動成為主流趨勢,個體生產熱情也就必須融入集體勞動熱情中;那些仍然具有個體生產熱情的勞動者,成了落后、需要被改造的對象。在作品中,通過展現集體勞動的歡快場面,直接或間接地對個體勞動達到規訓效果。《三里灣》中合作社派頭比互助組強,互助組派頭比單干戶強。社里干活,老人、婦女、小孩熱鬧非常;單干戶干活,氣氛冷清。一褒一貶,作者的敘事態度蘊含其間。敘事態度體現了作者的立場和姿態選擇。趙樹理選擇這種態度,顯然是有意為之。早在1951年9月,趙樹理提出“現在的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6]1955年《三里灣》發表,趙樹理對個體生產的態度發生轉變,這種轉變與合作化的進程相關,此時農業合作化程度已經很高,再提出個體生產的積極性,顯然不合時宜。《創業史》中郭世富購買“百日黃”稻種,與互助組進行生產比賽,梁生寶根本沒放在眼里。梁生寶看到的是大家在集體勞動中表現的美德,并認為“私”是農民吃虧結仇的根源。梁生寶對個體生產的態度以及總結,形成了對個體生產的規勸,確指個體勞動必須加入集體勞動中才有意義。梁生寶的所思所想,顯現了作者對個體生產的規勸立場。
當時,個體生產的積極性,往往與“資本主義”標簽黏合在一起。集體勞動共同富裕,作為共同的奮斗目標,個體勞動、個人發家致富便不合時宜。在個人層面,農民想通過農業勞動,實現發家致富。在國家層面,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互助合作、自愿互利的農業合作化,以糧食的大量產出,支援國家的工業化建設,這是邁向社會主義的重要一步,目標是共同富裕。這種只顧自己發家的思想,是集體共同富裕目標的對立面。因而在小說中,個人發家思想不斷被規訓、勸導。《三里灣》中范登高因為買騾子和雇傭王小聚,產生了走資還是走社兩條道路的爭論,要不斷檢討思想。《創業史》中郭振山因為買了地,在整黨會上檢討自發思想。個體單干者不僅與資本主義、個人發家思想黏合,而且與思想落后、道德問題掛鉤,“這就是將個體生產者推到合法但不合理,法容理不容的位置,讓其接受公理、情義的道德訓誡。”[7]《三里灣》中“常有理”尖滑小氣,對媳婦陳菊英留飯和互助組管飯問題上,失了仁義;為阻攔開渠去告狀,只顧個人利益,漠視集體利益,失了人心。《創業史》中王二直杠(退互助組)指導兒子打兒媳,性格古怪執拗,可憐但不受歡迎。參加集體勞動的人有昂揚積極的形象,堅持單干者帶有缺陷的標簽,這也成為十七年合作化小說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固定策略。
對個體生產積極性的否認、個人發家思想的規訓、單干者落后形象的塑造,對比確認了集體勞動的必要性。柳青說:“在這個斗爭中,應該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村的陣地、千方百計顯示集體勞動生產的優越性……”[8]隨著集體勞動形象的光輝塑造,個體勞動矮化,集體意志凸顯,個體意志逐漸被淹沒。
二、皆大歡喜:矛盾沖突的遮蔽
1955年,毛澤東同志《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中提出:“發展合作社的原則是自愿互利。牲口(連地主富農的在內)入社,都要合理作價,貧農不要在這方面占便宜。”[9]自愿是入社的前提,互利是農民持續在社的保障,強調了發展合作社的方向。對于牲口入社相關的問題,明確“合理作價”的處置辦法。
十七年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關于爭取入社的情節,形成了固定的沖突模式。沖突的結果,總是問題得以“解決”,落后分子思想扭轉,加入合作社,結局皆大歡喜。以“自愿”為前提的入社,在沖突的解決過程中,隱藏著個人的非“自愿”。在政權意志與個人意志沖突時,作者選擇遵從政權意志,進而對個人意志進行遮蔽。這代表了作者的敘事立場,也顯露出作者在無法調和兩者矛盾時,采取的縫合策略。《三里灣》中刀把的問題的解決,是馬多壽的兒子(革命干部),主動獻地的結果;馬多壽入社,是因為再沒了辦法;范登高在黨員招牌即將不保的情況下,表示愿意入社。《創業史》中梁大老漢退組后又入社,是因為收到了在部隊的兒子讓入社的信件,但是梁大老漢入社后,仍然不愛聽農業社的事情。從這幾個人物的表現中,可以發現,人物從不入社到入社的轉變,不是因為個人思想的覺悟,或者發現了農業社的優越性,然后自主自愿入社,而是小說人物對政治話語屈從的結果。
入社還是不入社,沖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矛盾。馬克思在談道農村公社時,論述了農業公社公有制和私有制因素的二重性,“‘農業公社’的構成形式只可以有兩種選擇:或者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后者戰勝前者。”[10]闡述了這可能逐漸成為公社解體的根源。中國的農業合作化是學習蘇聯經驗而來,帶有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的二重性,而個人所有的生產資料在轉化為公共集體所有的過程中,個體和集體的訴求沖撞,一直是合作社中矛盾的沖突點。通過政府引導,矛盾解決,使個體融入積極入社的潮流中,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敘事。換句話說:土地和牲畜等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越高,矛盾沖突的表現力度就越小。然而這個矛盾并未解決,只是代表政權意志的話語在文本中的凸顯,使得個人的真實意愿被遮蔽了。
還有牲畜入社問題,“最近許多地方發生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現象……”“有的省估計至少殺了三十萬頭……”[11]對于現實中大規模殺害、買賣牲畜的事件,在小說中,表現為殺害、買賣牲畜的事件被成功阻止,并達到“皆大歡喜”。趙樹理《三里灣》特意寫了“回驢”一節。袁丁未在入社前一天把驢賣掉,在買賣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由副區長主持要回了驢;范登高因感覺自己兩頭騾子入社吃虧,想把騾子賣掉,后來沒有賣成。柳青的《創業史》中梁大老漢把入了社的黑馬牽走,準備賣掉,被社員奪回。《山鄉巨變》中張桂秋擔心牛入社折價低,想偷偷殺牛,被村里的干部和民兵手執刀槍棍棒阻止了。《三里灣》中“回驢”尚有輕松詼諧的氛圍,《創業史》中奪回黑馬成為小規模爭執,《山鄉巨變》中逐漸發展為劍拔弩張的局勢。無論是個人入社、土地入社,還是牲畜的處置,個人都逐漸喪失了變革之初那個“自愿”的前提,而演化成為一種政策推行下的被動接受。作者并沒有無視這個問題,而是在處理相關情節時,有意減弱了政策推行與個人意愿之間的沖突,展現為小說中皆大歡喜的結局。
三、矛盾轉化:合作社的資金難題
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進,合作社的數量迅速增多,加入合作社的戶數成倍增長。1955年年底,“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190萬多個,參加社的戶數達7,500余萬,占全國總戶數的63.3%,每個農業生產社的參加戶數平均為39.6戶。”[12]在國家層面,人們積極入社,紅紅火火辦社,農業合作化形勢一片大好。在合作社層面,管理分配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合作社的公共資金,是影響社里投入產出的重要因素。合作社運營的資金難題,從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一直存在。通過國家幫扶、集體克服,本應是集體共同承擔的資金問題,在作者的敘事策略下,轉化為主人公“克服困難”的一部分,通過解決這個“困難”,凸顯英雄人物解決“困難”的能力,塑造出盡心盡力為社服務的形象。
農業合作化運動,把農村中的個體經濟轉變成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有組織地進行生產、分配工作。1955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頒布,這是有關合作社生產、管理、分配的系統性章程。其中明確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包括:社員交納的股份基金;生產的收入;社員的投資。社員的股份基金,分為購買種子、肥料的生產費股份基金和購買牲畜、農具的公有化股份基金。[13]這筆資金也成為貧下中農的負擔,難以繳納。國家通過發放借款,“從1955年下半年起,到1956年底止,共發放了7.5億元,幫助4,000萬戶貧農和下中農(包括貧苦漁民和牧民),解決了繳納入社基金的困難。”[14]還有社里開支大、負債多是普遍情況。[15]這就在合作化運動紅紅火火發展的敘事下,顯現出不和諧的聲音。
合作社成立以后,推廣種植新技術、大量開辟荒地、大規模修建農田水利設施,包括社內生產管理,所需資金不少。《三里灣》中王金生的筆記本上記著“公、畜、欠、配、合”,其中“欠”是指社里欠外債的問題。《三里灣》中外債問題成為初期合作社眾多問題中的一個。《創業史》中梁生寶拿自己賣荸薺的錢做墊底資金,為互助組進終南山砍竹子做準備。進山之前,梁生寶訂立供銷社掃帚合同,取得預付金,解決人們的生活難題。《艷陽天》中東山塢高級農業社,蕭長春仍然把錢借給社里,為兩個隊添買席子、家什。合作社資金問題解決,社里危機解除,凸顯了帶頭人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英雄形象的塑造,削弱了合作社運營問題的表現力度,把經濟上東拼西湊、寅吃卯糧的現象,巧妙轉變為克服困難的積極書寫。英雄人物舍己為社的敘事,緩解了眾人經濟上的壓力,也增強了人們對合作社的信心。
通過出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敘事情節,作者成功塑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全心全意為社著想,成為合作社領頭人的主要特征。這種英雄化的敘事,強化了英雄的個人魅力,也達到了對合作化運動負面影響的有效遮蔽。對社內帶頭人形象的塑造,正體現了柳青所說“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任務是創造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16],這也是“文學的黨性要求”。作者有意識地塑造典型的過程,也完成了對合作化運動發展歷程的書寫。
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三里灣》和《創業史》的書寫,采取了行為規訓、沖突遮蔽、矛盾轉化的敘事策略。作品對現實問題的藝術性處理,灌注著作者的認識和傾向性。敘事立場的選擇,一方面是作者基于對合作化運動的認識,贊同互助合作是正確的道路;另一方面是作者對政策推行與民眾思想意識的矛盾沖突,進行的溫和化處理。趙樹理和柳青身處變革運動的中心,深切感知農民內心的情感和精神的變化,對這場運動做出了深負社會責任感的回答,最終呈現出這類頗具特色的時代性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