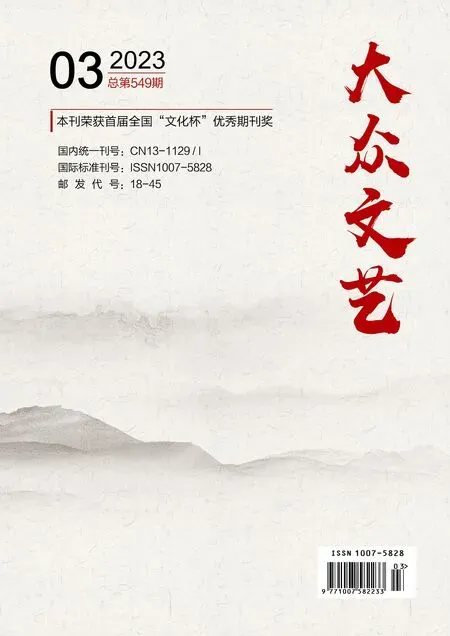創傷理論下《遠山淡影》與《我輩孤雛》的對比研究
王 玥
(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蘇南京 210000)
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是當代著名的日裔英籍小說家。他的作品大都具有國際視野,以不同國家為背景,圍繞創傷與回憶展開,探索過去、當下與未來。《遠山淡影》(1983年)是其第一部作品,講述了妮基探望住在英國鄉村的母親悅子,引發的對二十年前長崎生活的回憶。《我輩孤雛》(2000年)借偵探小說外殼,書寫班克斯尋找父母失蹤謎案的事實。
“創傷”一詞,最早源于醫學與精神領域,指身體受傷的地方或精神遭到的傷害。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擴展到了歷史、文學、社會學等領域。凱西·卡魯斯在《無主的經驗:創傷、敘述和歷史》中指出:“創傷是在突發事件或災難性事件面前,個體原有的經驗被覆蓋,而受創者對這些事件本身通常表現出延遲,以幻覺和其他入侵性的現象重復出現的無法控制的反應。”[1]如今,越來越多的作家關注創傷主題,通過作品來書寫創傷,講述創傷事件以求重構自我獲得治愈能力。
一、悅子與班克斯的創傷根源和創傷表現
1.悅子與班克斯的創傷根源
《遠山淡影》由主人公悅子碎片化的回憶與現實敘事構成,在斷斷續續的回憶中發現小說有兩條主線,一條是現實中悅子與妮基在英國的故事,另一條是回憶里悅子、佐知子與萬里子的故事。受到悅子破碎而模糊不清的回憶影響,閱讀過程中極易對人物產生混淆感,直到小說結尾,悅子說漏了嘴,“那天景子很高興,我們坐了纜車”[2],但在回憶中坐纜車的是悅子、佐知子與萬里子,因此讀者才能夠最終確定悅子就是佐知子,景子就是萬里子。悅子之所以假托別人的故事回憶自己的過去,是作者有意為之,石黑一雄表示:“某個人覺得自己的經歷太過痛苦不堪、無法啟口,于是借用別人的故事來講自己的故事。”[3]悅子經受多重創傷,自己苦難無法言說,只能通過虛構人物來表達創傷。
《我輩孤雛》同樣以文學的形式述說難以言表的創傷經歷。與悅子虛構人物第三人稱講述創傷故事不同,班克斯以第一人稱進行自我敘述完成創傷書寫,但是模糊的童年記憶帶有強烈的虛偽色彩。雖然兩部作品敘述手法不同,但主人公都經歷了戰爭、文化和家庭創傷。
首先是戰爭創傷。表面上看,《遠山淡影》中景子自殺是悅子創傷的直接來源,但是戰爭導致其深層次創傷。遭受原子彈摧殘后的長崎處在破碎與重生之中,戰爭使悅子失去了戀人中村。《我輩孤雛》中班克斯從小生活的上海戰火紛飛,是戰爭導致班克斯父母離奇失蹤,所以戰爭創傷是一切創傷的根源。其次是文化創傷。《遠山淡影》中家破人亡的悅子迫切期望離開長崎,帶著景子遠赴英國。身處異國的悅子生活飄忽不定,難以融入英國文化。《我輩孤雛》中班克斯擁有雙重文化背景,從小生活在上海租界,后因父母失蹤被送回英國。從小在上海長大的班克斯無法真正融入英國社會,在兩國文化中對自我身份歸屬產生焦慮感。最后是家庭創傷。戰爭導致悅子失去了親人,家破人亡的悅子孤身帶著景子居住長崎。班克斯兒時家庭幸福美滿,后慘遭變故,先是父親無故失蹤,后又發現母親也不知去向,從此變成一個孤兒。
2.悅子與班克斯的創傷表現
創傷在具體的語境中表現為特定形式,即經歷創傷事件的人往往會刻意逃避事件或與之相關的情景和人。瑞士著名心理學家阿貝爾認為,在非自然敘事語境下“人物可以做出很多在真實世界中不可能的事情,例如,他們有可能異化為別人。”[4]
首先《遠山淡影》中,悅子將自我塑造為對抗形象,通過質疑來解構自我表現創傷,在三重創傷下,她虛構了與自己截然相反的人物來訴說事件。在小女兒妮基提起自殺的大女兒景子時,悅子的思維突然跳躍到了佐知子的身上,“只是因為這是今年四月妮基來我這里時的情形,正是在那段時間里,我在這么多年后又想起了佐知子。”[2]景子的自殺使悅子極度痛苦與自責,只能假裝講述別人的故事來訴說內心的悔恨與自責。回憶里悅子是熱愛家庭、傳統本分的家庭主婦,而佐知子卻是口頭說著一切為了女兒,實際自私自利的母親。從虛構的佐知子可見,真正的悅子始終無法擺脫戰爭陰影,只能假借佐知子表達自己渴望逃離苦難之地的想法。為了兼顧母職,悅子以移民英國可以給景子更好地生活為借口,帶景子一同離開,但也正是因為對陌生未來估計不足的決定導致了更大的痛苦—景子的自殺。創傷事件后,受創者難以接受事實,會主動躲避或欺騙與創傷事件有關的情況和人。在與妮基外出時,悅子遇見了女兒們的鋼琴老師沃特斯太太,當沃特森太太問起景子時,悅子假裝景子仍獨自一人生活在曼徹斯特,此時的悅子仍不敢直面景子死亡的事實。
其次,《我輩孤雛》中班克斯則是企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強大的英雄形象來進行麻木逃避與刻意遺忘,與《遠山淡影》中悅子虛構人物形成鮮明對照。與老友奧斯本的交談中,班克斯認為自己很好地融入了集體,正如到校第一天,班克斯就發現同學們站著交談時都有一套固定的肢體語言,而他也很快就把這套肢體語言運用得爐火純青,然而老友對班克斯的形容卻與他本人的回憶天差地別,評價他“真是怪胎一個”[5]。在多爾切斯特飯店與上校回憶返回英國的往事時,班克斯“清清楚楚記得自己很快便隨遇而安”[5],但上校卻記得當時的班克斯“畏畏縮縮而悶悶不樂,一丁點的小事就能讓他掉眼淚”[5]。班克斯的自我認知與他人認知存在差距,甚至完全對立,他所表達的形象不過是為了躲避傷痛而否認事實而已。經歷創傷事件的人會變得更敏感,缺乏安全感,強大的英雄形象給予班克斯無限的安全感,使其陷入自我幻想中,虛構的情節如現實般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腦海里,緩和真實生活帶來的焦慮與悲痛。雖然沉湎于幻想一定意義上能夠使其遠離創傷,但實際只會讓他與現實越行越遠,最終導致幻境破滅,日后行動的錯誤與受創的增加。
創傷的呈現方式多種多樣,除上述情況外,還會通過夢境、閃回等方式反復呈現,凱西·卡魯斯認為:“受到創傷的人往往在他們的內心承載著一段不可能的往事”[6]創傷帶給受創者的并不只是短暫的劇痛,而是持續不斷的麻木與痛楚,具體表現為難以控制的幻象、臆想和噩夢等的產生。《遠山淡影》中,悅子經歷了幾次相同的夢,夢見前一天在公園里看見的蕩秋千的小女孩。起初悅子只當是個普通的夢,但當夢境不斷重復,她才逐漸意識到看似在蕩秋千的小女孩實際卻是懸掛在秋千上,正如悅子腦海中景子自殺的景象,弗洛伊德認為“夢是被壓抑的本能欲望”[8],重復的夢實際是悅子的傷痛與不安,是景子自殺帶給悅子擺脫不了的陰影。不同于悅子通過夢境重感創傷,《我輩孤雛》中班克斯則是在幻象之中偽裝自己,只有幻象打破才會感到傷痛。班克斯為了躲避創傷傷痛而過度依賴童年記憶,始終堅信父母被關押在老房子里,但現實是他不可能在二十多年后,在正處戰亂的上海,還在同一所老房子里找到父母,種種跡象表明,這位名偵探只是自始至終都活在自己虛偽扭曲的回憶中。
二、弱勢群體的創傷根源與創傷表現
前文主要論述了作品主人公的個人創傷,實際上作品中的人物也是各類受創者,創傷理論中,赫爾曼后期研究突破了傳統性別群體的局限,將關注點更多地放在了婦女兒童老人身上,《遠山淡影》和《我輩孤雛》中也呈現了各樣弱勢群體的創傷。
1.兒童創傷
《遠山淡影》中,兒童創傷表現為自我逃避。回憶里,萬里子不斷提到一個陌生的女人,后來佐知子告知那是小時候萬里子在河邊看到的一個把嬰兒沉溺在河中的女人,而此場景又與后來佐知子當著萬里子的面把她的貓沉溺在水中的場景如出一轍,對此萬里子卻沒有反抗,只是把頭扭了過去。如果說前一個場景給萬里子帶來的是驚嚇,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童年陰影,那么后來的萬里子面對母親的行為只剩下了麻木和無感。萬里子是兒童受創者的代表,她的童年不僅被剝奪了優渥的生活環境,也受到了戰爭帶來的驚嚇。
如果說萬里子的創傷表現為自我逃避,那么《我輩孤雛》中秋良的形象則體現了創傷帶來的自我懷疑。作為班克斯的兒時玩伴,秋良自孩童時期就知道只能待在比較安全的公共租界,不可以靠近戰火不斷的閘北區。受父母思想的灌輸,秋良自幼以日本為傲,不斷地和班克斯宣揚“日本已經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大國”[5],當父母吵架時,秋良也會質疑自己“不夠日本化”[5]。他的身份認知具有混亂性,當他被送回日本上學,但很快又從日本回到了上海,他由于其“異國風格”[5]而與身邊的人格格不入,痛苦不堪,因此身份的難以認同也讓秋良深受文化創傷之痛。
2.老人創傷
《遠山淡影》中,以緒方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的創傷顯而易見。戰后日本結束了相對封閉的狀態,民主意識開始崛起。緒方先生曾經的學生重夫發文批判舊時的教學模式與思想,認為“是最具破壞力的謊言。”[2]從對國民教育的態度中可以看出,緒方先生仍堅守舊時的價值觀念,害怕戰爭所帶來的變化,強調個人對國家的絕對服從,他認為,“人人借著民主的名義丟掉忠誠”[2]。面對戰后文化思想變遷,重夫站在了緒方先生的對立面,這就使許多像重夫這樣的年輕人順應了時代的發展,而給以緒方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帶來了創傷。
《我輩孤雛》中,塞西爾爵士則代表老一輩價值在戰時的新文化沖擊下逐漸崩塌。塞西爾爵士原是英國聲名顯赫的政治家,對于戰爭有著清晰的認識,他認為,“文明的力量搶占上風”[5]。爵士在莎拉的勸說下來到上海,企圖憑借自己的影響力阻止戰爭,但最終在上海沉迷賭博,甚至在賭輸后肆意辱罵毆打莎拉。塞西爾爵士在倫敦的高貴博識形象與在上海的瘋狂賭徒形象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他的文明信念不復存在。來到異國后,爵士因接觸了不同文化,感受到了母國文化與異域文化之間的碰撞,仍堅守老一套無法改變現狀,最終戰爭導致的文化創傷將其擊垮而荒誕度日。
3.婦女創傷
《遠山淡影》中,二戰后日本社會的種種變化滲透到日本家庭內部,悅子丈夫的同事花田曾威脅妻子,表示如果選舉中妻子投票給不同的人,他將用高爾夫球棍打她,由于戰前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女性社會地位低下,丈夫不愿妻子違背自己意愿,暴力讓妻子經歷家庭創傷,其本質為社會封建思想導致婦女遭受性別歧視。妻子不懼威脅堅持投給另一位被選人,并表示“打算報告警察說你政治脅迫”[2]。社會民主意識的普遍讓日本婦女地位發生改變,開始接觸新的社會思潮,擺脫封建思想,獲得了參政權,政治意識也開始覺醒。
《我輩孤雛》中黛安娜雖有覺醒但在社會壓制下只能無奈妥協,其創傷直接反映了社會對女性的壓迫與不公。黛安娜集外在美與內在美于一身,她懷有遠大抱負,卻以失敗告終。為了抵抗鴉片貿易,黛安娜強迫丈夫離開公司,導致丈夫不堪壓力與情人私奔,后來又與中國軍閥王顧達成協議,以為可以阻斷鴉片來源而成為他的姨太太。但在男權思想嚴重的社會,她的美貌只吸引來了庸俗的男人,丈夫與情人的私奔以及成為軍閥姨太太的打擊都使黛安娜飽受家庭創傷。此外,由于性別歧視觀念嚴重,實際的社會狀況只會限制黛安娜的發展與價值,于是她只能回歸家庭,只希望做好一個母親的職責,為了兒子而舍棄自己。
結語
文學是最有力的表征之一,通過創傷書寫來敘述人的精神世界。根據創傷理論,與外部世界建立關系是創傷復原的基礎,創傷敘述是幸存者與外界建立聯系的方式[8],《遠山淡影》中悅子虛構一個與自己相反的人物,用自我欺騙的方式進行回述,最后卻又暴露自己的偽裝,未能將真實事件向他人表述,因此悅子沒有獲得治愈。而《我輩孤雛》中班克斯則成功與他人重建聯系。其父母失蹤真相是父親不堪母親壓迫與情婦私奔,客死他鄉,母親為阻止鴉片貿易成為中國軍閥的姨太太,姑姑撫養自己的錢財也來自母親委身的軍閥。現實與幻象大相徑庭,得知真相的班克斯先是極力否認,在痛苦失望后逐漸冷靜,找到了癡呆的母親并乞求原諒。班克斯回歸現實并承認孤兒的身份反映其初步的創傷治愈。根據赫爾曼治療創傷幸存者的經驗,“幸存者在某一時刻一定會感到與另一個人的聯系,也會因另一個人的慷慨、善意和寬容而感到與他的聯系,由此開始與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聯系”[8],班克斯離開英國前收養了一個名叫詹妮弗的加拿大女孩,結尾處長大的詹妮弗表示即使結婚后也要為他留一間屋子,與他同住,她的言語給班克斯帶來了極大的安慰,“那樣的談話,正是我多年來得以慰藉的源泉”[6]。與悅子仍與外界隔絕不同,班克斯重新融入社會,成功地從創傷中恢復自我。
《遠山淡影》和《我輩孤雛》通過塑造一個個受創者形象,將對人生、社會等的問題呈現出來。創傷理論研究的當代價值在于,人類需要克服的不僅是身體上的創傷,進入新世紀,創傷還可以表現為對人類精神文明的威脅。因此創傷研究有助于喚起大眾對受創者的重視與關注,這不論對個人、家庭還是社會都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