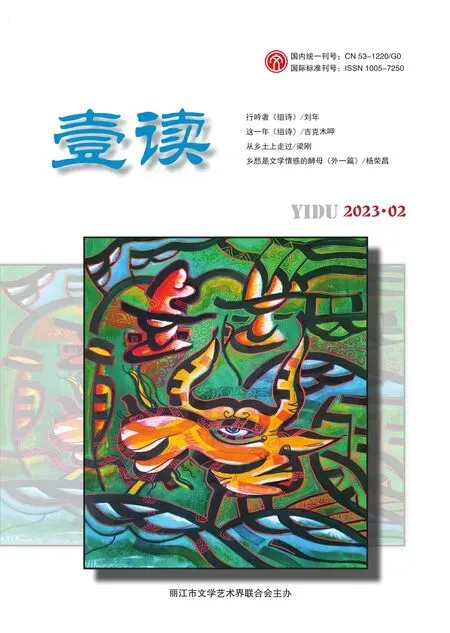行無素白
◆雷煥春
曾經來過麗江幾次,沒有太多特別的印象,我不過是裹著人世的喧囂涌進麗江的人潮,覺得它與所有的商業古鎮中流淌著的浮躁并無區別。
只為來而來,只為離開而離開,并無分別心。所有的旅游古鎮都有著同樣的手鼓拍打著相同的招攬節拍,同樣的服飾從統一的批發商手里輾轉到了不同的人身上,貼出“我是游客”的標簽。還有那些款式重復的廉價飾品充當著許多人的一次性裝飾,那些燈光昏暗的酒吧創造了多少虛幻的故事,一直覺得那些并無深刻內涵的營銷方式只將艱深的營銷學表現出很少的一部分。
機械的行走注定不能深入內心,我不曾心動,也不曾留戀,只是于千萬過客當中普通的一人。我習慣了在擁擠中麻木地低頭行走,只有在夜色暗涌時,坐在逼仄的陽臺書桌前,才能將想象從現實的苦厄中放回到天馬行空。重組,創造,虛實相入,以一種生命經過人世的方法錄下一些蛛絲馬跡。
八月中的這個清晨,當我睜開朦朧的睡眼從十七樓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低矮民房上空的湛藍映襯著軟綿綿的白云,這萬古的藍與潔凈的白將遼闊的意義表現得極其深刻。
一種不能自持的吸引力,讓我迅速起床走到窗前,我看見整個城區的房屋建筑像有誰在半空中劃過一條禁高令似的保持著相同高度,唯有我此時所住的酒店獨聳云霄。
舉起手機,廣角鏡頭變得狹窄,它根本容不下所見之景,天空的深遠還在往更遠的地方延伸,浮動的云極盡悠閑地在天空邁著碎步。那山,那峰巒雄偉的山,那連綿起伏的山,似守護的神祇數著祈禱的佛珠守在城市的四周。
就在這個清晨,我從官房酒店十七樓的窗戶愛上了這個城市。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時間的沉淀,為了快速出名以某種噱頭使之獲得短暫的收益是一種災難。這母性的城市有什么錯呢?地處邊陲想要發展的城市有什么錯呢?那些被推上風口浪尖的輿論將由制造錯誤的人們去買單。
我所憎惡的還在持續,而我所未深入的正在內心情感的波濤上揚帆起航。
深深地愛上麗江,愛上麗江被人們口耳相傳浮艷的外表下純粹的靈魂。當我從文學的養分中吸飲到一滴甘露,表面人為制造的泡沫并不能一如既往地遮蔽我的雙眼,遮蔽我的心,我的發現在持續,我的期待在持續,我的愛,在持續。
他們親切的語言里夾著特有的地方特色普通話進入耳廓,我仿佛在另一個國度遇見我的鄉親,淳樸的民族風情一陣陣撲面而來。這里不是我的家鄉,卻使我的思緒如電影回放一般,生我養我的彝鄉村落里那早已忘卻的人情世故一幕幕閃過腦際。
麗江的多面性在此次短暫的行程中,我只能觸及到她歷史底蘊深厚的冰山一角。就如常人看我,總以商人的角度,就如常人看麗江,總以游客的角度。人們最擅長在自己無限的腦補中給對方披上印象的外衣。
哦!哪個城市的燈紅不是蕩漾著酒綠?為什么單把指頭戳向麗江呢?誘惑的魔鬼只會進入貪婪的人心。淳樸的人在七星街給我指路,白衣人戴著口罩給我診療,納西阿媽為我縫補衣物,彝人小伙唱著熱情的敬酒歌灌醉我的耳朵,他們也將自己灌醉,再從大雜燴的平凡生活中捋出些空靈的詩意,因文學而來,因詩歌而真摯。
當我進入雪山秘境,路過東巴谷,險峻的峽谷深不見底。
雪山腳下的草地是一塊大自然編織的地毯,滿地的野花在溫差異常的境況中艷麗地開著,一種花兒襯托著另一種花兒,一種顏色襯托另一種顏色,顯現出各自獨有的植物特征,絕無矯揉造作的姿態,自然天成的和諧畫面使人流連忘返。
野花們的頑強在不經意中傳遞給我一種韌性,天然的、純粹的、堅不可摧的韌性,使我心靈深處那些隱秘,那些不可傾訴與搖擺不定的在這一刻得到了加持,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
高聳如云的雪山上因融化的雪水經過長年累月的流淌,在絕壁上畫出千萬根白色的拉絲線條,從高峰中向下蜿蜒著,青褐色的巨石冷峻、莊嚴,似神諭不可冒犯,以高處不勝寒的絕對冷靜護佑一方生靈。
漫步白沙古鎮,站在寫滿東巴文的圍墻前,墻上明艷的色彩沖擊著我的感官。我細細辨認這種獨特的文字,每一個字都接近一個物體、意象,仿佛給我這樣的東巴文盲用惟妙惟肖的形態表現出它所包含的用意,傳遞東巴文古老的信息。新石器時代遺存的巖畫、圖案疏密有致的蠟染、以杜鵑木為原料的木雕,每一種藝術的創造靈感都取材于日常的生活,是智者發現美并創造了偉大的作品。“人類最高靈魂的品質就存在于自然與人造品之間的和諧之中。”我被一種來源于自然的、民族特有的強大的神秘感所包圍著,平日里散漫無主的卑微感在這里變得專一、敬畏,內心有一股暖流緩緩溢向全身。
我這微不足道的、淺表的敘述僅僅處于短暫的時間表層,而那絕學的東巴文化早已被譽為世界唯一存活著的文字,智者集經學,醫術,歌舞,書畫,史料為一體,千百年來一直被世人口耳相傳。
對于麗江,我這樣的表述可能沒有任何價值,而它的貴在于讓我內心真實的情感找到一處出口,我與我內在的靈魂融為一體。所有這一切的源泉,在雪山腳下,在野花開遍的草地上,在群山默默守著藍月谷寶石般的流水聲中,在牛兒搖著尾巴驅趕蠅蟲的樹林里,在納西阿媽給我剪裁衣服時的慈祥笑容里,我不可抑制地愛上麗江的山水,愛上麗江的人文。我不否認也因這里有一位作家好友,便赴了這趟文學之約,也或許是每一場人與人、人與物的相遇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不早不晚,恰好順遂。
這里的一切景物,我無法用我內心匱乏的知識一一如散文家一樣寫出細致的、妙筆生花的句子,去描述、去贊美;我僅僅是懷著一份真誠的幸福感奔跑在野花盛放的草地上,宛如其中的一種野花,生長在另一片貧乏的土地上。
這匆匆的行程,這短暫的停留在時間的車輪中滾滾而去,麗江的古跡、人情風俗、技藝、文化傳承如血液般世世代代流淌在后人的血管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