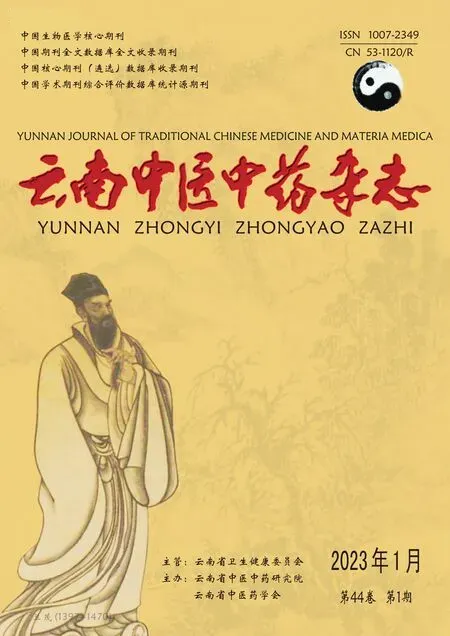郭志華教授辨治心律失常經驗*
陳景怡,魏佳明,袁歆荃,郭志華
(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 長沙 410208)
心律失常(arrhythmia)是臨床上最為多發和嚴重的一類心血管疾病,指在心臟傳導過程中,由各種原因引起的心臟起搏點—“竇房結”的激動異常,導致心電活動不能順利下傳,進而出現心跳節律和頻率的異常[1]。中醫古籍并未載錄心悸這一病名,但早在《黃帝內經》中就有諸如“心澹澹大動”、“心掣”、“心下鼓”等類似心律失常的描述。因患者主要表現為自覺心中跳動不安、時休時作,呈驚恐之貌,嚴重者不能自主、甚至出現死亡,故臨床上多將心律失常劃歸于中醫學中“心悸”和“怔忡”等病證的范疇。目前,現代醫學對心律失常的治療主要可分為兩類,包括藥物治療及非藥物治療(即器械輔助治療),盡管療效值得肯定,但都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良反應[2]。而中醫藥在診療疾病時,采用個體化治療手段,講求宏觀整體和微觀辨證的統一,重“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3]之理,對心律失常的診治較西醫有較為明顯的優勢。
郭志華教授為“湖湘名醫”,湖南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主任醫師,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博士后。從事中醫內科及中西醫結合內科教研、臨床工作三十余載,著手成春,擅用中醫藥辨證治療心血管內科相關疾病,尤善中醫藥辨治心律失常。每于臨證時,郭教授思之甚深,師古而不泥古,創新理論而用之于臨床,常獲良效。筆者有幸跟隨郭教授門診學習聆聽,受益頗豐,現將郭教授辨治心律失常的臨床經驗總結如下,以饗醫者共勉之。
1 病因病機闡微
歷代醫家對心悸的病因病機有不同維度多層次的見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有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復感于邪,內舍于心[4]”,可見,外感邪氣痹阻心脈可致心悸;巢元方所著《諸病源候論》中提出心藏神,主一身之血脈運行,久病體虛者,正氣虧虛,腎氣失充,脾胃失于運化,氣血生化乏源,心之氣陰耗而血脈損,心神失于濡養,可發為驚悸。張介賓在《類經》中曰:“心為臟腑所主,而總統魂魄,并該意志……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5]”,認為五志過極可誘發心悸病癥;清代醫家王清任在其所作《醫林改錯》中尤重血瘀致病之說,創制“血府逐瘀湯”這一經典名方以破胸中血瘀。郭教授總結前人經驗,在闡釋心律失常的病因病機時以“本病虛實夾雜而虛多實少,總屬本虛標實之證”一句而括。年老久病體虛,情志過極,感受外邪,飲食失宜等耗傷氣血陰陽,致心神失于濡養而受擾,痰濁、水飲、火熱、瘀血等實邪阻滯心脈,心神不安,亦可作心悸。
2 辨證論治,病證結合
2.1 快慢分治,“調”則心安 心律失常在臨床上通常根據心搏的快慢分為快速性和緩慢性兩種類型,其中快速性心律失常包括竇性心動過速、房性和室性及房室交界區的期前收縮、心房和心室顫動等,緩慢性心律失常包括較為常見的竇性心動過緩、病竇綜合征及房室傳導阻滯等[1]。對于快速性心律失常,郭教授認為多作為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的并發癥或是失治誤治后的后遺癥而出現,其病機關鍵可概括為“熱”、“毒”、“虛”三字。機體感受風熱時行之毒邪首犯表,表不解漸則化熱入里,里熱毒邪壅盛內犯于心,導致心之陰傷氣耗,心脈失養,血脈不利,則發為心悸,臨床上患者多見一派氣陰虛損夾雜熱毒瘀阻之象。而緩慢性心律失常多為風濕性心臟病患者的常見癥狀,病機可總結為“虛”、“瘀”、“痰”三字。此類型心律失常患者多見于中老年人群,年老體虛者多心氣心陽不足而見“心動悸,脈結代”,如《諸病源候論》所述:“心氣不足,則……驚悸,恍惚……是為心氣之虛[6]”,提示心之陽氣虧耗易導致心悸病癥的發生。同時,郭教授強調“氣為血帥,血為氣母”,陽氣虧虛者無力運行血液停于心脈,陽失溫煦之職而聚痰濕阻滯心絡,亦作緩慢性心律失常。古訓有云“調者,和也;逆則宜和,和則調也[7]”,郭教授謹遵古訓,重視陰陽氣血的調和之道。治療上,對于快速性心律失常者主張清調熱毒以補耗傷之氣陰,而緩慢性心律失常者則主張調補氣血以行痰濕。
2.2 補通兼施,擅用經方
2.2.1 補氣陰益心肺以扶正氣 《傷寒論淺注補正》一書有載“正氣大虧,無陽以宣其氣,更無陰以養其心,此脈結代、心動悸所由來也”[8]。可見,氣虛日久而傷陽,陽損及陰,則為氣陰兩虛。若癥見心悸時作,心神不寧,胸悶短氣,乏力懶言,身熱烘然汗出,舌紅少苔,脈象細數或結代,辨證屬氣陰兩虛之證者,治當以益氣養陰之法。郭教授臨證擅用生脈散加減,此方最早見于“易水學派”創始人張元素的《醫學啟源》,是一劑經典補氣陰之方,因效佳而被廣泛用于臨床。書中詳細記載,“麥門冬,氣寒,味微苦甘,治肺中伏火,脈氣欲絕,加五味子,人參二味,為生脈散”[9]。郭教授認為“生脈散一方雖為補益肺之氣陰方,然心肺兩臟相通,心主血脈,肺朝百脈而輔心行血,肺臟氣陰得補則心脈受濡,心氣復充則脈復。”方中五味子味酸性甘溫,既擅生津止渴、斂肺止汗,又助心神安寧;人參補益心腎肺脾四臟之氣,亦可生津安神;麥門冬味甘微苦性微寒,擅滋養肺胃而生津液。三藥一補、一清、一斂合用,共奏益氣養陰斂汗之效,使心肺得益。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生脈散具有保護心肌,有效改善心肌缺氧,提高心肌耐受力,增強心功能的藥理作用[10]。遣方用藥時,郭教授多慮負擔,將人參一味改為與其性味功效較為相近的太子參代替。
2.2.2 化痰濕行氣血以祛邪氣 “味過于甘,心氣喘滿”[4]、“心之隧道被脂膏瘀窄而氣不宣暢”[11],由此可見,喜食肥甘厚味者易生痰濕,痰濁之邪易阻遏氣機痹阻心脈,發為心悸。若癥見心悸,胸悶時作痛,形體肥胖,四肢沉重,氣短,痰涎量多,舌體胖大邊有齒痕,苔白膩,脈沉滑者,辨為痰阻胸陽,治以豁痰化濁通心陽之法。選方時,郭教授常以瓜蔞薤白半夏湯為基礎方加減化裁。瓜蔞薤白半夏湯出自醫圣張仲景所著《金匱要略》一書,該方由瓜蔞、薤白、半夏以及白酒四物組成,但多棄白酒而用之,藥雖減而效亦佳。郭教授認為本方雖為胸痹心痛者而設,但在臨床運用此方治療心律失常也收到滿意的療效。方中半夏性辛溫而燥化痰濕力強,配以瓜蔞、薤白二藥,其豁痰理氣、通陽散結之效倍增。現代藥理學研究證實,瓜蔞薤白半夏湯可以降低血液黏稠度,降血脂,具有改善心肌微循環,提高心肌耐氧力,抗心律失常作用[12]。“氣屬陽,痰與血同屬陰,易于膠結凝固,氣血流暢則津液并行,無痰以生”[13],故臨證時郭教授多配伍川芎、丹參等藥以加強行氣活血,宣通心陽之力,此兩味藥可起到保護心肌、抗血栓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14-15]。
3 典型病案
患者李某,女,62歲,形體肥胖,于2020年9月30日首次就診。反復胸悶心慌伴短氣1年。經心電圖檢查提示,竇性心律、頻發室性早搏。刻下癥見:陣發性心慌胸悶、氣短,勞累時癥狀加重,常汗出,乏力,時頭暈、口干口苦,二便調,納可,夜寐欠佳,舌質淡白邊稍紅,苔薄黃,脈弦。既往脂肪肝20余年。查體:心律不齊,心率86次/min,脈率86次/min,各瓣膜聽診區未聞及額外心音及其他病理性雜音。西醫診斷:頻發室性早搏。辨病為心悸,證屬氣陰兩虛,痰阻胸陽證,治以益氣養陰,豁痰寬胸為主,選方生脈散合瓜蔞薤白半夏湯加減。太子參20 g,黃芪15 g,柏子仁10 g,生地黃10 g,瓜蔞皮10 g,法半夏10 g,麥冬10 g,五味子10 g,葛根10 g,紅景天10 g,首烏藤15 g,靈芝15 g,遠志10 g,合歡花15 g,丹參10 g,枸杞子15 g,菊花10 g,炙甘草10 g,上方14劑,每日煎服1劑,分2次溫服。兩周后復診,患者心慌、失眠癥狀較前緩解,仍氣短,口稍干未見口苦,飲食較前欠佳。在前方中去菊花1味,加陳皮15 g,山楂15 g,繼服14劑。復過兩周后三診,患者心慌氣短明顯緩解,未見其他特殊不適,前方不變,繼予以20劑鞏固療效,現患者病情逐漸好轉。
按:初診時患者表現為本虛標實之證,患者心悸頻發,符合張仲景所言之“心動悸”,伴汗出,氣短。氣虛不可收氣,見短氣,病位在心,汗為心之液,心氣虧虛則汗失固攝,然汗為陰液,頻汗出則陰虧,使心之氣陰兩傷。此證本為氣虛,勞則耗氣更甚,故心慌氣短癥狀多在勞累后加重。乏力,口干苦,舌邊紅,苔薄黃為氣陰兩虛之候。郭教授認為,患者平素喜食肥甘厚味,形體肥胖,痰濕內生,加之心氣虧虛,無力推動,痰阻氣機而痹阻心脈,則發為心悸,故予生脈散合瓜蔞薤白半夏湯,以補益氣陰,祛痰寬胸以散結。輔以丹參,合歡花化瘀生新,加柏子仁、首烏藤、靈芝、合歡花、遠志養心安神以定悸。全方標實兼治,氣血并調故效顯。二診時,患者諸癥減,睡眠安,而脾胃不佳,基于前方量不變加予陳皮,山楂以健脾開胃。三診時服藥28劑盡,患者言通身輕快,心慌短氣少見,遂守方繼續予以20劑,現患者病情平穩,未訴心悸及其他特殊不適。
4 小結
郭教授臨證辨治心律失常時敬遵古訓,博采眾長而有自得,常誡以“辨證論治”,將此四字貫穿于診治全程,重辨病與辨證的結合,反復總結經驗。強調心律失常的病機虛實夾雜,本虛標實,虛者多以氣陰兩虛常見,實者多痰濕與氣滯血瘀之說。施治時多用歷代經典名方兼治標本,但臨床病情復雜多變,不可偏執一方,應隨證治之,加減化裁,做到理法方藥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