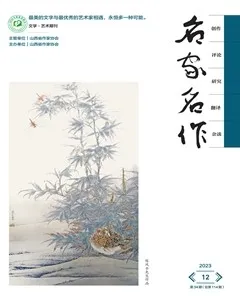自然的頌歌:賴特建筑理論與老子哲學的邂逅
周恣帆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賴特本人樂于分享自己的設計理念,他一生中發表了大量演講與著作向大眾述說自己的見解。賴特“有機建筑”理念首次發表于1908 年的Architecture Record 雜志;隨后他在1912 年的Japanese Print:Interpretation 中贊揚了日本浮世繪版畫的簡約美感和東方藝術給他帶來的創作靈感;賴特在1943 年發表自傳An Autobiography,他在里面談到自己在辜鴻銘陪同下的中國之行;接下來,他又在The Future of Architecture 中提到老子哲學所闡述的空間觀念與他所追尋的有機建筑空間的核心相一致[1]。
1947 年,我國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在《建筑市鎮設計的新觀點》一文中記敘了自己前往美國訪問賴特的故事:當時已經八十高齡的賴特在被問到“什么是建筑的核心理念”時,他回答道:“中國的建筑師只要了解中國古代哲人老子的幾句話就行了。”[2]早在1949 年之前,就有西方的建筑大師揭示了我們祖輩先哲的智慧,如今的我們在面對“中國特色設計理念”這一時代之問時,不妨也回頭看,或許答案就在那個百家爭鳴、充滿魅力的時代。
現如今中國設計學教育總體上沿用一百年前西方包豪斯的教育體系,導致設計學類的學生作品或多或少帶有諸如“現代主義”“國際風格”遺風,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呼應和回溯仍舊不足。這種現象與中國設計在現代時期長期缺席有關,其影響與后果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非常多優秀的設計理念值得學習和借鑒,筆者希望通過分析西方現代主義建筑大師對中國古老哲學思想的關切和借鑒,為中國現代設計提供啟發。
二、東方哲學對賴特建筑思想的影響
(一)第一階段——首次接觸東方文化
賴特首次接觸東方文化是他在芝加哥的第一任雇主——約瑟夫·萊曼·希爾斯比的專屬圖書館里,在那里,他讀了一些有關東方藝術對歐洲影響的書籍,對于日本浮世繪版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聰明的賴特在他后來的制圖中模仿日本浮世繪中的留白技巧,這在當時的美國是從未有過的,也成為賴特后來到建筑家沙利文工作室中求職的重要敲門磚。
(二)第二階段——草原風格的正式形成
在芝加哥博覽會后,賴特產生了對東方文化更加積極的探索精神,在這不久之后建成的自宅——橡樹園之家(Oak park house)被認為是賴特草原風格的初步探索。橡樹園之家兼顧住宅與工作室功能,整個建筑非常低矮,并且石材用料的肌理也力求從視覺效果上貼近大地、導向自然。經過一番思考與沉淀,賴特在草原風格時期的代表作——羅比住宅問世,在當時的美國建筑界產生了一波討論,得到了足夠關注的賴特得以有資本繼續自己的建筑探索。
(三)第三階段——The Book of Tea、東京帝國飯店與辜鴻銘
進入20 世紀,伴隨大機器生產時代而來的“世紀末”思潮令西方世界陷入被工具理性剝奪靈性和自由的焦慮之中,而后人們發現,東方文化內蘊恰好彌補了這種不安和空洞感,因此,“東風西漸”的熱潮浩浩蕩蕩地拉開。1906 年,日本思想家、美術教育家岡倉天心(KaKuzo OkaKura)的著作《茶之書》(The Book of Tea)在美國問世。他在書中總結了中國哲學的影響:“倫理有孔子、美學有老子、宗教有佛陀。”他認為老子哲學對整個亞洲藝術審美有著至高的引領作用[3]。賴特于1912 年受贈此書,他在后來的文章中提到那時自己的感受:“原來早在耶穌之前東方就有位智者闡明了空間的地位與意義,而我覺得自己能夠領悟他的思想,并將其付諸實踐,為此我感到驕傲。”[4]
最讓他驚艷的是老子關于空間“有無空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概念與定義——“房屋的實體不在于屋頂也不在于墻壁,而是在于屋頂與墻壁圍合而成的空間之中,器皿的有用之處在于它能夠盛水而不在于它的材料與樣式……”賴特直言:“老子說出來了,我卻把他蓋出來了。”反映出他對于老子空間觀念的認同和實踐的決心。
1914 年,日本政府邀請賴特,希望他能夠擔任東京帝國飯店的主設計師。在為東京帝國飯店尋找地毯的途中賴特獲得機會造訪中國,拜訪了熱衷于將中國文化與藝術傳播到西方的學者辜鴻銘[5]。中國之行加深了賴特對于東方哲學的理解,他意識到中國的古典建筑形式與思想文化是他所青睞的日本建筑與藝術的啟示根源[6],要想了解東方,最直接的方法是讀懂老子。
三、老子哲學在賴特有機建筑中的體現
(一)“鑿戶牖以為室”與“建筑本體論”
從古至今,西方建筑風格多受到致力于追求超越現實、向上飛升成為神明的神本主義宗教的影響,重工建筑項目多為教堂。這讓如今保留下來的眾多教堂建筑孤獨地矗立在場地里,與周圍格格不入,多充當游客觀光的背景板。總體來看,西方建筑遵照引以為傲的透視理論思想、以長寬高三個緯度為基礎發展。相比之下,東方建筑對自然場景和人造建筑間關系的推敲就做得更為深刻和出色,并且中國傳統空間觀念其實是按照四個維度的方向進行的——內部空間、外部空間、虛空間和時間。中國古建筑多是群體的自由組合,不同的功能被安排在不同的建筑單體內,中間通過游廊聯結,室內空間隔斷則可以根據使用者需求自由移動。
老子在他的著作中闡明的空間觀念:“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中的“無”和“道”分別代表空間和空間的生命力和連續性。賴特正是受到這些思想的強烈啟發,并且直言不諱地表達對其認可的態度:“這種空間才是房屋的實體的想法,早在耶穌五百年前的老子就已經提出了。”[7]于是,這種對于空間的獨特認知使得賴特從同時期其他建筑師中脫穎而出,在同行們奉召“由外向內,注重裝飾,體量空間”的背景下開拓了“由內向外,注重整體,連續空間”的全新設計思路與方法。
(二)“天人合一”與“有機建筑”
賴特一生都在他的作品中找尋自然性,然而,如何在建筑中最大限度地保護自然,始終是賴特不得不面對的一大問題。他最終在中國和日本的園林設計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國古典園林中屢見不鮮的“借景”手法——對自然最大的尊重和保護,就是將其納入室內的一部分。這一點在他設計作品中體現最明顯的莫過于流水別墅——被評價為賴特職業生涯中最輝煌的一座建筑。
流水別墅從選址到建成無不體現著賴特對環境的重視及在尊重自然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流水別墅是一個懸挑框架的造型,地基被選定在巨大的飄石上,賴特解釋道:“巖石經過千萬年的風雨至今巋然不動,已經說明了這樣的位置是適合的、是穩固的。”這種向自然取經的設計方法,在當時人才輩出的建筑師群體中仍舊是罕見的。建筑的入口設計一直是賴特關注的重點,這點在流水別墅中也有所體現——流水別墅帶給人們的體驗與漫游迷宮頗為相似,只不過這個迷宮需要參考的是光線,順著室外投射進的自然光和流水聲便能找到通向室內的道路。同時,進入別墅的三條小路入口處都做得特別矮小,人們需要先虔誠地通過一段幽靜隱蔽的小路,才能來到寬敞明亮的室內。這種入口的處理手法讓我們第一時間就想到中國古典園林的造園手段,即通過縮小入園空間尺度,讓原本不大的園林帶給人們更為寬闊的心理感受。
(三)“見素抱樸”與“材料本性”
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中的“素”的本意是蠶絲的天然光澤,“樸”是木頭未被雕琢過的狀態,這句話教導我們減少自己的私心和欲望,多多關注事物本身的、原始天然的狀態,從中體會到生命的本真,如此才能達到“常善救物,故無棄物”[8]的境界。賴特是否讀過這句話我們已經無從可考,但是他在選擇建筑材料方面的偏好確實與老子的思想不謀而合。在新時代背景下,當越來越多的新材料建筑拔地而起時,逆趨勢發出反對千篇一律的此類現代建筑聲音的賴特無疑是勇敢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賴特反對的是“千篇一律”而不是新材料。實際上,他接受任何一種材料的存在,只是反對忽視材料特性、像機器一樣一味制造流水線建筑的行為,并且稱其為“一種白癡一樣的浪費”[9]。受到信仰影響,賴特對于材料天然特性的尊重是伴隨他職業生涯始終的,他主張“發揮材料的自然之美,掌握各種材料的想象力,材料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美的風格,這取決于建筑師如何使用它”,他對材料的形態、紋理、色澤、力學和化學性能等做了認真且詳細的研究,他指出“每一種材料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故事”,材料伴隨著賴特設計風格的成長,也讓我們得以見證他設計思想的演變。
(四)“小國寡民”與“廣畝城市”
老子和賴特,兩個生活在飛速發展時代中的人,面對膨脹的、動蕩的社會狀況,他們做出的見解跨越時空達成了一致。“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在動蕩的春秋末期,老子描繪了人類社會最初始的狀態——安居樂業、清心寡欲、人心單純,這也是老子所追求的“道”的終極目標。兩千多年后,賴特在面對同樣急速發展以至于經濟大蕭條的社會,做出了同老子同樣的思考——“今日的社會沒有人關注人類的急速發展究竟是健康成長的興奮還是疾病的高熱癥狀”,對于此,賴特針對美國中產階級,于1935 年提出了“廣畝城市(Broadacre City)”的城市規劃理念。
“廣畝城市”又稱為“有機城市”[10],在這種城市規劃中,較高的、綜合性功能的樓房被安排在城市的角落,中心區域聚集的是低矮的住宅:在這里,每戶人家都有獨立的住宅、出行工具和根據人口比例分配的綠地空間,不同的社區按照植物種類不同來劃分,同時多樣的植物也會帶來新鮮的空氣。在這樣的城市中,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滿足高品質生活的前提下更加貼近自然,極大程度上消除階級,社區之間沒有優劣之分,只有個性之間的區別,這樣的劃分原則使得人們的欲望得以極大的削減。
四、老子哲學在賴特建筑實踐中的運用——以古根海姆博物館流線設計為例
所羅門·R·古根海姆博物館是賴特收到美國商人所羅門·古根海姆邀請所作,這是他職業生涯晚期最重要的項目,也是他在大都市紐約建成的唯一一件建筑作品。古根海姆博物館承載了賴特豐厚的建筑思想,以其超凡的形態、獨特的動線、創新的展覽空間確立了其在建筑史上不朽的地位,也成為賴特的代表作品之一。
(一)流線分析
主展廳是動線最精彩的部分,游客需要先乘電梯到達頂層,再沿坡道順時針回旋向下,依次參觀展品,整個參觀路線長430m,坡度3%,由螺旋坡道包圍,在中庭中部形成一處開敞的中庭空間,中庭由玻璃頂覆蓋,為中庭及展廳提供自然采光。
許多批評家對古根海姆博物館的游客體驗呈現出消極態度,認為斜坡帶給人們匆忙通過的心理暗示。然而,賴特這位有機建筑大師卻將內部的坡度比作波浪,他希望人們漫步其中感受到的是“像靜止的水波一樣連綿不斷的感覺”。這似乎暗示著藝術沒有終點,也好像是在照應20 世紀50 年代的美國“沒有終點、無窮動”的美國精神[11]。
(二)流線設計所體現的哲學理念
筆者選擇從哲學的意義來理解,游覽博物館中的美術作品獲得精神層面的享受,好似上山,我們既要能登上藝術的高地,也要逐漸降落到紛繁的世間。從上向下的游覽體驗仿佛也在告訴我們上山容易下山難,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好比老子的“上山行修,下山行道”,他認為真正的道士能夠“上山”求隱尋道的同時,也要能夠“下山”將自己的德行傳遞給世人,將自己的領悟散播到世間各處。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也有著相似的理念:“上山”意味著凈化思想、提升修養、獲取智慧,意味著你將在思想的空中樓閣里自我修煉;“下山”意味著尋求同伴、融入社會、參與行動、輸出語言,這代表你將會成為現實中的人,與其他現實中的同類產生交集。
或許賴特本人在設計古根海姆博物館的流線規劃時并沒有思考到哲學這樣深刻的層面,而只是覺得有趣、比較符合本人的設計理念,但是作為職業生涯晚期的作品,當時賴特的設計手法早已爐火純青,在東方文化、特別是老子哲學對他產生的深刻影響或許早已潛移默化地應用于博物館的各處。結合之前對于賴特東方情結的分析和賴特本人對于老子哲學的喜愛,筆者認為這樣的解讀是合理且成立的。
五、結語
老子與賴特,兩位不同領域的大家,相隔將近兩千年的思想碰撞,不僅具有建筑學與設計學的研究意義,并且這種中西文化理念的聯結與溝通是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和學習的。21 世紀的世界是文化深度融合的世界,我們要厘清中西方文化、傳統美學智慧與現代建筑藝術思潮之間的價值轉換與文化融通,讓東方美學與理念煥發出新的光彩與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