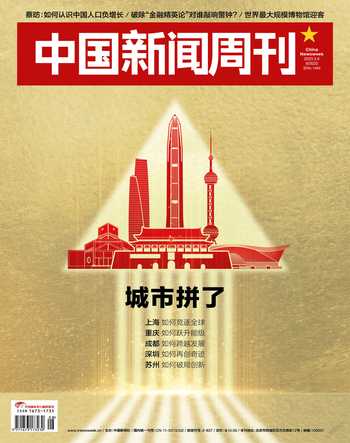美國援助烏克蘭的外交盤算
孫晉

2月20日,烏克蘭基輔的馬林斯基宮,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中右)與美國總統拜登(中左)舉行會晤。圖/澎湃影像?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自烏克蘭危機升級一年來首次訪問基輔,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在2月3日剛剛宣布向烏克蘭追加22億美元新軍事援助計劃后,拜登在這次訪問中再次提出數十億“直接預算援助”,以進一步“增強烏克蘭的武裝抵抗能力”。
美國《政客》雜志援引白宮高級官員的話說,拜登原本計劃在2022年就訪問基輔,只是基于后勤和安全考慮才一拖再拖。過去幾個月,拜登曾不止一次抱怨“他們不會讓我越過邊境”。與此同時,國務院、特勤局、五角大樓為此行進行了長達數月的協調,直到2月20日,一列戒備森嚴、車窗緊閉的八節車廂火車載著拜登到達基輔。
陰差陽錯的是,這次拖延日久的突然訪問“恰好”趕上俄烏沖突一周年,又“恰好”在拜登基本明確參加2024年總統選舉后成行。一些美國媒體認為拜登“在基輔宣布啟動第二任期的選戰”。塔斯社則援引俄羅斯專家的話說,拜登趕在20日訪問基輔,是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普京將于21日向國家杜馬發表講話的注意力,是美俄“宣傳對抗”的又一次升級。
顯然,拜登此行有多樣的目的。但在美國專家的多數分析中,“加速”都是一個關鍵詞。考慮到2024年是美國大選之年,華盛頓外交政策界的普遍觀點認為,拜登其實有意在2023年底之前推動結束俄烏間的主要戰事。只是,這種“加速”是加大對烏援助、讓烏克蘭獲得新的戰場優勢,還是推動澤連斯基接受更現實的談判條件、盡快回到和平進程上,尚未可知。
近期,美國外交政策目標逐漸調整,已經朝這個“加速”的方向努力,至少實現沖突降級,以將戰略重心繼續向亞太地區轉移。美國外交界也開始討論戰后武器流向追蹤管理、俄羅斯凍結財產處置、俄羅斯未來政治秩序、烏克蘭戰后經濟重建等技術性問題。俄烏間的沖突仍在繼續,但一年多來遭受猛烈沖擊的美國外交政策,又將走向何方?
2022年2月24日凌晨,俄軍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當天,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俄羅斯儲蓄銀行等主要銀行及24個白俄羅斯主體;25日,美國商務部對俄宣布技術貿易制裁;26日,美國聯合歐盟和七國集團主要成員國宣布對俄采取聯合行動,將多個俄羅斯銀行移出全球銀行電匯SWIFT信息系統,阻止俄央行使用外匯儲備資產,并限制俄羅斯企業;27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俄羅斯央行、財政部和主權基金。
此前的2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令承認頓涅茨克及盧甘斯克為“獨立國家”,拜登隨即簽署1406號總統令宣布對該地區實施投資及貿易制裁。次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俄羅斯國家開發銀行(VEB)和工業通訊銀行(PSB)、五家俄羅斯企業,并對俄羅斯國債采取限制。彼時,美國主要外交智庫討論的重點是,普京簽署法令并派兵兩地是否意味著俄羅斯“與烏克蘭展開更廣泛的戰爭”。2月24日危機升級后,美國政府依然采取快速制裁外交響應為主、軍援情報支持為輔的政策,恰恰體現出華府政策界未能準確預判沖突升級,也并不確定局勢走向。
危機升級第一周,彌漫在華盛頓的是悲觀情緒,主流觀點認為澤連斯基政府會像1939年的波蘭一樣,在一個月左右迅速崩潰。“去年2月,俄羅斯發起‘特別軍事行動’時,即使是其最熱心的外國支持者也預計烏克蘭極為有限的防御工事將在幾天內崩潰。”畢竟,當年波蘭在36天內被德國和蘇聯擊潰并瓜分。同樣也是1939年,即便是在蘇芬戰爭中,芬蘭也展現出遠超預計的抵抗能力,但為期4個半月蘇芬戰爭的結果仍是蘇勝芬敗,最終芬蘭同意割讓11%的領土并簽署和平協定。
對美方而言,當時尤其不確定的是澤連斯基政府有無抵抗意志、有無抵抗能力以及究竟能抵抗多久。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當時美國政府一方面在公開場合給予基輔全力聲援,但另一方面包括時任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內的美英兩國高級官員卻私下親自力勸澤連斯基“到倫敦組建流亡政權”,至少應將政府西遷到利沃夫。約翰遜甚至向澤連斯基承諾會為其領導的“烏克蘭流亡政府”提供庇護。
2022年3月1日,即危機升級一周之際,成為美國相關外交政策的第一個分界線。在此之前,看似美國領導七國集團(G7)宣布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但是這些措施以軟制裁為主,“雷聲大雨點小”,實際落實很少。直到澤連斯基政府出乎國際社會預料地挺過了第一周且沒有“跑路”,華盛頓各智庫的討論重點才轉向“升級對俄制裁能否阻止俄羅斯繼續用兵”。這意味著直到這時分析人士才初步確信,這不會是一場“形勢一邊倒”的閃電戰。
此后在3月2日、3日和7日,美國商務部、交通部、財政部、國務院才相繼宣布新一輪對俄制裁措施。七國集團和歐盟在3月11日宣布新一輪聯合制裁行動,在3月16日正式成立聯合制裁工作組。3月14日,美國對外關系協會主席哈斯發表題為“從可選之戰到持久之戰”的署名文章,預示著政策界放棄了先前認為戰事可通過斡旋施壓而可選可避的決策出發點,其預設條件調整為:這很可能是一次持久戰,基輔不會迅速完敗,莫斯科也不會輕易取勝。
確信俄烏戰局向長期化發展后,美國一系列外交政策開始落地,這總體上包括三個方面:孤立“敵占方”,援立盟友方,中立第三方。
孤立“敵占方”,是指美國向歐洲各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中斷與俄羅斯的經貿往來,從而瓦解“敵占方”在持久戰中的相持能力。在2022年3月中下旬,很多歐洲國家彼時相信俄軍仍有通過升級動員來取得軍事勝利的可能。因此,3月24日的七國集團和歐盟領導人在北約總部布魯塞爾的會談,只是強調全面落實已經宣布的制裁措施,沒有宣布新的制裁。
4月初,以涉及“屠殺平民”的布查事件為契機,美國協調七國集團和歐盟迅速調整外交政策,全力開展壓力外交攻勢。4月6日,七國集團和歐盟以布查事件為由宣布對俄新一輪大規模制裁。隨后三天里,美國財政部、商務部和白宮宣布全面金融制裁,切斷與俄羅斯的一切商貿往來。4月8日,圍繞布查事件和馬里烏波爾戰事,美國外交界全力啟動“俄羅斯是否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大討論。經過一系列努力,美國最終說服七國集團和歐盟在5月8日發表共同聲明,歐盟同意分步終止自俄羅斯的能源進口,追隨美國逐步斷絕與俄羅斯的商貿往來。
6月27日在德國召開的七國集團峰會再次強調了這一立場,要求協調一致“將俄羅斯從全球經濟中孤立出去,打擊規避制裁活動”。9月2日,在美國財長耶倫的協調斡旋下,七國集團財長最終敲定落實對俄羅斯石油限價措施。
援立盟友方,是指美國開始關注“持久戰”中的長期困難,圍繞如何長期堅持下去的系列問題向歐洲各國提供援助,從而提升盟友方在“持久戰”中的相持能力。
這方面首當其沖的是難民問題。2022年3月24日,美國對外關系協會研究小組首次關注烏克蘭難民問題,當時估計會有超過300萬難民涌向波蘭及其他鄰國。僅僅6天后,這一預測被上調至700萬人。由此,美國啟動自馬歇爾計劃以來最大規模的對歐援助。
2022 年初以來,美國向烏克蘭提供近 480 億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人道主義物資援助、財政援助和軍事援助。這些援助主要由3月、5月和 9月的三個國會撥款法案提供,均發生在美國政府確信澤連斯基政府沒有“跑路”并具備頑強抵抗意志、可靠抵抗動員能力、能將俄烏戰事帶入相持階段以后。目前美國對烏援助規模相當于歐盟(300億美元)的1.6倍、英國(80億美元)的6倍、德國(60億美元)的8倍或是法國(12億美元)的40倍。
中立第三方,是指自確認俄烏戰事進入相持階段以來,美國外交界開始全面斡旋第三方國家與俄烏雙方及美國的關系,從而設法通過經濟孤立削弱“敵占方”在持久戰中的相持能力。這方面美國外交政策是在官方立場上設法勸說各第三方國家盡可能保持中立。同時,美國媒體則不斷“敲打”各國,通過新聞報道和政府官員發聲“譴責”乃至污名化各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正常貿易活動,希望通過輿論壓力來讓各第三方盡量減少與莫斯科的貿易往來。
總的來說,華盛頓政策界對拜登政府的俄烏政策持肯定態度。進入2023年2月,美歐外交界的研判展望更加樂觀,甚至開始總結各國一年來如何“以驚人的成功解決了(信心)問題”,維持了國內對其烏克蘭戰爭外交政策上的支持。
如今,在俄烏沖突升級一周年之際,美國政策界再次出現分歧。一種觀點認為,當下符合美國利益的外交戰略不應該是迅速結束俄烏戰事,而應該是保持對俄烏問題的持續關注,保持美國對俄烏戰事的高強度投入,從而保持對俄軍的持續消耗。
一些專家還認為,與美國 2022 年 7150 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總額相比,對烏援助金額顯得微不足道。“這場戰爭為美國侵蝕削弱俄羅斯的常規防御能力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美國花費其國防預算的 5.6% 來摧毀俄羅斯近一半的常規軍事能力,這似乎是一項不可思議的投資。每年僅花費 400 億美元,就會侵蝕 1000億至1500 億美元的威脅價值,即兩到三倍的回報”。
這些觀點是否能占據主流,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俄烏戰局下一步的發展。自“烏軍在 2022 年的最后四個月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以來,有美方專家主張2023年烏軍能否鞏固戰果擴大優勢極為關鍵。這種“2023年乃決定性之年”的觀點,亦促使美德等國在2023年1月確認向烏克蘭提供先進主戰坦克,以強化烏軍進攻能力,盡快結束相持階段,推動烏方依托軍事戰果啟動與俄談判。
與之對應的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既然俄烏戰事已不再是美國和北約的首要威脅,所謂“印太問題”特別是“應對中國崛起”,才是美國外交戰略的首要重點。有分析認為,烏克蘭危機升級前,美國主導下的歐洲安全秩序,因北約失去其戰略目標而瀕臨瓦解,俄烏沖突的出現幫助美國解決了這一難題,為北約的復蘇與重振找到了“共同的目標”。
不過,具體外交政策的選擇還受到美國國內政治議程的影響。考慮到2024年是美國大選之年,有觀點認為,拜登“已緊急敦促澤連斯基政府鞏固戰果并盡可能發起反擊”,因為若能在2023年底前結束俄烏戰場主要戰事,拜登將以勝利者的姿態全身心投入2024年大選。另一方面,共和黨主導的國會則試圖阻止美國政府在2023年給予烏克蘭更多援助。本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略微占多數的共和黨人(52% 對 48%)希望他們的國會代表反對向烏克蘭提供更多資金。
目前尚不能確定拜登會作出怎樣的選擇。美國近期的民調顯示,選民的首要關切是年屆80歲的拜登能否勝任又一個四年任期。考慮到親抵戰區這一先前12位總統都屢試不爽的助選做法有助于提振他低迷的支持率,指責他年事已高的說法也許會因此而弱化。相比特普朗訪問阿富汗和伊拉克全程都在戒備森嚴的美軍基地內,拜登坐火車抵達的基輔之行使得2024 年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無論是特朗普還是佛羅里達州州長或其他人,都沒法在勇氣上對其質疑。此外,歷史上,美國選民多支持處于戰爭中的總統繼續連任。
目前,美國外交界主要智庫已開始討論“戰爭是否會在 2023 年結束” 以及“結束烏克蘭戰爭需要什么條件”,也開始討論一些烏克蘭戰后經濟重建的技術性問題 。俄烏沖突仍在繼續,但自阿富汗撤軍以來重心不得不因此放在俄烏局勢上的美國外交政策,或將出現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