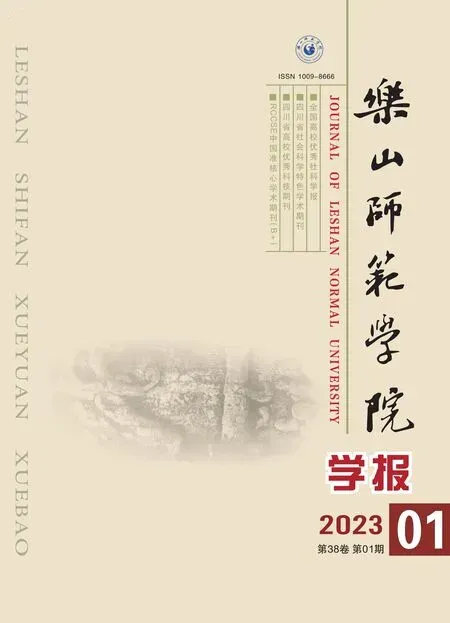蘇軾與文同研究二題
張小花,慶振軒
(1.蘭州交通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2.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蘇軾與文同的交往是宋代文壇上的一段佳話,二人不僅有姻親之誼,而且互相引為詩詞、繪畫藝術上的知音。二人相互唱和、交游的詩詞及書信較多。蘇軾與文同交往的作品已有學者羅琴先生加以統計,本文在前人學者開拓之功的基礎上,進行查缺補漏,得出85首(篇)的最新數字,并經過詳細考察,確定幾篇難以系年的作品的具體寫作時間。同時,對蘇軾與文同“從表兄弟”的關系進行考證,厘清概念。以期對蘇軾與文同研究的深入和細化提供借鑒。
一、蘇軾有關文同詩文創作篇目考訂
檢索文獻,蘇軾父子與文同頗多詩文、書信交往,羅琴《文同與二蘇的交游及交往詩文系年考》一文對此詳加考述并加以系年,其開拓之功自不待言。但羅女士個別詩文的系年及統計篇目還可討論。
文同有關蘇軾的詩文今存19首(篇),蘇洵有關文同的詩1首,蘇軾有關文同的詩文79首(篇),蘇轍有關文同的詩文55首(篇)。[1]
有羅琴先生大作在先,后之研討文同、蘇軾交游詩文者多祖其說,如:庫萬曉《文同和蘇軾關系研究》一文即沿述其論;喻世華先生有多篇研究蘇軾大作發布,亦在文章中寫道:“根據羅琴女士的考證——蘇軾有關文同的詩文79首(篇)。”[2]但詳加檢索,據羅琴一文統計蘇軾與文同有關詩文篇目或有失誤。
首先,羅文某些字面易令人重復計算。比如文中《小簡》出現3次:“熙寧十年,丁巳1077年,文同60歲”[1],引蘇軾《小簡》2篇。其一為文同與蘇轍議兒女婚事,蘇軾作《小簡》:“今日沿汴赴任,與弟同行。聞與可與之議姻,極為喜幸。”[1]其二為“文同寄贈六言小集,蘇軾有書答謝。蘇軾《小簡》:‘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有見。’”[1]“元豐元年,戊午1078年,文同61歲”,再引蘇軾《小簡》一篇:“見乞浙郡,不知得否?——若得與兄聯棹南行,一段異事也。”[1]此三篇《小簡》分別見于蘇軾《與文與可書十一首》之三、之五、之九。
蘇軾與文同書信往來,《蘇軾文集·佚文匯編》卷二收《與文與可十一首》,其中六首皆作于元豐元年。又收《與文與可三首》,亦作于本年。而對蘇軾的這三篇《小簡》沒有明確其已收于《與文與可十一首》,極易引起重復計算。
其次,羅文在文末認為蘇軾與文與可交游詩文“尚有以下諸作寫作時間地點不明,未能系年,即蘇軾的《文與可琴銘》《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戒壇院文與可墨竹贊》《文與可枯木贊》《跋文與可論草書后》《跋文與可紆竹》《與可拾詩》”[1],共計七篇。但其“熙寧四年,辛亥1071年,文同54歲”[1]即有以下一段文字:
蘇軾過潁州(安徽阜陽),拜謁歐陽修,盛贊文同詩才。《仇池筆記》卷下,“余昔時對歐陽公頌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1]
查蘇軾《仇池筆記》卷下有《與可拾詩》,文字與羅文所引完全相同,則《與可拾詩》可以確定為蘇軾熙寧四年(1071)之作。文字表述可明確為“《仇池筆記》卷下《與可拾詩》條”,且不可重復計算。而《文與可琴銘》,羅琴女士明確其為“元豐四年,辛酉1081年”[1]蘇軾所作,文曰:“蘇軾作《文與可琴銘》,寫明‘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1]如此,則《與可拾詩》與《文與可琴銘》不可列入難以系年之作。如此之類,易引起篇目計算的差誤。
最后,涉及蘇軾與文同交游的詩文尚有未系年,及未被列入難以系年篇目者數篇。羅文“元豐元年,戊午1078年”[1]下引蘇軾《與李公擇書》云:“邁往南京,為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與文與可子,呼去干事。”[1]此書見于蘇軾《與李公擇書十七首》之五,注云“元豐元年秋冬作于徐州”[3]5606,但文與可亡后,蘇軾作于元豐二年或三年的《與李公擇書》,卻未被收錄。其文云:“與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壽,又哀其極貧,后事索然。而子由婿其少子,頗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賢而文,久遠卻不復憂,惟目下不可不助他耳。”[3]5626此信見于蘇軾《與李公擇書十七首》之第十五。蘇軾與友人書信往來頗多,其《與朱康叔二十首》第一書亦涉及文同身后事:“與可船旦夕到此,為之泫然。想公亦爾也。”[3]6471該書“元豐三年四月作于黃州”[3]6472。
元祐元年,文同之子文務光病逝之后,蘇軾寄書勸慰文同夫人,書云:“事已無可奈何,千萬寬中強解勉也。舍弟婦自聞逸民之喪,憂惱殊甚,恐久成疾。”(《與親家母一首》)[3]8635-8636
蘇軾《文驥字說》,作于元祐三年(1088)。文驥為文務光之子,文同之孫,蘇轍外孫。文務光死后,蘇轍接女兒與外孫來家,并親自教育。蘇軾為其取名并寫《字說》,這在蘇軾的文集中并不多見,足見他對文驥的疼愛與厚望。此文分兩部分:前一部分作于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后一部分作于是年十月。文曰:
馬之于德,力盡于蹄嚙,智盡于竊銜詭轡。以蹄嚙之力為千里,以竊詭之智為道迷,此之為驥。文與可學士之孫,逸民秀才之子,蘇子由侍郎之外孫,小名驥孫,因名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字之曰元德。元祐三年外伯翁東坡居士書。
東坡居士言:驥孫才五歲,入吾家,見先府君畫像,曰:“我嘗見于大慈寺中和院。”試呼出相之,骨法已奇,神氣沉穩。此兒一日千里,吾輩猶及見之。他日學問,知驥之在德不在力,尚不辜東坡之言。元祐三年十月癸酉門下后省書。[3]1046
關于古人命名取字的淵源,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云:“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后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義無大異焉。”[4]蘇軾為文同之孫命名文驥,字元德,以“千里馬”譬喻侄孫,期望他日后學問道德一日千里。
蘇軾與文同的神交終東坡一生。元符三年(1100)二月蘇軾所作《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三首之一曰:“老可能為竹寫真,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心境都將付臥輪。”[3]5065詩作感懷文與可之墨竹傳神寫照,對幼子蘇過得其真傳感到欣慰。此外,蘇軾寫作時間未詳的《書張少公判狀》亦少有論者言及,其文曰:
張旭為常熟尉,有父老訟事,為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訟,亦為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為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斗而草書長,此殆謬也。[3]7796
除上述篇目外,還有明代李日華《六研齋三筆》錄載,《蘇軾資料匯編》收錄,孔凡禮《蘇軾年譜》卷二十一引述,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引用并名為《書竹石后》一文,移錄如下:
昔歲,余嘗偕方竹逸尋凈觀長老,至其東齋小閣中,壁有與可所畫竹石,其根莖脈縷,牙角節葉,無不臻理,非世之工人所能者。與可論畫竹木,於形既不可失,而理更當知;生死新老,煙云風雨,必曲盡真態,合於天造,厭于人意;而形理兩全,然后可言曉畫。故非達才明理,不能辯論也。今竹逸求余畫竹,因妄襲與可法則為之,并書舊事為贈。元豐五年八月四日,眉山蘇軾。[3]8886
可見,蘇軾與文同交游的詩文,在羅琴統計的基礎上,去除復重,添加缺失,有關詩文應為85首(篇)。這是研究蘇軾與文同交游的基礎。
二、蘇軾與文同是否表兄弟關系考證
在部分介紹文同或研究蘇軾與文同關系的文章中,往往誤以為二人乃表兄弟的關系,如徐麗《蘇軾與文同》一文即認為:
蘇軾與文同的交往就很獨特,蘇軾與文同是遠親,蘇軾稱文同為從表兄—不僅如此,文同的兒子還與蘇轍的女兒結為姻親,蘇文兩家親上加親,這種深厚的親情和友情,使得蘇軾在文同去世后十四年還有祭文同的文字出現,十分難得。[5]
有些文章在題目中徑稱《蘇軾有個表哥叫文同》[6]、《蘇軾表哥文同:詩詞書畫“四絕”》[7]。但揆諸實際,蘇軾從未稱文同為“從表兄”,蘇軾與文同并非表兄弟關系。查閱有關史料,蘇軾在與文同書信往來、詩文唱酬以及追念緬懷中,或稱“余友文與可”“友人文與可”“吾友文君名同”;或稱“與可老兄”“老兄”;文同之子與蘇轍之女聯姻,蘇軾稱文同“親家翁”;文同去世,蘇軾稱其為“亡友”;有時蘇軾謙稱“劣弟”;在《祭文與可文》《再祭文與可文》中均自稱“從表弟”。這一切都意在“以見與可于予親厚無間者也”。[3]1155但正如此,人們誤以為蘇軾、文同乃表兄弟。而此誤傳較早見于葉夢得,其說曰: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為中表兄弟,相厚。為人靖深,超然不嬰世事。善畫墨竹,作詩賦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譏笑,同極以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8]
《宋史·文同傳》沿用此次種說法,也說“軾,同之從表弟也”[9]。故而之后以訛傳訛,歷代許多文人學者均認為他們是親戚關系。關于蘇軾文同非表兄弟的問題,孔凡禮《蘇軾年譜》、羅琴《文同與二蘇交往及交游詩文系年》等文均有明晰的文字論述,茲摘錄于下:
(蘇軾和文同洋州園池三十首)《金石錄續編》卷十六著錄,題作《寄題與可學士洋州園池三十首》,下署“從表弟蘇軾上”,此前云“熙寧九年三月四日東武西齋”—詳考史實,蘇、文實非中表,“從表弟”云云不過極言其親近,非同一般。《佚文匯編》卷二《與張安道》第一簡末云“從表侄蘇軾頓首”。蘇軾與張方平(安道)亦無親戚關系,稱“從表侄”,亦極言其親近。[10]
羅琴女士亦就蘇軾《文與可字說》刻石署名“從表弟蘇軾”一事,從蘇文兩家的家世淵源加以考述:
蘇軾作《文與可字說》。南宋乾道中汪應辰主持刻石于成都府治之《西樓書帖》有落款云:“熙寧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從表弟蘇軾上。”文同為西漢蜀郡太守文翁之后,其后一支定居永泰。文同“曾祖彥明,祖廷蘊,考昌翰,皆儒服不仕”,“考公以公贈尚書都官郎中,妣李氏,仁壽縣太君”。“文同娶衛氏,追封旌德縣君。再娶李氏,封永和縣君。”(范百祿《文公墓志銘》)三蘇為武則天朝宰相蘇味道之后,世居眉州,家世漸衰。蘇洵妻程氏,蘇軾前妻王弗,繼室王閏之,蘇轍妻史氏,蘇、文兩家皆不顯,無官場之往來,分居永泰與眉州,無聯姻之關系。因此,文同與二蘇實無中表關系。蘇軾自稱為文同之“從表弟”,乃是表示一種親密、親切之意。[1]
之后研究者也認同孔、羅的論斷,如彭敏《蘇軾與文同的交誼》[11]、葉翔羚《蘇軾的交游與文學》均引述了羅琴女士的上述結論;葉翔羚一文還根據“蘇軾蘇轍兄弟皆為親族觀念很重之人,若詩文作品中出現親戚關系,一般會加以說明,在人名前冠以親戚關系,然而在于文同的詩文往來過程中均無此現象”[12]作為旁證,再次肯定蘇軾與文同絕非從表兄弟關系。
總之,因蘇軾自稱“從表弟”而撰文言蘇軾、文同乃中表兄弟是望文生義。由此,蘇軾有關文同的詩文中何以會蘊含特別深厚的情感,是我們要致力于探尋的所在。
三、結語
蘇軾治平元年(1064)與文同初識,元豐二年(1079)文同去世,期間二人聚少離多,更多是通過詩詞書畫互通情誼,探討書畫創作心得,共同開創了湖州畫派。蘇軾欽佩文同的人品才華,視為書畫藝術方面唯一的知音,同樣也把自己視為文同藝術上的知己,文同默認這一事實。因此,文同的逝世,使蘇軾失去了一位摯友,失去了藝術上的知音。正如他在《祭文與可學士文》中所寫:“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3]6985因此蘇軾才會在文同去世后的十幾年間對故友念念不忘,不僅僅是對二人友誼的懷念和眷戀,也隱含著對知音難覓的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