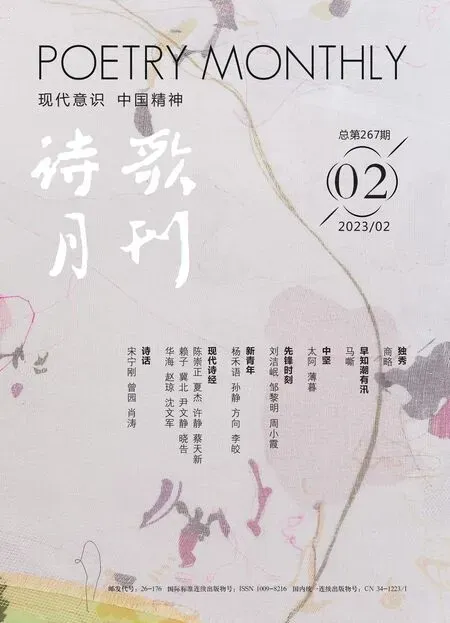油畫中的女人(組詩)
孫靜
差錯
她的桌子上擺放著《焚舟紀》
她說起話來滔滔不絕
她吐出的每個字
無一例外變成一粒塵埃
秋蟬在驚惶
奔跑在良知的前面
追問、懷疑、猜忌
她打開厚重的《焚舟紀》
讀著里面一篇簡短的波德萊爾傳
后來將書合上
嘴里又在滔滔不絕地講話
對著另一個人
夏天滴落在她的窗簾上
她潦草拒斥
嘴里又在滔滔不絕地
吐露著塵埃
秋蟬又發出驚厥的提琴聲
以聲音丈量著世界上一切的流動
觀察著,無以為信著
被看不見的空氣折磨著
向自己介紹自己
鏡子站在我的面前篡奪,回想著我的一生
將我介紹給宇宙:
掠奪與榮耀
同時流在她的毛細血管
止不住突涌棕灰色激流的軀體
注定要流干的洶涌之河
瓦爾登湖渙散
她站在講臺上,向班上所有人說
你們要找到自己的瓦爾登湖
后來她私下里和我說
你找到了你的瓦爾登湖
這一切或許是幻象
我的湖洶涌澎湃,驟又渙散
我的瓦爾登湖在夜空自白了幾百年
又憑空消失好幾秒鐘
我抓啊找啊跑啊舞啊躺在森林里死亡啊
她卻消失在這個地球上
帶上我的瓦爾登湖
人間蒸發在我的腦神經中
留下大片的影子——
就像一片銀色的被單飛舞在太陽之下
留下我直勾勾的眼神
留下我再也無法停下的腳步聲
油畫中的女人
掛在墻上的那幅油畫
金色的古典邊框內
仰臥一個女人
火紅色的胸罩中逸出體香
下身穿戴著火紅色輕紗短褲
世人早已將她命名
包括她身上的一切
畫家在她的耳垂上
一邊栽種了一朵白玫瑰
又感到某種枯燥
放棄了自己的畫作
到森林中打獵了一只漫步中的美洲豹
從她/他尚有呼吸的皮毛上
剪下兩枚硬幣大小的圓
貼在畫中女人的耳垂上
遮蓋了先前的白玫瑰
畫家讓她
一邊燃燒著火焰
一邊冷凍著冰霜
后又把冰霜拋棄
金色邊框中的她
擺在那里軟弱的身軀即刻碎落
支離破敗
像泥土捏成的一座雕塑
雨水從天而降,她頃刻融化
雨水順著地下排水系統流走
她被夾帶其中
再也拼不成完整的自己
如果我不認識你
如果我不認識你
就讓風來抱擁你
如果我不認識那個真實的你
歲月剎那間變成一塊
從街邊的閑人酒館里
買來的提拉米蘇,吞下它
分不清廉價或是高貴的過往,就變成
一只輕飄飄曼舞的蝴蝶
某出悲喜劇的上演,仰賴于
它在花叢間的密謀
如果我從不認識你
我從來也不曾熟識我自己——
一百六十度的爐上之血
找不到家鄉的瘦弱白蛾
好端端休克與緘默的濃烈傍晚
密度過高、過于壓迫神經的午夜
皮扎尼克永恒的怪誕之手
在這個香風拂面的夜晚
我看著這首二十年前未完成的詩
無能為力地加上這最后的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