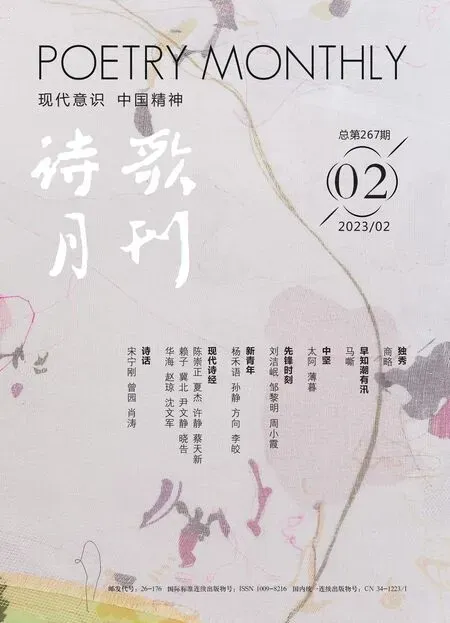我準備諷刺這個世界一次
曾園
去年底買到南野的詩集《語言繁華》,最近慢慢讀完了。在我看來,這部詩集或可稱得上2021 年最佳詩集之一。
南野在20 世紀80 年代躋身國內前十名詩人行列,90 年代初卻淡出詩歌界。原因也許在他說過的這段話里:“當代詩的一個明顯變化就是從詩歌運動到詩歌活動,活動的模式(凸顯等級的座位與發言次序,演藝式的朗誦與吃喝游玩項目等)則從程序到內容,日益呈現……文化格局中形成的慣例,它由官場與商界延伸過來,再到學術界、文學界,詩歌終于全面地被世俗形態俘獲。”南野有篇文章叫作《詩,將在詩人中選擇詩人》,顯然他覺得選擇權已經暗中轉移了。
今天的人(即使是詩人)很難相信這種轉移改變了什么。馬修·阿諾德在《當前文學批評的功能》里說:“埃斯庫羅斯和莎士比亞的時代使我們感受到他們先前的名望。……有一塊希望的土地,批評只能對它作出召喚。這塊希望的土地并不是我們可以進入的,我們將死于荒野……”也許,至少在南野看來,詩人的名望曾經是真金白銀的。但現在,這種“詩人名望”早就經歷了長久的持續貶值,一直貶到他不想再去維持與爭取什么了。
名望之貶值有時以詩人名聲大面積擴散方式體現,“對海子某首詩歌的普遍商業性圖解”讓他更感失望。這首詩應該是大家熟悉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在大海邊擁有一所房子的人,不太可能是海子。真正能擁有海邊房子的詩人倒有一個,就是美國詩人羅賓遜·杰弗斯。1919 年他在加利福尼亞蒙特雷半島南部的卡爾梅自建了一座石屋。他一直是南野喜愛的詩人,他寫下的多首歌頌海角與巖礁的詩在《語言繁華》中有多處回響。
杰弗斯在《四月勁風》中寫道:“大海刺戳著西岸,把花崗巖/洗得雪白,杯子滿溢出來,世界的舞蹈游戲變得過分熱烈。”南野在《恐怖海岸》中以更為猛烈的風格回應:“大海蒼茫,海岸如廢墟。巍峨的破損……”
海子的房子是虛構的,南野也早就寫出一首關于建房之不可能的詩:《筑巢者》。他以一種精確的神秘感寫道:“你的父親是一只鳥/他死在荒地上/現在該是你來補償的時候。”從“朦朧詩”開始,詩人都在尋找自己與傳統相處方式,如北島的《回答》、韓東的《有關大雁塔》、歐陽江河的《懸棺》等。《筑巢者》在這一批杰作中顯得既精致,又充滿了濃郁的超現實主義味道。
即使是在現實世界,“筑巢者”感受到的不僅是海子對虛構房產的譫妄之詩的虛妄。因為房產廣告商不僅將海子的詩意劫掠一空,他們還將房地產新哲學(被劫掠的荷爾德林詩句)大規模投放到我們視野中:“人應當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那么詩人還要與人爭論何為詩意嗎?南野覺得可以一試,他在《致謝黃昏》一詩中寫道:“我想,領會與承受黑暗就是詩意地生活。”
請別誤解,詩人不是買不起房才去“領會與承受黑暗”。南野有房有車,在這本《語言繁華》詩集里,他的車出現次數很多。但既然“詩歌活動”與“商業性圖解”已更乏味,有房有車的人為何要寫一本詩集諷刺世界?難道其他詩人諷刺得還不夠嗎?
遠遠不夠。更多的時候諷刺的方向錯了。某媒體精英詩人常在詩中宣泄他對城市現代文明的憤怒,他揭露商業文明的虛偽,怒斥高架橋的陰暗,痛苦而悔恨地思念夕陽下的麥地。我不知道進城務工的農民是否會同意他的觀點。另一位更為顯赫的首都詩人,他灼熱的批判激情從未停歇,這些年他怒吼的對象突然變成了資本,我不知道他對資本及資本背后的看不見的人又了解多少……
那么好吧,南野又有何不同呢?至少,他的誠懇是強勁有力的。他描述突如其來的老年:“我在老去/起碼比昨天老。像河流比前一時刻渾濁/怒氣更大。”他對老年進行估值:“像風一樣地談論,像風一樣在樹頂上/在屋頂上,在空中自語,這就是蒼老呵。”
“我準備諷刺這個世界一次/ 我選擇了一些詞語/未及開口,這些語詞的鋒芒使我驚訝。”值得警惕的是,南野并沒有完成諷刺這一行為,“未完成”本身是他寫作的內容。諷刺在那一刻,也許在他看來是無價值的。
什么是有價值的呢?在《滿屋木柴》一詩中,他感嘆:“被砍伐的普遍的理想主義喬木/春日開花,冬季落葉。/未來時枯死,或轉化為火焰。”不過,他的同情像一枚信封一樣是有邊界的,“為欲望而耗費智能”只配得到無情裁決:“取代欲望的總是死亡的意象,每一代的存在都是如此,或者說時間提供的就是這些。”
南野對自己也沒有溫情,連書名都來自于一首帶有不祥篇名的詩《服用了藥物》:“譫妄之刻,語言繁華。”絕不自戀,這在逐年老去的男詩人中似乎是不多見的。
在早年的詩里,他像一個弈棋者那樣精密布局,書寫的內容讓我們將他看作是某個虛構之地的狩獵者、筑巢者。現在,他是杭州一個無目的的駕駛者,詩歌質地讓人想起大屏幕高清電影中的昏蒙畫面。一首詩有時僅描述一個狀態:“我們在房間里看電視,剝開橘子/感覺到天際陰沉下來,暴雨的季節隆重來臨/有一部分人陷入緊張狀態。”(《緊張狀態》)沒有傳統的敘事結構,更沒有故事。
然而,歌者與聽眾的古老契約依然有效。讀者閱讀這部詩集獲得的是另外的愉悅。南野飽含哲理的獨白是有誘惑力的。曾經他總能寫出值得讀者劃線的句子:“活著?活著無非是記憶的增值。”現在,他在忘我獨白的同時會引入評論者的冷酷提醒:“什么都看不見啊,看到的就是全部。”或者,階段性思考被隱身歌隊嘲諷:“忽略本質,然而未曾有本質。”
他的沉思是有魅力的。《秋日來臨》中他珍視這種能力:“而如果我不能思考,如樹木隨風呼嘯/不能在大風中緘默。我在浪費空氣嗎?”《病中俳句》中他在病房窗前站立,“煙雨迷蒙的冬日早晨/第一千輛轎車駛入醫院的停車場沉思”。
曾經總是有那么多新事物,而現在什么都不新了。他反思自己:“就這個世界眼下的存在來說/不知大腦為何保存了我未曾閱歷的景象/掩去已無法令人吃驚的世事。”(《眼前物事》)
他于是細心搜集那些屬于這個時代的轉瞬即逝的驚奇片刻:“我在玻璃墻內領受此驚雷。”(《九行詩》)這是時代的全新場景。昔日的驚雷自然是擊打在曠野之上的。但這種被動“領受”是他不滿的。他質問“領受者”(沒準是他自己):“你是誰,身著黑衣悠閑地靠在沙發上閱讀?”
另一些則是幻象,當然是時代的新經驗所激發出來的“靠近云頂處,烏鴉疾馳與碩大的銀色客機對語”,這種對話能有什么結果?“一個病入膏肓的殺手閱讀晚報”,這種閱讀又有什么結果?密布攝像頭的城市,一部關于殺手的合情合理的小說是寫不出來的。
“不講點笑話如何度過此冬/世界的華美機器就在話語的浸潤中轉動”。笑話好笑與否倒也無所謂,編織這些精美的幻象,總歸不過是“他與一個詞的糾葛未能了結”。
也許《語言繁華》不是一本告訴我們關于這個時代總體看法的書,但這是一本防止詩歌被濫用、詩歌聲望貶值的書。
如果我們僅有孤零零的一種“拔高式”閱讀方式,可能就無法完成這本詩集的閱讀。也許為此書我們還得發明出好幾種新的閱讀方式。提問其實就是一種:公開言說私人痛苦在詩中為何成了體面方式?比如眾多幻象碎片最后為何不匯聚為一個高音或號角,而是一個陳述,一個畫面,一句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