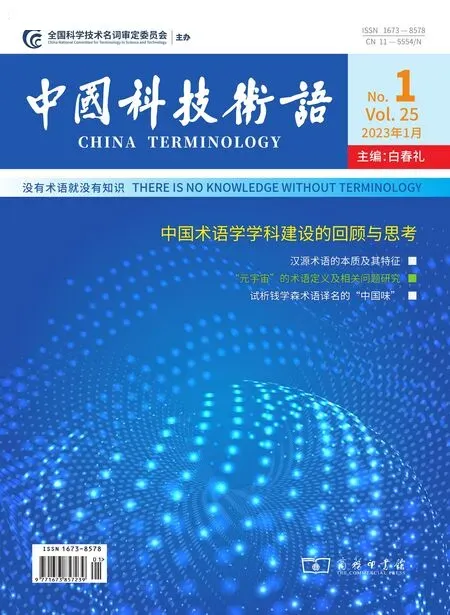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命名發展探究
邢露露 鄔菊艷
(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上海 200093)
新冠自暴發以來,對人類生活產生極大影響,與該疾病相關的語言和文化現象也日益引起學界關注,如楊全紅、胡萍萍探討了“火神山”與“雷神山”英譯、COVID-19、herd immunity(群體免疫)和sovereign immunity(主權豁免)漢譯問題[1];周紅霞、梁步敏考察了Wuhan Virus、China Virus等污名化問題[2];殷健則提出“新冠肺炎”相關術語的命名在西方出現了消極傳播與構建,有損中國文化安全[3],已有研究加深了我們對新冠術語的理解,是本研究的起點。但是,本文認為,新冠病毒和疾病名稱不僅是靜態的術語,更是動態發展的命名過程,這個過程與人類對該病毒和疾病的認知過程協同發展,而且這種動態命名機制對很多流行性疾病具有普遍性價值,非常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4]。
本文將梳理漢語名稱“新冠肺炎”與英語名稱COVID-19在不同時段的發展歷程,探討該新術語的起源、發展與確定的過程。新冠病毒起源時期,人們采用“范疇化”策略命名病毒,將其初步歸類,便于研究治療;新冠病毒發展時期,感染病例不斷增加,人們不自覺采用“信息回避”策略再次命名病毒;新冠病毒成熟確定時期,人類對該病毒基因序號、疾病特征、感染病毒后患者的臨床反應以及治療措施均已有足夠認知,權衡多種因素命名,采用“綜合”策略正式命名。
1 范疇化
范疇(category),即類別。人們基于互動體驗,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普遍本質在思維上的概括反映,以主客觀互動為基礎對事物進行歸類,由此產生類別。范疇化(categorization),即分類的認知心理過程,是人類從千差萬別的事物中看到相似性,并據此將可分辨的事物處理為相同的類別,從而形成概念的過程[5]78。范疇化是人類認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范疇化是范疇形成的基礎,而范疇則是范疇化的結果。范疇和范疇化滲透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水果”是一個范疇,蘋果、香蕉、橘子屬于這個范疇中的典型成員,西紅柿則屬于“水果”范疇中的邊緣成員。當圣女果新產出時,人們將其認知為小的西紅柿,小西紅柿屬于西紅柿;同時,圣女果一般都生吃,與“水果”范疇中的典型成員蘋果、香蕉和橘子有共同特征,由此,圣女果被認知為“水果”范疇,這是圣女果被范疇化的過程。新冠肺炎疾病的漢語和英語名稱的命名也經歷了范疇化的認知過程。
國內,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將這種新近出現的傳染性疾病對外公布時稱之為“不明原因肺炎”,2020年1月3日則認為這是一種“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在后續的基因組定序研究中發現,引起該疾病的病毒在電子顯微鏡下呈球形、上有皇冠凸起,是一種“冠狀病毒”,因此2月7日,國家衛健委將病毒漢語名稱確定為“新型冠狀病毒”,簡稱“新冠病毒”,而由該病毒引起的肺炎則稱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國際,2020年1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將疾病暫時命名為2019-nCoV,n表示novel(新型),CoV表示Coronavirus(冠狀病毒);1月30日,世衛組織又將疾病名稱修改為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2019新型冠狀病毒急性呼吸道疾病);2月11日,世衛組織最后將疾病名稱正式確定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2019冠狀病毒病),簡稱COVID-19。
以上新冠疾病命名過程表明,隨著人類對該疾病認知的不斷深化,該疾病命名呈現動態發展趨勢。具體而言,新冠起源初期,醫護人員發現該疾病伴隨咳嗽、感冒、發燒等肺炎常見癥狀,且肺部最先發炎,稱其為“不明原因肺炎”或“新型肺炎”,表明該疾病隸屬“肺炎”范疇。而“肺炎”根據感染的病原體不同,可分為細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原體肺炎、真菌性肺炎、放射性肺炎等,細分后的范疇導向更加明確[6]。進一步研究發現,這類肺炎主要由某種病毒引起,由此將其命名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表明該疾病隸屬“病毒性肺炎”范疇。盡管該階段并不清楚由哪種病毒引起,但這種范疇化的命名機制可為研究和醫護人員抗擊疫情提供明確的導向:進一步尋找引起該疾病的特定病毒。“病毒”范疇中,根據病毒形狀不同,可分為球狀病毒、磚狀病毒、鏈狀病毒、冠狀病毒等。因此,“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名稱顯示該疾病隸屬“冠狀病毒肺炎”范疇,此時,人類對這種不明原因病毒的認知更為深入了。后續又對這種新型冠狀病毒一代一代的變異株進行研究,發現該病毒的多種變異株基本在“冠狀病毒”范疇內發展,世衛組織則用希臘字母將其命名為“α株”(阿爾法株)、“β株”(貝塔株)、“Δ株”(德爾塔株)、“ο株”(奧密克戎株)等,這些病毒都屬于“新型冠狀病毒”范疇。因此又有了“阿爾法病毒性肺炎”“貝塔病毒性肺炎”“德爾塔病毒性肺炎”和“奧密克戎病毒性肺炎”等疾病名稱。
從“不明原因肺炎”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再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及“奧密克戎病毒性肺炎”等名稱發展的過程,與人類認知病毒和疾病的認知發展過程相協同,而這兩者的發展過程本質始終遵循范疇化的認知思維模式。又如2022年全球開始興起不明原因兒童肝炎,據世衛組織報告,5月17日,全球已出現超過400例不明原因兒童肝炎病例,研究人員正在對致病原進行調查。與新冠初期命名十分類似,因不確定此次疫情致病原,運用范疇化策略初步歸類為“不明肝炎”,確定“肝炎”范疇后,我們可以預見科研人員將沿著這一范疇繼續細分,不斷深化認知。總而言之,范疇化的認知思維方式對疾病名稱的命名和疾病本身的探索道路具有普遍性意義。
2 信息回避
回避,是人類應對充滿不確定性世界的一種普遍方式。無論出于主動或被動原因,人們通常會存在拒絕、避免或延遲獲取可利用信息的規避行為,因此,回避,也常被稱為“信息回避”或“信息規避”。信息回避是一種不尋求信息的特殊行為[7],信息回避驅動因素大致可分為個人因素、信息因素和環境因素。個人因素,包括認知因素和情緒因素,認知因素是指人們為了減少認知努力,更傾向于接受與自己認知結果相似的信息,以避免認知失調;情緒因素是指人們面對過載信息,會產生不滿意感與倦怠情緒,面對與自己認知相矛盾的信息易產生焦慮不安、失望恐懼等負面情緒。信息因素,體現在信息數量、信息質量與信息表現形式上,信息數量過載,信息質量良莠不齊,信息與用戶之間的可信度、相關性與互動性難以確認,以及各種不同信息表現形式,都會影響用戶信息回避。環境因素,包括社交媒體特征因素與社會性因素,社交媒體特征因素,根據阿爾伯特·班杜拉提出的社會認知理論,個人、行為與環境三者之間存在交互決定關系[7],環境對個體的行為產生重要影響,而作為無數用戶線上活動的主要場所的社交媒體,勢必也會對個體用戶行為產生影響;社會性因素,則包括政治影響、文化價值觀等其他因素。
新冠疾病命名過程中也常常體現信息回避動因,例如,信息回避驅動因素對污名化名稱的出現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個人因素中,認知沖突與負面情緒是污名化原因之一。人類面對新冠這樣一種極具傳染性且不斷變異的病毒,原有的認知水平難以應對感染人數激增的局面,導致認知失調。焦慮不安、恐懼害怕等負面情緒會讓人們傾向于選擇與本國無關的名稱,造成病毒與我們無關的錯覺假象,這是面對不確定事物的自我保護機制,從而達到減少負面情緒,維持樂觀的目的。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曾在社交媒體稱新冠病毒為Wuhan Virus、China Virus或Kungfu Virus,以減少美國人民的消極情緒。信息因素中,過量疫情信息推送是疫情時期網絡常態,疫情信息質量參差不齊,社交媒體上充斥大量未經證實就廣為傳播的錯誤信息與謠言,多元化的信息形式逼迫網民花費大量時間閱讀同一主題,影響甄別信息能力與信息認知能力,從而進一步促進疫情虛假信息傳播。環境因素中,社交媒體受到國家、政治、種族與文化價值觀等社會性因素影響,選擇性地報道相關疫情事件,難免出現以污名化名稱報道疫情信息。
回顧人類發展史,很多傳染性疾病都背負污名,有些涉及國家與地區名稱,如“西班牙流感”“香港腳”“中東呼吸綜合征”等;有些涉及動物名稱,如“豬流感”“鼠疫”等,使人們對這些動物產生錯誤認知,如“豬流感”暴發期間,國際豬肉價格持續走低。這些名稱一般都在傳染性疾病發生初期,人類出于恐懼等負面情緒,對其進行了信息回避的命名機制處理,但是污名化的疾病名稱一旦約定俗成便很難更改。
面對傳染性疾病名稱問題,世衛組織已多次呼吁:拒絕使用污名化名稱。2015年世衛組織與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世界衛生組織命名新人類傳染病的最佳做法》(WorldHealthOrganizationBestPracticefortheNamingofNewHumanInfectiousDisease),提出對新發現傳染性疾病命名的指導原則,即疾病名稱不應涉及任何國家與地區、職業與動物,應該使用中性、科學、方便發音、與疾病相關的術語,而且盡可能避免使用如不明、致命、流行等引起過度恐慌的術語[8]。本文也認為,信息時代面對傳染性疾病,社交媒體不僅需要持續報道權威官方消息,切斷謠言流傳路徑,也應該增強推送消息的針對性,正確把握輿論方向,而社交媒體下的個體用戶,不僅要增強信息篩選能力,提升自身信息素養,也應該保持樂觀心態,積極調解控制情緒。
3 綜合
相較于信息回避的消極處理,應用綜合的方法命名疾病是一種更加積極正面的策略。本文所謂綜合,是指綜合考慮科學性、經濟性、能產性與國際性等多種因素,減少疾病名稱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使疾病名稱逐步趨于規范。
3.1 科學性
我國法定傳染病命名方式有病原學命名、流行病學命名、借詞命名、編序命名等,其中,病原學命名與流行病學命名可歸為醫學范疇,后兩種方式可歸于非醫學范疇,一般疾病名稱是多種命名方式的組合與交叉。以病原學方式命名的疾病名稱應體現病毒病原、細菌病原或寄生蟲病原等多種病原體信息;以流行病學方式命名的疾病名稱應體現傳染源、易感人群、流行特征、病因等流行病學信息;以臨床學命名的疾病名稱應包含癥狀體征與病理部位等相關臨床信息;而以非醫學范疇方式命名的疾病名稱應體現音譯命名、天干地支、字母數字等與序號相關信息[9]。
“新冠肺炎”這一疾病名稱符合我國法定傳染病命名方式,“新冠”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簡稱,新型冠狀病毒就是導致此次新冠肺炎的關鍵病原體,體現病原學命名方式;“肺”是指肺部是該疾病最先受到病毒侵害的身體器官,體現臨床學命名方式中的病理部位特征;“炎”是指發炎等癥狀,體現了臨床命名方式中的癥狀體征特征。雖只有短短四字,卻反映出疾病病原學特征與臨床學信息,是病原學與流行病學兩種命名方式的交叉組合,符合科學認知,包含豐富的疾病細節信息,因而具有科學性。
新冠肺炎的英語名稱COVID-19,全稱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從英語單詞Corona(冠狀的)中析取,-VI-從單詞virus(病毒)中析取,-D指disease(疾病),三個析取成分拼接組合成COVID,表示“冠狀病毒疾病”,2019指該疾病首次出現的年份。可見,英文名稱中既包含關鍵病原體,也體現病毒名稱,還包括發生的具體時間,英文疾病名稱也體現了疾病命名的科學性。
從疾病命名的科學性視角看2003年的“非典”疾病名稱,似乎缺乏一定的科學性。“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簡稱,該名稱既未能體現出致病原名稱和具體病癥,也沒有包含疫情發生的關鍵年份等信息,該名稱曾一度被詬病。而從上文對“新冠肺炎”的命名方式看,10多年后的中國在疾病命名方面顯然更加成熟、更具有科學性。
3.2 經濟性
Martinet提出,語言運轉的基本原則就是語言經濟原則(the Principle of Language Economy),即人們在保證使用語言完成特定交際功能情況下,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對言語活動力量中的消耗做出符合經濟要求的安排[10]1。語言經濟原則,也稱語言經濟性,是規約語言使用的普遍原則之一,語言經濟的前提是保證語義的完整性,不同語言常常體現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語言經濟特征。
國家衛健委最初提議的暫定名稱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將這一名稱與后面形成的正式名稱“新冠肺炎”對比可知,“新型冠狀病毒”縮略為“新冠”,簡潔明了,同時也保留了關鍵醫學專業信息,再加上“肺炎”表明該病毒侵害的器官和癥狀,組成了一個語言完整但又經濟簡約的四字偏正短語,音節平仄相對,朗朗上口。漢語強調偶字易適、奇字難安,因而偶數或四字格類的術語更符合漢語民族講究對稱的民族心理[11]。而四字格短語能降低人們認知難度,更易記憶傳播,如“新冠病毒”“新冠肺炎”“新冠疫情”。
世界衛生組織最初的暫定名稱為SARS-CoV-2、 2019-nCoV和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這些名稱與正式名稱COVID-19相比,顯然,COVID-19不僅準確包含了關鍵信息,而且比非正式名稱更加經濟簡潔、易于傳播。同時,英語疾病名稱中還常利用縮略拼接形式體現語言經濟性。2021年韋氏、牛津兩本詞典所選的年度詞匯分別是vaccine(疫苗)、vax(疫苗),后者是前者的縮略形式,vax通過提取vaccine的前兩個字母va-,剩余部分用發音類似的字母x表示,僅3個字母就表達原本7個字母單詞的含義,而且vax具有很強的構詞能力,隨著疫情的發展,衍生出一系列vax詞組, 如vax-site(疫苗接種點)、fully-vaxxed(完全接種疫苗)、anti-vax(反對接種疫苗)、vaxer(贊同接種疫苗的人)、anti-vaxer(反對接種疫苗的人)等。這種縮寫方式體現了英語語言特有的經濟性,在保證簡約的同時亦能保證語義的完整度,如傳染性疾病AIDS(艾滋病)、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等都是通過首字母大寫組成一個新單詞,形式簡約且意義完整,體現語言的經濟原則。
3.3 能產性
從能產性而言,雖然沒有人希望傳染病層出不窮,但現實有時并非盡如人意,為了標識隨時可能出現的傳染病變異體,傳染病命名應該體現能產性[9]。人類應用藥物和疫苗抗擊病毒,與此同時,病毒自身也在不斷變異,產生多種變異株。為了跟蹤檢測病毒變化,世衛組織用希臘字母命名變異毒株,如α、β、δ、ο等,國內則采取音譯希臘字母方式命名這些毒株,如阿爾法株、貝塔株、德爾塔株、奧密克戎株等,體現非醫學范疇中的借詞命名方式。
世衛組織根據病毒公共風險大小,依次將新冠變異毒株分為三類,第一類是VOC(variant of concern關注突變株),是指使流行病學傳播性增加或疫苗、治理方法有效性降低的一種變體;第二類是VOI(variant of interest待觀察突變株),是指經預測或已知會影響病毒特征的遺傳變化,并確定在多個國家導致重大社區傳播或病例數量不斷增加的一種變體;第三類是VUM(variant under monitoring監控突變株),是指一種具有遺傳變化的SARS-CoV-2變體,人類懷疑該變體會影響病毒特征,有跡象表明可構成未來風險[12]。而世衛官網發布的最新每周病理學更新報告(2022年5月3日)顯示,目前流通的關注突變體包括δ和ο,以前循環的包括α(Alpha)、β(Beta)和γ(Gamma),目前沒有流行的待觀察突變株,以前循環的包括ε(Epsilon) 、ζ(Zeta)、η(Eta)、θ(Theta)、ι(Lota)、κ(Kappa)、λ(Lambda)、μ(Mu)、ν(Nu)和ξ(Xi)。監控突變株因在醫學上不太確定是否對人類構成風險,所以暫未命名[11]。三類變異毒株中,關注突變株對人類生命健康威脅最大,傳播風險極高,所以該類毒株受到人們廣泛關注。現在奧密克戎已成為全球主導毒株,其下又包含不同譜系,如BA.2、BA.4、BA.5,各個譜系下還有亞變體,如變異株BA.4.6也引起了衛生官員的密切關注[13]。
截至目前,新冠變異毒株已經命名到希臘字母表中的第15位奧密克戎,可預見新冠病毒毒株若再次變異將繼續沿著希臘字母表順序命名。這種希臘字母加阿拉伯數字的組合命名方式體現了疾病名稱的能產性與層次性,即使面對不斷變異的毒株,人類仍然會科學監測,智能命名。
3.4 國際性
科學無國界,疫情當前,各國更需加強合作共同抗疫,疾病名稱也需要體現國際性。世衛組織宣布疾病官方名稱為COVID-19,這一名稱未涉及任何國家與地區,中性、科學,自此外媒報道疫情也都是采用COVID-19與pandemic等科學客觀的詞語,減少了針對地域歧視的污名化名稱,疾病的污名化名稱既不科學,也容易引起國際糾紛,對國際抗疫合作產生負面影響。
世衛組織根據希臘字母表順序命名變異毒株也體現國際性。公元前11世紀,腓尼基人創造出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腓尼基字母。腓尼基人通過航海將腓尼基字母傳播至希臘地區,希臘人對腓尼基字母進行修改與借鑒,在此基礎之上創造了希臘字母,并增添元音字母,使之成為世界上最早包含元音的字母表[14]。希臘符號廣泛應用于數學、天文、物理、醫學等諸多學科,希臘字母也對希臘文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應用對世界文明都產生深遠影響的希臘字母則表明了世衛組織在命名變異毒株的客觀性與國際性。
理論上,疾病名稱命名不僅需要考慮科學性、經濟性、能產性與國際性原則,還有如單義性、協調性、穩定性、得體性等因素也應適當考察。“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生動體現了術語名稱命名過程之艱辛,疾病名稱的命名也不例外。任何疾病名稱的命名從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總是處于動態發展過程中,隨著人類對病毒和疾病認知的不斷加深,疾病名稱的命名方式也不斷完善。
4 結論
本文結合多種病毒傳染病名稱,探討了英語、漢語新冠疾病術語的命名發展歷程,該歷程反映了人類認識新疾病普遍的認知心理過程,是人類思維共同性的體現。疫情發展初期,人類遵循范疇化的認知機制將疾病初步歸類于特定的基本范疇,隨著對疾病認知的加深,進一步范疇化至特定的下義范疇。疫情暴發期,感染人數激增,個人因素、信息因素與社會因素都使得人們訴諸信息回避,疫情下的信息回避不免出現疾病污名化名稱,國際組織此時采取行動以減少信息回避現象。最后疫情發展至成熟階段,疾病名稱的命名最終回歸理性,通常會兼顧科學性、經濟性、能產性和國際性等多重原則綜合命名。基于人類認知思維的普遍性和共通性,該命名機制具有相對廣泛性和普適作用,對未來類似病毒或疫情的命名規則具有指導意義。如目前在全世界發現的猴痘疫情(the Monkeypox epidemic),猴痘病毒1958年在猴子體內初次發現,由此命名為“猴痘病毒”,這是初步范疇化認知的體現。隨著人類也開始感染此病毒,而且感染人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世衛組織正發動全球專家為猴痘病毒、分化枝及所致疾病重新命名,后續名稱將緊隨研究的最新發現成果。此外,“猴痘”的疾病名稱涉及“猴子”這一動物,使得人們對猴子有偏見,造成污名化問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世衛組織會綜合考慮多種因素,體現該疾病命名的綜合性和科學性。可見,任何疾病名稱的命名都可能一波三折,難以盡善盡美,其中既有人類認知促進名稱表征不斷發展的過程,也受制于名稱在傳播和使用過程中各種主體的博弈與選擇[9]。傳染性疾病對人類生活產生極大影響,病毒自身不斷變異,研究病毒及變異體名稱命名過程對今后傳染性疾病具有一定指導意義與可預見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人類共同抗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