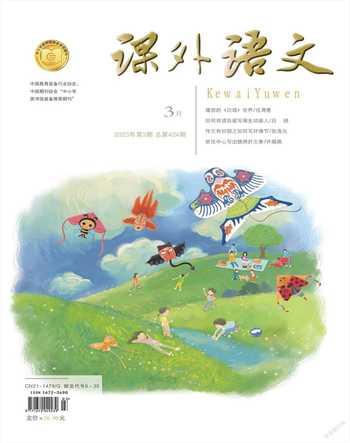從《天凈沙·秋思》看詩(shī)歌意象組合的藝術(shù)效果
趙正雄
作為元代最杰出的戲劇家之一的馬致遠(yuǎn),其《天凈沙·秋思》以不著一字寫“愁”,卻寫盡漂泊游子秋天背井離鄉(xiāng)之“愁”、孤獨(dú)無(wú)依之“愁”、漂泊羈旅之“愁”、窮困潦倒之“愁”、抱負(fù)難施之“愁”、民族危亡之“愁”而聞名。將秋天悲涼的景象與作者的滿懷愁情合而為一,將情感抒發(fā)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這首28字的小令,因其“深得唐人絕句妙境”的藝術(shù)魅力而膾炙人口,馬致遠(yuǎn)也因這首《天凈沙·秋思》被后人譽(yù)為“秋思之祖”。反復(fù)品讀作品,《天凈沙·秋思》中意象組合所帶來(lái)的富有張力的詩(shī)歌意境,讓我們感受到其獨(dú)有的藝術(shù)魅力和表達(dá)效果。
為表達(dá)特定的審美理想或思想感情,詩(shī)人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往往會(huì)借助一些客觀的事物或形象,這些特定的客觀事物或形象,在具體的環(huán)境下融入詩(shī)人的情感和思想,最后形成主觀與客觀相統(tǒng)一的符號(hào)化表象,這就是詩(shī)歌的意象。
意象是詩(shī)人所見所聞的客觀生活場(chǎng)景與詩(shī)人所思所想的主觀思想感情在當(dāng)下的碰撞和交融。詩(shī)人立足獨(dú)有的視角和獨(dú)特的審美立場(chǎng),將具體的事物寄托以濃厚的情感,生成帶有溫度的詩(shī)歌意象,創(chuàng)造性地搭建了一個(gè)用文字塑造出來(lái)的藝術(shù)景象和詩(shī)歌境界。
詩(shī)歌意象是詩(shī)歌的基本構(gòu)成要素,是承載詩(shī)歌思想與情感的靈魂和本質(zhì)特征,它對(duì)彰顯詩(shī)歌的主題思想和表達(dá)作者的情緒態(tài)度往往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天凈沙·秋思》這首小令中的若干意象,就通過獨(dú)立表意和組合表意等多種方式,為我們呈現(xiàn)出時(shí)間、空間的強(qiáng)大張力,在有限的文字背后,感受到豐富的畫面和作者無(wú)限的想象,以及帶給讀者的強(qiáng)大震撼與共鳴。
一、單獨(dú)意象拼接出的秋景之“愁”
“枯藤”是小令中出現(xiàn)的第一個(gè)意象。深褐色的干枯樹藤,被寒冷與秋風(fēng)榨干了生命的最后一絲水分,干癟、脆弱,沒有一絲生機(jī),仿佛用手輕輕一捏就會(huì)徹底斷裂、破碎。在杜甫《登高》一詩(shī)中也有“無(wú)邊落木蕭蕭下”的詩(shī)句,其中“落木”就是指秋天凋零的落葉,用“木”代替“葉”,表現(xiàn)出樹木枯葉凋零的蕭條與悲涼。可見,“枯藤”一詞剛開場(chǎng)就已經(jīng)奠定了這首小令悲戚、蒼涼的基調(diào)。
“老樹”緊隨“枯藤”之后,更是把整個(gè)畫面的亮度再次拉低不少。原本干枯的樹藤就已經(jīng)讓畫面毫無(wú)生機(jī)了,“老樹”二字讓畫面又多了一重壓抑與束縛。凋盡了葉子的老樹,本已足夠蕭索,現(xiàn)在又被枯藤纏繞,動(dòng)彈不得。往日盛夏時(shí)的繁茂之態(tài)已經(jīng)全無(wú)痕跡,根根枯藤仿佛層層枷鎖,讓老樹喪失了最后一絲掙扎的勇氣。
“昏鴉”的出現(xiàn)雖然讓眼前的畫面有了一絲動(dòng)態(tài),卻在色彩上又把畫面的亮度進(jìn)一步拉低。黑色的烏鴉在黃昏時(shí)歸巢,刺耳的鳴叫聲劃破天空的寧?kù)o,讓獨(dú)行的路人心中陡然升起一陣酸楚和疼痛。
如果說(shuō)開篇已經(jīng)確定了作者在這首詩(shī)中想表達(dá)的愁思之情,那么,后面出現(xiàn)的這三個(gè)看似人畜無(wú)害的詩(shī)歌意象,才是戳痛詩(shī)人內(nèi)心傷處的真正暴擊點(diǎn)。
“小橋”“流水”“人家”,靜謐溫情的人間煙火,點(diǎn)亮了詩(shī)人心中對(duì)家的期盼。忍不住駐足流連眼前的平和自然,暫時(shí)想用這份寧?kù)o滌蕩自己飽經(jīng)風(fēng)霜、千瘡百孔的心。然而,眼前的潺潺流水,如時(shí)光不逆般自向東流,匯入廣闊的江海;裊裊炊煙,平常百姓家,也許正在茶余飯后聊敘家常。然而,就是這樣的簡(jiǎn)單生活,對(duì)詩(shī)人而言卻是咫尺天涯的奢望。
抬頭仰望,樹上的“昏鴉”也已歸巢,連一只自然中的鳥兒都有所依所棲,自己卻客在他鄉(xiāng)。前行不知其所往,回首又難覓歸途。悲愴之情郁結(jié)在胸,仿佛自己也被那命運(yùn)的“枯藤”緊鎖,再也無(wú)法按捺心中的悲戚與委屈,兩汪濁淚伴著長(zhǎng)空中烏鴉的鳴叫聲,在眼眶中沸騰、翻滾。
“古道”的意象出現(xiàn)時(shí),詩(shī)人已經(jīng)繼續(xù)踏上了漂泊的旅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lái)者”的古道上,留下多少求索的腳步?然而“路曼曼其修遠(yuǎn)兮”,此時(shí)的羈旅中,只有詩(shī)人獨(dú)自“上下求索”。前路何其渺茫,目的地又在何方?對(duì)未知的迷茫與恐懼,讓詩(shī)人頓覺不寒而栗,下意識(shí)地緊了緊衣襟。
也許是蕭瑟的“西風(fēng)”讓詩(shī)人有了偷偷抹去眼淚的機(jī)會(huì),可是,泛紅的眼睛卻無(wú)法隱藏他的傷痛與愁苦。“西風(fēng)緊,北雁南飛”,是時(shí)候繼續(xù)追尋夢(mèng)想了。
騎上嶙峋的“瘦馬”,此時(shí)的畫面多了一重悲壯。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窘迫不僅讓詩(shī)人沒有了追夢(mèng)者的意氣風(fēng)發(fā),就連陪伴他一起的最忠實(shí)的老馬也因?yàn)槁猛镜穆L(zhǎng)和奔波勞碌,沒有了曾經(jīng)的健碩挺拔。連老馬都瘦得皮下見骨,可見此時(shí)的詩(shī)人,更是形容枯槁,身體瘦弱。盡管如此,這一人一馬都執(zhí)拗而倔強(qiáng)地再次踏上征程,為心中那個(gè)不滅的夢(mèng)想,無(wú)悔追逐。
“夕陽(yáng)無(wú)限好,只是近黃昏”,“夕陽(yáng)”的意象仿佛在昭示作者內(nèi)心對(duì)已知未來(lái)的無(wú)奈和不甘,然而卻無(wú)法憑靠一己之力對(duì)此有所改變。“夕陽(yáng)西下”,是詩(shī)人對(duì)那個(gè)黑暗時(shí)代的詛咒,期待更好的未來(lái),同時(shí)對(duì)自己已經(jīng)逝去的青春又有著無(wú)盡的嗟嘆和悲涼。
“斷腸人”是小令中的最后一個(gè)意象,穿過歷史的塵煙,依稀看到詩(shī)人騎在馬背上孤獨(dú)的背影在微微顫抖。落日的余暉中,他的身影瘦削而單薄,顫抖的雙肩終于暴露了他的脆弱,在余暉散盡的時(shí)刻宣泄出來(lái)。“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凄清的曠野上,我仿佛聽到詩(shī)人肝腸寸斷的嗚咽,偶爾引得幾聲烏鴉的鳴叫,又或是那忽遠(yuǎn)忽近的抽泣聲,已經(jīng)完全被淙淙的小橋流水聲淹沒。
詩(shī)人的背影越來(lái)越遠(yuǎn),直至天涯盡頭。天涯是何處?游子離家,身所在之處,處處皆天涯。
二、組合意象對(duì)比出的秋時(shí)之“愁”
單獨(dú)來(lái)看,詩(shī)中的每一個(gè)意象都是通過搭建具體的意境,把詩(shī)人帶入到各自不同的愁情中,然而意象組合之后,時(shí)間、空間的立體呈現(xiàn),動(dòng)態(tài)、靜態(tài)的組合畫面,直擊心靈的感受體驗(yàn),讓這首詩(shī)歌的張力更加巨大,情感更加震撼。
“枯藤老樹昏鴉”和“小橋流水人家”這兩組畫面從色彩明暗上是有明顯對(duì)比的。“枯藤老樹昏鴉”,在一片死寂中,突然聽到烏鴉艱澀的“呱呱”鳴叫,突兀、可怖。纏繞著枯藤的老樹,落盡樹葉,根根枝丫向天空之上延伸,樹下仰望,那便是向天伸出的五指、手掌和巨大的臂膊。烏鴉的叫喊正是那個(gè)時(shí)代被壓抑的民族的憤恨與吶喊,尖銳、刺耳。“小橋流水人家”則是一幅暖色調(diào)。青石板密密搭起的小橋,結(jié)滿了綠色的苔蘚,潺潺的河水發(fā)出叮咚悅耳的聲音,沿著曲曲彎彎的小路,一戶人家窗上映出了搖曳的燭光,升騰起的炊煙甚至讓人感受到了空氣的溫度,有了吸引人靠近的魔力。
然而,這兩組畫面對(duì)比之后,就會(huì)出現(xiàn)強(qiáng)大的時(shí)空拉伸感。一面是冰冷凄寒,一面是溫暖和諧。然而,這樣的溫暖也好、凄寒也罷,竟然無(wú)一是他的歸處。就連一只鳥都有巢可歸,天大地大,此時(shí)卻無(wú)詩(shī)人立足存身之處,竟如游魂野鬼般,不知?dú)w處。
此時(shí)的詩(shī)人,內(nèi)心空洞無(wú)力而匱乏。他的心灰意冷不僅是因?yàn)檠矍暗那榫埃且驗(yàn)樗肷脑庥觥U紊希慕y(tǒng)治讓腹有詩(shī)書的漢人在朝堂之上根本沒有用武之處,自己的遠(yuǎn)大抱負(fù)難以實(shí)現(xiàn);生活中,堂堂七尺男兒,卻對(duì)自己潦倒的生活無(wú)能為力,窘迫的物質(zhì)生活更讓他的尊嚴(yán)沒有安放之地。
“古道西風(fēng)瘦馬”和“斷腸人”的畫面,對(duì)比出詩(shī)人內(nèi)心世界的徹底崩塌。前行的路上,詩(shī)人不過是一個(gè)迷途的孩子,他有家無(wú)法回歸,前路又不知去處,凜冽西風(fēng)讓他的冰冷感受直接從內(nèi)心外化到他的體感溫度。身上的單衣,已經(jīng)抗不住西風(fēng)的呼嘯而至,透骨的凄清讓他更是升起思?xì)w之心。萬(wàn)千人間煙火明明有溫暖之處,卻沒有一處屬于自己,羈旅之愁、漂泊之苦、抱負(fù)難展之痛、民族欺壓之悲一浪高過一浪,鋪天蓋地向這個(gè)身體單薄羸弱的男人洶涌澎湃而來(lái)。
于是,“夕陽(yáng)西下”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淚水再也無(wú)法抑制,他在狂野中發(fā)出的呼天搶地的悲鳴沒有人知曉,畢竟在他身側(cè)相伴的也只有那匹瘦馬。于是,“斷腸人”成了這首詩(shī)最后的一個(gè)意象。肝腸寸斷,這是何等的傷痛,才能讓詩(shī)人有這樣徹骨之痛的體感?所以,于家,寫盡了一個(gè)游子背井離鄉(xiāng)之“愁”,孤獨(dú)無(wú)依之“愁”;于身,滿目皆是詩(shī)人漂泊羈旅之“愁”,窮困潦倒之“愁”;于國(guó),更是一腔抱負(fù)難施之“愁”,異族統(tǒng)治壓迫下的民族危亡之“愁”。
這所有的“愁”情,都被這些看似獨(dú)立,實(shí)則密切相依的詩(shī)歌意象表現(xiàn)出來(lái)。不得不說(shuō),馬致遠(yuǎn)的《天凈沙·秋思》真不愧為無(wú)法逾越的“秋思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