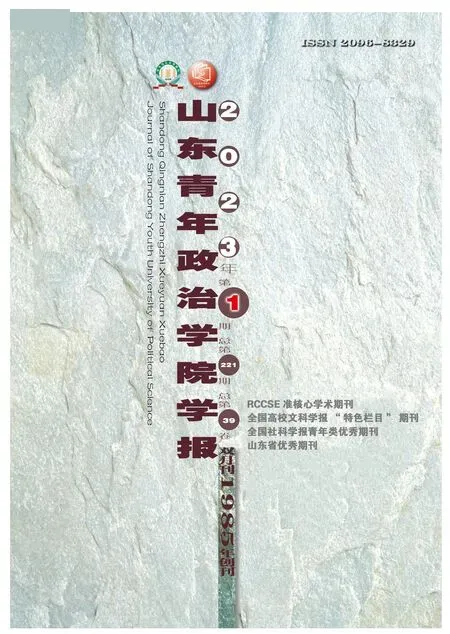12-14周歲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懲治的理論省視與優化適用
——再論《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條
馬 逍
(鄭州大學 法學院,鄭州 450046)
面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嚴峻態勢,我國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在學界關于“不變論”“升高論”“降低論”“彈性論”的爭議與呼聲中,正式通過《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條將刑事責任年齡進行了有限下調,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由原來的14周歲調整至12周歲,從而為12-14周歲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的刑事懲治提供了法律依據。根據該款的具體規定,如若12-14周歲的低齡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應當負刑事責任。然而,由于目前尚未形成系統的司法適用指導標準,對于該條款的理解與適用在學界仍存在爭議,引起廣泛探討。因而,筆者將以此修訂為視角,針對下調刑事責任年齡后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爭議與困境展開系統探討,以期能夠為低齡未成年人的犯罪防治優化提供一定思路。
一、下調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立論根基
(一)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嚴峻態勢的社會治理需要
近年來,我國呈現出一定的犯罪低齡化趨勢,以未成年人為作案主體的校園霸凌、違法犯罪等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例如,2015年10月18日,湖南省邵東縣三名13歲的未成年人為實施搶劫而將一名52周歲的女教師殺害,后被移送工讀學校[1];2016年6月13日,四川省金川縣一名13歲少年為搶一部手機,利用汽油將過路的23歲女教師燒成重傷,并在之后幾天內又接連犯下盜竊和搶奪等行為,最終因未成年而被釋放回家尤其監護人看守教育[2];2019年10月20日,大連一名13歲男孩企圖對一名10歲女童實施性侵,后因女童反抗而將其殺害并拋尸至小區灌木叢,因其未滿14周歲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引起輿論極大憤慨[3];2021年2月17日,陜西省漢中市勉縣一名13歲的男孩將鄰居家一名6歲的男童殺害并藏尸[4]。
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最高檢”)于2022年6月1日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1)》(以下簡稱“《未檢白皮書》(2021)”),“未成年人犯罪數量出現反彈”“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等已然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特征中的典型表現。[5]顯然,無論是根據前述典型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呈現出的惡性程度,還是根據最高檢通過《未檢白皮書》(2021)披露出來的未成年人犯罪特點,未成年人作案時的心理成熟度以及手段惡劣度均有所提升。由此可見,隨著社會發展的加速轉型,未成年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得到顯著改善,相應的其身心特點較以往產生了明顯變化,相對更為成熟。因而,在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現象趨勢仍較為凸顯的情況下,需要通過各種措施予以有效遏制。此時,刑事規制自然也成為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選擇。
(二)積極刑法觀于低齡未成年人犯罪規制的貫徹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的刑事立法領域表現較為活躍,自1997年《刑法》生效以來的短短20余年內已經陸續通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涉及諸多罪名、罪狀及其法定刑的調整。由此,學界對于我國刑事立法的基本立場和理念形成諸多爭議。例如,有學者認為,根據國外刑事立法的最新動向以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刑事立法的要求,犯罪化在我國具有必要性。[6]有學者認為,“固守相對簡單化的傳統觀念在當下 中國未必合時宜……中國社會轉型的情勢決定了未來的立法必須具有能動性,增設新罪是很長歷史時期內立法上的核心任務。”[7]也有學者認為,適度犯罪化作為我國當前刑事立法的總體趨勢,從法益保護層面而言具有相應必要,也不違背刑法謙抑性,因而應采納積極主義刑法觀。[8]顯然,前述學者均是對“我國刑事立法應秉持積極主義刑法觀”這一觀點持肯定與支持態度。但與之相反,也有學者認為我國不應過度依賴刑法,積極刑法觀的貫徹會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后果。例如,有學者認為,我國當前已經呈現過度犯罪化的態勢,從而導致“我國現在存在著‘過度刑法化’的社會治理現狀,這是社會治理的病態化現象。”[9]有學者認為,積極刑法觀導向下的我國預防性立法使得刑法成為“一種控制社會的工具,而非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的手段”。[10]但無論學界如何爭論,我國刑事立法中的積極主義刑法觀已然得到規范層面的貫徹與證實。
顯然,《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未成年人犯罪懲治中的刑事責任年齡下調也是積極主義刑法觀的鮮明體現。一方面,下調刑事責任年齡體現了刑事實體法對于社會公眾吁求的積極回應。面對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惡劣態勢,社會輿論不斷呼吁我國刑事責任年齡下調,以此對低齡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予以刑事懲治,從而實現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力打擊。另一方面,下調刑事責任年齡體現了刑事實體法對公眾生命健康權法益保護的強化。社會公眾的生命健康權是其所享有的基本人權。但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前的以往,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嚴重侵犯他人生命健康權的行為卻無法受到刑事追責。由此,不同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權因加害主體不同體現出一定的保護程度不同,這對于公眾而言有些難以接受。因此,通過下調刑事責任年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顯著強化社會公眾的生命健康權法益保護,優化完善我國的刑事法律秩序。
(三)教育刑理念在低齡未成年人犯罪規制的貫穿
“受自然科學方法論與科學工具理性主義的推動,教育刑在時代背景底蘊的支撐下應運而生。”[11]不同于報應刑論強調報應或報復應為刑罰本質的觀點,教育刑理論以教育作為刑罰的本質和刑罰的目的,強調將刑罰的教育功能貫穿于刑罰適用的始終,最終通過刑罰實現犯罪的預防。換言之,教育刑論在本質上其實就是目的刑論,以犯罪預防作為刑罰實踐的核心側重。然而,教育刑論中對刑罰教育功能的重視雖然具有理論和實踐層面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但一味地單方面強調刑罰的教育功能其實同樣偏離了刑罰的應然作用,也不利于安撫受害人及其親屬乃至社會公眾的報應情緒。因而,兼具報應與預防的并合主義刑罰觀是契合治理現代化方向的合理選擇。況且,在這種并合主義刑罰觀中同樣能夠體現出教育刑理念,畢竟蘊含于刑罰觀的教育刑理念并不等同于教育刑論本身。
刑罰適用過程中的教育刑理念強調犯罪人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的考察,以通過教育消減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為目標,從而實現犯罪的預防,這貫穿于《刑法》參與低齡未成年人犯罪規制的始終。一方面,低齡未成年人相較于成年人而言,其身心特點并不成熟,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也存在相應不足,這在一定程度表明低齡未成年人在實施相應觸法行為時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有所降低。由此,對于低齡未成年人的一般觸法行為而言,由于其人身危險性和主觀惡性相對不高,此時即便通過刑事手段予以處置,也無法達到如成年人犯罪規制那樣的犯罪預防之理想目標,因而《刑法》一般對其不予介入。另一方面,對于如故意殺人、造成嚴重后果的故意傷害等惡性刑事案件,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與主觀惡性相比一般觸法行為而言顯著抬升,甚至表現出不亞于成年人的惡劣程度。也正是基于這種原因,《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刑事責任年齡予以有限下調,對12-14周歲低齡未成年人的犯罪予以刑事追訴。但考慮到刑罰的教育功能和目的,《刑法》對該類犯罪主體的特定犯罪之追訴同時作出了嚴格限制,以兼顧風險刑法理論與“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
(四)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符合國際刑事立法的趨勢
橫向對比國際社會的其他國家與地區,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難題顯然并非我國獨有。同我國一樣,這些國家與地區在面臨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時也存在關于刑事責任年齡劃定的爭論與質疑。但無論采用何種標準,以低齡未成年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作為刑事責任能力的核心與本質已然成為普遍共識,并成為指導國際社會界定刑事責任年齡的參照依據。
就國際社會相關組織倡議而言,其往往是在充分尊重少年兒童權益保護最大化的基礎上,結合各國、各地區實際情況與差異,最終提出符合各國經濟、社會、文化等發展情形最大公約數的相應建議。例如,1985年的《聯合國少年司法規則最低限度的標準規則》第2條對少年的定義作出明確的年齡范圍限定,指出各國應當結合本國的經濟發展、社會文明程度、傳統文化影響等各種因素最終通過法律的形式將未成年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進行明確,并建議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范圍應在7周歲至18周歲之間或18周歲以上。2007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0號一般性意見——少年司法中的兒童權利》認為12周歲及以上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規定是國際上可接受的水平,而不應將其界定得過低。但同時,該文件認為就被控犯有嚴重罪行或者被視為足夠成熟可承擔刑事責任的兒童,允許存在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以外的個案處理。
縱覽聯合國各成員國關于低齡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其普遍設置在0至16周歲之間。當然,此處所謂0周歲,并非指嬰兒也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而是這些國家并未對刑事責任年齡作出明確規定,且當其面對相應的犯罪行為時也會采取一系列的感化教育矯治甚至限制自由的措施予以應對,例如古巴、馬來西亞、盧森堡等。主要受英美法系影響的國家與地區則普遍將刑事責任年齡設置在7至10周歲之間,例如英國、美國、瑞士、新加坡、印度等。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國家與地區普遍將刑事責任年齡設置為12周歲,例如巴西、墨西哥、安哥拉等。將刑事責任年齡設置為13周歲的國家與地區普遍受法國的影響較大,例如希臘、以色列、中非共和國、剛果等。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設置為14周歲的則主要受蘇聯影響,例如朝鮮、拉脫維亞、阿爾巴尼亞等。此外,還有部分國家將刑事責任年齡設置在15周歲,例如捷克、瑞典、丹麥、芬蘭等,以及比利時、阿根廷等極少數以16周歲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國家與地區。[12]
綜上可見,世界上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刑事責任年齡均設置在14周歲以下。并且,隨著經濟社會和法律文化的發展,世界各國各地區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調整在近年來也有所顯現。例如,以英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由于之前的刑事責任年齡過低而有上調至接近12周歲的趨勢,以德國、日本為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也產生了關于刑事責任年齡是否下調的爭論。[13]換言之,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調整至12周歲已經逐漸成為國際主流趨勢。因此,我國《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下調是同國際刑事立法趨勢相契合的。
二、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追訴的爭點
(一)爭點之一: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否有違兒童利益保護最大化原則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相關規定,兒童利益保護最大化原則應當成為世界各國、各地區處理未成年人觸法案件時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我國“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對此也予以了深刻踐行。也正是基于這種立場,無論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前關于是否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爭論,還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關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正當性證成,學界均存在不同觀點。
反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學者認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立法規定損害了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并主要從以下方面予以論證:其一,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有違我國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刑事政策。在此觀點看來,未成年人犯罪并非是單一因素決定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促動的結果,因而面對低齡未成年人的觸法行為首先應當予以教育感化而非刑事懲治。《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使得我國對未成年人的刑罰處遇過于嚴苛,有違“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背離未成年人特殊保護刑事政策。[14]其二,從刑罰適用的功效來看,單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難以有效遏制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有論者認為,監禁刑的適用容易導致“交叉感染”情形的出現,并且容易導致服刑的未成年人被“標簽化”,從而不利于低齡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最終使得刑罰的犯罪預防作用大打折扣。[15]其三,雖然經濟社會的發展導致未成年人的身體發育日益成熟化,但身體特征等外觀的成熟并不能表明未成年人的心理成熟。究其原因,未成年人的心理成熟度相比而言受社會環境影響更大,而非僅僅是由物質條件和身體成熟度等決定,因而將未成年人的身體成熟等同于心理成熟缺乏事實依據。[16]
支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學者則持相反觀點,認為該立法規定恰恰保證了兒童利益的保護最大化,并從以下方面予以相應展開:其一,隨著社會的發展,低齡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均發生較大變化,已然具有相應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在相關學者看來,判斷低齡未成年人是否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根本在于刑事責任能力也即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本身,刑事責任年齡只是其相應的表現要素,其并非不可改變。況且,根據社會發展的現實情況,低齡未成年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有所上升已然成為現實。[17]其二,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立法規定及其配套制度規定恰恰能夠起到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作用。在論者看來,既往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并未同成年人有效分開,從而導致未成年人司法改革躊躇不前,甚至隱有助長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之勢,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刑法修正案(十一)》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以及設置專門矯治教育等規定,并輔之以《家庭教育促進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制度更新,更好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18]其三,對加害人利益與被害人利益有效衡量,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的立法規定能夠最大程度地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對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降低的探討不能僅僅將關注點聚焦于未成年犯罪人,而應同時涵蓋受害人利益。根據相關案件的現實折射,低齡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往往也以低齡未成年人作為犯罪對象,并對受害者及其近親屬造成嚴重的身心損害。因而,對于12-14周歲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的規制能夠顯著提升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
(二)爭點之二:低齡未成年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罪、行之爭
對于低齡未成年人的犯罪懲治,兼顧考量犯罪遏制和兒童利益保護最大化的情況下,學界普遍主張對于低齡未成年人的犯罪打擊要盡量克制,也由此形成對相關刑法規定的限制解釋立場。這種限制解釋立場曾貫穿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14-16周歲未成年人承擔八種特定情形刑事責任的探討之中,并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關于12-14周歲未成年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理解中得到延伸。
不少學者認為當前《刑法》第17條第3款規定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之“罪”并非單純指罪名,而應當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行為。例如,姜敏教授指出,雖然該條款并未直接表明低齡未成年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是指罪名還是行為,但從其與第2款規定銜接以及體系化的角度來看,應該將其理解為行為而非罪名。[19]唐稷堯教授亦認為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主體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應當是行為類型已經成為我國司法機關的一貫立場,因而其認為12-14周歲的低齡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條款可以適用于所有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類型的行為。[20]但同時也有論者對此類觀點提出質疑,并從文義解釋、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等方面剖析,主張該條款中的低齡未成年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應當為罪名而非行為類型。[21]顯然,學界關于12-14周歲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限制程度之不同理解僅僅是基于解釋方法、解釋立場等的不同,正是這種解釋立場和解釋方法的差異性應用方導致了學界關于該規定中“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罪、行之爭,也即“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罪名與行為訟爭。
(三)爭點之三:第17條第3款規定各實體限制要件的適用關系爭議
不同于14-16周歲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訴,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刑法》第17條第3款對12-14周歲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同時規定了三個實體性要件,從而對相應的追訴啟動程序作出了嚴格限制。其中,“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是罪質要件,“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是結果要件,“情節惡劣”是情節要件,只有三要件同時滿足后方能進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核準追訴程序。但是,對于各個實體限制要件具體呈何種關系,同樣是理論界和實務界尚未解決的困惑與難題。
例如,有觀點認為該款規定中的罪質要件與結果要件之間是一一對應關系,即:“故意殺人”對應“致人死亡”結果,而“故意傷害”對應“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有觀點認為結果要件是對罪質要件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僅僅是對故意傷害罪的限制,也即“致人死亡”與“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等均是對故意傷害罪的限定;有觀點認為三個實體性要件是層層遞進的限制關系,此時結果要件是對罪質要件的限制,并且這種限制不局限于故意傷害罪,而是同時涵蓋故意殺人罪;而對于“情節惡劣”這一情節要件,則有觀點從禁止重復評價的角度認為情節惡劣不應當包括結果要件中的“以特別殘忍手段”[22],但也有觀點認為情節惡劣應當包括“以特別殘忍手段”,且多應用于故意殺人罪的判斷場合[23]。
(四)爭點之四:下調刑事責任年齡后是否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肇始并興盛于英美法系國家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處置規則,其力圖“通過彌補憑借年齡劃分刑事責任的非靈活性問題,以適用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為原則,以“惡意”突破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推定為例外,以“惡意+特殊年齡段=刑事責任能力”為判定標準,最終實現對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低齡化的有效矯治。”[24]由于“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靈活性優勢,我國學界對其也予以廣泛關注,并逐漸形成了該規則是否可引入我國的本土化之爭,并且這種長期以來的理論爭議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仍處于延續狀態之中。
否定論學者的觀點不一而足,并主要呈現出兩種論證邏輯:一是“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不存在本土化空間;二是《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剛性做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例如,有學者認為,“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內涵已經通過我國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分段式劃分與嚴格適用限定予以體現,而且這種分段式的年齡劃分制度同“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本身存在互斥性,因而該規則在我國不具有相應的司法價值與適用意義。[25]也有學者認為,在我國《刑法》已經明確規定了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情況下,“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因違反明確性原則而有違罪刑法定,并且會對刑事訴訟證明提出新挑戰,甚至會引發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濫用,因而與其考量“惡意補足年齡規則”而不如直接通過刑事責任年齡的立法規定予以“一刀切”。[26]
肯定論者則認為,即便《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然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方式對低齡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規制,但這并不影響“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我國的本土化改造與適用。例如,有學者認為:雖然當前的立法已經將刑事責任年齡予以固定,但這并非表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就是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應對的終點。面對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齡化現象,固定刑事責任年齡的做法對于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刑事責任年齡以下未成年人,刑法仍然無法介入,這不符合普通人的正義觀與法感情,因而有必要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27]有學者認為“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作為補充性規則的引入,并沒有改變我國的“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方針,也未對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進行沖擊,通過對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各類范圍限縮對“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予以改良,能夠適應我國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需要。[28]
綜觀當前關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下調后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懲治的理論研究,雖探討甚多、涉及甚廣,但其中的爭議核心焦點無外乎是前述四點內容要素,而這些爭議恰恰又是影響該條款具體適用的核心內容。由此,基于犯罪治理和兒童利益保護的雙重價值,該條款的規范適用與司法優化應當圍繞該四種爭點予以展開。
三、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追訴的優化路向
(一)恪守“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消極主義刑事司法立場
雖然“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與方針并不排斥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懲治態度,并由此為《刑法修正案(十一)》有限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的刑罰擴張做法提供了相應合理的正當性論據。但同時需要注意,“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根本和重心為“教育”之特征并未改變,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教育”矯治和預防應當始終置于“懲罰”手段之前。由此,雖然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擴大刑法處罰范圍屬于積極主義刑法觀在刑事立法層面的落實,但其并不違背兒童利益保護最大化原則,因而我們仍需要在司法層面秉持消極主義刑事司法立場,在刑罰適用的過程中保持刑法所應有的謙抑性。
消極主義刑事司法立場是與積極主義刑法觀相對應的刑事司法觀,其并非是指司法機關在面對相關類型案件時采取偏向不作為的消極態度,而是指刑法在該類案件的處理中應當保持充分地克制,不到不得已之時不得輕易適用。顯然,這與立法層面的積極主義刑法觀并不互斥,甚至能夠在推動刑事治理現代化的道路上同向發力。“刑法作為抵抗社會違法行為的最后一段防線,應根據一定的規則控制其處罰范圍,在運用道德,習慣,風俗等非正式的社會控制手段和民事、行政等其他法律手段能夠有效調整社會關系,規制違法行為時,就沒有必要發動刑法”。[29]究其原因,刑罰首先并不能從源頭改變未成年不健康的犯罪心理,同時也會讓其脫離社會,并且可能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有色眼鏡看待。因而,對于未成年犯罪人,我們應該更多的關注其犯罪原因,同時審視家庭、校園、社會等多方面的因素,從而通過刑罰以外的其他手段予以先期預防和后期打擊,而非簡單用刑罰加以規制。換言之,無論是出于降低未成年人犯罪可能性的目的,還是出于讓未成年犯罪人擁有健康心理、重新回歸社會的目標,刑法規制都不應當是最有效也是最優先選擇的制裁手段與措施。
(二)從嚴采用“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罪名說”解釋
為契合兒童利益保護最大化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原則,對于低齡未成年人犯罪進行“從嚴解釋”將較為寬泛與模糊的規定予以明確化,從而限縮自由裁量與主觀解釋的空間,這其實正是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與刑事立法本意的貫徹。由此,筆者認為對于12-14周歲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立法條款中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以“罪名說”作為從嚴解釋的結論,其相比“罪行說”而言更能貼合相應的涉未成年人犯罪懲治之立法目的。
其一,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來看,將“罪”理解為“罪名”更符合相應的刑事法治立場。無論是理論中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之界分與稱謂,還是我國司法機關關于《刑法》分則各個具體罪名的名稱確認,“罪”之一詞均應當被理解為相應的“罪名”,例如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搶劫罪、盜竊罪等莫不如此,刑事司法判決也是以相應罪名的確定最終實現對犯罪人定罪量刑。
其二,12-14周歲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條款中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之理解無需參照14-16周歲未成年人進行體系解釋。原因在于,12-14周歲的低齡未成年人和14-16周歲的未成年人在以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為核心的刑事責任能力方面有所不同。相比而言,12-14周歲低齡未成年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顯然更低,此時如若參照14-16周歲的未成年人應負刑事責任情形予以解釋,雖然符合體系解釋的邏輯與結論,但其并不一定能夠符合12-14周歲未成年人主體相對于14-16周歲未成年人主體的特殊性。況且,即便對12-14周歲未成年犯罪主體應負刑事責任情形的解釋結論不同于14-16周歲未成年犯罪主體,二者也不產生必然的沖突與排斥,其僅僅是解釋基點與利益考量有所不同而已。
其三,“罪行說”的最終歸宿也是“罪名”,因而其與“罪名說”并無實質不同。即便堅持“罪行說”觀點的學者認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罪為行為類型而非罪名,但其最終卻同樣認為具體的定罪中多數應當定性為“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等罪名,從而回歸到了“罪名”的范疇之內。例如,綁架中的殺人行為,多以故意殺人罪而非綁架罪論處;搶劫中造成的重傷或殺人行為,多分別以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而非作為搶劫罪的加重量刑情節論處等。綜觀相應學者的觀點,不難發現,學者關于“罪行說”的論證及其結論,最終的定性仍然是以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的犯罪構成為核心判斷標準。因此,從這種論證邏輯和結論來看,筆者認為“罪行說”和“罪名說”并無本質不同,“罪行說”最終其實也是落腳于“罪名說”。
(三)追訴時嚴守各實體性限制要件層層遞進限縮的判斷標準
《刑法》第17條第3款關于12-14周歲低齡未成年人追訴標準中的“罪質要件”“結果要件”“情節要件”并非是平行關系,而應當予以判斷時的遞進式限縮理解,其中結果要件是對罪質要件的限縮,情節要件又是在結果要件基礎上的進一步縮限,只有三個實體性限制要件同時滿足后,方可進入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核準追訴程序,對相應的未成年犯罪人予以刑事責任追究。
一方面,遞進限縮式理解形成的判斷基準能夠兼具刑罰制裁機能與兒童利益保護最大化,從而實現刑罰預防與懲罰的雙重目的。在這種遞進限縮式理解下,各個實體性限制要件的具體適用應當主要分為三步走:第一步,結合未成年犯罪人的主客觀表現,依照犯罪構成標準將其行為嚴格框定于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之內;第二步,根據未成年犯罪人因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等違法犯罪所造成的具體后果,將非基于特別殘忍手段實施、重傷結果以下等情形的故意殺人未遂和故意傷害罪之追訴予以排除,也即只有“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方能納入情節要件的考量范圍內;第三步,綜合未成年犯罪主體的犯罪手段、犯罪情節、罪前罪后表現等一系列要素,綜合判斷犯罪人相關犯罪情節的惡劣與否,并以此推斷是否納入最后的核準追訴程序。
另一方面,“情節惡劣”的實體性限制要件不應包括結果要件內的“以特別殘忍手段”。誠然,“以特別殘忍手段”作為犯罪情節的重要表現,在各個分則罪名的具體罪狀中一般被認定為“情節惡劣”情形,從而構成相應的加重犯罪構成或加重量刑情節,但在本條款之中卻不宜將其同等理解。理由在于,該條款的結果要件中關于“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描述采取了“手段+結果”的規范模式,這就表明如果不存在“以特別殘忍手段”的情形,即使“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也不宜納入相應規制。換言之,結果要件中的“以特別殘忍手段”在實質層面就是對后果的限定,并已然成為結果要件的一部分。此時,如若將其再次納入“情節惡劣”這一情節要件中予以考量,難免存在重復評價之嫌,有違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四)下調刑事責任年齡后“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本土改造
雖然未成年人的生理與心理特征同其所處的年齡階段密切相關,但年齡并非決定刑事責任能力的核心因素。相反,恰恰是刑事責任能力的具備決定了刑事年齡的下調。因而,由未成年人的年齡推定刑事責任能力,雖然具有相應合理性,但難免存在本末倒置之虞。由此,通過單純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以遏制低齡未成年人犯罪雖然具有科學性與合理性,但其并不能實現相應“完全遏制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預期目標與理想機能。這就表明,認為“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同我國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相互排斥且不具有本土化適用空間的觀點存在不合理性。況且,“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彈性調整對于補充“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剛性不足、對于全方位遏制具有相應刑事責任能力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與功能。但需要注意,基于我國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實際情況,結合兒童利益保護最大化原則的倡導,“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補充并非是對英美法系國家相應理念與制度的全盤引入,而是應當在現有的刑事立法規定基礎上予以適用上的嚴格限制,進行符合中國刑事治理能力現代化需求的本土化改造。
其一,“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適用的年齡范圍。根據我國《刑法》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劃分,已然推定為12-14周歲的未成年人對造成嚴重損害后果且情節惡劣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具有相應的主觀惡意,應當予以刑事追訴。由此通過反向解釋的方法可以推斷,根據《刑法》規定,12-14周歲未成年人對于綁架、投放危險物質等危害行為被推定為不具有相應刑事責任能力。顯然,這種結論是存在一定邏輯悖論的。其值得質疑之處就在于:《刑法》一方面承認了12-14周歲未成年人具有一定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但又為何對不同情形下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予以區分對待?這很明顯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因而,結合“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本質內涵與我國《刑法》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階段劃分,本土化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應當適用于12-14周歲的未成年人,從而對該年齡階段未成年人隨著社會發展而逐漸心智成熟的現實作出合理回應。
其二,“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適用的犯罪類型。我國《刑法》第17條第2款對于14-16周歲未成年人應負刑事責任的情形明確列舉了八種犯罪類型。根據該八種類型犯罪的實際特點,其所蘊含的犯罪惡性與不正當性相比其他犯罪而言非常明顯,能夠為一般具有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自然人和單位所識別。因而,本土化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應當立足于我國刑事立法精神與規定,符合我國未成年人心智變化程度的漸進性特征。由此,我國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不應參照國外無犯罪類型區分的做法,而是參照14-16周歲未成年人應負刑事責任的情形,適用于相應的八種特定類型犯罪,從而兼具社會治理效益與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雙重機能。
其三,“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適用的證明標準。在英美法系國家,不同國家或地區對于“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適用時的“惡意”證明之標準也是不盡相同的。例如,英國采用的是排除合理懷疑標準,而美國采用的則是優勢證據規則。[30]顯然,相應的證明標準是與本國刑事訴訟制度相適應的。因而,我國關于“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適用的證明標準同樣應當以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為剛性要求,即入罪時需要達到“證據確實充分”且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如若無法達到排除合理懷疑或辯護方能夠提出不具有相應刑事責任能力可能性的證據時,就無法利用該規則予以刑事追訴。
其四,“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適用的程序要求。由于“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適用是對剛性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有限彈性突破,因而應當對其設置嚴格的審查程序予以刑事追訴的啟動,這能夠較大程度地避免國家刑罰權的不當濫用,防止公民權利被侵蝕。結合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和追訴程序,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展開:一方面,充分運用檢察聽證制度,將“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適用后的惡意聽證程序融入其中,以此結合社會公眾、生理專家和心理專家等各方面意見,對其所具有的刑事責任能力進行全面充分地論證,以對其具有的“惡意”精準認定;另一方面,參照12-14周歲未成年人應負刑事責任的法定追訴程序情形,將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程序運用至“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適用之中,通過嚴苛的程序設置增強刑事追訴或不起訴決定的權威性,保證“惡意”認定的準確性。
《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立法規定順應了我國犯罪低齡化的趨勢和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求,但其目前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適用和理論爭議仍然尚待厘清。因而,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立法模式之正當性、“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罪行內涵、各實體性限制要件之間的適用邏輯關系以及“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當前引入等再次予以理論澄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豐富相應的理論成果并推動該立法規定的實踐適用,這也是助推我國刑事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