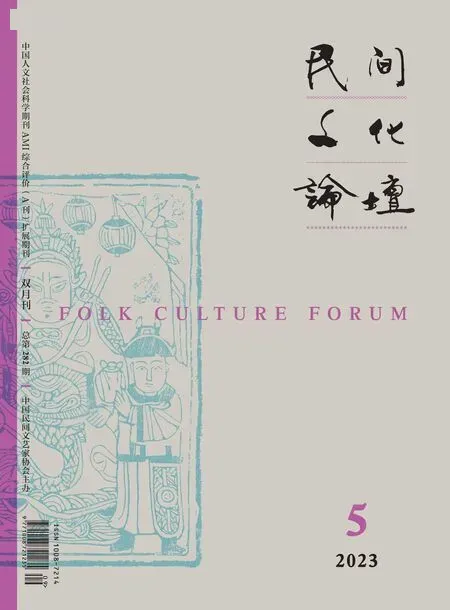手機微信群對民歌演唱與傳承的影響
—— 基于白族民歌微信演唱群的考察
楊曉勤
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民歌的傳承面臨極大的考驗。民歌似乎“不屬于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它已不再是必需的”①陳泳超:《白茆山歌的現代傳承史:以“革命”為標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第144 頁。,自發演唱行為的銳減、民歌的舞臺化傾向、歌手的青黃不接……這些不爭的事實令人擔憂,學界對此也多有闡發。然而近年來,手機微信演唱群的涌現,卻使得民歌的傳承迎來枯木逢春的契機。往昔那種弦歌聲四起的傳統演唱氛圍雖不復存在,但對于民歌愛好者而言,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一機在手”,便可如愛麗絲由兔穴步入仙境一般,穿越時空融入民歌的世界。
自2015 年以來,筆者先后加入了十余個以演唱白族民歌(俗稱白曲)為宗旨的微信群,其規模大者近五百人,小者數十人,皆由操白語的民歌愛好者自發組成,其成員構成以農村人口為主體,地域分布主要為大理劍川、洱源、云龍、鶴慶、祥云以及麗江玉龍、怒江蘭坪等滇西少數民族聚居區,少量來自浙江、廣東、上海等外省市(因婚嫁、打工等緣故至此),筆者對這些微信群進行了持續性的跟蹤調查,并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資料。本文將以此為案例,在與傳統語境相比較的基礎上揭示微信演唱的特點,以便深入探究民歌演唱與傳承在數字媒體時代的嬗變。
一、微信的演唱時空
傳統的演唱多發生于田間地頭、山林湖澤等自然之境以及聚會、節慶、婚嫁等集體活動場合,為使演唱能順暢、省力地持續下去,對歌多為面對面進行,即便初時相距較遠,待搭上腔后歌手也會循聲靠攏。微信演唱卻徹底顛覆了上述場景。因手機的可移動性和遠距離、即時通信功能,人們對空間的經驗和認知不再受到“在場”的地域性活動的支配,以網絡信號所支持的流動空間取代了傳統意義上的社會時空,故而由地理環境造成的空間界限幾近于無。現在,歌手可以隨心所欲地在微信中邀約他人對唱,即便相隔千山萬水也可瞬間接通,“以歌會友”真正步入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理想境界。有學者曾抱怨數碼設備帶來了比工業時代的剝削更為高效的“新的奴隸制”,因為它“把每一個地點都變成一個工位,把每一段時間都變成工作時間”①[德]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程巍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51—52 頁。,使人們無法從工作中逃遁。這一弊端對民歌演唱而言反成了利處:用戶一旦登錄微信演唱群,無論何時何地都能邀人一展歌喉,可謂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時空上的表演自由。
以出生于20 世紀70 年代的女歌手S 的演唱經歷為例。S 的演唱水平在劍川縣女歌手中可謂首屈一指,但因她的丈夫認為唱曲是傷風敗俗之事,長期對她采取壓制措施,所以S在婚后很少有機會公開演唱。白族文人楊新旗在《山水劍川》中曾述及2002 年他赴馬登鄉調查白曲的往事,說是鄉里選派一女、一男為其表演對唱,但那女子的丈夫死活不允許她去唱,直到鄉干部以婦聯的名義、搬出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法令來,她丈夫才勉強同意。②楊新旗:《山水劍川》,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93—94 頁。書中所言女子正是S。2016 年筆者輾轉聯系采訪S 時,她深恐丈夫聞及白曲之事會出言不遜,使訪客難堪,故不敢在家中接待。十余年過去了,S 的丈夫仍未改變對白曲的態度,仍認為妻子唱曲有損體面,但對S 來說,借助手機這一媒介,她已能輕易擺脫丈夫的禁令、利用各種零碎時間與他人進行遠距離對唱,故其演唱行為比以前更為活躍。
此外,某些關于演唱空間的禁忌也隨之被打破。白族民歌多為戶外歌,尤其情歌(俗稱花柳曲)歷來嚴禁居家演唱,如立于石龍村本主廟內的鄉規碑上就鐫刻著“凡里巷五倫所系,長者出入,不得亂唱淫曲”的字樣。然而借助手機微信,歌手即便居家,只要獨處一室并壓低嗓音,便能與群友盡興地談情唱愛,哪怕不眠不休也無人干涉,“人家舞獅用燈籠,兄妹咱們用網絡,半夜咱們舞得歡,卻無人察覺”。
社會空間在地理意義上的削弱,必然也會帶來因演唱場景的不協調而導致歌手情感交流不對稱的問題。在傳統演唱中,只有居于同一場景的歌手才可能建立對唱關系,然而在微信演唱中,歌手往往身處異地、環境不同,這種差異性無疑會對演唱行為構成影響。由于歌手在微信對唱時慣用手機揚聲器播放語音,其所處環境中產生的自然音、人為噪音以及周圍群眾的言談笑鬧等一系列聲響,難免干擾對方的演唱情緒。通常來說,若歌手甲在演唱時是獨自一人,他希望與其對唱的歌手乙也是獨處的,即便不是,其周遭的人也該斂息悄聲,否則他極易終止表演。這種情形表明:身處由網絡信號構建的流動表演空間的歌手們,一方面享受著不受地理位置阻隔和束縛的自由,一方面仍難逃往昔在傳統演唱場景中養成的思維定勢——即對唱者之間存在著不容削弱的“表演劇班”關系。“表演劇班”(簡稱劇班)一詞由社會人類學家歐文·戈夫曼所提出,意為“在表演同一常規程序時相互協同配合的任何一組人”③[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馮鋼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70 頁。,本文借用此術語來強調傳統演唱場景中對唱者之間形成的緊密合作、共同對“外”的特殊關系。在傳統演唱場景中,對唱的歌手雖為臨時組合,卻是合二為一的整體,共同面對聚集在身邊的觀眾并竭力在他們跟前維持特定的情境。但在微信演唱時,若獨處的甲發覺與之對唱的乙正處于其他社交場合,他不僅擔心雙方的劇班關系會因此遭到破壞,而且懷疑乙與其身邊的人群構成了另一個劇班,自己反倒成了被孤立于劇班之外的角色。在這種疑慮的困擾下,甲對乙演唱背景中的音聲有著近乎敏感的關注,如果不甚喧鬧,或者那些聲響與乙本身無直接關聯,譬如集市的人聲、街頭的車馬聲、廠區的機器聲等,甲就會打消顧慮、全情投入演唱;反之,一旦判定乙與身邊的人有著頻繁的互動,甲便會覺得彼此間的劇班關系已破裂,而手機那一端的聚集者才是“一條船上的人”,這不僅令他倍感失落,也對“敵眾我寡”的格局心生不滿,尤其當對方語音中傳來眾人的開懷大笑時,這種負面情緒會迅速發酵。與傳統對唱中觀眾笑聲越多、歌手越是亢奮的情形不同,因手機中那遙遠的哄笑聲強化了對方(乙及其身邊人)是一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表演劇班的印象,甲頓覺自己成了一個被“劇班共謀”①歐文·戈夫曼用“劇班共謀”指稱劇班成員之間的一種密謀溝通,這種溝通方式隱蔽而謹慎,不會對在觀眾面前促成的假象構成威脅。參見[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馮鋼譯,第151 頁。所隔離的局外人——他們也許正暗中對他的演唱品頭論足、說三道四,但這些秘密的貶損卻統統不為他所知。這種不愉快的情感體驗,使他很難將演唱持續下去。
若歌手乙正在同時進行其他游戲,如玩撲克、打麻將等,即便其身邊的人保持靜默,歌手甲也通常會放棄對唱,因為他會將對方視為一個更密切的游戲團體。事實上,一心二用之舉,譬如一邊演唱一邊做飯、澆灌、放牧、開車等,在微信對唱中極為常見,并不會招致對方歌手的反感,歌手在意的主要是表演者之間能否建立起穩定的劇班關系。
二、微信群中歌手與聽眾的互動
歌手與聽眾的角色原是可以互換的,每個歌手都同時是聽眾,每個聽眾也都是潛在的歌手。這里所言的二者,其角色定位被置于每一場演唱活動的具體情境中,即正演唱的人和正聆聽的人。微信群中的演唱是在聽眾的參與、監督和評判中進行的,屬于公共性娛樂活動,這一點與大庭廣眾下發生的傳統對唱類同,但又呈現出一些異于后者的特征。
(一)歌手與聽眾的關聯變得松散
沃爾特·翁曾敏銳地察覺:當一個人面對他人說話時,聽眾不僅結為一個整體,而且與說話人也結為一個整體;設若說話人發書面材料給聽眾閱讀,使聽眾變為讀者,那么“每個讀者就進入他個人的閱讀世界,于是,聽眾這個整體就被粉碎了”。翁將此現象歸因為:“文字與印刷使人分離為個體。”②[美]沃爾特·翁:《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56 頁。與此相似的是,在微信群中,手機的個體運用使得聽眾同樣被分崩離析,而不再像傳統演唱情境中所呈現的——聽眾是一個整體,而且與歌手也結為一個整體。
在傳統演唱活動中,聽眾或三五成群地散布于歌手附近,或密密匝匝地將歌手圍在中心,多數時候是凝神靜聽,逢到會心處則笑聲不斷,只有當對唱陷入僵局時,才會有圍觀者插入,打個圓場或者縫合幾句,以使表演持續下去,極少出現貿然打斷他人表演的現象。這種融洽的氛圍在微信演唱中卻不多見,由于缺乏地理上的“在場”,每個手機聽眾得以進入他個人的聆聽世界,其行為也少了許多束縛,一人分飾二角——歌手與聽眾的情況屢見不鮮,即使是純粹的聽眾也希望即時發表言論以獲得存在感。如韓炳哲所言:“今天的我們不再是信息的被動接收者和消費者,而是主動的發送者和生產者。我們不再滿足于被動地消費信息,而是希望自己能夠主動地去生產信息、完成交流。”③[德]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程巍譯,第26 頁。故而當歌手正在微信群中唱得熱火朝天時,常有聽眾打斷他們的表演,或欲強行取代,或自說自話,發表一些與正在進行的表演毫不相干的言論。顯然,在微信群中難以組成一個團結的、內在同質的群體單位,歌手與聽眾之間的關系變得松懈、散漫,更傾向于各自為政。那種將數字群稱為“完全沒有群體性的靈魂或者群體性的思想”①[德]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程巍譯,第17 頁。的說法雖有些偏激,然而就微信演唱群而言,其云集者雖眾,實則難以形成如傳統對唱中歌手與聽眾融為一體的氛圍。
(二)歌手的避忌心理或有增無減
白曲微信演唱群中的成員往往少則數十、多則數百,其規模遠超傳統演唱場景,況且一個白曲愛好者往往同時加入多個微信演唱群,其信息接收量極大。事實上,入群不僅是一種主動行為,也時常包含著被動的因素。群主多熱衷于四處攬人,其因有二:一是人們慣以群中人數的多寡來評判群主的人緣和魅力,認為賓客盈“門”者,其人必通達明理,而“門”可羅雀者則乏善可陳。二是規模越大的群,其成員流失率越低,因大群中“人多嘴雜”、高潮迭起,不似小群常逢冷場,如一潭死水。在這些由龐雜個體匯集而成的新群體里,歌手唱曲時難免心生顧慮,最常見的是對冤家對頭的避諱。結怨的根由,既有因日常糾葛而生的厭憎,也有因演唱而起的沖突、競爭。在現場演唱中,人們與避忌對象相遇的幾率要遠遠低于微信群中。就地理空間而言,一個人很難在同一時段內現身于多個歌場,但這在網絡空間里卻是易如反掌,尤其通過回溯性的查收信息,人們可以“親歷”多個歌場。因此,對于生性敏感的歌手來說,微信群容易使他產生一種被人監視的不安全感,很難消除戒心。
手機本是一種強調私密性的媒介,但微信群的運用卻使其私密性減弱、公共性增強。就此而言,微信演唱在使人從身體位移中獲得解放的同時,也為其心靈套上了新的桎梏。
(三)聽眾對歌手的特殊褒獎——“紅包”
在微信群中,聽眾往往毫不吝惜地對歌手予以贊美和褒賞,它們多以語音、圖片和表情符號等來傳達,其中最實惠的方式莫過于“發紅包”,金額以10 元以內居多,且多為偶數以示吉利。
收到紅包的歌手通常會禮貌地道謝或贊美對方。搶紅包失利時,歌手也會發一發“勞者不得食”的怨言,或對那些“搶紅包時很積極,唱白曲時往后縮”的群友出語譏誚,如:“氣不過,唱曲不如搶紅包,豹子也追不上狗,一個沒搶著。”所發紅包即便指名道姓給某位歌手,也經常會被旁人搶走,有的是因為識字不多而誤搶,有的則是故意為之。一旦出現這種情形,聽眾便會紛紛提醒錯搶者,責成其速退紅包,甚至以主持公道的名義群起而攻之。在群友們看來,“搶紅包”一事無關金錢,而關乎人品,不能使發紅包者的心意落空,更不能因哄搶者的劣行玷污整個群體的素質,即如群友所言“不能讓人家看扁我們群里的人”。這種討伐有時會上升至人格侮辱,群友們在數字人的假面之下只顧逞口舌之快,群中很快變得烏煙瘴氣,群主因此將群解散之事也不鮮見。因一個小小的紅包使得演唱群分崩離析,這同時說明由數字個體匯集而成的群的脆弱性——即便是一個數百人的大群也可瞬間解體,與其產生一般無可預料。
三、微信演唱的形式特征
(一)以異性對唱為主
對唱形式受到人們青睞的原因如下:
一是與口語思維的特性有關。微信演唱群中的成員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群中交流主要依靠語音并輔之以表情符號,極少使用文字,故可被視為一個小型的口語社會。而“在口語文化里,長時間的思考和他人的交流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①[美]沃爾特·翁:《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何道寬譯,第25 頁。。民歌的演唱也是如此,如歌手所唱:“人說對手配對手,好曲難離好搭檔。”不僅長時間的即興演唱是在你來我往的交鋒中催生的,就連傳統敘事歌(俗稱本子曲)也多為對話體。這說明,在口語社會里,“你一言我一語”的交流方式較之自說自話,不僅有利于促進思考,還有助于增強記憶。
二是與人的表現欲望有關。數字媒體加劇了人類的個體化,“支配數字交流的并不是‘博愛’,而是自戀。”②[德]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程巍譯,第70 頁。在群中的人雖多以匿名現身,卻比往常更迫切地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全力展示自我以引人矚目,而“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表演情境極大地鼓舞了這種熱情。因此,五音不全的人也不懼在群中獻藝,羞于當眾表演的人也能旁若無人地高歌。
群中對唱多在異性之間進行,同性之間偶有對唱,其持續時間也較短。民眾一般認為:“唱曲自古男女配,兄弟兩人調難尋”“公雞不鳴母雞鳴,母雞相啄不好聽”,同性對唱多為日常寒暄,客氣有余而趣味不足,而異性對唱以情歌為主,自然更受追捧。
(二)以曲調緊湊為宜
在傳統演唱中,人們只關注整場演唱活動持續的時長,而不在意單曲耗時的長短,但在微信演唱中,由于微信語音的限制時長為60 秒,單曲的時長變得不容忽視——對于超出了60 秒的演唱,若是以一個語音的形式發送,勢必“爛尾”;若是以多個語音的形式發送,則破壞了歌曲的連貫性。因此,歌手在微信演唱時,都傾向于選擇短小、緊湊的曲調,盡量將每一首唱曲控制在1 分鐘之內。
白族民歌中流行的唱詞格式為山花體③雙闋八句,首句限腳韻、律調,逢偶句押韻、押調。,若采用劍川洱源壩區白族調④此名稱襲自伍國棟《白族音樂志》中對白族調的分類稱謂。參見伍國棟:《白族音樂志》,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 年,第57 頁。(簡稱“劍川調”)的唱法,每首的最佳演唱時長約為45—55 秒,短了顯得急促倉皇,長了則嫌拖泥帶水。由于劍川調的演唱時長,與微信語音的限制時長極為匹配,故在微信演唱中大行其道,即便是一些原本流行其他唱法的地域的歌手,也紛紛改弦易轍。譬如麗江石頭鄉的白族調(俗稱“石頭調”),其曲調悠揚綿長、一唱三嘆,單曲演唱時長需1 分鐘以上,于是當地歌手在微信演唱時大多棄用石頭調、改唱劍川調。因微信語音的時長限制,竟然導致了某些曲式在民間的興衰,這是筆者未曾預料的。數字媒體以一種隱秘的方式,對人類生活進行著全方位的重新編程,可惜我們對這一過程的感知往往是遲鈍、滯后的。
(三)以碎片式演唱居多
微信群中歌手的演唱隨意性很強,或興之所至,或見縫插針,又往往毫無征兆地戛然而止。時間與地點的不拘,固然使歌手能充分利用“邊角廢料”的時間,卻難以保有持久而專注的注意力,其演唱也因此變得支離破碎,往往“熱身”甫畢,就匆匆退場,因此,歌手的表演有時很沖動,有時又漫不經心,而聽眾的反饋又不總是及時的,這在一定程度也會削弱歌手的表演欲望。加之參與者眾,搶唱的現象時有發生,故此較之現場演唱,微信演唱的唱詞連貫性不強,常顯得零碎、散亂。對唱雙方因無法保持同等的交流節奏,常是“你唱東來我唱西,天一腳來地一腳”,多自說自話且缺乏相對穩定的主題,不僅歌手唱著別扭,聽眾也不知所云。這種碎片式的演唱雖能以此起彼伏的聲響制造熱鬧的表象,但久而久之會給人帶來類似“信息疲勞綜合征”的不適感。
四、微信演唱的內容特征
(一)演唱的競爭色彩減弱
1.勝負難以分曉
現場演唱時,除非因不可抗拒因素①如天氣驟變、配偶鬧場等。導致演唱被迫中斷,否則會持續至一方曲盡詞窮為止,但在微信演唱中,勝負卻難以明辨。一方面由于聽眾不再能充當“現場”證人,歌手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形下,可以適時尋找借口全身而退,以避免直面落敗的結局;一方面由于與聽眾缺乏面對面的交流,歌手不再執著于聽眾對他本人及其表演的看法,更多抱著“自適其適”的心態,因此興盡則退、不再勉強撐場。
歌手對其貿然中止演唱所作的解釋,常見的有三類:一是手機和網絡出現故障。諸如“手機沒電了”“手機太卡”“信號不好”之類理由一出口,對方只得作罷。二是受外界干擾。如有客人造訪、家人阻撓、臨時被派工等,因事發突然而不得已終止演唱。三是內急。這類理由多出于男歌手之口,雖近于粗俗,但對方也不便苛責。如:
再答你話小妹子,唱著唱著暫停下,今天啤酒喝多了,跑出去一轉。
古說男人有三急,上趟廁所也無妨,這曲唱罷不唱了,咱歇息一會。
其實在現場對唱中,歌手以排泄為由中止演唱的情形是罕見的,但這一理由卻在微信群中頻繁出現,對排泄物的提及常能給人們帶來歡笑,于是隱身于網絡的歌手也樂于自曝“其丑”,以喜劇方式撤離舞臺。
歌手對其中止演唱所作的合理化解釋,其真假大都無從查證,勝負雖不再分明,卻使處于下風者能體面退場,這對于提高新手的積極性倒是大有禆益。
2.歌手的應變能力被弱化
在現場對唱時,曲與曲之間的停頓不過數秒,這要求歌手具備敏銳的反應能力,幾乎在聆聽對方唱詞的同時,其腦海中便產生應對之辭,才能毫無遲滯地做到“你有來言,我有去語”。然而在微信演唱中,唱和時停頓的時間變得更具延伸性,考慮到網絡信號的傳輸等原因,即便停頓數十秒,對方與聽眾一般也能予以諒解。一些在微信群中成長起來的新歌手,因缺乏現場對唱的歷練,對花較長時間構思應答之辭習以為常,并不認為是技藝不精所致。如以下案例:
某日,女歌手H 與男歌手K 在某群中對唱,女的嫌男的跟唱速度偏慢,男的說:“不是我對不上,而是至少需要3 分鐘。”他進而解釋:“1 分鐘用來聽(你唱),1 分鐘用來想,1 分鐘用來(我)唱。”②微信群“寶山一家親”,發布日期2016 年4 月15 日,瀏覽日期:2022 年12 月23 日。
此例中女歌手在民間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因初涉微信演唱群,仍以現場對唱的接唱速度來要求對方。而男歌手是在微信演唱群中出道的新手,所以理直氣壯地提出了“唱和一曲需耗時3 分鐘”的說法。其實,那用于思考的“1 分鐘”,是在微信演唱的特定情境中形成的,難以見容于現場表演。數字媒體的去真實性,極大地減輕了歌手的創作壓力,使他的行為更易于偽裝,應變能力也隨之弱化。所以,微信對唱的持續時間總體低于現場對唱,譬如通宵達旦的對唱在集會中較為常見,卻從未見于微信群中。
(二)演唱中的對抗性增強
語言形式的暴力在口語文化不可避免,因為“一切語言交流必須是面對面的說話,涉及聲音的你來我往,人與人的關系因此就比較緊密——既有相互吸引,更有相互對立。”③[美]沃爾特·翁:《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何道寬譯,第34 頁。微信群中以歌泄憤的案例不勝臚列,歌手之間借唱曲相互詬詈,聽眾也紛紛站隊、參與交鋒。微信演唱為何比現場演唱更易引起沖突?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群成員在“忠誠感”的驅動下,常會主動充當群內“公序良俗”捍衛者的角色。微信演唱群雖只是一個偶然聚合的群體,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成員會不同程度地產生對該群的“忠誠感”。“忠誠感”的產生,一方面因為成員的個體愛好與演唱群的創辦宗旨相契合,使其有種“找到組織”的歸屬感。另一方面也是群本身“類家”的吸引力所致。群內弦歌不絕的場面以及“晨昏定省”式的問候、絮絮叨叨的聊天……,會給躋身其中者帶來一種特殊的親情體驗,加之演唱群中的成員多以兄弟姐妹相稱,越發使人對這一小型的擬家共同體心生依戀。這種忠誠感的存在,使得成員多少有一種主持公道的責任感,在發覺其他成員有不妥當的言辭時,會爭相出面指摘,以期維護群內秩序和群體形象。
其二,處于微信交流狀態的人們,其行為更易于沖動。韓炳哲認為數字媒體是一種散播沖動的媒介,“數字交流讓人可以馬上發泄沖動,這種即時性所傳遞的沖動要多于傳統的模擬交流”①[德]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程巍譯,第6 頁。。在微信群虛擬的演唱空間里,每個人都可能因自己的表演而博得眾人的矚目,這種“重要人物”的感覺著實使人陶醉,因此他不吝表達自己的想法,就算片言只語也要一吐為快,尤其與其他群成員話不投機時,更是將曲辭化為劍戟投向對手,措辭愈激烈愈好,語氣越強勢越妙,一派“彈唱間檣櫓灰飛煙滅”的豪情。
其三、微信演唱群中的成員多以網名示人,這種匿名性加劇了沖突的出現。“尊重是與姓名相聯系的,匿名與尊重互相排斥”②[德]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程巍譯,第5 頁。,真實的姓名是相互認可與信賴的基礎,匿名總給人一種遮遮掩掩的感覺,難怪古語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形容處世坦蕩、磊落。在匿名交流的微信空間內,禮貌與尊重或被棄若敝履,人們反規范的行為傾向卻愈演愈烈,輕率的言論隨口而出,蟄伏的戾氣一觸即發。不得不說,在匿名的假面具下,現實生活中溫馴的綿羊,也會變為虛擬空間中兇殘的鬣狗。
(三)糾錯類歌曲增多
所謂糾錯指歌手糾正演唱中的失誤,這失誤既有來自自身的,也有來自他人的。前者屬于自我更正,后者屬于傳授演唱經驗,無論何種,對于提高演唱技藝都是有益的。以下分別述之:
1.自糾型
現場演唱如覆水難收,倘若歌手對其所唱不甚滿意,也無法“回爐”重唱。但在微信演唱中,即興創作的壓力被極大緩解,歌手可以較為從容地斟酌其唱詞,對有瑕疵的新成品也能及時“返工”重唱。有時是初唱之曲在韻腳、句式方面有誤,通過重唱使其合乎格律;有時是初唱并無失范之處,但重唱在遣詞造句方面更為精巧。這類自我糾錯式的重唱源于較強的內省心理,歌手利用微信交流的延遲性,以嚴苛的態度反觀其演唱并予以修正,努力使其表演以更完美的形態呈現出來。
2.他糾型
在現場演唱的緊張節奏下,旁人很難當眾指出歌手的紕漏,對“病曲”只能不了了之,否則有攪局之嫌。但在微信群中,人們可以對演唱隨意臧否,加之利用微信語音的回放與重播功能,原本脫口即逝的歌曲在聽覺的空間中被定格下來,這使得演唱中的瑕疵也纖毫畢現。因此,一些老歌手熱衷于為“病曲”糾錯,這既是傳授演唱經驗,也是對自身權威的樹立。
常見的糾錯除了針對歌辭格律、唱腔曲調等,還涉及演唱狀態的問題。在現場演唱中,歌手會竭力給觀眾留下理想化的印象,故其表演狀態多是積極、亢奮的;但在微信演唱中,觀眾的“現場缺席”或令歌手產生身處“后臺”的錯覺,令其卸下表演者面對觀眾時應具的偽裝,因此歌手的演唱有時顯得漫不經心,這顯然與聽眾對于表演者的角色期待有偏差,容易給聽眾造成一種“有口無心”的印象。一旦聽眾懷疑歌手并未專注于其表演行為,常忍不住加以批評,如:
說給阿妹你聽著,我看你是沒力氣,唱出白曲沒精神,是否沒吃飯?
像似燈泡被停電,像似車子沒有油,若唱不起就歇歇,吃飽再出來!
至于被糾錯者的反應則因人而異、因群有別。生性謙遜者樂于接受批評,甚至主動致謝;玩世不恭者會滿不在乎地承認失誤,同時以“唱曲只是圖熱鬧,諸位何必太計較”之類唱辭加以搪塞;倨傲自矜者則不予理會,通過漠視對方來表達其對抗情緒,甚至予以反訐。此外,同一人在不同群中的反應也可能存在差異。“一個人有多少個社會自我,這取決于他關心多少個不同群體的看法。通常,面對每個不同的群體,他都會表現出自我中某個特殊的方面。”①[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馮鋼譯,第39 頁。在一個大腕云集且秩序井然的微信群中,被糾錯者的反應大多友善、和緩,而在一個多由無名之輩構成的微信群中,因缺乏權威人物的震懾,對于被糾錯的反應傾向于冷淡或逆反。
結 語
波茲曼曾以柯勒律治的詩句“到處都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來比喻現代社會中的信息過剩現象,即“在信息的海洋里,卻找不到一點有用的信息”②[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艷、吳燕莛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62 頁。。這種現象在微信演唱群中也不免存在,因演唱的時空限制被極大突破,演唱行為發生得更為頻繁,呈現出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然而,數量的激增并不意味著質量的精進,唱詞良莠不齊、魚龍混雜,鮮有傳唱的佳作問世。饒是如此,微信演唱對于民歌的繁榮仍然功不可沒。少數民族民歌傳承在當代社會面臨的困境主要緣自兩方面:一是大量中青年離鄉求學、務工,與口頭傳統被迫剝離;二是語言生態的失衡,使得年輕一代對以母語演唱的民歌產生情感隔閡與理解障礙。這些現象雖難以逆轉,但微信演唱群的活躍卻起到了有效的緩解作用,從筆者對白曲微信演唱群的追蹤調查來看:許多背井離鄉者在鄉愁的驅使下,經常泡在群中聽曲、聊天,一些原本與白語環境疏離的、居于城鎮的青少年在偶入白曲群后,出于民族認同感或新鮮感,也開始練習白語、學唱白曲。可以說,微信演唱群在網絡空間中以“聲音”的形式,部分還原了白曲表演鼎盛期的情境,使群成員(歌手以及潛在的歌手)浸潤于其間并“被濡化著”③[美]艾倫·帕·梅里亞姆:《音樂人類學》,穆謙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 年,第151 頁。,這對于白曲的傳承和發展無疑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