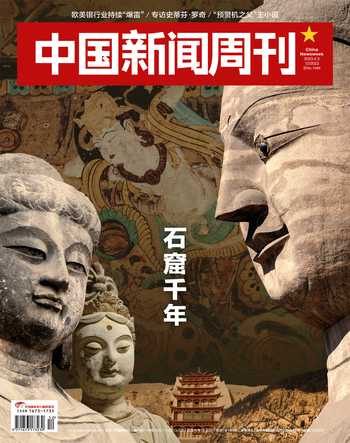年輕人“上香”:不過是尋求一種確定性
維舟
現在網上流行一個梗:“在上班和上學之間,選擇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間,選擇了求佛。”如果你以為這只是年輕人的一句玩笑,那就錯了:今年以來寺廟相關景區門票訂單量不僅暴增,而且預定門票的人群中,90后、00后接近半數。
這是讓很多人都看不懂的一個現象:社會愈加現代化、年輕一代所受的教育也更好了,為什么他們竟會轉身去求神拜佛?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這說到底還是年輕人沒能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致于把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有媒體就評論認為,這樣的生活之路“顯然走偏了”,畢竟向神靈禱告是虛妄的,“奮斗才是青春的底色”。
然而,“上香”并不必然只是指望天降橫財,和“奮斗”也未必矛盾。正如另一家媒體指出的,僅僅說教沒什么用,“與其憂心年輕人上香,不如關心他們在‘求’什么”,從根子上解決他們的內在心理需求。
年輕人為什么上香?我以為是由于他們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大增,原子化的個體又缺乏社會網絡和公共機構可以求助,無論是父母還是親友都無法有力地回應他們的困惑和面臨的挑戰,此時,神佛就成了最后的替代選擇。
古人之所以求助神佛,與其說是愚昧無知,不如說是他們那時還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對一系列影響自己人生的外部力量都無能為力,于是轉而相信這都是冥冥中有神靈的力量在左右。社會學家楊慶堃在所著《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中指出:“生活越艱難,人們越是傾向于尋求巫術和宗教的幫助;越是貧困的階層,其成員也就越迷信。”
這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相比其他人,貧窮的人更難掌控自己的生活,因而宿命論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可取的人生態度——把一切歸結為“命運”,那就卸下了自己的心理負擔,不用再為那些重要、但自己卻無能為力的事而煩惱。
歷史學家基思·托馬斯曾指出一個耐人深思的現象:近代早期的英格蘭既是“科學文明曙光”的時代,也是占星術流行的巔峰。他在研究了近代早期英格蘭大眾信仰后指出:民眾之所以迷戀那些巫術、星座,與其說是愚昧,倒不如說是它們能在功能上填補了科學、宗教留下的空白。直到深入的現代化使得人們越來越有信心掌控外部環境,理性、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公共機構和法律規范的不斷完善,更使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無須求助于巫術就能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漸漸地,巫術就不再是最優、更別提是唯一選擇了,到最后,它甚至成為多余的了——如果吃藥就能治好病,為什么還要求助神佛?
這樣說來,那到了今天這樣現代的社會,又有什么必要上香?
荷蘭可說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以其世俗、理性著稱于世,號稱“海上馬車夫”的荷蘭海員更是這段歷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角之一,然而正如《倫勃朗時代的荷蘭》一書中所言,“平時看上去很兇悍的人卻是尼德蘭最迷信的海員”。因為海上生活要面臨大海無法預測的種種風險,哪怕一個再有經驗的水手也有難以應對的時候,此時除了跪下來祈禱上帝外別無良策。
仔細觀察一下,你就會發現,越是在那些結果難以預測的領域,人們就越是迷信。“墨菲定律”中有一句俏皮話:“散彈坑中沒有無神論者。”在危機四伏的戰場上,沒有人能避開所有風險。同樣的,球賽結果極難預測(所以才緊張刺激),再老練的球員和體育記者都無法料見最終比分,因而球場上的迷信也格外突出,以致于有人相信章魚能預測世界杯結果。
即便是現代化的社會,也還是做不到掌控所有風險,甚至風險可能反倒比以前更大更多了。農民的生活是高度重復性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懇種地就是,至于天要下雨,那也不是自己能管得了的。然而到了現代社會,每個人從就學、就業、投資到生活日常,幾乎無不面臨著抉擇,社會的容錯率又低,一步錯步步錯,而大部分風險又遠遠超出個體所能掌控的程度。
這樣,從傳統社會網絡中脫嵌出來的個體,赫然發現自己要面對復雜的不確定性,而社會卻又默認這都是個人的責任,這就給他們施加了極大的精神壓力。這些年社會彌漫著焦慮,這不是偶然的,因為焦慮感的由來,說到底就是“面對不確定性,想控制又控制不了”。
無論是焦慮還是上香,本質上是一種對不確定性的恐懼。此時,“上香”就提供了稀缺的確定性——靈不靈且另說,但至少讓人把這種壓力轉嫁給了一個超自然存在,最后就算事沒成,那也是屬于玄學的范疇。
客觀地說,當人們面對一個龐大、莫測又無法掌控的不確定世界時,“上香”確實可以堅定他們的信心,撫慰心靈,并在法律難以保障的時候約束立約者的行為。因而看似吊詭的是:求神可能“迷信”,但卻并不必然是“落后”的。
有一次,同事出差回來,談起一路見聞,驚訝地發現廣東人非常迷信,另一位廣東籍同事面不改色地說:“不是廣東人迷信,是有錢人都迷信啦。”
這話其實頗有幾分道理。自古以來,閩粵一帶就有悠久的出海傳統,而從事海外貿易不僅需要巨額投資,而且是高風險高利潤的事業。正因此,對這些地方的人來說,在神靈面前的契約所奠定的商業同盟、信仰所帶來的敢闖敢干,都是他們更好應對風險時極為關鍵的。
魯迅晚年曾在雜文《〈如此廣州〉讀后感》中說,很多人對廣東人的迷信“加以譏刺”,他也承認“廣東人的迷信似乎確也很不小”,“然而廣東人的迷信卻迷信得認真,有魄力”,不像江浙一帶只不過搞點儀式糊弄一下:“廣東人的迷信,是不足為法的,但那認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而“中國有許多事情都只剩下一個空名和假樣,就為了不認真的緣故”。
魯迅在意的并不是“迷信”本身,而是信眾的主體態度:如果是自發的、認真的信仰,那也是好的,這樣才能投入地把事做好。同樣的,現在真正關鍵的恐怕也不是年輕人上香本身,而是他們是否有一種認真做事的精神,從而更好地應對自己所面臨的種種不確定性。
不確定本身是個中性詞,未必就一定帶來恐懼,不確定也可能是機遇,相對于一潭死水的確定性,上一輩也曾有許多人拋棄“鐵飯碗”毅然下海。他們面對的也是不確定性,但沒有恐懼,更多的是相信“明天會更好”,盡管也是因為一窮二白,沒什么可失去的,但更重要的是對未來的憧憬。對未來有好的預期讓人傾向于選擇挑戰,擁抱不確定性,反之則寧愿選擇穩定。
就此而言,現在更值得警惕的,是社會上彌漫的保守、畏懼風險的心態。風險社會里沒有“絕對安全”這回事,但國人常有一個牢不可破的幻想:只要抱的大腿夠粗、飯碗夠鐵、自己的欲求夠低,就能換來安全。大多數人更加傾向于接受確定性帶來的痛苦,而非不確定性帶來的痛苦——誰也不知道地火何時上涌,就選擇那個最堅固的巖塊吧。
英國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創造了“朝不保夕族”(precariat)一詞,認為現在的新工人階層普遍受困于“4A”,即焦慮(anxiety)、失范(anomie)、異化(alienation)和憤怒(anger)。雇主們總是期待他們心甘情愿地拋開個人生活需要,去適應不可預測的時間表和不確定的職業前景,“你總在被評估、被打分。一直要擔心下一塊面包在哪里,這意味著對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
這確實是當下無數年輕人的現實處境。美國著名劇作家莫斯·哈特在自傳中就曾感嘆:“我愿意斗膽做出這樣的猜測:在一切成功的職業生涯的宏大設計中,運氣始終是一個強有力的影響因素。”所謂“運氣”,其實說白了就是一些普通人不可控的偶然性外部因素。僅僅責備年輕人“迷信”,加以“奮斗”的說教,并不能解決他們的困境,關鍵之處在于如何減少這種外部風險,給他們提供支持,重新奪回對生活的控制感。
這當然需要社會公共機構給予更多的保障,鼓勵人與人之間的橫向聯結,而不是任由孤立個體去面對和承擔所有風險,否則沒有人能堅強到搞定所有問題。現代社會要開辟出新領域、新可能,無不需要冒險,但“冒險”并不意味著讓人不系保險帶一躍而下,而應當是在提供充足支持的情況下,鼓勵人們向前探索未知。
年輕人上香,已經不是為了神靈面前的契約,而是個人主義的風險管理寄托,尋求好運來贏回對生活的掌控感。然而“好運”究竟從哪里來?在這個龐大的時代,每個人面臨的不可控變量極多,也確實可能隨時陷入復雜的潛規則,但這并不意味著個體什么也做不了。一個常識健全、認知正常的普通人,也能在暗礁遍布的大海上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這與其說是“運氣”,不如說是一種活出自我的“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