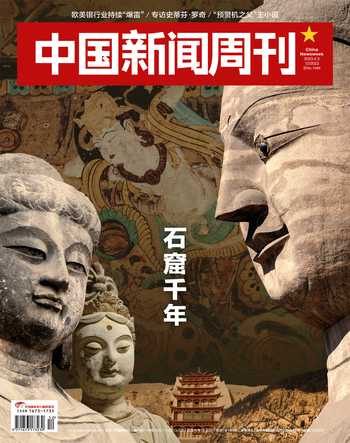哈爾濱清理編外人員
佟西中

圖/視覺中國
哈爾濱開始向編外人員“動刀”了。3月20日,哈爾濱市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發布消息,市級機關事業單位開展編外用人清理規范工作。該消息一經公布即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按照當地公布的《哈爾濱市級機關事業單位編外用人清理規范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清理工作從3月開始到6月底結束,分自檢自查、組織實施、檢查督導三個階段實施。
根據《方案》,本次專項整治行動的實施對象為哈爾濱市級機關、市屬事業單位現有雇員、行業專職人員、工勤人員和單位自聘人員(統稱“編外用人”)。
哈爾濱市機構編制辦一位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按照有關方面要求,哈爾濱市正按照確定的《方案》,依法依規開展這項工作。“各地其實也在不同程度地開展,只是方式方法不盡相同。”他說。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到了優化機構編制資源配置,地方黨政機關人員編制精減工作,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結合實際研究確定。
在此背景下,哈爾濱市清理編外人員尤其引人關注。哪些編外人員會被清理,又如何清理?
“編外”是相對編內而言的。編內人員即在編人員,一般指國家財政負擔其經費開支的各級各類機關、事業單位以及部分特殊機構等單位的正式工作人員。
就編制類型看,行政編和事業編最為民眾所知。據悉,哈爾濱市此次清理的“編外人員”指,市級機關、市屬事業單位現有雇員、行業專職人員、工勤人員和單位自聘人員。
從總體看,《方案》比較完整,包括工作目標、工作原則、清理范圍及對象、主要任務、組織實施、工作要求等內容。
哪些人會被清理?《方案》在主要任務中提到,精簡編外用人員額、清理規范用人行為。其中清理規范用人行為列舉了11條,包括行政執法、財務管理、人事管理、涉密等崗位使用的編外人員;臨時性、階段性工作已完成、合同已到期未再續聘的編外人員;人員使用與審批崗位不一致的編外人員;主動離職、考核評估不適崗的編外人員;既沒有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又未實行勞務派遣的編外人員;已推行社會化服務外包仍自行聘用并混合使用的編外人員;歷史遺留問題產生的編外人員。
另外,超出員額控制標準的編外用人和行業專職人員,可以通過社會化服務外包的保安、保潔、綠化、食堂等崗位的工勤人員,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其他情形,也在被清理范圍之內。
《方案》還提到,醫院、高職高專、公證處、仲裁辦等用人主體要結合專業和實際需要,自主開展自聘人員清理規范工作,并逐步將已自聘人員轉化為社會化服務外包形式。
除清理規范用人行為,編外用人員額也要精簡。《方案》提到,市級機關事業單位現有編制內人員能保證工作正常開展的,不使用編外人員。用人單位要制定編外用人員額年度精簡計劃,市直機關編外用人原則上5年內精簡完畢,每年精簡不少于本單位編外用人員額的20%。市直事業單位編外用人結合職能調整情況及空編率適度精簡(空編率5%~15%,編外用人精簡5%;空編率15%~25%,編外用人精簡10%;空編率大于25%,編外用人精簡15%)。
一位組織系統官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稱,空編率越大,編外用人精簡幅度越大,這是符合邏輯的。空編率越大,代表可用編制內人員數量越大,可優先使用編制內人力資源。
前述哈爾濱市機構編制辦工作人員說,這是統籌編內和編外關系,編內編外調整一盤棋。
編外用工在各地普遍存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不單是哈爾濱市,沿海發達省份也存在類似現象,編外用工的現象在全國都比較普遍。
中國人民大學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劉昕也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很多地方的機關事業單位編外用工現象非常突出,編外用工即使不占用編制,但仍然以財政支付費用為主。
馬亮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編制是剛性約束,有的地方政府卡得很嚴,擴編、增編需要嚴格的程序,而現實中人員需求量大,所以存在編外用工的現象。

哈爾濱市政府辦公大樓。《方案》中列舉了11條清理規范用人行為,包括行政執法、財務管理、人事管理、涉密等崗位使用的編外人員。圖/視覺中國
其次,可能是編制資源配置不合理。馬亮說,中央政府缺人,可以從地方政府借調,省級地方政府缺人,可以從下級政府借調。但基層政府缺人,無法借調,只能以編外用工形式解決。
除了上述原因,劉昕補充說,各單位在使用編外用工時,往往缺乏足夠的約束機制,自行擴張的情況屢有發生,這就導致行政成本越來越高。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地方政府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原主任魏娜說,編外人員大量增加,一方面與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務增加相關,另一方面與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有關。
魏娜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從現實情況看,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務和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在增多。管理事務增加的同時,政府的職能也要轉變,如果管理方式不科學,也會增加編外人員。
在魏娜看來,政府及用人單位對編外人員缺乏管理、缺乏監督,也是編外人員增加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理編外人員之前,哈爾濱近年至少開展過兩輪事業單位改革,對機關事業單位編制“動刀”。
2018年,哈爾濱市制定《市直機關事業單位實施控編減編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并提出了相關目標。
據哈爾濱機構編制網消息,截止到2020年11月底,市直機關(含直屬參公事業單位)編制總量精簡21.5%,市直事業單位編制總量精簡36.2%,超額完成三年行動目標。
另據《黑龍江日報》2021年7月報道,繼2018年啟動并完成一輪事業單位機構改革后,哈爾濱接續實施深化事業單位改革試點工作,哈爾濱市事業單位機構編制規模進一步壓縮。
報道提到,哈爾濱市本級機構精簡47個,占比19.3%,事業編制精簡8246名,占比25.3%。市轄區機構精簡177個,占比21%,事業編制精簡7816名,占比22%。
近期公布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到,地方黨政機關人員編制精減工作,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結合實際研究確定。
公開報道顯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公布后,哈爾濱是首個公布清理編外人員方案的城市,但在此之前,多地已開始清理編外人員。
今年2月,安徽省桐城市召開市編外人員清理規范工作座談會。會議表示,清理清退不是最終目的,而要以此為契機,規范整頓編外用人亂象,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和服務水平。
再之前,2022年湖北省房縣開展了編外聘用人員清理規范工作。同年湖北省監利市召開會議,決定對監利市全市機關事業單位編外聘用人員進行清理規范。
此外,據海南媒體報道,2021年海南省萬寧市285家行政事業單位清理編外人員1336人,年度節省財政開支3079萬余元。
哈爾濱此次明確出臺《方案》開始清理編外人員,釋放了什么信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聶輝華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可能有兩層含意:一是中央已經決定精減編制,地方政府會有所動作,編外、編內又是緊密相關,在清理編外人員后,還可能進一步精減編內人員;二是地方財政吃緊。疫情三年,財政支出加大,清理編外人員,可減輕財政負擔,提高治理效能。
魏娜也認為,清理編外人員是信號,先從清理編外人員開始,然后逐步精減編內人員。她特別提到,對于編外人員,也不適宜“一清了之”,應該留有過渡期。
值得一提的是,哈爾濱公布的《方案》中提到,用人單位要依法依規開展人員清理工作,暢通編外人員退出機制,保障編外人員合法權益,推行社會化服務。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人力資源研究會測評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白智立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前多地推進編外人員清理工作,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地方政府因疫情等因素,財政壓力加大,“清理”編外人員可節約行政資源。二是貫徹一直以來精兵簡政、減員增效的傳統。三是需要對編外人員進行規范管理。
白智立還表示,要加強制度建設,填補編外人員隊伍管理制度的空白。“編外人員對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不能一味否定其作用和功能,應該以此為契機積極推進編制管理的改革。”他說。
劉昕提到,清理編外人員要避免“一刀切”,避免流于形式,要明確各單位的組織定位和承擔的主要職責,然后據此進行科學的核算,人員配置要盡可能合理。
一般來說,改革都涉及利益的調整與分配,精簡編制與清理規范編外人員亦如此。
多位黨政機關人士、事業單位受訪者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編內與編外,不同的部門、機構、地域,情況都各不相同。有受訪者甚至坦言,在實踐中一些地方確實存在“關系戶問題”。
而從現實角度看,被清退的編外人員,可能面臨失業、再就業的問題,如果年齡偏大,還可能會更難就業。
那么,怎樣清理,如何取舍?就擺在了地方政府面前。哈爾濱公布的《方案》,對此進行了積極探索。
在工作原則方面,《方案》提到,“區分不同機構性質,統籌編內和編外關系,嚴格控制編外聘用人員,從嚴規范適用崗位、職責權限和各項管理制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務效能”。
《方案》提到,按照“誰使用、誰負責、誰清理”的要求,嚴格遵循有關法律法規開展清理規范工作,要積極穩妥、以人為本,妥善處理好各方面關系,深入做好有關人員思想工作,切實保障職工合法權益,確保清理規范工作平穩有序推進。
具體而言,包括通過清查行業文件,精準摸清底數,按照“誰用人、誰統計、誰備案”原則,對編外人員進行動態實名登記和管理,進而按照前述“誰使用、誰負責、誰清理”原則,進行清理和規范。
對于編外人員退出,《方案》有相關規定,包括暢通編外人員退出機制,保障編外人員合法權益,推行社會化服務,對用工量大的獨立辦公單位可單獨采購實行服務外包,零散用工單位可歸口機關事務管理部門集中統一采購實行服務外包。
《方案》還提到,對現有已訂立勞動合同但未到期的工勤人員設置1至2年過渡期,過渡期內按照單位性質,通過現行經費渠道予以保障,過渡期滿后,相應崗位變更為政府采購服務。
此外,在實施方面,分自檢自查、組織實施、檢查督導三個階段,每個階段規定了時間和相關安排。在工作要求方面,“一把手親自抓好落實”。哈爾濱還組織編辦、人社、財政、民政、公安、消防救援、機關事務、紀檢監察等部門建立健全協作配合機制,抽調工作人員組成工作專班,對清理規范工作進行檢查指導。
聶輝華認為,《方案》體現了一定的策略性,也考慮到了可操作性,但沒有統一的標準。“比如,具體到編外人員個體,到底誰退出?誰留下?”他說,最好給出具體的標準,告訴公眾到底以何為依據,比如年齡、學歷等客觀標準,如果標準不明則容易給“人為操作”提供空間。
對此,有觀點認為,“一刀切”不失為一種“公平”的辦法。所謂“一刀切”即將編外人員全部清退。
一位基層公務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全部清退)根本不現實,政府、事業單位,對編外人員是有現實需求的。”他舉例說,政府部門通常都有司機和文印室文員,而這往往不占用編制名額。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編內、編外在工作層面多有明顯區別,其中,編外人員多是事務性、輔助性工作,通常不會接觸到核心業務。一位地方公務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編外人員定位就是輔助”。
魏娜也認為,對編外人員“一刀切”全部清退,是不現實的。“三定方案”——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是確定的,如果增編需要法定程序,需要遵守相關規定,論證增編合理性。
“政府的改革目標是縮減規模,而不是增加編制。”她說,這就需要轉變職能、規范管理,如果不轉變管理方式,搞人海戰術,“多少人干事也是不夠用的”。
在魏娜看來,統籌編內與編外,根源還在于政府管理職能與管理方式的轉變。她提到,政府首先要確定職能任務,如果管理任務增加,需要補充編內人員,還是增加編外人員,這需要論證測算,“編外人員始終是輔助,所占比例需要測算,管理要科學規范”。
白智立認為,最理想的狀態是實行科學的職位分類基礎上的編制管理,但現實中存在職位分類實行不徹底,編制管理不盡理想等問題,還不能人、崗、事、編完全適配。“從當前情況看,全部清理編外人員,不僅不合理,而且做不到。”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