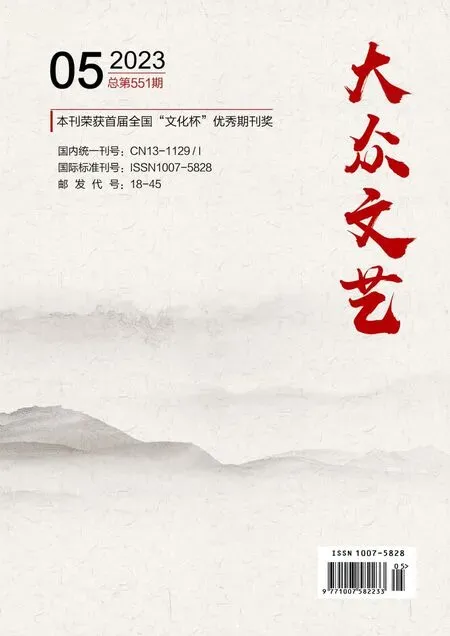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藝術創作與近代德國無產階級運動
王禹童
(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市 100091)
近代西方現實主義藝術創作與其所處的時代大勢與社會思潮共享著同一條生命線,緣此生命線溯流而上探索之,必不可忽略二十世紀德國著名女性版畫藝術家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其作品與十九至二十世紀無產階級工人運動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自中國現代版畫藝術的開拓者魯迅先生將其作品引入我國始,這一偉大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在我國革命藝術發展史上在諸多先進藝術家的創作中起到了深刻的指導作用,于傳統版畫藝術的基礎之上掀起了強勁的進步思潮,具有向標般的地位。時至今日,在眾多版畫作品中仍能窺見珂勒惠支的遺風,其作品作為世界藝術舞臺上永遠屬于無產階級勞動者的一枚不可磨滅的足印,將永為后人所稱道,并加以反復的研習與省悟。
一、凱綏·珂勒惠支之藝術理念形成背景概述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愛國主義的浪潮席卷了德意志。國家統一的呼求在社會各界中的影響逐漸提高,德意志各階級國民集合其最高利益和追求,將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作為首要目標。而與此同時,工人運動也隨同國家力量的上升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展逐漸擴展與成熟,德意志工人階級進一步組織并聯合起來,開始在德意志的民族區域內創建具有新生氣息的代表其自身權益的獨立政黨。一八六三年五月,德意志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全德工人聯合會成立,這意味著德國工人運動于其進步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德意志無產階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發展與壯大。
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原名凱綏·勖密特(Kaethe Schmidt),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出生在德國柯尼斯堡的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中。[1]凱綏的祖父與外祖父均崇尚法國革命并曾投身于民主運動,父親是一位建筑師,也是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哥哥康拉特·勖密特與恩格斯曾是舊識,在恩格斯的思想影響下,成了一名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曾擔任過《前進報》的編輯;其家人同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人亦有交情。在這樣的家庭與人際關系的熏染與影響下,凱綏逐漸成長起來,并逐漸展露出其在藝術方面的愛好與才能。凱綏少年受英國畫家荷加斯的銅版畫作品觸動甚深,并在年紀尚小時便開始學習素描技法,十四歲時便進入柏林女子繪畫學校。在教師斯滔發·培倫(Stauffer Bern)的指導下,凱綏接觸了當代德國杰出雕塑家與銅版畫家麥克思·克林格爾(Max Klinger)的作品,從中,她悉知了德國勞動人民于人世水火中的苦難生活。這與其童年時觀看碼頭工人與水手的艱辛勞動的記憶產生了巨大共鳴,并對其早期的作品風格造成了真切的影響。對于凱綏本人而言,克格爾的作品的啟蒙是她創作的起點。[2]
而德國工人運動的議會斗爭道路同樣開始于一八六七年。當年八月,北德意志邦聯國會第一次實行全體男性公民普遍、平等、直接的選舉制度。德意志工人政黨領袖積極參加了這次邦聯國會議員的選舉,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和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當選為第一屆邦聯國會議員,這是德國工人階級代表第一次在容克資產階級的合法機構——議會中擁有了代表,為德國工人階級開始于議會中從事斗爭提供了基本條件。此后,德國工人政黨的議會斗爭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工人政黨在國會選舉中的選票數量逐年增加、增長迅速,到一八九八年,再次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3]而在一八八八年,凱綏來到慕尼黑,開始又一段求學生涯。在這座城市,此間,她也曾聆聽過工人領袖倍倍爾的演講,時常前往參加社會主義者們發起的群眾集會,汲取其思想理論與實踐經驗。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德意志成為社會主義的大本營,社會民主黨在數次大選中贏得席位,一八九一年,《愛爾福特綱領》發表,宣告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基本目標和社會主義原則,并闡述了黨的直接政治要求。該《綱領》在十九世紀末的無產階級工人運動中造成了顯著影響,進一步推動了其開展的進程;同年,凱綏與同為社會主義者的卡爾·珂勒惠支醫生結為伉儷,婚后,二人定居在柏林的工人區中,卡爾·珂勒惠支同時經營起了一間專門救治工人的醫療保健所,在工作與生活的間隙里,二人幾乎無時無刻在同勞苦大眾交流與共事,對世間疾苦與下層民眾饑寒交迫的生活的理解如同切膚之痛銘刻在凱綏的骨髓中。于是,在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期間,凱綏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信念與藝術理想,開啟了她的創作道路,將靈感的筆尖伸向民眾的吶喊與抗爭,勇敢揭露階級矛盾,自此,她的許多優秀藝術作品便如同警世鐘般逐漸涌現。
凱綏懷著對民眾的真切、平凡、博大的愛進行創作,以版畫——粗獷樸實、明朗純粹的藝術表現方式創作出屬于勞動人民的血與淚的繪畫詩歌,其作品不僅是寫實的敘述,更是社會的痛訴與時代的呼求。
二、凱綏·珂勒惠支早期藝術創作主旨與德意志工農運動
一八九三年德國劇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劇本《織工》的首次演出。該劇目取材于一八四四年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的真實事件:工廠主與官僚地主之間的相互勾結造成了工廠與農村中肆虐的剝削,苦命的織工不僅承受著廠主的壓迫,同時又要繳納所謂的“紡織稅”這一荒謬稅務;在殘酷剝削下的工人的加薪請求被工頭的暴力壓制行為所駁回、唱著諷刺歌兒的工人遭到逮捕后,工人們壓抑許久的憤懣與痛苦終于在沉默的苦難中得以洶涌而出,六月四日,在西里西亞歐根山麓兩個紡織村鎮彼特斯瓦爾道和朗根比勞,爆發了這場由紡織工人群體自發組織與進行的目的為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的起義,工人們以簡陋的武器同政府軍艱難抗爭,最終于六日因不敵增援而遭鎮壓,起義宣告結束。根據這一事件與本場演出,開始進行她的版畫創作,并自次年始,開始打磨她的第一系列成名作——《織工一揆》(EinWeberaufstand)。該組作品共耗時約四年完成,以《窮苦》(Not)(石版畫)、《死亡》(Tod)(石版畫)、《商議》(Beratung)(石版畫)、《織工隊》(Weberzug)(銅版畫)、《突擊》(Sturm)(銅版畫)和《收場》(Ende)(銅版畫)等六幅作品組成,著重描繪了織工們承受的深重苦難、團結一致在掙扎中奮起抗爭、在遭受殘暴鎮壓后遭遇的失敗等場面,以強有力的直面現實的風暴般的手法將勞動人民的悲哀、苦痛與壓抑的怒火傾瀉在觀者的眼前。貧窮與困苦,抗爭與死亡,在殘暴鎮壓后的落幕,工人們的尸體橫置地上,仿佛人類發展史那龐大身軀上的一塊塊抹不去的創痕。[4]珂勒惠支手握刻刀,將歷史的沉淪、政局的壓抑、階級的矛盾與人民的苦難一刀刀割裂,涌出的鮮血凝成了六幅作品,一八九八年,這一系列作品在柏林的展覽會上展出,一經披露,便引起了強烈的轟動。這是珂勒惠支首次以版畫為刀鋒為無產階級人民而戰斗,亦為她自身的藝術創作理念與心路歷程鑄就了一塊里程碑,這位在先進思潮的陶冶下成長的優秀的女性藝術家,就此縱身躍入無產階級斗爭與革命的洪流中去。
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八年間,凱綏致力于完成她的另一部心血之作:連續版畫《農民戰爭》(Bauernkrieg)。本系列作品共七幅,且均為銅版畫。該組作品取材于一五二四年起發生在德意志的農民戰爭之現實事件。十六世紀初期,在封建領主、貴族、官員帶來的沉重稅務與徭役的壓迫下茍延殘喘的身為奴隸的農人們不堪重荷,在馬丁·路德(MartinLuther)掀起的宗教改革浪潮下,農人們受到新教思想的鼓舞而精神覺醒,奮起反抗苛捐雜稅,攻擊地主貴胄,起義風波搖撼全國,并擴展到德語南部地區,最終在政府的血腥鎮壓下平息。這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是近代德國最大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一,影響深遠直至珂勒惠所在的當時,借由這一題材,她再度創作了這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組畫。該系列作品的上半部分依舊以農人們在疾苦中勞作的形象作為鋪墊,農夫在辛勞中曲折了腰身,農婦遭受可怖的凌辱,勞動人民的苦難集小流而成洪濤,蓄勢待發著要為那封建統治下的壓迫與剝削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沖擊。系列作品之高潮為其中第五幅——《反抗》(Losbruch),畫中的農人們手持粗糲的農具為武器在草場上奮力沖鋒,正前方一位婦女揮舞有力的臂膀向起義的隊伍發出喝令,勞動者勇猛而悲壯的反抗的靈魂如同炬火一般迸發而出,直要把一切官僚地主都燒盡;在接下來的作品中,依舊是起義遭受鎮壓后的凄涼之景象,然而農人們遭縛的身軀依舊立著,在起義失敗的終局里,依舊是無產階級人民精神不滅、不朽的象征。這組作品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對整個德國繪畫界都造成了非凡的轟動,并受到克林格爾等知名畫家的高度贊揚。
從《織工一揆》到《農民戰爭》,珂勒惠支創作生涯早期的諸多名作均以發生在近代德意志的工農運動為主要題材,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無產階級運動浪潮之中,這些巨作如同強烈的作用力推動疾水向前奔涌,發揮著無產階級革命藝術的獨特作用,釋放出屬于一位年青的女性版畫藝術家的不可被動搖與磨滅的能量。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數年中,除這兩個系列的作品之外,珂勒惠支還進行了少數獨立作品創作,如一八九九年完成的取材于歌德所作詩劇《浮士德》(Faust)的《格萊親》(Gretchen)、一九零一年完成的取材于法國大革命的《斷頭臺邊的舞蹈》(Tanz Um Die Guillotine)等,涌現著其強烈的個人特色。《斷頭臺邊的舞蹈》雖并非取材于德意志無產階級運動,卻依舊將目光投向了下層民眾,眾人將新建好的斷頭臺環環圍住,呼喊著跳起加爾瑪弱兒舞,峭壁樣的房屋堆疊著,灰暗的底色襯托出人的肢體,壓抑的畫面中,如同可以聽到急促的鼓點、驟雨般的腳步與嘶鳴般的呼喊。在這一時期珂勒惠支的藝術創作理念與風格在逐漸鞏固,為無產階級與廣大勞動群眾發出的雄渾吶喊充盈著她的畫布,屬于飛速發展前行中的時代的戰斗激情與決意與現實主義表達手法的冷酷與坦誠并存,使得她以雙目、雙耳、雙手求索而見證的無產階級革命理想躍然畫面之上。
三、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凱綏·珂勒惠支藝術創作中心思想的鞏固
一九一零——一九三零年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后,珂勒惠支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時而不得不面對彷徨卻始終持續發展的上升階段。這一時期,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爭政策的失敗、民生問題的尖銳化、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宣傳工作在社會各界中如火如荼地開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之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示范性影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德國爆發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十一月革命。全德國各地都紛紛爆發了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工人士兵蘇維埃。一九一九年,領導了柏林數十萬工人為反對艾伯特政府篡奪革命成果和撤銷獨立社會民主黨左派而舉行的總罷工與武裝起義的德國青年運動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與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被反革命集團殺害,事件發生后,珂勒惠支對李卜克內西的儀容作畫了速寫,隨后又一副具有紀念意義的作品——《紀念李卜克內西》在她毅然的筆觸與刀鋒下誕生。此后的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組畫《戰爭》(Krieg)中的七幅作品相繼完成。在此作品中,她將目光再度轉回至勞動人民,記述戰爭為平凡民眾帶來的苦難。
進入三十年代初期,隨著社會主義思想的進一步成長和發展,珂勒惠支以此為道路而形成的創作理念亦在同步走向更加深入的成熟期。在這一時期,珂勒惠支所表現的畫面中出現了以往作品里不常可見的喜悅神色,如《母與子》(Mutter Und Kind)中流露出的真切情感表達,這與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發展路途上的不斷上升的態勢具備著難解難分的關聯性。然而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臺,德意志第三帝國走上歷史舞臺后,局勢隨即急轉直下步入嚴峻境地,珂勒惠支面對這一態勢,堅定了抵制的立場,她與作家亨利希·曼(Heinrich·Mann)共同簽名,參與到呼吁黨內左翼成員聯合起來共同抵抗法西斯勢力的號召中。在大量進步文學家藝術家蒙受迫害的危機中,珂勒惠支依舊堅持自身的藝術創作理念,縱使處在自身被逐出學院、取消職位,個人安全遭受巨大威脅的時刻,她仍保持著創作的狀態,并完成了組畫《死亡》(Tod)等名作,抒發著抗爭的勇氣與行走于為廣大無產階級民眾求索、反抗的道路上的決心。
在珂勒惠支的個人藝術觀點中,她始終堅持“藝術家和人民當相互了解”,并將此深刻貫徹到她的藝術創作手法之中,這使得她的版畫作品具備了相當程度的人文氣息與強烈的現實主義表現力,對于其展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與高度的藝術性的獻身于無產階級革命道路與理想的創作理念而言,這一舉措與方式對于其中心思想的穩健發展與傳達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珂勒惠支直言不諱地承認她的藝術究其在純粹的藝術層面上的意義而言并不“純粹”,是一種“有目的”藝術[5],同時將此于創作中一以貫之,使得其作品得以緊貼時代的路徑、匍匐于群眾的行走遺留的足跡之上前行,成為國際工人運動如火如荼發展壯大的時代中的藝術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道深黑的刻痕,以銘刻下的血汗同吶喊一同并作世界革命藝術中的一聲強有力的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