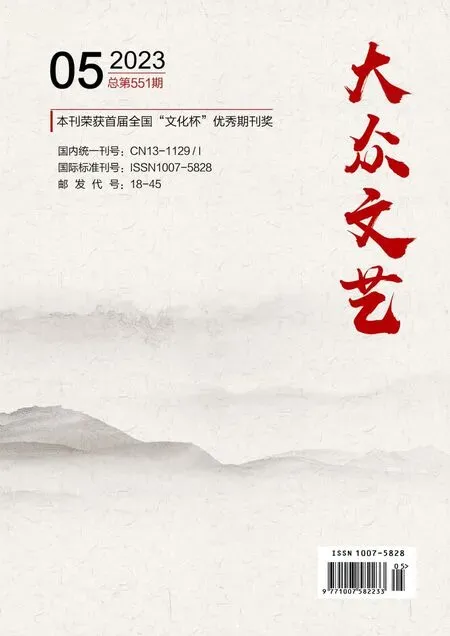從城市化到士紳化:回顧成都玉林四十年更新歷程*
藍意穎 史先哲 張家月 李旖旎 包晨晨
(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 610041)
一、引言
今天的“玉林”,是一個文化上的概念,而非行政區劃意義上的區域,它表達了一種“成都的”生活方式。在地理范圍上,“玉林”北至一環路南三段,南至二環路南三段,東至人民南路四段,西至高新大道永豐路,具體包括了成都市武侯區玉林街道的玉林北路社區、玉林東路社區、倪家橋社區、青春島社區和成都市高新區芳草街道的蓓蕾社區、沙子堰社區,本文所進行的梳理針對的就是這一區域內發生的城市建設和街區改造。
二、文獻綜述
在傳統的理論意義上,一個城市的從無到有,會經歷集中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的三個階段,士紳化則發生在逆城市化之后,是衰落的市中心再度復蘇的過程。但不同于再城市化進程在原土地上進行新建,士紳化指的則是在原有建筑基礎上發生的更新。從城市化到士紳化,構成了城市生命的一種連續的發展脈絡。
士紳化概念最早由R.格拉斯(Ruth Glass)于1964年提出,其定義隨著士紳化現象的階段變化、地區拓展而不斷復雜化、多元化。E.克拉克(E.Clark)對士紳化的定義結合了地理范疇和歷史脈絡的雙重視角,即“士紳化”既是土地使用者人口屬性變化的過程,也是建成環境變化的過程,一方面新土地使用者相較原使用者而言具有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另一方面資本的再投入使得街區面貌發生改變。
士紳化研究的分析離不開生產端理論與消費端理論。一方面,生產端理論強調宏觀經濟因素對士紳化的影響,這一學派最經典的概念便是尼爾·史密斯提出的租隙理論,“租隙”(rent gap)指的是房地產的現況價值和士紳化后價值之間的差額,這一差值的大小與該地區的士紳化機會呈正相關的關系。因此,通過租隙,我們可以一定程度預測士紳化將會開展的地區,史密斯也確實通過這一理論精準預測了紐約多個小區的士紳化。基于租隙理論,史密斯也批判性地認為,士紳化的本質只是資本的回歸,而非“人”的回歸。[1]另一方面,消費端理論則關注士紳化群體的社會文化特征,認為士紳化是后工業化社會催生的新中產階層塑造的,他們在居住空間的消費實踐折射出特有的審美偏好和價值觀念。
士紳化研究中期,出現了生產端理論和消費端理論的二元論爭鳴,將生產與消費、供給予需求、結構與能動性、經濟與文化相互對立。[2]但在1990年代初以后,士紳化研究開始尋求士紳化二元論的互補性。C.哈姆內特(C.Hamnett)將士紳化二元爭論看作是一葉障目,即生產端與消費端理論實際上都是整個士紳化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進一步,L.李斯采用A.吉登斯(A.Giddens)的結構二重性來論證了士紳化二元論的互補性、辯證的二重性,同時與其他學者提出“星球士紳化”(planetary gentrification),強調士紳化理論的去歐美中心化和本土地方化,并通過比較研究的路徑探討全球的紳士化現象,以其期構建更復雜、更多元化的士紳化理論架構。[2]
士紳化有許多細分類型,存量更新的新時代以來,商業紳士化(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這一士紳化類型逐漸獲得學術關注。商業紳士化描述的是士紳化過程中的商業變遷部分,具體標志便是在大城市衰落的鄰里出現獨具美學或文化氛圍的商業形式,包括咖啡館、時裝店、藝術商店等等,在士紳化景觀上呈現符號化、美化特征,在商品種類上呈現高端化特征,在消費群體上呈現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特征。[3]零售紳士化是商業紳士化的一種類型,指社區里的地方性商業逐漸被大型連鎖高檔門店替代的現象。
在以西方思想和經驗為主導的士紳化研究背景下,中國的士紳化研究也提供了新的案例證據。中國士紳化的本土特殊性包括發生區域復雜性、發生方式多元化、郊區化與士紳化時空共存性等。南京和上海的商業紳士化研究尤為突出,既發現多業態并存路徑等傳統問題,也提出中國商業士紳化動力復雜性、士紳化與全球化之關系等新問題。
三、城市玉林的誕生
玉林的第一次更新歷程,也是玉林的城市化過程。玉林最初是農村耕地,白日舉目皆是農田瓦舍,夜里只有鶯飛蛙鳴。新中國成立后的成都政府將環繞城區的近郊農村設立為金牛區,而玉林最初便被劃歸在其中。
直到我國進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渡期,成都市修訂了城市總體規劃:“強調城市功能的完善,確立了環狀加放射的城市路網格局,形成單中心的城市結構,其主導思想是控制城市規模和完善城市基礎設施,”于是,20世紀80年代的玉林開始迎來國有企業及其單位宿舍的進駐,中房集團也在玉林修建其玉林小區、玉林橫街花園等,樓房、街道便開始代替玉林的耕地,使得“早期的城市玉林”初具形態,在1986年被歸入了原東城區。到了90年代中期,倪家橋以南至二環路的“南片區”也陸續結束城市化建設,標志著玉林城市化的完成,也意味著成都郊區城市化的部分實現。[4]
本屆展覽仍由四大版塊組成:西部人畫西部、學術邀請展、團體邀請展及高原論壇。西部人畫西部版塊得到了全國范圍特別是西部省份藝術家的響應。主辦單位組織資深專家對應征的油畫、雕塑1200余件作品,進行了嚴格的初評及復評工作,最終共入選作品351件,其中油畫283件、獲獎41件,雕塑68件、獲獎24件。總體數量、質量高于往屆,尤其是本屆首次征集的雕塑作品,幾乎均出于專業藝術家之手,其作品質量之高,具備了全國專業雕塑展覽的水準。陜西美博精選出3件獲獎雕塑作品放大落地,展出期間安放在館大門前適當位置,此舉為展覽營造了濃郁的藝術氣氛,引起觀眾對雕塑藝術濃厚的興趣。
在這一過程中,玉林的老成都氣息和文化藝術底蘊被奠定下來。
其一,老成都的城市記憶和生活方式在這片土地生根發芽。駐扎玉林的成都市乳品公司曾是成都唯一的生奶集中消毒單位,養活了幾代成都人,被市民親切地稱呼為“奶管部”,是老成都人記憶中最難忘的地方之一。[5]而玉林占道農貿市場更是曾成為成都最大的占道農貿市場,大大小小的攤點參差錯落,以豐富多樣的農產品給養了玉林小區的數萬居民。每日的市場里,吆喝聲、鳴笛聲、炒菜噼啪聲此起彼伏,直至夜里11點仍是燈火通明,熙熙攘攘。不僅如此,90年代末的玉林西路和玉林東路更是開滿了飯店,每到飯點,馬路上便支滿桌椅,人們就坐在人行道上吃飯,行人在其間穿行。玉林的市井味與煙火氣,就是在那個時候醞釀起來。
其二,文化與藝術融入了玉林人的生活之中。一方面,玉林儼然成了藝術家的客廳,沙子堰的大板房聚集起了大批畫家,住在玉林的翟永明又號召起眾多詩人。藝術家們常常下午畫畫,傍晚吃火鍋,夜里便去小酒館聚會,翟永明的白夜則聚集著談天說地的文人,到深夜里聚會的桌子加長到了墻角又轉彎。另一方面,玉林轄區文化協會積極深入社區,舉辦“壩壩電影”等活動,而玉林生活廣場的音樂房子和玉林西路的小酒館將音樂與大眾聯結起來,孕育出了眾多國內知名音樂人。在那時的玉林,文化藝術與市井煙火就是以消弭界限的方式共融并存著。
四、玉林的士紳化轉型
20世紀初,藝術家們因為生活和藝術的需要逐漸搬出玉林。2010年,玉林曾嘗試打造服裝一條街,火熱一時,然而2010年電商的興起奪走了大量市場份額,使得玉林西路的服裝店慢慢走向關張。同時,2010年后的成都城市規劃也發生了轉變,城市產業結構開始轉向多領域共同發展,于是雨后春筍般的新酒吧開始分走玉林的人流。漸漸地,小酒館將演出搬到了芳沁店,白夜搬去了寬窄巷子,老酒館也停止對外營業,曾經乘著改革浪潮而熱火朝天的玉林也就走入了衰落的時期。這一興衰的歷程,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的演化結果。新的城市化比舊的城市化更能吸引大眾,而如何從中破局,是所有走入衰落的老街區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2017年,趙雷的一曲《成都》偶然將玉林再度推入大眾的視野,2021年,玉林特色商業街區正式開街,玉林實現了士紳化的轉身。值得注意的是,玉林的士紳化并不是借助逆城市化帶來的城市空心化而發生的。玉林的新生看似存在一定機緣的巧合,但實則是持續的善意與持久的關切所結出的累累碩果。一方面,玉林的城市更新從未止步,始終等候著玉林再受矚目的那一刻,另一方面,若沒有當年小酒館老板唐蕾對獨立音樂人的滿懷善意,就不會有趙雷充滿感慨的這么一曲。玉林的城市更新,是宏觀力量與個體意志共同塑造的結果。
在文化藝術方面,成都銀杏文化節于2010年在玉林錦繡巷開幕,既為錦繡巷帶來了人氣,又為其注入了銀杏文化底蘊。2018年,院子文化創意園誕生了,它是成都第一個與社區融合的文創園區,由玉林街道邀請小酒館主理人史雷共同創辦。一年一度的國際唱片店日、各類文化藝術市集在這里輪番舉辦,既延續了小酒館關愛小眾的文化精神,又進一步將獨立創作者、獨立商戶與社區聯結起來,幫助玉林的社區力量和社會力量形成了一種“血與肉的關系”。
在社區打造方面,2009年的《芳草轄區更新策劃方案》將歸屬高新區的芳草街道更新為“數字生活社區”,旨在通過互聯網、數字化技術完成街區更新。2019年,成都開啟了社區改造計劃,主題是“各美其美”“一社一品”。到了2020年8月,成都市政府又聚焦一環路環線,開始打造包括玉林在內的“市井生活圈”,融合生態、生產、生活,通過局部提升、口袋公園、立面提升實現城市微更新,通過業態更新、街道空間、慢行體系提升街巷活力。2021年11月,成都市推出《成都市“中優”區域城市有機更新總體規劃》,于是,玉林四巷六號的老舊房屋被改造為“愛轉角”文創街區,老舊的蓓蕾社區里打造出了還原老成都生活場景的火燒堰巷碧翠廊,為步行、自行車、公交車服務的慢行系統也得到進一步更新。不僅如此,老舊小區加裝電梯工程也陸續啟動,社區養老服務中心逐漸完善。可以說,在商業士紳化的進程中,玉林從未丟棄生活居住區的本位功能。
另一方面,具備文化敏感性的獨立商戶、擁有獨特審美偏好的中青年消費者也參與到了玉林士紳化景觀的塑造之中。布迪厄認為,品味是個體習性在實踐活動中的具體表現,具有等級區分的性質,實際上是“文化資本”的外在表現。[6]在玉林,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彰顯文化與品位的趣味符號,比如消費者的入時妝發、配飾、大牌衣帽,店內陳列的爵士樂黑膠唱片、老電影碟片、文史哲書籍等,當然,街巷里林立的咖啡店、精釀酒館、古著商店更是構成了一種文化符號集合體,它們都參與塑造了今天玉林的文化氣質。
然而,人們在玉林這一場域中展演的“慣習”卻又呈現出一種復雜性,在玉林的精品咖啡店坐了一下午的年輕人,下一站或許就是街頭巷尾的蒼蠅館子。同樣地,許多商戶也樂于成為玉林市井的一部分。玉林的商業景觀變遷并不完全符合商業士紳化中的零售紳士化的定義,新興的獨立商店并沒有替代原本的傳統商戶,而是實現了和諧的共存。這種“共存”不僅是指在麻將館、按摩店和咖啡店、書店能在空間上比肩排列,還意味著雙方在文化內核里實現了交融并存,比如玉林的獨立咖啡店樂于使用老成都特色的木制桌椅,甚至在空間設計上模仿老成都茶館的院落。更重要的是,新玉林人在生活理念上繼承了老成都充滿煙火氣的文化氣質,比如彩虹街的青年組織“海浪公社”專注于社區營造和城市更新,嘗試鏈接政府、居民和文化創作者三方,期望讓更多人了解到社區與人之間的緊密關系。事實上,包容性早就扎根在玉林的文化基因里,今天玉林的文化書店通過讀書會將城市里的高級知識分子與熱愛閱讀的大眾聯結起來,三三兩兩的文學青年會坐在書店門口讀書、飲酒、彈琴,恰恰是20世紀末玉林小酒館、白夜情狀的另一種演繹。
此外,作為“語境”的玉林“鄰里”也塑造著玉林的“語境”。社區巷口烤蛋烘糕的奶奶就住在社區里,和自己兒媳婦換班擺攤,酒吧門口售賣鹵味的叔叔也住在玉林,妻兒常常前來看望,不僅如此,部分新興獨立商鋪的店主本身便是玉林多年的住戶,他們過去在別處謀生,又順著時代的潮流返回故地。也就是說,玉林社群自身作為一種語境組成了玉林的煙火氣、市井味,同時,玉林社群本身也在歷史變遷中創造著語境、重塑著自己所生活的這方土地。
總的來說,玉林的商業士紳化帶來的不僅僅是景觀的改變,更有深層社區力量和社會力量的進一步緊密聯結。在對生產段和消費端的雙重關照中,我們可以看到玉林士紳化所帶來的正是“人”和生活的回歸。
結語
簡·雅各布斯認為,真正讓街區可愛且充滿活力的是持續的自我更新。回顧過去的四十年,從城市化到士紳化,玉林從未停止自我更新的步伐。玉林的更新歷程,可以被看作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的一個縮影。玉林經歷了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城市化紅利,走過了城市化進程中的淘汰與衰敗,并最終在存量更新的時代趨向中通過本土化的更新實現了轉型與升級。玉林的更新模式,為中國特色城市化提供了一種個案經驗。
同時,正如曾作為玉林老居民的畫家何多苓所認為的那樣,“如今玉林的形態,是與玉林的原住民同時生長起來的,而不是后來硬插進去的東西,這即是它的可貴之處。”玉林的城市化與士紳化形成了一條深邃而連貫的脈絡,內里是老成都文化充滿人文關懷與市井煙火的細密紋理,這種本土地方化的特質也使得玉林的城市更新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意義的士紳化內涵,為中國城市的士紳化研究話語體系及中國城市的士紳化進程研究提供了一種都市民族志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