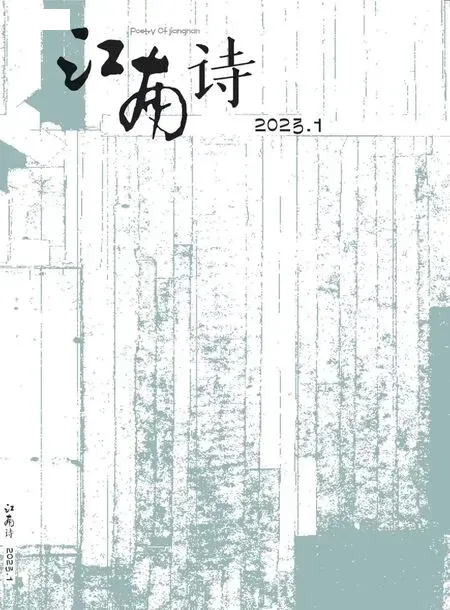南歌子與萊茵河(十一首)
◎張文斌
外 婆
七十歲那年,珊溪水庫攔壩蓄水
你放下小鋤和藤藍
以移民的身份,到陌生的地方安家
你的七十年,是山風吹過水面,驚起連綿的漣漪
最終消逝
你的記憶反復傾倒出起伏的山巒
那個世襲的小小村落
溪水和瀑布互稱親戚
祖屋前似乎還掛著魚網
疏煙淡月,子規聲斷
你習慣在嬌慣多年的溪流里
捉魚、浣紗和沐浴
中風以后,你寡言少語
消瘦枯槁,一枚細弱的燈芯于油燈之上飄搖
你已經無法站立,望一望
那些窗外的鳥
正飛越山頭
替你察看長松巨石、回溪斷崖和峰頂山腳
許多年前,風水先生為你選好的
那塊后山墳地,已埋在水底
誰也不知道,你的夢里
都是水聲不息
舊屋圓洞床舊壁上的一對鴛鴦
停在你二十歲的枕旁
它們的羽毛,絢爛如初
黃坦芥菜
一棵芥菜,與我擁有一樣的戶籍
它的根,長在黃坦
長在青悠悠的田頭里
它與我身懷相似的秘密
在排列整齊的土地上
最初看到松針上的露水滴落
倒映著戴勝鳥的鳴叫
后來,遠離鄉村,遵循排列好的秩序
一葉障目虛度此生
在鋪滿陽光的田野中
反復儲藏著風聲和雨露
曾經與菜粉蝶竊竊私語
和家雀耳鬢廝磨
那些泡菜壇子 多么耐心地等待
在新折的傷口上撒上鹽
抖動的碎葉卻什么也沒說
陷入壇中無邊的寂靜
山岔口偶遇
再次站在山路的岔口
有過剎那間的恍惚
想象著當時你迎面走來的情景
不知你居住的山村離這里有多遠
如果我是山神,我就一定知道你在哪里
山月照臨,蟲鳴響起
夢像一面鏡子
時常能照醒你的嬌容
那岔口,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
偶遇,是一種告別
如一條小魚在溪水里
撞上一朵寂寞的云影
偶遇,往往是自己一手制造痛苦
又不斷被痛苦折磨的起始
掛 念
山霧時而繚繞,時而散盡
水云寺的寒磬,聲聲傳遠
汽車顧自走在盤山公路
我胸前喂養的虎嘯重回山林
山口的風翻動整個夜晚
星星在寂靜的山谷中
照亮自身卻彼此不相識
雨季漫漫
山路上的藤蔓,不斷伸長分枝
將我緊緊纏繞,快要窒息
葉子上掛滿了水珠
雨水秘密地收藏我一生的雜草和泥濘
墻上秋草搖曳
一陣風吹過來了,村莊的方向
像抬頭可見的白云
在我的凝望里,仿佛觸手可及
又漸漸遠去
水云峰
它放慢了我的記憶
我的繁華和荒涼皆于此地升起
黑麂、黃腹角雉、獼猴、穿山甲
臨溪照見了自己的模樣
我走過的每一道山脊,留下了它們覓食和繁衍的印跡
甜楮、木荷、青栲、杜英、紅楠
保持著喬木的形象,知道一切所愛
都化為黑土
山風撫摸著每一個季節,說出成長
牽牛花、蒲公英、狗尾巴草
青苔緊貼著巖石,不肯泄露我的乳名
南 窗
水云峰腳下,我獨自一人坐在南窗
玉米飽滿的額角沒有哀愁
身為鄉村教師的父母
總是囑咐我苦讀詩書
讓讀過的書壘成石路
通往山外的云嶺
我的目光撫摸著云嶺山田
耕者戴笠披蓑,犁頭挖開新的隱秘和春天
臨溪瓦舍
犬兒佇立,紅衣樵女負柴而歸
童年的鐵環滾動著天空的白云
我只在村角,保留著一個側影
要穿著青山的大鞋
步入河流,像出爐的鋼水
等待新的模型
山 外
從童年到少年
主峰、側峰、山坡、溝谷
溪巖突兀,樹苔深染,嶺壑崖梁
幾至閉目能詳。聽大人講
水云峰背面,下了山便是
另一個世界
唯有蒼鷹,在晚暮中
銜著我的心事,扶搖而去
十七歲那年夏天,我背起行囊
沿著崎嶇的高嶺
頭一回翻過了水云峰
站在際坳塘山口,松濤陣陣
山風吹起求學的衣襟
我身后龐大的隊伍
是太陽編織的光線
遙遠的事物
農家瓦房,屋檐下的柴禾
散亂擺放
凋零的植物,燃起火熱的灶膛
沿著灰燼的道路
村居的日子在慢慢熄滅的火星中
又燒開了新一天的糧食
門前的小池塘
雀鳥翻飛于水面
飛得再遠
也只是和影子的一次較量
它們會飛回水面,在臨死之前
點出轉瞬即逝的波痕
柏林的早晨
施普雷河畔,晨曦
是二戰的血獸
草尖上有許多游魂的無字淚水
一只起早過路的蝸牛,忘記了往昔
從路的這一側到另一側
一場長途跋涉,伴隨著
不可控的風險
一群金發女子離河很近
看不出水面上那張濕漉漉的臉
她們騎車疾行,看見我被驚嚇的樣子
開懷大笑。作為一個來自文明古國的洋人
相逢即是緣分,應該保持風度
岸邊有一老者在垂釣
時間在狩獵,幸存也是一種煎熬
沃爾多夫小鎮
海德堡南十五公里,內卡爾縣
的一個小鎮。晚上九點多了
天色依然很亮
雷陣雨后的小鎮,異常冷清
彼此的房子都很相似
屋前房后的各式植物
修剪很整齊,像前額的留海
毗鄰的法蘭克福機場上空
時見沖天的飛機,這是對夜空反復的傷害
路邊一段護墻上
爬滿老樹的根莖
仿若千年老巫婆的手
這里路人罕見
偶爾幾聲夜鳥鳴叫的聲音
令人揪心,也叫醒了我心中的故鄉
再見了,法蘭克福
又下雨了,望著萊茵河水
穿城而過,越走越遠
我知道,回去的時候來到了
再見,萊茵河
我不是藍天上的白云
可以在你懷里云舒云卷
我不是河里的三文魚
可以溯河洄游
再見了,萊茵河畔
那葡萄架下的晚餐
酸菜酸到骨子里
現在仍然倒吸冷氣
那么大的豬手
被西餐刀一層層削去
只剩下骨頭,我不禁想起
三十年前初次上解剖課時的情形
我強忍反胃,想到筷子的諸多好處
再見了,公路兩側的田園
那大片金黃的麥田
長勢喜人的玉米和馬鈴薯
還有散落在田野上的草垛
這萬畝良田我捎帶不走
再見了,沃爾多夫小鎮
這座沉寂內斂的小鎮
夕陽,要到晚上十點才肯離去
家家戶戶窗臺上的花
都是開給別人看的
鳶尾、含笑花、麒麟花和大花曼陀羅
一半以上的祖籍
都來自中國
在這里,我見到了從波恩
趕來,多年未見的外甥和
他的孩子們,他們是一群香蕉人
他們能講不太流利的漢語
卻連錯別字都不會寫
再見了,小鎮南邊那片大森林
我每天在這里晨跑
跑遠了常常迷路
橡樹、冷杉、白樺樹
以及腎蕨、九重葛
還有許多叫不出名的灌木
喬木和草本植物
四處蔓生的咸豐草
一個皇帝的尊名
在這里與野草組成了現實主義
矢車菊,德國的國花
沿著溪流的兩岸,一直開下去
淡藍色、淡紅色和白色
我唯獨喜歡紫色
我在這片陌生的森林里
沒有榮幸,遇見浣熊或者石豹
卻能清晰聽見
松果掉落的聲音
我會常常走神
想起老家的無邊松林
和那些熟識的松鼠們
再見了,法蘭克福大教堂
再見了,法蘭克福電視塔
飛機正在升空
我無法與你們一一辭別
只能用帶著黃坦泥土氣息的方言
與你們說聲
“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