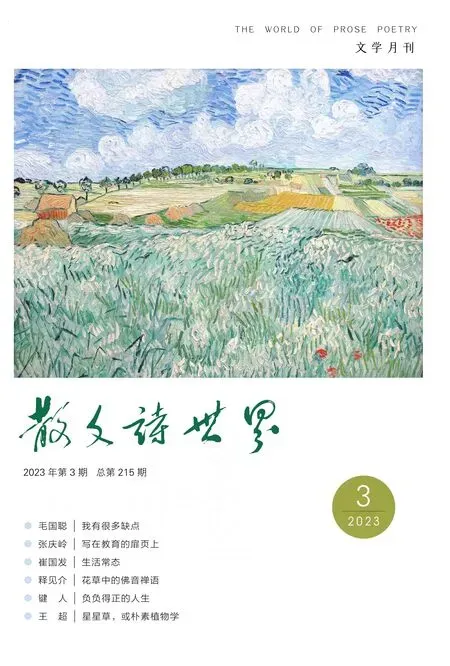十二生肖或動物自白選章
鄭勁松(重慶)
之5:龍
在這個光榮的生肖榜上,我排名居中,但影響最大。因為曾經,在這個國度兩千年間,我象征著至高無上。
最神圣最神秘,也就最虛無,我是唯一一個沒有存在的存在。因為誰也沒有真正見過我,甚至沒誰能將我準確刻畫。比如,那個著名的葉公,當我真從宣紙上現形,他代表的人類早已魄散魂飛。
都說我能呼風喚雨飛沙走石,能大能小,能升能降。小則隱藏真跡,大則吐霧生云。升則飛騰太空之間,降則潛伏波濤之內。這同樣只是傳說,只是人類在為某種目的制造合理的想象。
其實,我都沒見過我,只是在人類那里,見到我的頭像牛而且有角,像鹿;我也有兇惡的嘴臉,鱷魚似的,有鱗甲保護皮肉,還有須,像蝦。因為要我飛我就飛,我也有腳,像天空的鷹。
我明白,我只是各種利益的組合,卻唯獨沒有自己,哪怕一根胡須。但那種氣度與精神,已被一個民族注冊。傳說我與鳳不是一般的親密,一起呈現某種需要的吉祥,或者權力與意志。可鳳就是風啊,一直無象無形。
回到這個生肖榜上,疑竇叢生。我是否誕生于一個古老的謊言,或者更古老的夢境?我比誰都高高在上,可天地之間,我始終見首不見尾。
偉大很久了,我就感到孤獨和疲憊,沒有存在感,如此空虛。我只在風里,在水中,在云之上,在縹緲之間,在意識之內。沒有歷史,也就沒有現實與未來。
出身過于高貴,我只能保持騰云駕霧的姿勢,永遠呆在神秘的祭壇上,所有的笑容都張牙舞爪,連同這個民族永遠朦朧的記憶。
之7:馬
只有我敢和不存在的龍,正面地站在一起,成為一種昂揚的精神。這也是被人駕馭的無奈,掠奪或追逐他們的江山,還有美女。
客觀地講,我應該屬于英雄與戰爭,我喜歡卷起塵土中的那些刀光劍影。要么在萬馬奔騰的歷史上對著西風嘶鳴,要么在萬馬齊喑的時代,暗自垂淚。
大多時候,人們騎在我的背上,打下江山,就會把我放逐南山。南山很美,有青草,青草香甜。我喜歡這樣的歸宿。我的故鄉始終在山林水草之間,把我遺忘,正是我的心愿。我從草原來,從來沒有改變吃草的習慣。只是吃著青草,我還忘不了抬頭張望。想在燦爛的云朵間, 尋找戰爭年代踏過的塵土、旗幟和鮮血。
偶爾,我也看到有一些兄弟從漢唐時代趕過來,背上駝著一個王朝,顯赫的鈴聲在沙漠深處,畫一條被絲綢命名的道路,很冷很熱很荒涼。一堆堆白骨埋在沙中。我知道,年代久遠的夢想一旦被狂風吹醒,就會痛徹心扉。
當然,與龍比,我更真實。人們把我們化作一種精神,與牛比,我更聰明。雖然牛頭一般不對馬嘴,當你一旦與我的眼睛對視,就會看到濕潤的哀傷。所謂牛馬不如,那不只是人的喟嘆,我感慨的是:不知猴年馬月,四季不再往返,始終暖如春天。
作為一匹功能喪失的老馬,幸好,我還能識得歸途。跟著青草露珠,還有咸陽古道,回到風馬牛不相及的遠方,隱居一萬年。
之11:狗
都說我是人類忠實的朋友,可我的忠誠如此卑微,不是搖尾乞憐就是依仗人勢。
請不要再說狗眼看人低,那是因為人類高高在上,以貌取人。很多時候,我只是人類隨機的借口,脫口而出的詞匯,把人類的丑強加我身。
一只狗也有著深刻的鄉愁,很多時候,我都十分懷念故鄉,懷念那些帶著方言的狂吠,在房前屋后,在河灘在山梁,我曾經像一個忠勇的戰士。
而今大多數的狗,來到城市或來自城市。有很多好看的品種,只是一種會動的玩具。當然,狗的地位大大提升,甚至超過人類。
好多人都開始像狗了,我們也開始像人。
之12:豬
很多時候,排名第一與最后,沒有本質區別。如同我在生肖榜上倒數第一,卻和人類最為親密。你看漢字的“家”,是不是全靠我的支撐。
當然,作為老百姓的盤中餐,我一直親切而珍貴。特別是臨近春節,以殺我作為引子,最濃烈的年味在我的血腥中傳遞,這是其他動物沒有的死亡儀式,或者說它們沒有的神圣的幸運。
我的全身,包括血液與皮毛,都在奉獻著價值。即使糞便也在供養田園的莊稼,它們還會盛開噴香的花朵,甚至招蜂引蝶,制造甜蜜。
不要罵我好吃懶做,我這點品行,是農人眼里健康的標志。是我和農婦手眼之間幸福的默契。我的成長是她的財富,她的辛酸是我的美味。不,是她看著我和我看到她,都像看到了美味。
與人比,我的一生極其短暫,卻伴著農人的四季。我不是那只特立獨行的豬,也沒有高老莊那頭出身高貴,但也不是飼養場成群結隊的那種。我只在茅檐低小的房間,與農夫知音般相隨。與咳嗽的炊煙、雞鳴、鳥啼,匯成美好的鄉村意境。
我的祖先和人類同在山林,必須記住這種血緣關系, 我只是一頭被老百姓使喚的豬。這是最初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