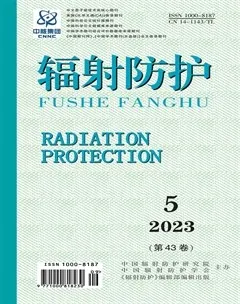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現況調查及影響因素分析
王蒙婷 楊素云 施冰梓



關鍵詞:核醫學;輻射防護;知識;態度;行為
核醫學是現代醫學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核醫學分子影像以及多模態分子影像成為核醫學的前沿和主流,在精準醫學中發揮著重要的支撐和引領作用[1-2]。核醫學在給疾病的治療、診斷以及預后帶來益處的同時,增加了核醫學科醫務人員的輻射接觸,在醫療過程中產生的人工電離輻射,給醫務工作人員帶來了潛在輻射損傷的威脅[3]。有研究表明:不論是接觸大劑量的電離輻射還是長期接觸低劑量的電離輻射均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大劑量電離輻射易造成急性放射損傷,長期接觸低劑量的電離輻射,導致患白血病、皮膚損傷、白內障等風險的增加[4-5],且人體不同組織對輻射敏感性不同[6]。有研究調查核醫學科工作人員的個人輻射劑量數值,明顯高于其他科室工作人員[7],并且從事核醫學工作的醫務人員甲狀腺異常率最高[8]。雖然關于電離輻射對人體危害的相關研究較多[9-10],卻未引起相關人員重視。核醫學科醫務人員的輻射防護知識的掌握程度、態度和行為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自身的安全,所以,調查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現狀,有助于了解臨床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從而為豐富輻射防護培訓內容、規范醫務人員的防護行為提供參考。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于2022年8月—9月,采取便利抽樣的方法,選擇從事核醫學科工作的醫務人員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核醫學科醫務人員;②獲得醫師、醫技、護士執業證書的醫務人員;③自愿參加本次調查研究。排除標準:①從事核醫學科工作年限小于半年的醫務人員;②核醫學科進修醫務人員。
1.2方法
輻射防護知信行調查問卷參考《醫學放射工作人員放射防護培訓規范》(GBZ/T149—2015)[11]、《電離輻射防護與輻射源安全基本標準》(GB18871—2002)[12]及相應文獻資料[13-14]的基礎上自行設計。通過線上及線下發放輻射防護知信行問卷,本次共發放問卷130份,回收問卷125份,兩份問卷不符合納入標準需剔除,最終有效問卷為123份,有效回收率為94.62%。該問卷分為4個部分:(1)一般資料調查。包括:年齡、性別、職務、工作年限、文化程度和職稱等;(2)輻射防護知識。包括基礎知識、輻射危害知識、法律法規等;(3)輻射防護態度。包括輻射防護培訓的參與、穿戴輻射防護用品的必要性等;(4)輻射防護行為。包括個人劑量計佩戴情況、職業健康檢查情況、輻射防護用具使用情況等。其中輻射防護知識共26題,每題正確得1分,錯誤不得分,多選題多選、錯選、漏選均不得分,滿分為26分,得分越高說明知識掌握情況越好;輻射防護態度及行為條目總分分別為7~21分和6~18分。最后轉為百分制計算,百分制分=(實際得分/總分)×100,百分制得分<60為差,60~90為良好(中等),>90為優秀(60分為及格分),輻射防護知信行問卷得分越高說明輻射防護知識掌握程度越高,態度、行為越積極。
1.3統計學處理
采用EXCEL軟件進行數據錄入,SPSS25.0版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定性資料以頻數及百分比(%)表示,符合正態分布的定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單因素分析采用t檢驗、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態分布的定量資料采用中位數(M)和四分位數(P25,P75)表示,單因素分析采用非參數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調查對象一般資料
123名醫務人員男性49人,女性74人;醫生37人,醫技38人,護士44人;大專及以下4人,本科72人,碩士研究生及以上47人;初級職稱40人,中級職稱59人,高級職稱24人;有子女的84人,沒有子女的39人,三甲醫院醫務人員113人,非三甲醫院醫務人員10人,詳細情況見表1。
2.2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識、態度和行為得分情況
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問卷總得分[M(P25,P75)]為76.92(70.77,83.08),知識得分57.69(50.00,69.23),態度得分95.24(80.95,100),行為得分83.33(72.22,100)。
2.3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識得分情況
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識正確率較低的知識題為:必備的輻射防護用品、核醫學放射性工作場所劃分、對輻射高度敏感的組織或器官、在事故應急和處置現場個人劑量的監測要求、《核醫學輻射防護與安全要求》發布時間、軔致輻射,正確率分別為5.69%、12.20%、20.33%、34.15%、34.96%、34.96%;正確率較高的知識題為:輻射的本質、輻射防護目的、核醫學實踐中的放射線來源、輻射事故上報時間、放射性核素噴濺時處理措施,正確率分別為98.37%、95.12%、89.43%、82.11%、78.86%,詳見表2。
核醫學科醫務人員對于輻射防護知識中輻射防護的法律法規以及輻射危害知識的正確率不足50%,分別為45.85%和47.80%,對于輻射防護的基礎知識、防護知識、應急知識知曉情況在60%以上,詳見表3。
2.4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態度得分情況
核醫學科醫務人員在輻射防護態度方面,其中69.92%會主動告知受檢者輻射危害,73.98%會特別關注孕、幼等人群的輻射防護,82.11%會在在崗期間定期參加輻射防護培訓課程,76.42%會通過其他途徑主動學習輻射防護的相關標準、指南和文獻,78.86%認為輻射防護在日常醫療診療過程中重要,73.17%認為有必要規范穿戴防護用品,87.80%認為進行輻射防護培訓有必要,詳見表4。
2.5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行為得分情況
核醫學科醫務人員在輻射防護行為方面,其中78.05%會在工作時佩戴個人劑量計,59.35%會關注個人劑量計的劑量監測結果,80.49%會穿戴輻射防護用具,63.41%會在工作中遵循輻射防護的規章制度、流程,50.41%會在工作中對患者的輻射劑量有所關注,50.41%會定期進行職業健康檢查,詳見表5。
2.6不同特征的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得分比較
對收集的數據進行秩和檢驗等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年齡、職稱、核醫學科工作年限、是否有子女以及是否定期參與輻射防護培訓為影響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的因素,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6。
2.7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以輻射防護知信行問卷得分總分為因變量,以年齡、職稱、核醫學科工作年限、是否有子女、是否參加輻射防護培訓/教育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是否有子女和是否參加輻射防護培訓/教育是輻射防護知信行的影響因素,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7和表8。
3討論
核醫學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讓大眾受益,人們可以得到準確的診斷結果以及精準的治療,但是醫務人員長期接觸低劑量電離輻射的問題也不能被忽略。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15]明確提出,在各種有害的化學、物理和生物等職業危害因素中,放射線是三大類重點職業危害之一。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AtomicEnergyAgency,IAEA)提出了要建設輻射防護安全文化理念,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RadiologicalProtection,ICRP)已經將輻射防護發展為一個原則體系,輻射損傷越來越受到國家、社會、人群的廣泛關注。醫療照射雖被歸為低劑量輻射,但目前尚缺乏最低輻射劑量標準的規定[16]。國內現行的《核醫學放射防護要求》(GBZ120—2020)[17]中提到應保障放射工作人員、患者或受檢者以及公眾的放射防護安全與健康,對工作人員所受的職業照射應加以限制,使其符合GB18871—2002職業照射劑量限值的規定,應對任何工作人員的職業照射水平進行控制,使之不超過下述限值:連續5年的年平均有效劑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不超過20mSv;任何1年中的有效劑量不超過50mSv;眼晶體的年當量劑量不超過150mSv;四肢(手和足)或皮膚的年當量劑量不超過500mSv。
“知信行”模式以心理學為基礎,由刺激理論和認知理論綜合形成,是一種人類健康相關行為的模式[18],通過知識獲取、信念產生、行為形成三個連續的過程促進人們健康行為的改變[19]。基于此,運用“知信行”模式,了解核醫學科醫務人員的輻射防護知識、態度和行為水平,可更好的促進核醫學醫務人員對輻射防護的認識,提高輻射防護意識。
3.1輻射防護知信行現狀分析
核醫學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問卷總分處于中等分數,但是輻射防護知識的及格率僅為45.53%,人數不達半數,知識題最低的正確率僅為5.69%,正確率不足60%的知識題占總知識題的46.15%,對于較為基礎但卻重要的內容正確率相對較低。輻射防護危害知識、法律法規的正確率相對較低,即使是從事輻射相關工作的專業醫務人員,對于輻射防護的法律法規、危害知識的掌握也不夠全面。醫務人員輻射防護態度以及行為得分明顯高于知識得分,這與國內外的研究結果一致[20-21]。由于輻射危害直接關系到自身,所以醫務人員在態度及行為上會更重視輻射防護。態度得分高于行為得分,醫務人員態度較為積極,但是在行為的某些方面,醫務人員重視程度低,例如只有一半的醫務人員關注個人劑量計的監測結果及會定期進行職業健康檢查。張露[22]研究發現有48.2%從事放射工作的醫務人員不知道個人劑量的監測結果,在知曉自己個人劑量監測結果的人中,有19.5%的人出現個人劑量的異常。郭瑋珍等[23]對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區的放射診療工作人員的個人劑量進行監測分析,結果顯示個人劑量監測異常檢出率較高。在對2020年全國醫療機構放射工作人員放射診療工作人員的個人劑量監測中,發現最常見原因為醫務人員不正確佩戴或使用個人劑量計,將劑量計留于放射場所[24]。由此可見,核醫學醫務人員對于個人劑量監測值缺乏關注,甚至不常佩戴個人劑量計。有研究發現,在對核醫學科及相關醫務人員進行健康檢查時,發現相關人員血象、淋巴細胞微核率等的異常變化,說明我國核醫學醫務人員存在輻射防護意識及行為不足的情況[3]。使用輻射防護設備是降低工作中輻射劑量的有效方式,從事核醫學工作的醫務人員應正確使用個人防護設備,關注個人劑量計監測結果,定期進行職業健康檢查,從而了解輻射接觸情況;相關單位應增加輻射防護設備的種類和數量,及時維護輻射防護設備,加強對個人劑量監測工作的管理,提高輻射監測工作的監管質量。
3.2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影響因素分析
3.2.1是否有子女
是否有子女是輻射防護知信行總分的影響因素之一,有子女的醫務人員相比沒有子女的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得分更高,可能原因是這些醫務人員有著孕育子女的責任,出于對孩子安全的考慮,人們往往會更重視輻射防護。女性是輻射效應的易傷人群[25],尤其是對于孕期女性來說,胚胎組織屬于對輻射高度敏感的組織,孕期女性如果長期處于電離輻射環境中,發生胚胎死亡、孕育畸胎、流產的可能性高于正常人群[26],所以,為了子女的健康考慮,女性不論是在輻射防護知識的學習上,還是態度和行為的實踐中,都會更加規范。
3.2.2是否定期參加輻射防護培訓/教育
是否定期參加輻射防護培訓/教育也是影響輻射防護知信行總分的因素,定期參加輻射防護培訓的醫務人員知信行得分高于沒有定期參加輻射防護培訓的醫務人員。可見在知信行模式中,知識是改變行為的基礎,較全面的輻射防護知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防護意識和防護行為,強化輻射防護知識的學習和教育對健康行為的形成意義重大。郝欣欣等[27]分析了放射診療工作人員在放射防護培訓前后知識、態度和行為的變化,通過放射防護培訓,放射防護知識知曉情況得分的提升對總平均得分的提升影響最大。歐盟委員會、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等[28-29]相關組織和機構也發布指南,強調需要對醫務人員進行輻射防護方面的教育和培訓。我國法律法規規定從事放射性工作的人員在崗前及在崗期間需要進行放射防護培訓,同時包括法律法規知識的培訓[30-31],并且《國家職業病防治規劃(2021—2025年)要求重點人群職業健康知識知曉率≥85%[32],輻射防護培訓是一個持續的過程[33]。在對西安市醫療機構214名放射科醫護人員的調查中,發現部分醫院的工作人員缺乏對輻射危害的認識,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醫院重視經濟效益和工作效率,忽視輻射防護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和醫務人員自身的綜合素質有關[34]。相關部門和單位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認真履行監管職能,從而保障從事放射性工作人員的職業安全。同時,朱衛國等[35]對我國非醫療放射工作單位輻射防護現狀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非醫療放射工作單位的輻射防護現狀與國家法規標準的要求尚有差距。非醫療放射工作單位也應積極定期開展相關輻射防護培訓和教育,對提高醫務人員的輻射防護意識具有積極意義。有相關研究調查醫學生對輻射防護相關知識的認知情況,結果表明醫學生對電離輻射的認知水平偏低[36],應將輻射安全內容納入學生課程里,促使學生形成對待電離輻射的正確態度,形成輻射防護的意識。
年齡、職稱、工作年限不是輻射防護知信行總分的影響因素,這與國外先前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37]。究其原因可能是職稱越高的醫務人員工作壓力及強度大;隨著年齡的增長,伴隨工作年限的增加,出現了職業緊張和職業倦怠感[22],醫務人員長期處于輻射暴露的環境,加重了醫務人員的心理負擔。在臨床工作中,醫療機構不僅需要關注醫務工作者的職業健康行為,還需要重視這類人群的心理健康,對于心理狀況不佳的醫務人員,需要采取心理干預。
4小結
綜上所述,核醫學科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知信行問卷總分良好,態度和行為較為積極,但輻射防護知識掌握不足。從事核醫學工作的醫務人員不可避免地接觸低劑量的電離輻射,但可以通過輻射防護相關措施來防止輻射產生的確定性效應的發生,將隨機效應的發生率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這需要相關衛生行政部門做好輻射防護培訓工作,采取多途徑多樣化的培訓方式,讓醫務人員潛移默化地形成正確的輻射防護態度,采取正確的防護行為;醫院及科室應加大對醫務人員輻射防護培訓及管理的力度,積極開展核醫學醫務人員的繼續教育,同時增加輻射防護設備的配置,定期對輻射防護設備的防護效果進行檢測,創造安全的醫療環境。輻射防護是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任務,一定要堅持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強化醫務人員輻射防護的認知,使其具備正確的態度和行為。醫務人員應做好自身輻射防護,遵守工作流程及規章制度,在工作中盡可能的減少輻射暴露,提高輻射防護的質量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