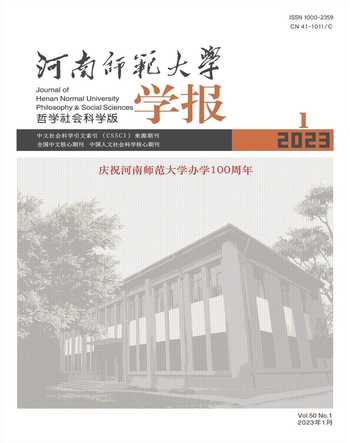光緒年間瞻對事件中成都將軍與川督之間的權力斗爭
王川 吳艾坪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3.01.11
摘要:乾隆年間,在清廷綏定大小金川戰役后,特設成都將軍一職,并賦予其重權,由此開啟川督、將軍共治川省的政治結構。乾嘉之際,二者能夠在政務和戰事中積極配合,為鞏固西南邊疆的統治發揮了作用。隨著國家承平日久,成都滿營的戰力亦日漸衰頹,加之將軍與川督在職權劃分上的模糊,以致在川省政務運作中川督逐漸勢大。光緒年間,川督鹿傳霖和成都將軍恭壽圍繞著瞻對改土歸流一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背后牽涉出清廷中央與西南諸省各官員之間的諸多斗爭。
關鍵詞:成都將軍;四川總督;瞻對;互相掣肘
中圖分類號:K2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359(2023)01-0079-07收稿日期:2022-01-10
成都將軍全稱為“鎮守成都等處地方將軍”,是為清廷最后一處設立的駐防將軍,亦是清廷在西南地區唯一設立的駐防將軍。自設立之初,清廷就賦予其職掌民族地區政務的重權。乾隆曾在諭旨里稱“成都將軍非它省城將軍可比”,更是說明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及地位《大學士阿桂為著速奏聞提審扎克素部落班昭是否拿獲嚴辦事寄信成都將軍明亮等》,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初七,《軍機處全宗滿文檔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18-009-000135-0001-0003。本文所引用的滿文檔案原文,均采用國際通行穆德麟夫(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轉寫法,漢文系自譯。翻譯時主要參照胡增益主編:《新滿漢大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鐘翰等主編:《簡明滿漢辭典》,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羽田亨:《滿和辭典》,國刊書行、Jerry Norman,Comprehensive Manchu-English Diction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年。。
除此之外,隨著成都將軍的設置,川省的政治結構也從以川督為重的“一元”轉為將軍、川督并重的“二元”。在政務運作過程中,二者的通力合作有益于政務的集思廣益,避免一方獨攬大權;另一方面,利用駐防將軍與各地督撫之間互相監視,相互掣肘,是清廷為了保證皇權所采用的一貫權術。同光之際,成都將軍與川督之間就曾出現二者針對某一具體事件而展開相互攻訐的案例。但無論是事件的影響力還是復雜程度皆不及光緒年間川督鹿傳霖與成都將軍恭壽處理瞻對改土歸流一案。
學界對于光緒年間鹿傳霖主持瞻對改土歸流一案已有頗多的學術成果,但學界的關注重點多聚焦于瞻對事件中清廷中樞、瞻對部落及西藏方面。對于此案的關鍵人物——成都將軍在此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及表現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挖掘空間。本文利用滿、漢檔案文獻,以成都將軍為視角,將成都將軍與川督之間的職權劃分與光緒瞻對事件的背景相結合,以期對研究晚清年間川邊民族地區的政治關系、權力斗爭等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鹿傳霖迅速收復瞻對
光緒十七年(1891),恭壽赴川任成都將軍。光緒二十一年(1895),鹿傳霖調川省任總督。作為川省最高級別的兩位官員,二者之間關系甚好,素有“昆弟交”之稱趙心愚,秦和平,王川:《康區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上)》,巴蜀書社,2006年,第39頁。,在此前處理四川民教等案上亦有合作《清德宗實錄》,卷375,光緒二十一年八月甲午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5冊,第906—907頁。,但鹿傳霖對于瞻對問題的處理不當,導致了二者關系的破裂。
瞻對,藏語意為“鐵疙瘩”,因地處川藏南道與北道的交接咽喉,位于康區的中心地帶,素有“康巴肚臍”之稱。該地區地形封閉,部族社會“番”風甚濃,加之受惡劣的地理環境影響,生產力較弱,故該地族民常以“夾壩”“夾壩”,在藏語中乃強盜之意,意為生活在瞻對地區的部落專以搶劫過客行旅財物為生。該處對于瞻對的“夾壩”這樣一種向外獲取資源的方式,是按照部落傳統和習慣從外部世界爭奪生存資源的方式和途徑來理解的。參見石碩《瞻對:小地方、大歷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節點與風云之地》,《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為生,因此對川藏大道的通暢,川邊康區的安穩造成了較大的威脅。自康熙以來,清廷屢次征討該地區亦無實效。同治二年(1863),清廷下旨川藏官兵合剿瞻對,合剿持續兩年,勝利后將該地賜予達賴,自此該地歸于藏屬《清穆宗實錄》,卷163,同治四年十二月乙巳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4冊,第768頁。。但駐瞻的藏方官員在該地施行苛虐暴政,引起當地土司及百姓不滿《清穆宗實錄》,卷282,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乙卯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5冊,第754頁。。加之光緒十四年(1888),清廷與英《藏印條約》簽訂后,達賴又欲借俄國來要挾清廷、英國之勢日益加劇。
鑒于此內憂外患之事態,鹿傳霖初任川督便密奏清廷,稱該地乃川省之門戶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2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302頁。,對英俄覬覦西藏及駐藏大臣在藏政令不通表示憂慮陳家琎、拉巴平措:《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2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2年,第10頁。。后多次在奏折中陳述“近年各土司弱肉強食,不無蠻觸相爭之事,然必其有罪可討,有隙可乘”吳豐培:《清代藏事輯要·續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頁。,“竊惟三瞻之地,南接里塘,為入藏通衢; 北界德格土司,為茶商入藏北路,居眾土司之中,形勢險要”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近代康藏重大事件資料選編》,第1編下,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99—1000頁。等語,謂之清廷瞻對地區之重要性,試圖說服清廷從達賴手上收回瞻對歸于川屬。并提出了一系列涉及改土歸流、通訊建設等方面的“保川圖藏”之策。
學界對于鹿傳霖的改土歸流之策的實施及過程已有共識,在此不再贅述。該策對清廷一直以來在瞻對的“舊癥”而言,不可謂不是一劑良藥。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六月初六日,瞻對地區發生沖突,清廷下旨道:“瞻對番官上年與明正土司越界出兵,經鹿傳霖等將駐瞻僧俗番官先后撤換,經降旨允準乃該革番官并不遵照撤換,近復帶兵越界滋事,干預章谷土司案件。勒令書立投瞻字樣,迨經委員前往切實開導,仍敢玩不遵從,添兵抗拒,藐玩梗頑,形同叛逆,自應懾以兵威,著鹿傳霖即飭羅以禮出關再行開導,曉以利害一面……如若仍執迷不悟,即著厚集兵力妥籌進……惟打箭爐與滇邊相通,該處教民雜處,尤恐集結為患,該督務當穩慎以圖,不可任其越界侵擾,亦不可因此激成邊釁是為至要。”《呈鹿傳霖瞻對番官近復越界滋事辦理情形等折奉旨單》,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初六,《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5728-037。此折原文系漢文。
可見,面對瞻對當地出現的問題,清廷并未采取激進的政策,而是考慮到了民族問題。通過此諭內容亦可看出此前幾次“開導”亦并未奏效《為番民叛藏派員開導情形會折并抄錄》(原件破損),光緒十六年,《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6190-010。此折原文系漢文。。此時,鹿傳霖以“禍機已伏,藏番冥頑倔強,隱有所恃,致有輕藐抗拒情事”為由,向清廷上奏“擬出兵收復三瞻后,議設流官妥籌善,從而以防邊患而固藩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光緒朝上諭檔》,第22冊,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74頁。。鹿傳霖的奏折得到了清廷認可,但清廷對鹿傳霖并不信任,遂派駐藏大臣文海前去與鹿傳霖會同辦理瞻對一案。
值得一提的是,正在清廷對鹿傳霖收復瞻對之策搖擺不定之時,給事中高燮曾上奏清廷中央支持鹿傳霖收復瞻對,他在奏折中寫道:“瞻對關系川藏大局,請飭籌經之策,請添設文武各員移駐打箭爐等處地方。”《奏為給事中高燮曾奏瞻對關系川藏大局請飭籌經久之策等折片奉旨恭呈慈覽事》,光緒二十二年,《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5731-109。此折原文系漢文。此人在后面彈劾成都將軍恭壽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鹿傳霖及川省軍隊的勇猛作戰下,駐瞻藏官被驅逐出川。鑒于此內憂外患之事態,鹿傳霖初任川督便密奏清廷,稱該地乃川省之門戶 王彥威、王亮輯編,李育民等點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5冊,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441頁。,對英俄覬覦西藏及駐藏大臣在藏政令不通表示憂慮。后多次在奏折中陳述“近年各土司弱肉強食,不無蠻觸相爭之事,然必其有罪可討,有隙可乘” 吳豐培:《清代藏事輯要·續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頁。,又有“竊惟三瞻之地,南接里塘,為入藏通衢; 北界德格土司,為茶商入藏北路,居眾土司之中,形勢險要”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4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321頁。等語,向清廷說明瞻對地區之重要性,試圖說服清廷從達賴手上收回瞻對歸于川屬。
二、成都將軍上奏彈劾鹿傳霖
正在鹿傳霖提出一系列涉及改土歸流、通訊建設等方面的“保川圖藏”之策之時,清廷此時態度卻發生變化。清廷擔心鹿傳霖此前所奏將瞻對改設漢官一折,不能攝伏達賴,反而導致藏地不安。清廷認為:若此番進剿得力,則在該地仍設番官,利于從長布置;若進剿失利,“驅番設漢”一策則無從談起《清德宗實錄》,卷395,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兩申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151頁。。故清廷傳諭鹿傳霖,令其以初四日電旨為斷,督飭將士,迅拔瞻巢,以安邊圉;設官一節,則俟后再行斟酌《呈鹿傳霖瞻對番官近復越界滋事辦理情形等折奉旨單》,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初六,《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5728-037。此折原文系漢文。。可見,清廷結合當時情形,借戰事未定而回避了鹿傳霖劃歸該地為“川屬”的建議。清廷如此搖擺不定的態度,間接鼓勵了達賴爭取該地歸為“藏屬”的企圖。加之達賴令駐京堪布將瞻對一事上告理藩院事務都統昆岡,昆岡與雍和宮扎薩克喇嘛羅卜藏曲、福佑寺達喇嘛羅卜藏降養、蔥度寺達喇嘛江曲扎喜等奏:“同治年間工布朗結父子叛亂,經達賴喇嘛自備軍餉征剿平復……伊子與該土司管事頭目人等復糾眾進瞻,多所爭奪,并有槍斃瞻對頭目及拆毀廟宇等事。嗣又至打箭爐賄通軍糧府轉去向四川總督捏詞借兵。該總督派去八營,由土兵引路,進瞻對助戰。守瞻營官聞有天兵,不敢出戰,將頭瞻二瞻一并讓出。帶兵官周萬順威嚇守瞻官堪布等,令速回藏……嗣經四川總督咨駐藏大臣文稱,瞻對地方嗣后即為四川總督所屬,不歸達賴喇嘛所管……將此情由呈報達賴喇嘛,為此冤抑,懇乞代奏,乞恩將瞻對賞還,以安邊服。”《奏為據駐京當差堪布等會同駐京各呼圖克圖等代達賴喇嘛申訴瞻對事宜以明冤抑由》,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軍機處檔折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機”142599。此折原文系漢文。從此折可見,在京呼圖可圖要求清廷將瞻對還于藏屬。此奏中還提到,如周萬順會同明正土司土兵進瞻,以致堪布無奈退出,屢次轉咨駐藏大臣懇其代奏未允等內容,雖與鹿傳霖疊次所稟情形很不相同,但這使得清廷明曉達賴對此事之態度,或加速了鹿傳霖對瞻對一事改革的消極態度。
光緒二十三年(1897)五月,鹿傳霖借德爾格忒土司改土歸流一案,在沒有征求恭壽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將“將軍”一銜列入其中向清廷上奏吳豐培:《清代藏事奏牘》,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023頁。。待清廷上諭傳至成都,恭壽才知此事,請求與鹿會同協商卻遭回避。七月,恭壽不滿此舉,遂上奏清廷中央:“該督辦理邊務事,或當別有深算,非奴才榛昧所能窺測。誠能有裨時局,無論會商與否,自當敬佩弗惶,奚敢妄持異議……奴才徒列銜名,第屬具文……嗣后凡有邊務事宜,即著該督辦理,無庸會列奴才銜名,以一事權而專責成,似于邊務不無裨益。”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近代康藏重大事件資料選編》,第1編上,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頁。向清廷“牢騷”一通后,光緒二十三年(1897)八月又密奏稱:“土司改土歸流督臣事前并未商辦徑行列銜具奏,據實奏聞一折。四川邊務事宜,向由總督會同將軍互商妥善,合詞具奏德爾格忒土司地,改土歸流一案,鹿傳霖并未知照恭壽,竟將該將軍銜名列入,與歷來辦法不符。并據該將軍奏稱該督不察虛實即飭委員張繼率師往取其地……所供情節與張繼所稟懸殊。現聞張繼在德爾格忒被圍,邊民之未必心服亦可想見等語,此案實在情形。”《清德宗實錄》,卷409,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丙子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338—339頁。
從恭壽此折可見,二者主要矛盾是由川督鹿傳霖并未按例在涉川邊民族事務上會同成都將軍協商,而擅自列銜造成的。而正是由于鹿傳霖的此舉導致了川邊民族地區的情形處于被動。除此之外,這一矛盾在其他史料亦有記載。查騫《邊藏風土記》中載:“時成都將軍恭壽庸且懦,鹿傳霖藐之,此次夷務改流諸大計,鹿未嘗籌商恭壽同一會銜。恭壽意不解,幕僚咸不平。”查騫:《邊藏風土記》,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第42頁。吳光耀在其《西藏改流本末紀》中亦記載:“乾隆朝特詔成都將軍統轄松、建文武,所以監察總督,分其權也。故總督奏松潘廳、建昌道夷務,應會銜將軍。是時成都將軍恭壽,鹿傳霖藐之,夷務奏案未嘗商將軍一會銜。恭壽未以介意,左右為不平。會瞻對土司訴諸達賴,以川督冤誣、川兵虜掠訟于朝,詔恭壽查辦。恭壽以實奏覆,鹿傳霖開缺。朝廷以為恭壽不欺,使代總督。”趙心愚,秦和平,王川:《康區藏族社會珍惜資料輯要(上)》,巴蜀書社,2006年,第3頁。翁同龢在其日記中也有恭壽彈劾鹿傳霖的記載:“恭壽報,仍以土司德爾格忒事訐鹿傳霖,請交文海查辦。電旨一,交文海。明一。”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8卷,中西書局,2012年,第3035頁。
綜觀上述史料可知,鹿傳霖在邊政問題上未遵照乾隆時期立下的“凡番地要務,須將軍、總督會同酌商后,會銜題奏”的流程,導致二人關系破裂。
事已至此,清廷只好出面調解二人,以“事關邊務,豈可掉以輕心,獨斷獨行”責備鹿傳霖,要求二人屏除成見,和衷商辦《清德宗實錄》,卷409,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丙子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338—339頁。。并命駐藏大臣文海介入調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89年,第23頁;《清德宗實錄》,卷409,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丁丑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339頁。。文海隨后上奏清廷,以鹿傳霖“輕聽委員張繼一面之詞……刻聞該土司父子夫婦皆無確供,督臣亦略有悔意,而決不認過,將錯就錯,貽害無窮”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4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314頁。。八月二十八日清廷電寄川省,以“鹿傳霖辦理未妥,責成該老土司仍舊管轄,毋庸改設流官,押至成都土司及其家屬,著一并釋放”《清德宗實錄》,卷409,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乙酉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344頁。。隨后,清廷以“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為由,將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地方,仍一律賞給達賴喇嘛收管,毋庸改土歸流王彥威、王亮輯編,李育民等點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5冊,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440頁。。并命四川總督鹿傳霖開缺來京,以山東巡撫李秉衡為四川總督,未到任前,以成都將軍恭壽兼署《清德宗實錄》,卷410,光緒二十三年九月戊子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346頁。。至此,鹿傳霖對瞻改土歸流宣告失敗。
既存研究多認為鹿傳霖改革失敗乃因遭受以成都將軍恭壽為首的反對而流產。此是其一,但二者背后的政治斗爭亦是導致失敗的重要方面。
首先,恭壽與鹿傳霖在瞻對事件分歧前可謂“昆弟交”,恭壽此前就有奏稱“實以界在疑似之間,致成騎虎之勢”而支持對瞻用兵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4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316頁。。后因鹿傳霖不予恭壽會商“夷務”致二者有隙。至鹿開缺后,該案由成都將軍恭壽暫署川督一職繼續善后,恭壽遵旨向清廷上奏,對鹿傳霖的改革提出了諸多疑問:“鹿傳霖若于懲創之后加以撫綏,一面咨商駐藏大臣,會咨達賴,令其嚴束番官,無任苛擾干預,則番眾必知感知懼,何致退有后言?自倡議改流,關外人心為之騷動。在鹿傳霖之意,以為瞻對系由藏入川之路,思欲收復其地,為邊境之屏藩。又誤聽該處地產五金,擬開利源,為富強之本。不知瞻對在打箭爐西北,系要路旁枝,并非入藏要隘。且其地并無礦苗,間有沙金之處,即竭一人一日之力,不足供一人一日之食。夷性至貪,設使果產五金,豈有數百年至今無人開采之理?又況荒遠不毛之地,地不可耕,民鮮知禮,恐既得之后,教養難施。設官戍兵,經費較巨。當此庫款支絀之際,何堪增此漏危……英人以印度茶葉入藏為利源大宗。幸藏番不食印茶,所以川省茶利不致外溢。以茶厄藏,藏番必改食印茶,不但必致生計立窮,且恐驅之外向。俄人垂涎印度已非一日。西藏不通,則印度無可乘之機……不知夷性反復無常,藏事既扶馭失宜,焉保其必無暗通之事?惟藏地間居兩大,俄視之為入印要津,英視之為開埠利藪。更恐邊釁一開,關系大局匪淺。且印藏界務,藏番以瞻對之故,挾制不肯會勘,日久遷延,失好邦交,英人借口生端,尤屬得不償失。”《奏聞瞻對關系川藏全局遵旨籌度棄取緣由》,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宮中檔奏折》,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宮”148217。此折原文系漢文。恭壽在暫署川督后幾乎全盤否定了鹿傳霖此前的改革舉措,從恭壽一系列奏折中看出,他多采取維穩舉措,遵循舊規。對此,鹿傳霖在十月二十二日的家書中,對此頗為不滿:“我卸任后恭大反我所為,內邊亦決計將瞻對予藏。時局如此,不可為矣,能平安回家即是福。以后直不堪設想。我交卸折尚剴切言之,若因此獲譴,索性罷職,省卻進京亦好。”吉晨:《鹿傳霖未刊家書中所見戊戌前后時局》,《文獻》,2017年第6期。
需要注意的是,此前在處理如甘肅拉布浪寺番僧滋擾川邊番寨等同樣為邊務的過程中,恭壽、鹿傳霖亦是做到了會銜上奏,身為川督的鹿傳霖似應知曉川邊政務的流程,為何唯獨在德爾格忒土司一案上選擇回避恭壽?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鹿傳霖獲得了獨立處理機宜的圣諭,在后來處理涉藏事務的過程中,有時與成都將軍恭壽商議,有時就只在奏折中簽一個將軍的虛銜而獨自處理了,以至于埋下籌瞻舉措不利的種子。并認為成都將軍恭壽本就為一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官員,對西藏地區形勢一無所知,卻妒賢嫉能,不愿別人有所作為”朱悅梅:《鹿傳霖保川圖藏舉措考析》,《西藏研究》,2012年第5期。。
但通過上述史料的記載可見,以上觀點似乎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首先,鹿傳霖究竟在德格一事上是否具有“獨立辦案權”?最初,鹿傳霖在處理瞻對一案時,清廷要求文海“即著暫駐成都與鹿傳霖和衷商辦”《清德宗實錄》,卷403,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庚戌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262頁。;又在鹿傳霖獨自上奏德爾格忒土司一案時,清廷仍著訥欽督同裕鋼一同處理。文海、訥欽皆系駐藏大臣,從官階上看并不在川督之下。俟恭壽上奏彈劾后,清廷下旨:“據稱德格歸流各土司,小有不安,實因謠傳所致。雜竹卡部落,經張繼親往開導,亦已聽命。察木多之倉儲巴,經該前督出示曉諭,各土司早已帖然無事,且提訊老土司父子,并無怨詞。奪吉色額手書番字供詞存卷可查,該處道里賦稅,未及兩月,均已查清,今忽而改圖,恐啟土司之輕藐,長藏番之刁風。”《清德宗實錄》,卷411,光緒二十三年十月甲戌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369頁。
此時,清廷卻并未就鹿傳霖所奏內容直接作出指示,而是一再囑咐此事關系川藏大局,著恭壽將其所奏各節,詳細參酌,令其毋得稍存成見,回護前奏。并飭其“儻敷衍了事,仍貽后患,恭壽亦不得辭其咎”《清德宗實錄》,卷411,光緒二十三年十月甲戌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369頁。。又有,文海入藏查辦案件之時,清廷做出指示:“接見達賴,務當宣布朝廷德意,善為操縱,并將應辦事宜隨時知照恭壽,會商妥辦,期臻盡善。”《清德宗實錄》,卷412,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子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378頁。從以上兩則指示可見,清廷都明確提及讓駐藏大臣或成都將軍來協助辦案。清廷著眼的并不在于具體措施如何推進,而是在于是否有一位要員能夠在事件發生時起到監督、掣肘的作用。正是由于此乃涉藏、涉外重大事件,故清廷采用“會商”的方式來重新調整、平衡、規劃事權。從清廷的角度來看,其目的是防止大權專斷、貽留后患。
其次,恭壽于光緒十七年(1891)十一月二十八日調任成都將軍后,曾親派員會辦青海玉樹番族頻年被川省德爾格土司欺凌磕索各案,并得到了清廷的認可《奏為阜和協副將徐聯奎等員委辦玉樹德格積案出力請分別獎敘事》,光緒二十年四月十九日,《宮中檔全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4-01-12-563-010。此折原文系漢文。。恭壽先后與鹿傳霖、劉秉璋在處理甘省拉布浪寺侵占川番各寨一案中合力兜剿,最終查明各款《奏為番僧侵占川番寨落查辦完結情形》,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五日,《軍機處檔折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機”138197。此折原文系漢文。。可見,恭壽對涉藏事務有著一定的了解與熟悉,并非一無所知。在鹿傳霖開缺后,恭壽兼署川督一職,處理了瞻對、德格案件的善后事務,平息了當地叛亂,照顧到了達賴的情緒,更重要的是使得清廷的形勢不再被動。此外,正如此前章節提及,恭壽在任職成都將軍期間,在興辦學堂、整頓旗務、協調處理教案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分見《奏為練兵圖強瀝陳管見事》,光緒朝(具奏日期不詳),《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5578-088。趙令志:《成都八旗駐防學校志校注》,引自西藏民族學院《藏族歷史與文化論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頁。《奏為查勘四川情形遵議武試改制瀝陳利弊事》,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5617-001。。由此可見,對恭壽任職成都將軍期間的表現似不應用“辦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來評價。
再次,成都將軍一職在嘉慶朝平定川陜楚白蓮教起義后,在戰時率兵出征的頻率上確實不及乾隆時期。在清代西南局勢趨于穩定的情況下,成都將軍影響力的下降亦是因勢使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成都將軍依舊是成都駐防最高軍政長官;在官銜上仍然與川督平等;其職能中依然保留著治理川邊事務的事權。換言之,川省民族地區政務的運作仍系川督與成都將軍“雙重管轄”的模式。特別是在制衡川督上,其影響及作用并未改變。這一點無論是在此前的同治年間令成都將軍魁玉徹查川督吳棠處理貪吏一案,還是此后宣統年間命成都將軍馬亮徹查趙爾豐,都是利用成都將軍一職來掣肘、調查涉案要員的有力證據。此前的史料亦尚未發現有關清廷削減成都將軍職權的記載。故從整個川省的行政模式到具體職權來看,此時的成都將軍似不應為“虛銜”。
最后,會銜制度系清代公文制度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在設置成都將軍之初,清廷明文規定“凡番地官員皆以將軍為政”“凡涉番地大小事件皆須一面呈報將軍,一面呈報總督,由總督、將軍會同酌商,聯銜題奏”《奏為管理番務文武酌議統轄章程事》,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0408-071,此件檔案原文系漢文。。乾隆立制之后,亦遵循此法執行。在特殊情況之下,如成都將軍與川督互為兼署之時,奏折最后須提及“將軍(或川督)系奴才(或臣)本職毋庸會銜”等注語。由此來看,鹿傳霖在涉及德格土司改土歸流的重要事件上,并未知會恭壽,擅自署銜上奏的做法不符合政務運作的程序。換言之,鹿傳霖此奏折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備官方認證的效應。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下,遇到特殊情況固然有經與權之間的靈活轉換,這樣的轉換須是在皇權干涉的情況下進行。鹿傳霖上奏之時,會銜完整,符合奏折要求,但此時清廷中樞尚未知曉此折系鹿傳霖擅自會銜。這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俟恭壽上奏陳述情況后,清廷果斷作出“四川邊務事宜,向由總督會同將軍互商妥善,合詞具奏。德爾格忒土司地改土歸流一案,鹿傳霖并未知照恭壽,竟將該將軍銜名列入,與歷來辦法不符”的諭旨《清德宗實錄》,卷409,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丙子條,中華書局,1987年,第6冊,第338頁。。即便是在特殊情況下為圖時效的應急措施,也仍須在清廷規定的制度下運作。特別是在經查鹿傳霖所辦此案時受張繼一面之詞所誤,就進一步加深了鹿傳霖的罪責。這也從側面體現出清朝公文制度上的僵硬。
三、事件的后續及影響
鹿傳霖與恭壽之間的矛盾隨著鹿傳霖卸職進京而告一段落,但圍繞著對恭壽的彈劾卻并未止于此。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二日,曾上奏公文支持過鹿傳霖收復瞻對的給事中高燮曾,連參三折向清廷彈劾恭壽。在奏折中高燮曾提到:“恭壽本平庸,未諳吏治,加以好諛嗜利,罔恤民艱,其縱容家丁也。有寵仆張姓者,在署中攬權納賄,每事托其關說……由張姓援引均居首要,所有補署各缺,優者納賄八千金余,亦論價有差,皆張姓居間過付其送人督署(按:此指恭壽)之款……本任寧遠府知府唐翼祖,上年十一月檄回本任,其后仍住省城,與督署家丁張姓結納,遂得股票局提調。總之,署督為將軍時尚知收斂,一署總督便任性妄為,貪劣眾著如此,其應如何懲警?”《奏為密陳四川成都將軍恭壽貪劣顯著請旨申飭事》,光緒二十四年(具體日期不詳),《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5370-007。此折原文系漢文。清廷再下旨“該給事中既稱恭壽貪劣顯著,吏治凋敝,物議沸騰,當有實跡可指”,命高燮曾迅速明白回奏。后高氏再上兩折參奏恭壽:“再臣聞四川成都將軍恭壽署理總督與為將軍時聲名迥異,貪劣顯著,吏治毒弊,物議沸騰,裕祿抵任時日不可知,而數月中川民已大受污吏剝削之害。懇祈勿俾敗壞邊疆大局幸甚。附片密陳。”《奏為回奏成都將軍恭壽參款事》,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3-5361-054。此折原文系漢文。
至于最后恭壽貪污一案如何處理,史料并未記載。事后不到兩個月,四川江北廳發生教案,當地哥老會蔓延至川西南地區,導致富民多被迫脅入會,清廷原命恭壽辦理,迅速持平辦結,但七月初七恭壽亡故,清廷命文光暫護四川總督、恩存暫署成都將軍。
就恭壽與鹿傳霖之間的矛盾而言,與此前恒訓與丁寶楨的案例有所不同。從最后處理的結果來看,清廷著眼全局,并非僅以二人不和而罷免鹿傳霖支持恭壽。學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駐藏大臣文海、成都將軍恭壽受達賴喇嘛之賂,以致瞻對屬藏康欣平:《從“收回”到“賞給”:1896—1897年間清廷處理瞻對歸屬事件析論》,《西藏研究》,2013年第1期。。鹿傳霖的家書或可佐證此說:“將軍又與我鬧累贅,亦其家丁張姓,因辦土司承襲得賄故也。”吉晨:《鹿傳霖未刊家書中所見戊戌前后時局》,《文獻》,2017年第6期。二者沖突除有個人因素外,官職之間的沖突也是一方面,清廷設成都將軍之職,最初是為制衡川督,雖可避免一方權力過大獨霸一方,在二人配合默契之時,會商之舉確能以圖全策;若二者有隙,易造成政令不通、效率低下。因該案涉及藏事,駐藏大臣也牽涉其中,三位大員相互掣肘更為復雜。民國時期有學者提出,“由是為大臣者與川督顯分畛域,各持意見。凡大臣所辦事件,川督不從過問,川督偶有規劃,大臣輒與齟齬,兩不相謀,邊事所以壞也”盧秀樟等:《清末民初藏事資料選編(1877-19190)》,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第4頁。 。
其次,瞻對一案亦摻雜有清廷各種派系政治斗爭的因素。鹿與清流派領袖李鴻藻素來交好,其家書中有記載云“又聞高陽仙逝,朝政無人主持,亦國運也”《鹿傳霖致鹿滂理函》,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鹿傳霖任川督時函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甲170-1。見吉晨《鹿傳霖未刊家書中所見戊戌前后時局》《文獻》,2017年第6期。,“聞高陽仙逝,果爾,內中主持無人,公事若掣肘,亦不得不思退步,指日科場又添忙累,亦混到何處算何處耳”,“瞻對收回,真可自強,而反如此疑畏,不肯降一諭旨。看此情形,我不被人劾去,亦必自退,不過遲早間耳。天下事不可為矣。高陽幸尚健步如常,此老竟不能爭,尚何望乎”《鹿傳霖致鹿瀛理函》,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鹿傳霖等存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案號:甲170-2。見吉晨《鹿傳霖未刊家書中所見戊戌前后時局》《文獻》,2017年第6期。。可見,李鴻藻的逝世使鹿傳霖預感到自己在川推行改革勢必阻礙重重。另外,陳寶琛在鹿傳霖墓志銘中所記“公檄軍討之,盡收三瞻地,乃請歸流設漢官,疏十數上,李文正公韙其言,文正薨,廷議中變。公爭益力屬,有蜚語上聞,乃解公職”陳寶琛:《皇清誥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贈太保鹿文端公墓志銘》,閔爾昌:《錄碑傳集補》,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9頁。,或可說明清廷中樞李鴻藻的逝世,對瞻對事件的處理結果存在著一定關系。該案也并非單純的滿漢官員對立,時任駐藏幫辦大臣的滿人訥欽就曾支持鹿傳霖“固川保藏”諸策,在鹿傳霖上奏清廷奏折時,就引用訥欽為己探得藏方持“察其情詞,雖多狡飾,而其心實已畏懼”之態吳豐培:《清代藏事輯要·續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1頁。。但鹿傳霖并不滿足得到訥欽的支持,后上書清廷以訥欽“到任未久,一切操縱機宜”《奏請下幫辦駐藏大臣訥欽為界務春間勘定不必待文海到藏即由訥欽知照印督前往會同畫界由》(此系附片》,光緒年間(具體時期不詳,朱批時期為光緒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軍機處檔折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機”137735。此折原文系漢文。為由,直接參與到涉藏事務的處理之中。
結語
鹿傳霖對瞻對地區實行改土歸流固然是一劑治理“良方”,但改革略顯急功近利,在其“政治后臺”失勢后,更是不惜與成都將軍、駐藏大臣等本職為涉藏事務的地方大員交惡,加之當時清廷內憂外患,并存在諸多掣肘的情況下,恐無力進行如此大規模徹底的改革。此案中瞻對雖位康區一隅,但當時該案外涉英、俄、印外交事務,內涉藏、川、青多省民族事宜,以及清廷中樞派系斗爭,牽一發而動全身。從當時自身情況出發,清廷在此進退兩難之際選擇妥協或是無奈之舉。
從光緒朝清廷對此案例的處理結果來看,因其國力日漸衰弱,晚清時期四川的權力格局呈現中央逐步放權之勢,在川省宦海中爾虞我詐、鉤心斗角的政治角力中,朝中各派系、裙帶關系、人際交往往往左右著政令的施行;官員之間互不信任,肆意誣告,相互攻訐,以致川邊地區諸多改革阻礙重重,嚴重影響了政務運作的流暢。
光緒年間鹿傳霖與恭壽之間矛盾的背后,實際是川督循例不問將軍態度,而擅自聯銜上奏,這說明至少在光緒年間番地事務由川督具體執行已成常態,成都將軍民族職權的喪失亦成必然的趨勢。最終,趙爾巽在任職川督期間奏請中樞裁撤將軍,成都將軍遂交出番地及綠營事權,專轄旗務。“從非其他省城將軍可比”到“權限虛有其名”,這一過程中,不僅體現出其地位、功能作用不斷式微的趨勢,更揭示了清代八旗駐防制度趨于衰敗的事實。在不能徹底解決八旗駐防制度內部及外部所存在的諸多結構性矛盾的情況下,最終導致其喪失了應有的功能。
The Power Struggle in Zhandui Event between Chengdu General and Sichuan Governor during the Guangxu Reign
Wang Chuan,Wu ?Aiping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after the Qing court decided on the Battle of Jinchuan, the post of general of Chengdu was set up and given heavy powers, thus open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Sichuan governor and Chengdu general to jointly govern Sichuan Province. At the time of Qianjia, the two were able to actively cooperate in government affairs and war,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rule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As the country has been peaceful for a long time, the combat power of the Chengdu manchu troops has also become more and more weak, coupled with the ambiguity of the division of functions and powers between the Chengdu general and the Sihuan governor, so that the Sichuan governor has gradually gained momentum in the operation of Sichuan Provinces government affairs. During the Guangxu period, the Sichuan governor Lu Chuanlin and the Chengdu general Gongshou engaged in a fierce dispute over the reform of the land, which involved many struggle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court and officials in the southwestern provinces.
Key words:Chengdu general;Sichuan governor;Zhan Dui;pinned down[責任編校王記錄]
作者簡介:王川(1969—),男,四川樂山人,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西南區域民族史研究;吳艾坪(1994—),男,重慶人,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講師,主要從事清代民族政治制度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2&ZD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