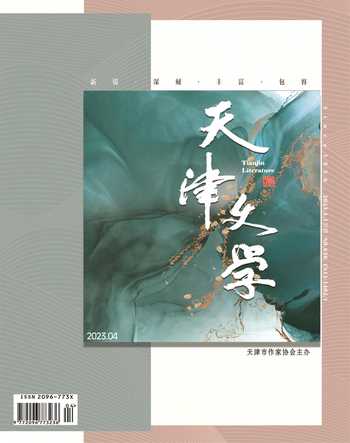百年老宅,與一個村莊的嬗變
在“如意”狀的甘肅版圖中段,自南向北鑲嵌著同樣形如“如意”的縣級行政區劃——山丹。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山馬公路這條空間上的中軸線成為這個縣城立體交通網最繁忙的一段。侯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就“裸露”在這條主干的枝葉上,它四面環山,屬位奇鎮管轄。
千百年來,這條中軸線刻錄、凝聚著一代代山丹人民的情感、記憶和夢想。海拔明顯高出這條中軸線的“小土包”,就在那里靜靜地看著山外的世界,常年積雪的祁連山、巍峨聳立的焉支山都在它的仰視下輪廓清晰、一覽無余。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侯山早已融入新時代“五彩山丹”渾然一體的發展卷軸中,在新時代新征程的畫卷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
面前這位老人叫陳云,盡管全身沾滿泥土,但依然口齒清晰、精神矍鑠,已經74歲的他是這座宅子的第三代主人,加上兒孫輩,一家五代人見證了這座“百年老宅”的興衰更替。
這是一座具有西北農村傳統民居建筑風格的宅院,穿斗式全木結構,建于民國年間。2022年9月17日,宅院里出現了一架威猛霸氣的裝載機。拆卸工人小心翼翼地取下大梁、圓木頂柱、檁子、椽頭和雕刻著各種花紋的窗格,生怕損壞一個部件。這一件件藏壓在歷史深處的雕刻品,散發著時間的包漿;一個個鮮為人知的奮斗故事隱藏在百年荒寒歲月中,連同曾有的光輝年代一樣,即將被時光掩埋。
陳爺和他的兒子陳文華在拆遷現場來回踱步,眼瞅著一面面墻壁被裝載機“扒拉”下來,又被一車車拉走。看得出,他們凝重的眼神里掩飾不住留戀和不舍,內心更是五味雜陳,但他們按捺這份不舍,為了將來幾代人能有更加美好的家園。談起市縣今年實施的生態及地質災害避險搬遷項目,村上人介紹,由于政策宣傳到位,村民們雖然有對往日家園的依戀,但對未來發展的思路都很認可,搬遷工作比較順利。
村上很多過去勤儉持家、耕讀傳家、孝悌和家的示范戶,也成為響應搬遷的典型戶。早年從霍城何家西坡搬遷到侯山的老何爺一輩子本分誠實、勤勞善良,“大集體年代”上溝打壩、栽樹修渠事事走在前面,是集體勞動的模范戶,他的德行和福氣傳了一代又一代,兩個孫女都是省城高校的在讀大學生;彭兆德過去是光榮的人民教師、公社干部,三個兒子里兩個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名牌大學的學生,一個是現任村干部;陳貴德是村上的資深“看水人”,默默守護了村上的自來水源頭十多年,他們都在各自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奉獻著自己的聰明才智。
斗轉星移,滄海桑田。鮮有一棟建筑像“陳氏老宅”“彭氏舊宅”一樣,在過去的流金歲月中封存了那么多臉孔、身影和故事,見證并參與了農村大地的深刻變遷,儲存了幾代人的集體記憶。昨天,它們佇立在夕陽下,等待和訴說塵封的往事;今天,它們在轟然中退出舞臺的中心,但曾經生活其中的人們,又開啟了新的使命和征途。
二
沒有浪濤,沒有喧鬧,一年四季的山丹河與山馬線這條如銀河般閃亮的中軸線蜿蜒并行,安詳而寧靜,在褶皺的歲月中,留下滿河碎影。
但這條被山丹人民視作“母親河”的古弱水河卻跟侯山幾乎沒有多大瓜葛,極度干旱缺水的侯山先民取水地遠在距離六七十公里外的祁連山冷龍嶺北坡后稍溝南岔,屬于霍城河流域紅巖壩自流灌區。水頭北下至霍城鎮泉頭村,經河西寨、周莊、沙溝,再沿山北下,經過李橋鄉巴寨、吳寧,就這樣曲曲彎彎、跌跌撞撞,原本清凌凌的“高原圣水”抵達村南口的時候,夾帶了大量的泥沙、柴屑、羊糞蛋蛋……盡管已渾濁不堪,水量銳減,但男女老幼卻個個心生歡喜,以最盛大的儀式迎接“生命瓊漿”的到來。
可以說,侯山的歷史就是一部與嚴酷的自然條件、惡劣的生存環境抗爭,與上游村落爭水的歷史,自從有了第一代侯山人,與水有關的故事幾乎就是侯山的全部故事,水一直被村人視作比金子還貴重的圣物。
曾經看過一篇權威文獻這樣描述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形成的差別,很重要的標準是400mm等降雨量線,多于400mm的降雨量就可以種地,少于400mm只能游牧。說實在話,這個條件就是整個山丹也不具備,更何況是更缺水的侯山。這個海拔高達兩千米的貧瘠山疙瘩,在貧瘠的四千畝耕地上養活了上千口村民,不能不說是奇跡。
我曾經只身一人行走在侯山人民的“生命河”紅巖壩渠的吳寧段、巴寨段,看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修渠人開鑿的一個個“地窩式”窯洞。看到散亂的水泥石板和瓦礫,過去修渠的印跡依稀可見,遮蔽著歲月,也厚待時光,讓往事在柔軟的回憶里,積字成章。站在山包上,聯想這條長蛇般的水渠汩汩奔涌,是以怎樣的情懷,護佑著侯山兒女歷經風雨一路走來,使這片土地葆有深沉的生機與活力?也仿佛看到了在漫長的水線沿途,身強力壯、頭戴氈笠、腰捆草繩的護渠領水人邊吹著口哨,邊扛著鐵鍬來回穿梭,嚴防死守著一個個堤壩閘口的安全。
過去人畜飲水全靠澇池,荒冰水、頭輪苗水、二輪苗水、胡麻水……每次來水時都要先把澇池灌滿。土澇池下面沒有防滲漏的混凝土設施,再加上蒸發量大,水貴如油,鄉親們特別珍惜水,在澇池周圍設置了圈墻,入口還加條石過門,這些過往的記憶每一項都滲透著時間的溫度,悄無聲息地一去不返。
兩年前,村東頭很久以前人畜共飲的大澇池竟然奇跡般復活了,大自然真是太神奇。枯萎多年的蘆葦發出新芽,四周栽植上了云杉、垂柳和榆葉梅,冬天還把蘆葦墩設計成冰雕,吸引了大量游人前來觀賞打卡。
三
“一組犁鏵锃亮發光,在一片平整的土地上來回作業,干燥的深褐色土塊便像海浪被行船破開一樣,向后翻去……”這是幾年來發生在村上幾個山坳里的勞動場景,人們揮汗如雨的身影和機器的轟鳴聲打破了大山的寂靜。
2019年,五社的丁云、四社的尚玉輝、三社的陳文華等幾位離任村干部在黨的富民政策指引和各級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瞄準了村里的這幾片撂荒地。先是東面的小東溝洼、南面的石溝,又到西面的紅山,再到北面的石坡,幾片地塊都基本保留了古老完好的S型梯田狀灌溉溝渠,從剛開始的幾十畝,到現在的幾百畝,從立春到入伏季,犁地、選種、壓膜、除草、壓秧、打杈,他們靠著辛勤勞作,硬是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試種成功了香甜可口的旱地西瓜。
早晚溫差大、紫外線強是侯山的鮮明氣候特征。這里產出的西瓜瓤頭厚,糖分高,液汁多,甘甜清脆,猶如冰糖在喉,實測得知這里的西瓜含糖量高達24%,遠遠高出許多地方西瓜6%左右的含糖量,慕名前來批發選購的本地、外地客商也越來越多。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他們創造出了每畝平均五百到兩千元不等的收入奇跡。“侯山西瓜”也儼然成為遠近聞名的一張靚麗的地方名片。
山里人愛草木,草木就是大山的孩子,草木繁茂就是大山的福分。如果說20年前國家實施的退耕還林工程使大山的人們認識到保護生態的重要性,那么山丹縣三北防護林五期等工程的縱深推進,則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美產業新百姓富”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目前,這里的全林地、草地、濕地總面積已經達到了3.9萬畝。從溝溝坎坎,坡坡梁梁,到山峰、岑石、野草、灌木、綠植就這樣一路繁茂著,用一種輕輕柔柔的溫暖,輕拂著侯山的每一寸土地。尤其在夏天,那滿山坳里毛糊糊的青瓜蛋子也增添到了云蒸霞蔚般的盛景當中,田野里、空氣中彌漫著甜美的清香和蔥蘢的味道。
“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越來越多的外地客商來到這往日安靜落寞的村莊,越來越多的村民愿意留在家鄉探索和打拼。他們給村子重新帶來了生機和活力。村里的生活不再是單調如一的,洋溢著新時代新技術帶來的多樣的可能性,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盼望也愈加熱切。
村上還把原來的村委會舊址改造出來,為村上40余名65歲以上的老人開辦了日間照料中心。這些老人年輕時大抵都是飽受磨難和辛勞的,晚年在這里可以找到精神歸宿與依靠。
2021年夏天,村民自發捐款,重啟修建了村上的地標性建筑牌坊樓。這座矗立在山墩上的村門上,書有“懷瑾致遠”四個大字,遒勁有力,既是對農耕、讀書、孝悌的敬重,也彰顯侯山村在新時代積極貫徹新發展理念向美而生的奮斗姿態。
未來的故事還將繼續,我們相信一切都會如約而至。這片大山,真像一壇陳年古釀,那縷綿長醇香在蒼穹大地久久徘徊、飄蕩。
段猷遠,1977年生,甘肅山丹人。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多次在《人民日報》《中國文化報》《黨的建設》《甘肅日報》《飛天》《當代敦煌》《甘泉》等報刊發表散文、小小說、報告文學等,有作品曾在“張掖文化旅游全民宣傳行動”中獲獎。
責任編輯:王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