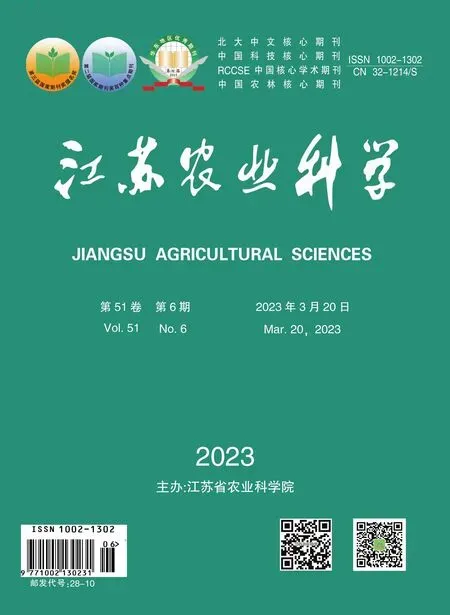基于形態標記和AFLP標記的山藥種質資源遺傳多樣性分析
趙 圓, 張艷芳, 楊 帆, 趙令敏, 陳 妍, 霍秀文
(內蒙古農業大學園藝與植物保護學院/內蒙古自治區野生特有蔬菜種質資源與種質創新重點實驗室,內蒙古呼和浩特 010019)
山藥(DioscoreaoppositaThunb.)為合目薯蕷科薯蕷屬,具備雙子葉特征特性的單子葉纏繞草質藤本植物,無性繁殖。山藥的主要產品器官為子葉下胚軸膨大形成的地下塊莖,其地下塊莖形狀呈長圓柱形,垂直生長[1]。山藥是純天然的滋補保健食物,含有多種營養物質,可食用,也可藥用,有調節脾胃、增強免疫、延緩衰老等效果,是世界上重要的十大食用塊莖類植物之一[2]。我國是山藥重要的原產地之一,在長期栽培過程中,因其適應性強、種植范圍廣,使得地區間相互引種,但山藥的體外培養和遺傳轉化方案尚未建立,導致山藥原有遺傳基礎已無法準確溯源,種質資源混亂,僅通過簡單形態學標記很難真實反映品種間的遺傳背景和親緣關系,分類鑒定難度大,不利于山藥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3]。
以DNA為基礎的分子標記是鑒定種質資源差異性最直接有效的遺傳分析方法,不受基因表達和地理環境的影響。其中,AFLP是基于PCR開發且效率很高的標記技術,只需少量純化的DNA,具有重復性好、穩定性強、靈敏度高等優點,極大地加快了育種進程[4]。許云等通過AFLP分子標記分析了111份大薯材料的遺傳多樣性,8對引物組合共擴增出1 286個多態性位點,占總位點數的99.61%,表明AFLP標記可以檢測出大薯較高的多態性,有效地分析材料間的遺傳關系[5]。Mengesha等采用AFLP基因指紋圖譜對43株不同群體的幾內亞山藥進行鑒定,分析發現,幾內亞山藥栽培品種間存在種內高度變異和種間低程度變異[6]。王丹等對21份馬鈴薯材料進行AFLP分析,并構建了能區分所有材料的指紋圖譜[7]。本研究通過AFLP分子標記結合形態標記的方式,對60份山藥種質資源進行聚類及遺傳多樣性分析,以進一步揭示山藥種質資源遺傳多樣性及親緣關系,以期為今后山藥種質資源的分類及優良品種的選育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與來源
供試材料為筆者所在課題組近年從河南省、河北省、山東省等山藥主產區收集到的60份山藥種質資源,均種植于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內蒙古農業大學種質資源圃,土質疏松,無石塊,肥力適中,無連作。山藥種質基本信息見表1。

表1 供試山藥材料編號及來源
1.2 試驗方法
1.2.1 主要形態指標調查 按照山藥的生物學特性,在山藥生長發育旺盛期和收獲期,分別觀察、計算山藥植株的地上部和地下部形態特征指標,具體參照許念芳等的測定方法[8]。形態多樣性調查的主要指標及賦值標準見表2。

表2 形態多樣性指標及賦值標準
1.2.2 DNA提取 2020年8月采集生長旺盛期健康、無病蟲害的山藥幼嫩葉片,裝入事先準備好的凍存管,迅速放入裝有液氮的采樣盒中,保持葉片新鮮,采集后立即進行DNA提取。山藥DNA的提取和濃度檢測詳見張佳佳等的方法[9]。
1.2.3 主要試劑及引物 參考孫瑞芬等的方法[10]設計接頭和引物序列(表3)。選擇性擴增引物由預擴增引物EcoRⅠ和MseⅠ序列末端加任意的3個堿基組成,各設計16個,共組合256對。

表3 接頭和引物序列
1.2.4 AFLP擴增及檢測 首先選用3個山藥品種(海口山藥、日本山藥-2、河南山藥-1)進行引物篩選,從256對引物中篩選出多態性較好的引物組合,然后進行60份材料的整體試驗。
1.2.4.1 酶切與連接 選用限制性內切酶EcoRⅠ和MseⅠ對植物組DNA進行雙酶切,酶切體系為:10×NEB Buffer 5 μL,EcoRⅠ/MseⅠ 2 μL,模板DNA1 μg,補ddH2O至50 μL。PCR程序為37 ℃溫育 10 min,65 ℃溫育20 min。
分別制備EcoRⅠ接頭和MseⅠ接頭:將E1(10 μmol/L)和E2(10 μmol/L)各10 μL于微量離心管中混勻,取另一離心管將M1(10 μmol/L)和M2(10 μmol/L)各10 μL混勻。PCR程序均為 95 ℃ 5 min,65 ℃ 10 min,37 ℃ 10 min,25 ℃ 10 min,4 ℃ 20 min。
連接體系為20 μL:T4DNA Ligation Buffer 2 μL,T4DNA Ligase(3 U/μL)0.5 μL,EcoRⅠ接頭/MseⅠ接頭 2 μL,酶切產物10 μL,ddH2O 5.5 μL。16 ℃連接過夜。
1.2.4.2 預擴增 將連接產物稀釋10倍作為預擴增模板,預擴增反應體系20 μL:rTaq酶10 μL,M0/E0 2 μL,10×連接產物2 μL,ddH2O 6 μL。PCR程序為:94 ℃預變性5 min;94 ℃變性30 s,56 ℃退火 60 s,72 ℃延伸60 s,30 次循環;72 ℃延伸10 min。
1.2.4.3 選擇性擴增 參照王志敏等對山藥塊莖不同發育時期相關差異基因的cDNA-AFLP分析中的反應體系及反應條件[11]進行選擇性擴增。
1.2.4.4 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及銀染 選擇性擴增產物95 ℃變性后經過8%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強堿法銀染顯色至出現清晰條帶,拍照保存,統計條帶。
1.2.5 數據處理與分析 利用SPSS 25.0軟件計算15個質量性狀的分布頻率;6個數量性狀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標準差、變異系數;參照吳金平等的方法[12]計算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采用DPS分析軟件中非加權類平均法對60份山藥種質進行Q型聚類分析,從中分析各材料的親緣關系。根據AFLP擴增條帶,構建“0、1”矩陣(有帶為1,無帶為0),利用POPGEN 32軟件統計多態性條帶數、有效等位基因數(Ne)、Shannon信息指數(I)等遺傳多樣性指數。使用NTSYS 2.1軟件計算不同材料間的遺傳相似性系數,并根據遺傳相似系數用UPGMA法進行聚類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山藥種質資源形態性狀多樣性
對60份山藥種質資源的21個性狀進行分析,不同性狀在不同材料間表現出不同的多樣性。由表4可知,在15個質量性狀中,除葉的缺裂均為淺裂外,其他14個質量性狀在不同級別上分布不均勻,遺傳多樣性指數最高的是葉形,為1.273 9,其次為葉色(1.000 0)。由表4可知,莖蔓以右旋為主;莖蔓顏色以紫色為主;莖蔓截面形狀以圓形為主;葉形多為戟形、心形;植株長勢中等;大多數無零余子;塊莖形狀以棍狀為主;塊莖表皮顏色以黃褐色為主;塊莖肉色多為白色;塊莖龍頭多為細長型;塊莖須根數100以上。由表5可知,6個數量性狀具有不同差異,塊莖質量的變異系數最大,達到75.88%,葉長變異系數最小,為12.43%。各數量性狀變異程度為塊莖質量>塊莖直徑>葉炳長>塊莖長>葉寬>葉長。

表4 15個質量性狀的分布及多樣性指數

表5 6個數量性狀的統計分析
2.2 山藥種質資源形態性狀的聚類分析
對60份山藥種質的田間形態數據進行系統聚類分析,結果如圖1所示。60份山藥種質的歐氏距離為1.081 6~11.425 9,說明所選材料的遺傳多樣性豐富。其中日本山藥-2(6)和日本山藥-3(31)之間遺傳距離最小,為1.081 6, 兩者間遺傳差異相對較小;大和長芋(22)和得澤紅皮山藥(57)之間遺傳距離最大,為11.425 9,兩者間遺傳差異相對較大。當遺傳距離為8.18時可將供試材料分為兩大類,河南焦作山藥(2)和沈陽草河口山藥(39)聚為一類,其他58份種質聚為一類,這2份種質的主要特征為莖蔓截面形狀為方形,而其他材料均為圓形。當遺傳距離在7.36時可將供試材料分為3個類群和一個單獨分支,大和長芋(22)單獨聚為一類,其主要特征為葉形較大、植株長勢強、有零余子、塊莖短粗產量高;云南品種曲靖山藥(29)、播樂賴皮山藥(49)、德澤紅皮山藥(57)聚為第一亞類,主要特征為莖蔓左旋、葉炳綠色、葉片為淺綠色心形、無零余子、塊莖表皮白色、薯肉白色、須根數100以上;其余材料聚為第二亞類。

2.3 AFLP擴增結果分析
選用3個山藥品種從256對引物中篩選出26對清晰且多態性較好的引物組合(表6),分別對60份材料進行選擇性擴增,共獲得多態性條帶580條,平均每對引物擴增22條多態性條帶,片段大小主要集中在100~750 bp之間,平均多態率78.44%,其中擴增條帶數最多的引物組合是E-GCT/M-GAC;擴增條帶數最少的引物組合是E-GCT/M-TGC。擴增多態率最高的是引物組合E-GCT/M-ACG,達到97.50%;擴增多態率最低的是引物組合E-CAG/M-AGT,為62.96%。Nei’s基因多樣性指數在0.111 5~0.335 5之間,平均值為0.198 8;Shannon信息指數在0.188 7~0.503 9之間,平均值為0.314 9,表明供試山藥種質具有較高的遺傳多樣性。圖2為引物組合E-GTT/M-TTC擴增后的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檢測圖。

表6 26對引物組合擴增產物多態性分析
2.4 聚類分析
采用NTSYS2.1.0軟件計算60份山藥種質的遺傳相似系數,用UPGMA法進行聚類分析(圖3)。60份山藥材料之間遺傳相似系數為0.619~0.922,表現出豐富的多樣性和相似性,其中溫縣鐵棒山藥(3)和細毛山藥(8)遺傳相似系數最大,為0.922,表明兩者間遺傳差異較小;廣淮(10)和德澤紅皮山藥(57)遺傳相似系數最小,為0.619,表明兩者間遺傳差異較大。


在遺傳相似系數為0.68時,60份山藥種質除廣淮(10)外,其他聚為一大類群,表明廣淮與其他種質間雖有共同的遺傳基因,但遺傳相似系數相對較小,存在較大的遺傳差異。在遺傳相似系數為0.74時,可將第一大類群分為2個亞類群和一個單獨分支,淮山藥(33)較為特殊單獨聚為一類,來源于云南地區的會澤山藥(46)、云南富民山藥(37)、播樂賴皮山藥(49)、得澤紅皮山藥(57)聚為第一亞類,其他材料聚為第二大亞類。
3 討論與結論
形態學標記是通過觀察植株的表型性狀來區分品種間差異,是評價種質遺傳多樣性最簡單直觀的方法,但易受外界環境和內在遺傳變異的影響[13]。本試驗對60份山藥種質21個表型性狀進行分析,在15個質量性狀中,除葉的缺裂均為淺裂外,其他14個質量性狀存在不同程度差異,遺傳多樣性指數最高的是葉形,其次為葉色;6個數量性狀平均變異系數為30.07%,塊莖質量的變異系數最大,葉長變異系數最小。通過形態學聚類發現歐氏距離為1.081 6~11.425 9,說明試驗所選材料表型差異大,遺傳多樣性豐富。楊明通過對30份山藥材料的13個形態指標進行分析,表明塊莖長、塊莖周長和葉形3個形態指標是彼此獨立的,對山藥的生長進化各有其重要意義,可以作為山藥形態學分類的標準[14]。李麗紅等對福建72個山藥地方品種資源的19個主要農藝性狀進行遺傳多樣性分析,其中12個質量性狀遺傳多樣性指數均介于0.738 3和1.568 3之間,平均值為1.017 3,葉片質地較高,零余子及是否開花較低,7個數量性狀的平均變異系數為33.17%[15],本試驗結果與之相近,說明山藥群體中存在豐富的表型變異。覃維治等根據表型性狀的遺傳差異將44份淮山藥種質分為4類,性狀相近且區域內生態環境相似的材料聚為一類,各個類群都存在著相應的形態學特征,12個質量性狀中,葉形的遺傳多樣性指數最高[16],本試驗結果與之一致,說明在通過表型性狀研究山藥遺傳多樣性時,除塊莖粗、塊莖長、塊莖質量這些對山藥產量起決定作用的指標外,葉形特點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參照《中國植物志》[17]有關山藥的信息及前人的一些研究,根據本試驗所收集到的數據,如葉片特點上可將本試驗中所用到的材料區分為薯蕷、參薯、日本薯蕷這三大類,薯蕷的葉片小至中、綠色、葉形為戟形、心形或三角形;參薯的葉片中至大、淺綠色、葉形多為心形;日本薯蕷葉片較大、深綠色、心形或三角形。其中參薯包括廣淮、曲靖山藥、德澤紅皮山藥、播樂賴皮山藥、會澤山藥、云南富民山藥,日本薯蕷包括日本山藥-2和日本山藥-3,其他山藥材料為薯蕷。
分子標記是從DNA水平直接反映品種間差異,普遍認為是最有效的遺傳標記方法[18-19]。本試驗用篩選出多態性較好的26對引物組合擴增出多態性條帶580條,平均每對引物擴增出22條多態性條帶,平均多態率78.44%;Nei’s基因多樣性指數、Shannon 信息指數平均值為0.198 8和0.314 9,遺傳相似系數在0.619~0.922之間,表現出材料間有豐富的多樣性和相似性。在遺傳相似系數為0.74時,可將60份山藥種質分為2個類群和2個單獨分支(廣淮、淮山藥),廣淮在聚類樹狀圖的根基處自成一類,根據形態特征和聚類分析應屬于參薯,主要分布在廣東,與其他地區相比廣東地區長夏無冬,降水充沛,農作物的生育期較長,可能在長期的生長發育過程中為適應環境產生了變異,易區別于其他品種;淮山藥在聚類中單獨分為一類可能由于其葉片較大、塊莖較小,與其他薯蕷種質差別較大造成的。Wu等對21個山藥地方品種進行遺傳多樣性分析,ISSR和SRAP的多態性分別為95.3%和93.5%,表明這些地方品種間存在較高的多態性[20]。華樹妹等利用RAPD標記方法對采集自福建各地的34份山藥資源進行遺傳多樣性研究,24對引物多態性比例達88.5%,當遺傳系數為0.66時,將34種資源劃分為扁山藥、普通山藥、福建大薯和參薯4類[21]。
本試驗采用形態學標記和AFLP分子標記2種方法聚類分析了60份山藥種質資源的遺傳多樣性。研究發現,山藥種質資源的形態聚類方式和AFLP標記聚類方式存在一定差異,形態學聚類結果顯示,當遺傳距離為8.18時可將供試材料分為兩大類,莖蔓截面為方形的2份材料河南焦作山藥(2)和沈陽草河口山藥(39)與其他58份種質分開,這兩者形態有相同特點但在基因水平不是特別相近,通過分子標記可將這2類種質區分開,表明DNA分子標記更能直接、準確地將山藥種質資源分類。部分山藥種質在2種聚類圖上都被聚到了一起,如日本山藥-2(6)和日本山藥-1(31)、河南山藥-2(32)和河南鐵棍-2(34)、太谷山藥-2(58)和山西山藥(59)相似系數都在0.800 0以上,表明它們之間可能是近緣關系或同一品種的不同品系經過地區間引種、人為定向選擇產生了種內變異,但遺傳相似度仍較高。當形態聚類遺傳距離在7.36時可將云南薯蕷中曲靖山藥(29)、播樂賴皮山藥(49)、德澤紅皮山藥(57)從其他資源中分出,而當分子聚類遺傳系數為0.716時,將來源于云南地區的會澤山藥(46)、云南富民山藥(37)、播樂賴皮山藥(49)、得澤紅皮山藥(57)從其他材料中分出,其主要特征為莖左旋、葉片淺綠色心形、不著生零余子、薯塊表皮和肉色均為白色,說明這些云南薯蕷無論從形態還是分子水平都與其他材料有著明顯差異,但單獨用一種標記方法很難將它們相互之間準確分開,而使用形態和分子結合的方法則可以將它們更好地區分開。該分類也與劉向宇利用表型性狀和ISSR分子標記方法對山藥種質資源分析所得到的結果[22]相似。黃姍通過SRAP標記聚類分析將94份山藥資源分為5類,其中前4類分別為薯蕷、褐苞薯蕷、山薯和參薯,與形態特征分類一致,而第5類的3份資源按形態分類屬于參薯類,在分子標記聚類分析中則自成一類,與其他參薯相比較存在特殊形態特征,表明分子標記研究種質資源較高準確性[23]。通過聚類分析發現,本試驗所選材料普遍為北方地區種植的薯蕷,缺少廣東、廣西主栽品種山薯和廣西、福建等地區的褐苞薯蕷,并不能代表我國所有山藥種質的遺傳背景,今后應多收集全國不同地區不同品種的山藥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形態學研究和分子研究結果存在差異在于它們在不同層面上表現植物的遺傳多樣性,形態學研究根據植物的表型性狀來區分遺傳變異和品系差異,而分子標記直接體現了種質之間的基因型差異,與基因表達和環境條件無關,因此其親緣關系分析結果更準確[24]。山藥具有很強的區域性,不同生態區域對同一種質的生長發育和形態特征有較大影響。因此,在遺傳多樣性研究中,選擇形態學標記與分子標記相結合,有助于更客觀、更準確地確定種質資源間的特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