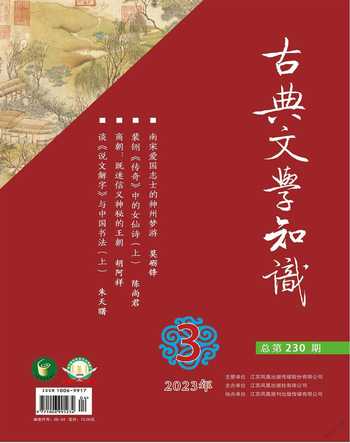《詩經》中的贈玉與愛情
《詩經》作為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較早反映當時的玉文化,為后來有關玉文化傳統的敘述開啟了先河。《詩經》中玉文化的政治內涵已被多次探討,而玉與民眾日常生活的內在聯系尚未得到還原,尤其是私人贈玉行為背后隱秘的愛情觀念值得發掘。
我們發現在《詩經》中有關“私人贈玉”的詩歌共有以下四首:
《國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毛傳》云:“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瑤,美石。”“玖,玉黑色。”《詩集傳》釋:“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目前學界多沿用朱子之說,將此詩釋為男女相好而相互贈答。
《鄭風·女曰雞鳴》:“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毛傳》云:“雜佩者,珩、璜、琚、瑀、沖牙之類。”《詩集傳》釋:“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歷來詩說雖對其主旨的詮釋互有參差,但對夫妻關系是明確的。
《王風·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此處“玖”應與《木瓜》的“玖”同義,也是玉名。
《邶風·靜女》:“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歷來對“彤管”的解釋“未詳何物”,或為女史的筆管,或為與莖類植物相關。據后文女子再贈荑草,男子反應更為熱烈驚喜,前者應不再是草類。而“有煒”之貌也絕非植物和筆類所有,由此推測“彤管”應為管狀玉器。
可見,私人贈玉多見于民間,發生于男女之間的偶遇幽會,事由以求愛為主。通過分析私人贈玉的行為特點,結合玉的特質,我們可以發現玉與人類情感表達的天然親和性,從而探究這一物媒深處積淀著的情愛觀念及其存在的關聯。
擇偶標準的兼容
選擇對象,外形條件往往是首要標準。《詩經》時期的擇偶審美也多重“色”的現象,許多詩歌都十分注重男女身形的具體描繪。但從贈玉行為我們可以發現其審美標準還存在一定的并驅性,做到了外形美與品行美的兼容。
《說文解字·釋玉》云:“玉,石之美者。”周人對玉,首先是愛其形美。陳性在《玉紀》中概括玉的特點為“體如凝脂,精光內蘊,質厚溫潤,脈理堅密,聲音洪亮”,可見玉具有與人相似的審美效應。因此《詩經》中詩人們常以玉來形容自己的求愛對象,“有女如玉”(《召南·野有死麕》)是山野之民以玉的通體晶瑩、質地細膩來形容自己的心愛之人,“彼其之子,美如玉”(《魏風·汾沮洳》)是采桑女對思慕之人相貌的贊美。而這里的“美如玉”已不限于外表之美,更是指對方“殊異乎公族”的人品。“將翱將翔,佩玉將將”(《鄭風·有女同車》)既是襯托孟姜的美貌,更是贊她美好的品德。可以清楚看出,玉中還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審美內涵,這是當時人們更為推崇的。因此贈玉予人既是對對方玉貌的肯定,也是對對方玉德的體認。以玉相授,不僅是為了增進感情,更是通過所贈之玉將自己的精神世界傳遞給對方,含蓄地表達自己“有玉”。
婚姻審美的預設
《詩經》時代的愛情,盡管處處顯露著遠古年代的古樸痕跡, 但它早已不再是人類童年時期純生理的本能需求了。它還注重情愛的長期發展,對情愛的歸宿—婚姻生活有了初步的預演,并將這種婚姻設想寄于玉中。
玉形美質堅、機理清澈,逾千年而不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與美好感情的內在特質相契合。人們將自我情感投射于玉中,以玉作為美滿婚姻的依托,傾注了風情男女純潔恒久、坦誠深摯的情感預期。這也形成了周人初步的婚姻審美觀,即建立在雙方真正的愛情基礎之上,有子孫為依托,婚后家庭和睦幸福,雙方能夠同心同德、白頭相守。人將其情移玉,再以玉贈人,玉的精神與人的情感相結合將饋贈雙方聯系在一起,玉成為牽系兩情的定情紐帶與情感見證。他們將彼此的婚姻藍圖注入玉佩之中,以贈玉的形式締結婚姻關系。
情愛巫術的滲透
葉舒憲指出:“最初,玉中潛含的‘德’并非倫理道德之德,而是神圣生命力崇拜之德,即與‘精’或‘靈’同義,相當于人類學所說的‘馬那’或‘靈力’。”(葉舒憲《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因此最初原始先民崇玉,并非玉被賦予的至高無上的道德內涵,而是認為玉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與靈力。從饋贈玉石的行為我們可以發現先民對玉原始的物靈觀念及這種特殊觀念在情愛意識中的滲透。
原始社會的先民認為萬物皆有靈,對神靈的崇拜主宰了人們的精神生活。他們認為玉是集山川之精華匯集而成,有通天之靈氣,“玉璧、玉琮、玉璜、玉龍正是作為中華先民首選的通天、升天頂級靈物而走上歷史舞臺”(楊伯達《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三編·上》)。而玉也因其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成為情愛關系中的巫術物媒。《詩經》中贈玉詩篇都隱約彰顯了這種巫術心理:《木瓜》中男子多次贈玉以加強關系的意圖;《丘中有麻》中女子特意“冀其有佩玖以贈己”;《靜女》中玉管是首份贈禮。這些都說明當時人們對玉有著非同尋常的珍愛之情,而玉本被視為靈性之物,是人們的護身符,具有異常的靈力。于是借助玉的靈力流入婚俗,贈玉成為加強和穩固情愛關系的巫術手段。人們將貼身佩玉贈予對方,是希望能通過相互接觸的感應魔力,使雙方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能長久保持聯系,以期永以為好。
禮樂約束下的相對自由
由于當時禮法的階級性及上古遺風的留存,民間婚嫁的觀念意識并未因為經濟形態的迭變而驟然消失,而是不斷地積極滲透,融入新的文化形態中,仍影響著先民的深層心理。在經歷過幾百年“厚別致遠”的婚姻后,男子不禁發出疑問:“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陳風·衡門》)可見在民間男女心中,身份地位的分庭抗禮并沒有真心實意的兩情相悅重要,表現了當時民間自主自由的婚戀意識,“兩姓”關系回歸到“兩性”關系的愛情本身意義。通過贈玉詩歌中部分言語暗示,我們也可以發現贈玉的男女往往不是通過父母同意、媒人介紹的私相授受。它們還將“閨房燕妮之情誼”直接載于篇章,靜女故意藏而不見的撩撥、士子留戀枕衾貪睡的慵懶。這些由衷的自我情感表達,完全沒有把“情”強附“禮”的外衣,與“禮”的“非受幣,不交不親”形成鮮明對比,再次印證了贈玉雙方情感的誠摯與關系的純粹。
不過,它們同樣傳遞出這樣一條信息:“情”之“樂”必須以“禮”的控制為前提,需達到真正的“禮樂合一”。所以《靜女》中少女才會俟于城隅、避而不見,直至情郎出現方敢緩緩現身;《木瓜》中他們用象征性物件寄寓情誼,將熱烈的愛意用含蓄的方式來表達;《丘中有麻》中女子才會多次催促男子能贈玉給自己,以正式確立情侶關系。這都說明他們的“情愛”仍受制于社會文化語境的潛在規約,最終都需“反納于禮”。贈玉代表的是婚娶之聘、納征之禮,玉的道德因子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禮的傳達,這在《女曰雞鳴》篇表現得尤為明顯。詩中夫婦在房中雅樂之余,也能樂而有節、愛而適度,各自做好分內要務:丈夫勤奮勞事、親賢樂善;妻子勉夫以勤、助成其德。可見,他們雖對情愛有坦然的心態,有放縱原始情欲的自由。但這種自由仍是需要歸結于禮的,是禮樂制度下的相對自由。這種禮制承認男女之情的天然本性,否定情欲聲色的過分放縱,認為情愛必須受到禮節理性的規約。其最終目的是希望將男女兩性關系納入一個正常的軌道,從而正夫婦以成人倫。這也表明當時的民間情愛觀已受到正統婚戀觀念的沖擊,過渡至民主性與封建性的雙重形態。
《詩經》時代贈玉行為已經走進民間,成為風情男女示愛結情的普遍方式。溫潤、堅貞、永恒的特質是玉之風骨的折射,潛移默化地浸染著人們的情感認知和愛情審美,同時人們也在用自己充沛的情感、真摯的愛意不斷豐富玉的內涵。他們真誠大方地表達自己的情與愛,張揚自己的個性與欲望,還具備初步的現代婚戀意識。這些意識最終也凝結成先民對情愛問題認識的價值內核,對后世的情愛觀念及愛情書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桃夭
桃之夭夭①,灼灼②其華。
之子于歸③,宜其室家④。
桃之夭夭,有蕡(fén)其實⑤。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zhēn)⑥。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小桃長得真姣好,紅紅的花兒多光耀。
這姑娘要出嫁了,家庭的生活定美好。
小桃長得真姣好,紅白的桃兒多肥飽。
這姑娘要出嫁了,家庭的生活定美好。
小桃長得真姣好,綠綠的葉兒多秀茂。
這姑娘要出嫁了,家人的生活定美好。
——鳳凰出版社《詩經全譯》
【注釋】
①朱熹:“夭夭,少好之貌。” ② 陳奐:“《廣雅》:‘灼灼,明也。’《玉篇》:‘灼灼,華盛貌。’盛與明同義。” ③朱熹:“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④馬瑞辰:“宜與儀通。《爾雅》:‘儀,善也。’”朱熹:“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⑤于省吾《雙劍誃詩經新證》:“蕡、墳、頒與賁古通。……頒、賁并應讀作斑。……然則有賁其實,即有斑其實。桃實將熟,紅白相間,其實斑然。” ⑥毛亨:“蓁蓁,至盛貌。”陳奐:“《廣雅》:‘蓁蓁,茂也。’”
陳馨怡 揚州大學文學院2022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