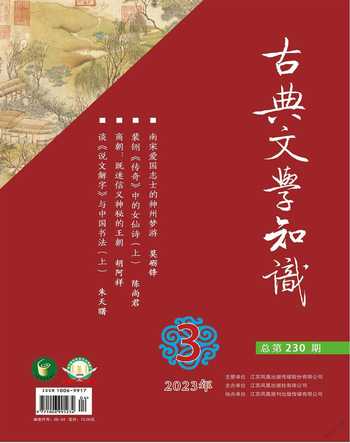說書大師施耐庵與同時空的共鳴者
袁世碩 孫琳


《水滸傳》現存最早刊本署“錢塘施耐庵的(dí)本,羅貫中編次”,或“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如實表明小說前大半部分是整合施耐庵演說的話本編次而成,這一部分敘寫魯智深、林沖、武松、宋江等人的人生轉折經歷,保持了施耐庵說書口語敘事特色,最明顯的是在敘事行文中頻頻插入說書人的話語,也多保持了宋代社會人生實相,鮮活生動,以及自然流淌出來頗為明顯官逼民反的傾向性。
由宋入元的說書大師
小說第八回敘述林沖遭高俅陷害,刺配滄州的一段情節,有三處敘述人的插話:一是“原來宋時的公人都叫端公”;二是“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作‘打金印’”;三是“這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仇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里,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在此處!”
第二十二回敘宋江怒殺閻婆惜,縣府捉拿,宋江躲進自家的地窨子,有段解釋性的插話:“且說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窨子?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往來,卻做家私在屋。宋時多有這般算的。”
以上情節多提及“宋時”,帶有較明顯的說話人口吻,說明這些情節都是源自“施耐庵的本”,施耐庵應當是由宋入元的著名說書大師。
《水滸傳》基本上是整合施耐庵的本作成的前七十回,從京中禁軍教頭王進為免遭主管官僚高俅的迫害出走開頭,魯智深是為救助遭到供應官家肉食的鄭屠欺凌的賣藝女子金翠蓮,三拳失手打死“鎮關西”,受到官府追捕,被迫出家做和尚避難的。禁軍教頭林沖是為防護妻子不受欺辱,得罪高衙內,遭到高俅陷害追殺,瀕臨死地,無奈投奔梁山的。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事,由家仇誅奸,殺嫂祭兄,斗殺西門慶犯罪,到仗義助友奪回快活林,遭到地方武官張都監陷害,必置之于死地,情不可遏,暴力犯禁,遂“血濺鴛鴦樓”。做鄆城縣押司的宋江明知晁蓋等人劫奪地方高官梁中書送往京都高官蔡京的生日賀禮財寶是“罪滅九族的勾當”,卻通信放走“智取生辰綱”的主犯,自己因此被閻婆惜要挾不得已殺人,也淪為官府追捕的逃犯。打劫官僚的財寶,本是主動暴力犯罪,在《宣和遺事》里只是一件歷史瑣事,而在小說中卻增加了事發前“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對窮苦民眾真實生活和心理著意書寫,將官員之惡由政治權力的隨意濫施,擴展到經濟財富的過度占有,故稱作“不義之財”,依《孟子》“行而宜之謂之義”的觀念,就把打劫官員的巨大財物,賦予了合乎情理的正義性,也就擴大了宋江知法犯法私放“犯了彌天大罪”的晁蓋等人的社會價值。由此,敘宋江逃避官府追捕和被判罪兩度流徙中發生的故事,一方面是受到社會多類人物間接的愛戴,一方面是屢遭官僚中人的陷害,自然而迂回地釀出宋江潯陽江頭“醉”題反詩,形成朝內外官僚勾結制造的所謂“謀反”要案,引出“梁山泊英雄劫法場”大規模的抗法,“宋江智取無為軍”對助惡的官僚中人過度殘忍的血腥報復,以及李逵要“殺去東京,奪了大宋皇帝的鳥位”的悖倫話,都無疑宣泄出編創者對封建官僚的憤恨心情。
《水滸傳》這部分由“智取生辰綱”引出宋江流徙江湖,將多方好漢聚集到宋江的故事中,形成梁山聚義的基本規模。這在宋末元初人“鈔撮舊集而成”的《宣和遺事》里,有“楊志籌押花石綱阻雪違限”“楊志途貧賣刀殺人刺配衛州”“石碣村晁蓋伙劫生辰綱”“宋江通信晁蓋等逃脫”“宋江殺閻婆惜題詩于壁”“宋江得天書有三十六將姓名”“宋江三十六將共反”,連續幾節所敘,“遺事”與小說所敘情節大體一致,差異是除掉敘事文的簡括,沒有鮮活的細節,也沒有宋江潛遁青州清風寨和刺配江州的苦難遭遇,“宋江三十六將共反”便沒有了現實人生的來龍去脈。
《宣和遺事》節錄稗史小說成書,文體不一,研究者發現數本,為之校訂。書中敘徽宗宿李師師家故事,類似話本,當據話本節錄。敘晁蓋伙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事,更無疑是節錄小說話本,閻婆惜事或有所改編,不能確認即為據《水滸傳》采錄之施耐庵“的本”,《水滸傳》特別是說書大師之“的本”,意味著當時流傳的還有別本。或者說在南宋末,如龔開《宋江三十六贊并序》所說:“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士大夫亦不見黜”。“街談巷語”自然主要是指市井瓦舍的講說,“士大夫亦不見黜”也自然是指士人的稗史筆記。《宣和遺事》可謂兼容并包,所以前后文體不一,意旨亦有士論與“民情”的差異。就其書內容來看,題名《宣和遺事》,旨在揭露宋徽宗之昏庸荒淫,蔡京、童貫等媚主誤國,這是偏安東南一隅的士人心中歷史遺恨,節錄話本中宋江聚義始末,只是作為那個朝代“遺事”中的插曲,沒有關注到社會狀況與輿情。
鄧牧《伯牙琴》之思想共鳴
與施耐庵大約同時的同城人鄧牧的相關政論,與其說話文本的官逼民反基本思想傾向及其“亂由上作”的基本精神息息相通,甚為吻合。鄧牧(1247—1306),錢塘人,親身經歷了由宋入元時元兵侵襲掠奪之難,自稱“三教外人”“大滌隱人”等,抗節不仕,隱居大滌山中。經時事巨變,他的某些思想從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一般文士的遺民心態,作政論文完全無所顧忌,不單對元統治者表示不滿,還振聾發聵地提出對君主制度的討伐,激烈抨擊當時社會至上至尊的帝王,稱:“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鄧牧《伯牙琴·君道》)揭露統治機構:“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并緣為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間,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竭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鄧牧《伯牙琴·吏道》)
鄧牧揭露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即如三百多年后黃宗羲改題《原君》文中所說:“君為天下之大害”“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后兩句引自《周易·系辭》,意謂隨意占有財富便是啟人為盜,精致美容便教人淫樂,個中就蘊含必招動亂的意思。《吏道篇》揭露大小官吏壓迫剝削人民,“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直接道出了人民怒怨,起來抗爭暴亂的必然性和正當性。其抨擊的對象不再只是“暴君”“贓官污吏”,而是帝王和官吏壓迫剝削罪惡的本性,完全顛覆了傳統的社會倫理的價值觀,所以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被視為“異端”。鄧牧從政治經濟的實處,揭示君主專制社會的本質為社會動亂之源,具有中國中世紀人道主義啟蒙精神,由之也就可以站在歷史維度上理解《水滸傳》的意旨表達,特別是整合其中的“施耐庵的本”的社會實相的現實主義書寫和塑造人物性格的文學特色。
袁世碩 山東大學文學院終身教授
孫琳 菏澤學院人文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