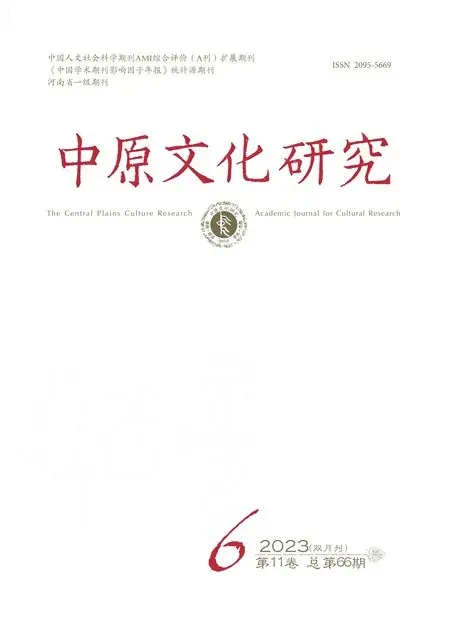“齊氣”說及其文學地理批評范式新探
陶禮天
曹丕《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批評專論,其論述邏輯非常嚴謹而緊密,從批評“文人相輕”發端,充分論證“文非一體”而人各有所長又各有所短,非是“通才”而“鮮能備善”,通過強調作家多為“偏才”而提出重視文學創作個性的理論,從而提出“四科八體”的文體論,所謂“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1]949。這就比前人更為明確、突出而且更有理論系統性地提出文體批評方法;又以建安七子及其創作作為案例批評,具體說明作家如何各有其個性、各有其長短,進而由此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的“文氣”說。《典論·論文》中評孔融的“體氣”說、評徐幹的“齊氣”說等,都可以視為其“文氣”說的內容。曹丕通過“文氣”說主張作家的氣質個性是形成各自獨特風格的主體原因,并明確說明作家作品的“文氣”,可以分為“清”和“濁”兩大類,直接影響了劉勰《文心雕龍》的“才有庸俊,氣有剛柔”說[2]505和“綴慮裁篇,務盈守氣”“風清骨峻,篇體光華”的“風骨”論[2]513-514。曹丕“文以氣為主”說,實際是從才性批評的角度,張揚了創作個性的意義,是故接著論述作家個人“立言”的不朽價值,其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章,既包括“四科八體”的作品,也更強調如徐幹《中論》那樣“成一家言”的子書專著。這體現的是中國古代的“文學”觀,包括所有文體的文章,簡稱謂之“文”。從文學批評立場看,上述的文體批評、才性批評、論建安七子作家作品的經典批評等,無不具有范式意義,對其后特別如《文心雕龍》等杰出文論著作的文學批評范式、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具有重要的影響。
本文通過研究,對曹丕《典論·論文》“齊氣”說作出新的探討,首先簡要交代曹丕《典論·論文》“齊氣”說解釋爭議之問題的由來,并基本認同《文選》李善的注解,認為曹丕提出的“齊氣”說,可以直接視為文學地理批評,而且具有范式意義,并對其后如《文心雕龍》等文論論著中有關文學地理批評思想具有重要影響;其次,結合班固《詩經·齊風》具有“舒緩之體”之說,進一步從文學地理批評角度,論述曹丕《典論·論文》“齊氣”說的兩個方面問題,一是討論劉勰和鍾嶸關于徐幹與王粲的比較評論,二是以東漢李巡《爾雅》注所謂“齊其氣清舒”和劉熙《釋名》所謂徐州“土氣舒緩”等解釋,指出曹丕“齊氣”說作為文學地理批評的淵源與依據;最后,簡要分析曹丕“齊氣”說作為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學地理批評,具有怎樣的范式意義。
一、“齊氣”解釋爭議問題之由來與辨正
曹丕《典論·論文》提出的“徐幹時有齊氣”說,李善《文選》注:“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文選》五臣注:“翰(李周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粲之儔也。”[1]948此后,關于“齊氣”歷來從李善注,少有質疑;文字上也不從《三國志》《藝文類聚》和《初學記》作“徐幹時有逸氣”。1948 年范寧發表《魏文帝〈典論·論文〉“齊氣”解》一文,以某本《初學記》(今不詳何本)“齊氣”作“高氣”為據,力主《文選》本為誤①。其后眾說紛紜,或以為文字有誤,或以為李善誤注,或從李善注并加以補正,還涉及相關諸多問題的討論,迄今僅發表的單篇論文就有20 多篇,這里不遑細說。
《文心雕龍·風骨》說: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并重氣之旨也。[2]513-514
可見,《文選》選錄的曹丕《典論·論文》作徐幹“時有齊氣”,文字不誤,《文心雕龍》引文作“齊氣”,可謂鐵證。《文心雕龍》諸多版本中,唯有元至正本和明弘治本作“濟氣”,明顯乃“齊氣”之誤②。而李善對“齊氣”注解,基本為正解,并無大誤。因為從文學地理學的理論立場看,曹丕的“齊氣”說,屬于文學地理批評,是對其前的《詩經》《楚辭》的文學地理批評的直接繼承,也是對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的地域文化觀和《漢書·地理志》“以詩證史”的方法與觀念的繼承。只是這方面的有關文學地理批評的理論淵源與批評傳承,或顯或隱,需要深入挖掘才能闡明。
李善拈出曹丕《典論·論文》“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一句中“斯累”一詞,認為曹丕意謂“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使“齊氣”成為具有一定的貶義色彩的批評,應不符合曹丕原意。因為即使曹丕確實如黃侃所言“文帝《論文》主于遒健,故以齊氣為嫌”[3],那么,曹丕之前,班固《漢書·地理志》說《詩經》之《齊風》具有“舒緩之體”的思想藝術特征,亦并非貶義;何況從曹丕存世作品看,正如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所評:“子桓慮詳而力緩”[2]700,徐幹在“力緩”方面與曹丕較為類同,結合其二人傳世作品,不難得到實證。是故李善的“斯累”之說和黃侃“以齊氣為嫌”之論,當難以成立。因為“文帝《論文》主于遒健”的事實,并不能必然推導出“故以齊氣為嫌”的結論。如《文心雕龍·樂府》說:“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制歌。”[2]101這里的“齊楚之氣”,僅為關于樂府的地域分布及其特點的表達,亦不妨直接視為一種文學地理批評,亦無褒貶之義。“齊楚之氣”即是“齊氣”和“楚氣”,分別指齊地和楚地的土風。曹丕《典論·論文》說: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聘驥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1]948
這里列舉建安七子作為當時最優秀的代表作家,采用的是史傳常用的書寫格式,就是介紹每一位作家的籍貫、名與字。表面上看,這是史家敘事“慣例”的襲用,也是日常生活中介紹人物的習慣,但實際上卻是別有深意。這個“深意”就是因為下文要評論每一位的所長所短,而每位作家的所長所短和創作個性、作品風格的文氣“清濁”,又與作家所來自的文化地域(作家的籍貫所屬之地)乃至與其流寓之地(文化地域)具有密切關系,雖然曹丕僅指出徐幹“時有齊氣”,是與其來自“齊地”有關,對其他作家都沒有論及,但已足以成為一種文學地理批評之范式。這應是與齊文化和《齊風》具有突出鮮明特點有關,而徐幹又具有這樣的特點,曹丕才作如此的論述,這是在前人相關表述的基礎上熔鑄出“齊氣”一詞,也可以說提出了文學批評上的“齊氣”說。這本身在理論邏輯上是自洽的,并不能用難道齊地的作家都具有這種“文體舒緩”的“齊氣”特點加以反駁,而認為如果這樣認為就邏輯不通;因為曹丕并沒有說,齊地的作家都如徐幹具有“齊氣”。
這七子的籍貫簡要統計說明如下:魯國孔融文舉,今山東曲阜市人,孔子第二十世孫;廣陵陳琳孔璋,廣陵射陽人,今江蘇揚州市寶應縣,屬江淮之間,其北為淮安市③;山陽王粲仲宣,山陽高平人,在今山東濟寧市鄒城西南,位于山東西南部,屬魯文化區④;北海徐幹偉長,北海劇人,今屬山東濰坊市寒亭區,該區朱里鎮匯泉莊東有徐幹墓,屬齊文化區⑤;陳留阮瑀元瑜,陳留尉氏人,今河南開封市尉氏縣,位于河淮之間的河南中東部平原地區,西鄰新鄭,春秋時為鄭國別獄所在地;汝南應玚德璉,汝南南頓人,漢代南頓縣治在今河南項城市西部的南頓鎮,位于潁水與汝水之間的河南中東部,屬于汝潁文化地域;東平劉楨公幹,東平國人,今屬山東泰安市寧陽縣,位于山東中西部,屬魯文化區⑥。
其中,今屬山東者4 人:孔融、王粲、劉楨和徐幹,前三者屬魯文化區人,唯徐幹屬齊文化區人;今屬河南者2 人:阮瑀、應玚;今屬江蘇揚州市者1 人,陳琳。其中值得特別說明者三人:孔融曾為齊地的北海國相6 年,東漢北海國的都城在今山東壽光市(屬濰坊市管的縣級市)東南;陳琳大約于漢少帝劉辯時期,在京城長安為何進主簿,后避亂奔冀州袁紹,其后歸順曹操,屬于由南入北的文人;王粲14 歲隨父居長安,16歲與族兄王凱從長安到荊州避亂,投奔劉表,32歲勸劉表之子劉琮一起歸順曹操,屬于建安七子中年少時即由北入南流寓荊州16 年的著名作家。三國曹魏時期,作家以北方人為主,可以做出詳細的統計,這就是當時的文學地圖,此處暫不詳細羅列說明。曹丕《典論·論文》接著說:
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園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1]948-949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對曹丕《典論·論文》提出的“徐幹時有齊氣”的“齊氣”一語,作了詳細注釋,論述很重要,現抄錄如下:
齊氣——黃叔琳評《文心雕龍·風骨》說:“氣是風骨之本。”氣在于作家謂之氣,形之文者謂之風骨。所以紀昀的評進一步指出:“氣即風骨,更無本末”。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文選學》引黃侃說:“文帝《論文》主于遒健,故以齊氣為嫌。”劉文典《三馀札記》:“《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作‘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典案《文心雕龍·風骨篇》作‘時有齊氣’,與《文選》合。《藝文類聚》五十三引無非字,余與《王粲傳》注引文同。李注翰(李周翰)注并以齊俗文體舒緩釋之,亦是望文生義,曲為之解耳。魏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雖言逸氣,然謂劉楨,非徐幹也。”案:李注有根據,并非望文生義。《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公子札來觀周樂,樂工“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注:“泱泱,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這是說齊詩有舒緩的風格。《漢書·朱博傳》說:齊部舒緩養名。顏師古注:“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論衡·率性》:“楚越之人處莊岳(齊街里名)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這都是說舒緩是齊地特殊的風俗習慣。是齊氣為舒緩的鐵證。由于齊俗舒緩的生活環境,影響到作家的個性和作品風格。所以說“徐幹時有齊氣”。逸氣是贊美之辭,齊氣乃是不足之稱。所以本文于“時有齊氣”一句之后,又來一轉筆,說“然粲之匹也”。《魏志》注引作逸氣,所以下一句轉筆作“然非粲匹也”。李善注符合文義。《文心雕龍·風骨》:“故魏文……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以齊氣與逸氣分別屬于徐、劉二人,則本文當依《文選》作齊氣為是。[4]
這里對本文認為曹丕的“齊氣”說就是一種文學地理批評,并且具有一種范式意義,具有較為重要的參考依據,分析說明如下:第一,結合劉文典的研究和《文心雕龍·風骨》篇的引文等文獻,論證說明曹丕《典論·論文》“徐幹時有齊氣”一句評論的文字,沒有錯誤;第二,《文選》李善注釋“徐幹時有齊氣”,以“齊俗文體舒緩釋之”,“符合文義”,并非如劉文典批評的那樣是“望文生義,曲為之解”[5];第三,在李善引《漢書·地理志》舉《齊風》說明“此亦其舒緩之體也”的基礎上,旁征博引更多文獻資料,論證說明:“舒緩是齊地特殊的風俗習慣。是齊氣舒緩的鐵證。由于齊俗舒緩的生活環境,影響到作家的個性和作品風格。所以說‘徐幹時有齊氣’。”問題由來已經說明,并且談了本文的思考與論述主旨,說明“徐幹時有齊氣”是指其如《齊風》一樣的“文體舒緩”,有“緩氣”的藝術特征、風格傾向[6],那么下文就接著對《齊風》具有怎樣的“舒緩”特點,嘗試加以分析。
二、《齊風》“文體舒緩”臆詮
《詩經》中的《齊風》屬于當時“北方文學”的東區,共11 篇。《史記·貨殖列傳》云: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7]
齊國富甲東海,士農工商賈五民皆有,文化風氣較為開放,為道家、法家的興盛之地。吳公子季札在魯觀齊樂云:“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8]1098季札有可能是從齊國霸主的實際政治地位著眼品評的,上文錄《中國歷代文論選》注“齊氣”引《左傳》服虔注云:“泱泱,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所謂“太和”主要就是自然平和之意。
班固《漢書·地理志》所謂“舒緩之體”,或還有夸誕之氣。但必須指明的是,服虔所謂“深遠”,有“太和之意”與班固所論并不完全相合。我們誦讀流傳至今的《詩經》中《齊風》11 篇歌詩,較難體會季札說的“國未可量”和服虔說的“太和之意”。因為讀詩與觀樂,其感受不可能全然相同,一偏重于聲而一偏重于辭義之故,我們即使吟誦時,不顧其詩“義”而專聽其吟誦之“聲”,那也不過是吟誦的一種語調,每個人的吟誦與體會也自會不同。既然如此,他們說的“舒緩深遠”和“舒緩之體”,除了根據季札觀樂的評論等文獻史料記載外,主要還是根據齊風詩歌的文本作出的判斷。
蓋風詩是入樂的,是歌詞,是與當時音樂演奏和舞蹈表演一起來歌唱的。如果說齊風的樂調是泱泱舒緩的,那么在歌詞中多少有所反映;如果服虔說的“太和之意”就是指他前面說的“舒緩深遠”,那么今天讀這流傳下來的《齊風》11 首詩,至少是在班固所舉的《還》和《著》中還可以有所體會。下文將結合具體作品,稍作分析。
《齊風》中《南山》《敝笱》《載驅》三詩,據《毛詩》小傳,是諷刺文姜通于齊侯的[9]340-345,既表現了齊國上層統治者的豪奢與放蕩,也側面表現了當地士人“足智,好議論”的風氣。這種“寬緩闊達”的“齊氣”,主要表現為文辭上善于夸飾,句尾多綴虛詞;節奏上較為疏宕(乃至松散),不太注重物色的細致描寫。例如《還》《猗嗟》二篇,幾乎每句加一個“兮”字,前者寫兩個獵人的互相贊美,后者贊揚一個少年的美貌與射技。句句綴一虛詞“兮”字,令人吟之、聽之感覺到其言辭的夸張和文氣的疏放。《漢書·地理志》云: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瑯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10]
班固舉證齊風的《還》《著》兩首風詩,作為“舒緩之體”的代表,正是從齊人的“舒緩闊達而足智”推論至齊風的“舒緩之體”的。《毛詩》說:“《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詩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并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并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并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9]331-332
《毛詩正義》:“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峱,乃刀反,《說文》云:‘峱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嶩’。”[9]331孔穎達正義云:
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值我于峱山之間兮,于是子即與我并行驅馬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9]331
可見齊士大夫們舒緩闊達,喜好“戲樂”而不務實事的風氣。班固的意思,似乎還兼顧“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以及“俟我于著乎而”所表達出的民俗風氣(生活習氣);也就是說,顧及其表現的內容和表現這種內容的形式這兩個方面來論說“舒緩之體”。齊風《著》詩云: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9]332-335
著,“門屏之間曰著”。《毛詩》小傳認為:“《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鄭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9]332《著》是寫一個貴族女子等待新郎迎娶的情景。三章九句,全詩只有“著”“庭”“堂”“素”“青”“黃”六個字不同,且每句句末綴兩個虛詞“乎而”,來表現她的期盼之情,回環往復,詠嘆有余,疏緩有致。總體而言,《還》與《著》之間的區別不大,而這兩首詩確實是《齊風》中較為典型的“舒緩之體”。班固所舉的這兩首中的三句詩,吟唱起來的節奏,感覺該是:“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俟我—于著—乎而”。按照這樣的節奏,我們今天吟起來、聽起來也覺得是“舒緩”的。因為在古漢語中,“之乎者也”等虛詞是起到句讀作用的。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解釋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正義云:“先儒以為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聲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長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取詩為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于樂之音聲。出言為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大賢師曠、季札之徒,其當有以知其趣也。”[8]1096本節所析,或有臆斷,然“出言為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音聲與歌詩之間必然存在一定聯系,所析僅為說明本文討論之問題而已。
三、從徐幹與王粲比較中提出的“齊氣”說
曹丕的“齊氣”說,是在徐幹與王粲創作個性的比較中提出的,探討曹丕“齊氣”說的內涵,應該要特別注意徐幹與王粲的比較研究,注意與六朝人關于此二人的一些評論結合起來加以考辨,如劉勰、鍾嶸等相關論述。前文已經引過《典論·論文》所論:“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園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曹丕在此說王粲與徐幹“然于他文,未能稱是”,這句話容易使人誤解或生出歧義,故先解釋一下:這里的“他文”不包括成一家之言的“專著”,如徐幹的子書《中論》;“未能稱是”意謂(在曹丕看來)王粲與徐幹的各類文體作品中,以其辭賦創作水平最高,而并不是說這二人的詩歌等其他文體的創作水平都不好、都不如別人。這段評論的開頭一句話的意思是說王粲很擅長創作辭賦,徐幹亦擅長創作辭賦,雖然徐幹時有“齊氣”,與王粲作品所表現的才性氣質、風格不同,但仍然可與王粲相匹敵。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徐幹時有齊氣”這句話,顯然應該理解為不僅是徐幹的辭賦作品,而是他的所有作品都具有“齊氣”的特點。“時有齊氣”之“時”字,雖然解釋為“有時”可通,但結合徐幹的性情與人品,解釋為“時常”,更符合邏輯。“時常”具有“齊氣”,仍然是包含“有時”沒有“齊氣”的內涵。這正可以解釋《文心雕龍·詮賦》篇所謂“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2]135,劉勰用的是正對,王粲和徐幹的賦都有遒壯有力的一面。所謂“時逢壯采”,這個“時”字表明其反面就是“時無壯采”,也就是“時有齊氣”。
劉勰《文心雕龍》評論作家作品以“才性”為主要方法。評王粲,《明詩》篇謂他與曹植能夠做到“兼善”,即能備“雅”“潤”“清”“麗”諸特點,超過其他詩人[2]67;《雜文》篇謂“仲宣《七釋》,致辨于事理”[2]255;《論說》篇謂“仲宣之《去伐》”,與嵇康《聲無哀樂論》等一樣,“師心獨見,鋒穎精密”[2]317;《神思》篇謂“仲宣舉筆似宿構”,雖“似宿構”之作與曹植、禰衡等人的一些作品相若,是快捷而成的短篇,但亦“思之速也”[2]494;《體性》篇謂“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2]506;《才略》篇謂“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玚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2]700;《程器》篇亦謂“仲宣輕脆以躁競”[2]719。評徐幹,除《詮賦》篇所謂“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和《才略》篇所謂“徐幹以賦論標美”外,《程器》篇謂“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2]719;《哀吊》篇謂“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2]240。另外,鍾嶸《詩品》列王粲于上品,評語卻說:“其源出于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余。”[11]37又列徐幹在下品說:“白馬與陳思贈答,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叩鐘’,亦能閑雅矣。”[11]129雖然“以莛叩鐘”之評屬于鍾嶸的個人意見,并不恰當,但特別指出徐幹五言詩具有“閑雅”的品格,與曹丕的“齊氣”之說具有一致性。綜述所引劉勰、鍾嶸對王粲、徐幹的評論,至少有以下三個要點:
一是王粲、徐幹他們各自不同文體以及同一種文體的藝術特點和風格特色都有不同;王粲和徐幹都擅長賦和論,劉勰認為王粲的賦作,發篇遒勁,鋪敘細密,也善于辨析事理,其“論”體文,善于立意,思想鋒利而邏輯嚴密;對王粲和徐幹詩作的評論,劉勰與鍾嶸的意見不同,但大體定位還是較為一致的。劉勰含其賦作一起評王粲為“七子之冠冕”,鍾嶸專論詩歌,亦定位王粲為上品,只是鍾嶸更崇尚曹植,故置王粲于曹植之后;劉勰認為徐幹也擅長賦和論,所謂“以賦論標美”,但是大概劉勰認為徐幹的詩寫得不如王粲的好,鍾嶸也僅列徐幹在下品,遠不及劉楨,但能夠“閑雅”。
二是“躁競”“躁銳”本指王粲之性格。就才性而言,王粲性情“躁銳”(性急而思銳)而才高,突出表現在其為文快捷、落筆果斷,而又能思致綿密,語言亦佳,很少有文辭表達上的瑕疵;而徐幹不僅詩格“閑雅”而且性情亦“閑雅”,人品溫和端正、“沉默”深沉而不議論是非,在創作上徐幹善于表現“哀辭”(善于敘悲),在建安文人中,這一點比較突出。
三是才性和作品直接相關。總體上看來,王粲的賦作遒勁有力與他的性情(側重在“性”而同時說明其“才”亦高)相關者多,而徐幹的賦作雖能“時逢壯采”,但主要與他“博通”的才華有關,其性情如“沉默”、善于體會悲哀之情等,卻不適合于創作“壯”“遒”之風格的作品。這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北海人徐幹賦作由于其個性原因而有不遒壯(也不夠緊密)的一面,這是與曹丕說徐幹“時有齊氣”相契的,也是與李善把“齊氣”解釋為“舒緩之體”相一致的。劉勰《體性》謂“仲宣躁銳”,《程器》謂“仲宣輕脆以躁競”,劉勰所論本于史書《三國志》及裴注,其性情氣質(性格)之“躁”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指其性情氣質在道德品性方面表現出的與別人“競”于名利,或可謂不如徐幹之純粹;第二,是指其性情氣質在行為言語上表現出的率直而不深沉。劉勰據此而論文學創作之才性問題。《三國志·魏書·杜襲傳》云:“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恰并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恰、襲。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恰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12]666《三國志·魏書·王粲傳》云:劉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裴注謂:“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侻者,簡易也。”[12]598并敘及“陳留路粹”文下,裴注引魚豢轉引韋仲將(誕)話說:“仲宣傷于肥憨。”[12]604《三國志·魏書·鍾會傳》裴注引《博物記》云:“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12]796總之,王粲大概矮小而憨胖,且體質不強壯,但性格急躁,任性率為,不如徐幹那樣性情“沉默”。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云“王粲率躁見嫌”[13],此正可與“沉默”的徐幹相匹對。
總之,徐幹性情有齊人之“寬緩”(司馬遷的用詞),而故有“舒緩之體”的“齊氣”,與王粲“躁競”不同;但其“博通”,雖“時有齊氣”,亦“時逢壯采”,擅長“賦”和“論”,可以與王粲相匹敵。
四、曹丕“齊氣”說與《尚書》之《禹貢》地理學
《中國歷代文論選》中對曹丕《典論·論文》“齊氣”一詞有很精到的注釋,已如前引,其中主要論及徐幹之“齊氣”源于齊地人的舒緩生活習氣。但這方面的研究,迄今學界似未關注到曹丕“齊氣”說與《禹貢》學“九州之氣”說的關系。
實際上,曹丕“齊氣”說不僅與班固《漢書·地理志》謂《齊詩》(即《詩經》之《齊風》)有“舒緩之體”說具有直接的淵源關系,這一點,《文選》李善注已經予以明確揭示;還可以從東漢李巡《爾雅》注和劉熙《釋名》有關解釋看其與《禹貢》學“九州之氣”說的關系。班固、李巡、劉熙有關論述,都屬于《禹貢》之學,其間具有一脈相承的知識與“觀念”。理解這一點非常必要,因為中國古代的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皆與《禹貢》學(包括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學術內容)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曹丕“齊氣”說亦是如此。李巡《爾雅注》已佚,在唐陸德明《爾雅音義》(《經典釋文》)之《釋地》篇有其關于“九州之氣”的注文⑦;其后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亦有引用李巡注文(見莊公十年),較陸德明引文為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等亦有引錄,但“齊曰營州”的注文中,缺引李巡之注;清揚州人黃奭有《爾雅李巡注》輯本一卷(見《漢學堂經解》),此不贅述。清畢沅疏證、王先謙補劉熙《釋名》(《釋名疏證補》)中有補輯:“《公羊疏》引李巡注《爾雅》云:‘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營。營,平也。’今為青州。”[14]51《典論·論文》“齊氣”之熔鑄成詞,蓋是脫胎于李巡《爾雅》注所謂“齊其氣清舒”等說。
劉熙,字成國,北海人,靈帝時曾任南安太守,建安初避亂至交趾,所撰《釋名》,歷來被譽為與《爾雅》《說文解字》并列的三大辭書。曹丕是否見到該著雖不可確證,但由此書可以了解曹丕那個歷史時期有關“齊氣”說相關問題的共同認識,這應該是沒有疑義的。《釋名》卷二《釋州國》,與《爾雅》“九州”的解釋,都是本于《禹貢》之學。先釋十三州名,再釋十三國名,又釋十八郡名,這些“名稱”都與地理環境(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土壤氣候、地理方位、天文分野等)或與“事宜”(文化習俗、政教禮制或人情物理等)有關,如云:“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又云:“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如此等等。其中與這里要說的問題直接相關者,為釋“徐州”“豫州”“荊州”之州名和“魯”“越”之國名等。其謂“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又,“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是說這二州都有安舒、寬舒之氣。這里就不一一引述。劉熙釋徐州得名源于其“土氣舒緩”之故等。這些解釋與李巡《爾雅注》是一致的,或即參考過李巡的注。可見,稱一個地方有“舒緩之氣”,并非冷僻之說。班固謂《齊詩》具有“舒緩之體”,曹丕自可據此謂徐幹“時有齊氣”。又,其謂:“荊州,取名于荊山也。必取荊為名者:荊,警也,南蠻數為寇逆其民,有道后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又,“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也”。又,“越,夷蠻之國,度越禮義,無所拘也”[14]45-53。這是從人的生活環境和性格、行為習慣等角度予以解釋的,說明一個地方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性格、行為習慣,會被人從某一個特定角度予以概括,這也是在曹丕之前和同時就存在的解釋。進而我們也就可以考慮到“齊氣”是與“齊地”(齊國)人的生活習慣、行為風俗等有關,這樣解釋也就很合理。
一個地方之“氣”,其“土氣”“風氣”等,這些概念內涵比較復雜。一是指地理方面的“自然之氣”,班固《漢書·地理志》所謂“系水土之風氣”,應包括地形地貌、氣候、物質方面的生活條件等綜合而成的一種自然特點;二是指生活在這種自然條件下的民人之“氣”,大概包括這個地區人群的一種生活方式、習慣習俗乃至個性氣質,甚至還包括體形體態、語言聲音等綜合而成的一種精神面貌。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是中國古代學者常常說的一個地方的“氣”,引申到文學創作風格和文學批評之中,也就要考慮這個地域的作家作品可能所具有的一種文學地域性特征,或者用這種地域之“氣”來說明作家作品的某種地域特征。這就是曹丕提出的“齊氣”說之思想淵源與知識背景。這種總括地說一個地方之“氣”是什么特征,帶有“感覺”“印象”的認知特征,既有一定的科學性,又帶有人類認知的一種模糊性、整體性、直觀性的思維特點,其中不一定完全科學和全面,有時難免從某一個角度去討論,所以可能會以偏概全,但是從整體上講,絕不是主觀臆斷,完全沒有道理。
李善注《典論·論文》的“齊氣”,引《漢書·地理志》所謂“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此亦舒緩之體也”。雖然略去班固“又曰:‘俟我于著乎而’”這一句,但已經明確揭示出班固《漢書·地理志》所論,就是曹丕《典論·論文》“徐幹時有齊氣”之本據,體現出一個注家的學術嚴肅性,要言不煩,所注基本不誤,既指明其出典,又闡釋其內涵。今人對李善此注生發出多種詮釋,有些解說者似乎未能仔細考察分析李善之所以這樣注解的緣由。自唐李善《文選》注釋“齊氣”為“文體舒緩”之義后,唐宋以至明清的作家、藝術家、文藝批評家,均用“齊氣”表示“舒緩”文體、格調或藝術筆法(如書法等)特點,容或存在差異,具體所指的內涵亦有不同,如結構不緊湊、筆力較軟等,但“舒緩”之內涵不變,無有嚴重歧說。
要之,關于曹丕《典論·論文》中所說的“齊氣”,唐李善所注基本不誤,有本據在焉。反而是今人之反駁,才多為臆斷。如何詮釋曹丕所說的“齊氣”說,從文學地理學的研究角度講,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
結 語
如上所論,曹丕《典論·論文》“齊氣”說,蓋為一種文學地理批評,且對《文心雕龍》中有關文學地理批評的思想與方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不難考見的。李巡《爾雅》注“漢南曰荊州”曰:“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荊。荊,強也。”[15]王粲年少時流寓荊州依劉表16年,其“躁競”的個性氣質,是否受到“其氣燥剛,稟性強梁”的荊州之氣影響,曹丕把王粲與具有“齊氣”的徐幹進行比較評論,是否內含這種文學地理批評的意見,不能“想當然”地臆斷。但如果我們撇開曹丕的評論,僅從文學地理學的理論視域看問題,可以說,王粲的創作不能不受到荊州當時的文化地域風氣的影響,這是題外話。
前文論述說明曹丕“齊氣”說,是一種文學地理批評,而且具有范式的意義。通過上文研究,可以看出這是從人地關系與文地關系出發,對作家作品的藝術特征與風格成因作出的分析。引申來講,“齊氣”說,關注到地域的生活習俗以及文化的與文學的傳統對作家作品的影響問題;從作家的才性批評和文體批評出發看,“齊氣”說突出強調體現在作品中的“文氣”即創作個性特點,又結合具體作家所擅長的文體及其文體風格進行評論;而且還注意到與其他擅長同一種文體的同時代的作家進行比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一種文學批評的系統性、客觀性與科學性,又不乏文學鑒賞的主觀體驗之精神。這對于我們今天開展文學地理批評與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構,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是故說曹丕“徐幹時有齊氣”這句話,具有豐富的文學地理批評的內涵,足以成為文學批評之一“說”。
注釋
①范寧:《魏文帝〈典論·論文〉“齊氣”解》,《國文月刊》1948 第1 期。②參見林其錟:《元至正刊本〈文心雕龍〉集校》,出自《〈文心雕龍〉集校合編》,暨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 頁;詹锳:《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1060-1061 頁。③陳琳籍貫據《孔融陳琳合集校注》,參見杜志勇:《孔融陳琳合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101 頁。④王粲籍貫據《王粲集校注》,參見張蕾:《王粲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1 頁。⑤徐幹籍貫據《徐幹集校注》,參見張玉書、邵先鋒:《徐幹集校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版,第1 頁。⑥阮瑀、應玚、劉楨籍貫據《阮瑀應玚劉楨合集校注》,參見林家驪:《阮瑀應玚劉楨合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1、53、403 頁。⑦陸德明著、張一弓點校:《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7-63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