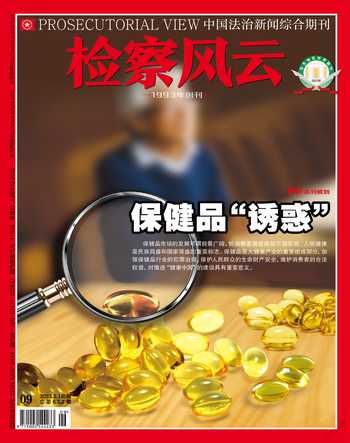危害藥品安全犯罪中“假藥、劣藥”解釋路徑
朱丹 張浩澤
從2019年《藥品管理法》修訂到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實施,再到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22年藥品犯罪司法解釋》)的頒布,無不彰顯著我國立法者與司法者對藥品安全的密切關注。但無論是立法條文,抑或司法解釋,都離不開對法律解釋方法的選擇運用。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將第141條及142條中涉及“假藥”“劣藥”認定參照《藥品管理法》的有關規定予以刪除,帶來刑事司法實踐中如何對“假藥”“劣藥”認定的問題。換而言之,刑事司法者面對危害藥品安全犯罪應采用形式解釋論還是實質解釋論?是采用形式刑法觀還是實質刑法觀?如何平衡“社會對嚴厲打擊危害藥品安全犯罪的需求”和“將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予以出罪”?刑事司法者須選擇適當的法律解釋路徑,才能真正實現對公眾健康法益的保護。
1979年《刑法》首次將生產、銷售假藥行為納入刑事規制范圍,并采用“結果犯”的立法模式。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藥品犯罪層出不窮,我國于1993年出臺《關于懲治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將藥品犯罪行為范圍擴充至生產、銷售劣藥,并將生產、銷售假藥犯罪認定改用“具體危害犯”的立法模式。此后,1997年《刑法》對藥品犯罪的規制基本沿用了1993年《決定》的制度設計,同時確定假藥犯罪“具體危險犯”的立法模式。由于司法實踐中對“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認定存在困難,刑事立法者于2011年出臺《刑法修正案(八)》,將生產、銷售假藥罪構成要件中的 “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刪除,改為“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
通過對我國藥品犯罪刑事立法過程的審視可見,當下以“抽象危險犯”立法模式應對“風險社會”“風險治理”的趨勢。立法者更追求以刑法機能實現提前預防藥品犯罪之目的。雖然“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但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頒布前,刑事司法者仍以危害藥品安全犯罪相關法律條文中的規定,即“假藥、劣藥”的規定參照《藥品管理法》規定為約束,并沒有實質判斷“假藥”“劣藥”的空間。而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假藥、劣藥的認定參照《藥品管理法》的有關規定”刪去,從而使刑事司法者擺脫《藥品管理法》的約束。那么,結合“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刑事司法者如何在相關案件中衡量何為“假藥”“劣藥”?此外,能夠達成共識的是,我國既要嚴厲打擊藥品犯罪,亦要注重對沒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予以出罪。
正如上文所言,刑事司法者面向藥品安全這一保護問題時,既要嚴厲打擊危害藥品安全的犯罪,又要保持刑法應有的理性克制。具體而言,刑事司法者對“假藥”“劣藥”的解釋不應拘泥于《藥品管理法》類公法,否則對危害藥品安全犯罪行為的打擊范圍將過窄。這可能也是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假藥、劣藥’的認定參照《藥品管理法》的有關規定”刪去的立法緣由。事實上,刑法對構成要件的解釋不僅須與《藥品管理法》銜接,更應當與民事規范予以銜接。
“民刑是否應當銜接”是目前學界熱議的話題,主要關涉經濟犯罪條文或知識產權犯罪條文中共有法律概念的解釋是否應統一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刑法具有獨立的立法目的及制度功效,因此刑事司法者對共有法律概念的解釋可以獨立進行。一般而言,持該論點者支持實質解釋方法,即刑事司法者對規范概念的解釋可以脫離其原有之意。也有學者認為刑法僅以保障法而存在,進而刑事司法者對共有法律概念的解釋應遵循前置法的規定。持該論點者更青睞形式解釋方法,即刑事司法者對規范概念的解釋應遵循字面含義。換言之,前置法對該規范概念的解釋不可被刑事司法違背。如有學者認為,不能超出文本形式含義的輻射范圍而進行實質性解釋,否則將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沖突。

藥品缺陷如果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就有被法律追責的可能
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爭議的背后事實上是形式刑法觀與實質刑法觀之爭。該爭議的核心分歧在于對刑事規范性質的不同認識。形式刑法觀認為刑事規范屬于行為規范,即刑法的設立目的是給公眾提供行動指南。其理論基礎在于刑法機能在于實現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結合。實質刑法觀雖然認可公眾行為預測可能性的重要性,但更認為刑法規范的本質是裁判規范。或言之,實質刑法觀更偏重刑法實質的妥當性,因此對構成要件的彈性解釋也在所難免。事實上,實質刑法觀原有之意是以實質的妥當性及實質解釋方法對某些沒有嚴重社會危害性行為予以出罪。
事實上,公眾的行為預測可能性是法的安定性核心要義。法律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制度規則,理應建立在公眾生活的可預測性之上。只有公眾可以預測社會活動的結果,法的秩序價值方能實現。在藥品安全秩序的法律規范構建含有技術型規范色彩的背景下,無論從法秩序統一性還是罪刑法定原則來看,刑事司法者都不宜在危害藥品安全犯罪的打擊中秉持實質解釋論。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假藥、劣藥的認定參照《藥品管理法》的有關規定”刪去,也不意味刑事立法者支持實質解釋論。
因此,本文認為,刑事司法者對“假藥”“劣藥”的解釋不僅可以參照民事規范以擴大范圍嚴厲打擊犯罪,更應當以民事規范的含義為解釋界限。如民法典第1202條至1207條規定了產品缺陷導致的法律責任。毫無疑問的是藥品也屬于產品一類。產品缺陷分為設計缺陷、制造缺陷和警示缺陷,據此假藥劣藥也可以包含此三類缺陷。如藥品設計缺陷可指由于設計因素導致的不合理危險,藥品制造缺陷可指在藥品制造過程中產生的不合理危險,藥品警示缺陷可指未做出適當警告說明的不合理危險。該類藥品缺陷如果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則都具有被法律追責的可能。
為了嚴厲打擊藥品犯罪行為,刑事司法者應注重民刑銜接,運用形式解釋方法將民事規范中的“缺陷藥品”納入刑事規制范圍。但刑事司法者亦要注重實質解釋方法對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行為予以出罪。正如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之爭,事實上也并非聚焦于刑事司法者到底是選擇徹底的形式解釋論還是絕對的實質解釋論。其爭議核心在于是形式解釋多一點還是實質解釋多一點的問題。
本文認為,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都具有獨立的價值功效。在危害藥品安全犯罪的打擊中,既要以形式解釋論合理擴大“假藥,劣藥”范圍,將缺陷藥品納入規制范圍,也要以實質解釋論對不具備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予以出罪,即在犯罪構成要件的具體認定中,嚴格以是否存在公眾健康法益侵害作為判斷標準。或者說,刑事司法者對藥品安全這一集體法益予以保護時,必須審視該集體法益是否能被還原至個人法益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