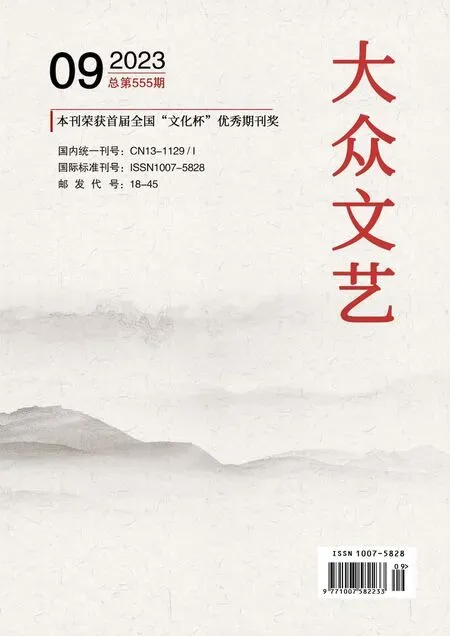秦公簋銘文章法的設計性研究*
吳云峰 中野仁人
(京都工藝纖維大學工藝科學研究科,日本京都 606-0953)
秦公簋,1919年出土于甘肅省天水市,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是春秋時期(前770-前476)秦國(前770-前207)的青銅食器。[1]秦公簋的發掘不僅為文字學、歷史學的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持,為書法的學習提供了良好的法書,研究其設計性,更是對當代字體設計的發展起到了啟示作用。秦公簋銘文(如圖1)在繼承大篆風格的基礎上,融入了秦國自身的獨特風貌,是秦統一后創立小篆的基礎,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從筆法上看,整體看似統一,實則富于微妙的變化;從章法上看,方正規整,重視實用性,反對過度裝飾。每個銘文均由活字模打造,是活字印刷術的雛形,此種鑄銘方式同時代實屬罕見,使銘文章法的布置有了全新的模式。

圖1 秦公簋銘文
筆法和章法是書法本體的兩個方面。章法又可分為小章法和大章法。小章法指漢字書寫的間架結構,表現為字形;大章法亦作“分布”,指對于書法作品全局的布置安排,類似于字體設計中版式的概念。文章將結合春秋時期秦系金文的發展史,從小章法和大章法兩個方面探究秦公簋銘文章法的設計性。
一、春秋時期秦系金文的發展過程
公元前770年,西周(前1046-前771)覆滅,周平王(?-前720)遷都洛邑,建立東周(前770-前256),是為春秋之始。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前1046-前221)、楚(?-前223)、秦、晉(前1033-前376)始大,政由方伯”,呈現“禮崩樂壞,諸侯割據”的形勢。動蕩分裂的政治局勢強烈地催生著觀念的轉變和思想的解放,迎來中國文化史上輝煌的發展時期。春秋中期以來,各諸侯國的書法逐漸擺脫大篆的束縛,開始書體革新。《詩大序》有云,“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這段話雖然說的是春秋以來的詩歌創作,卻也道出了各諸侯國書體革新的根本原因。當統一的意志能夠有效奉行時,文化的向心力也會表現得鮮明而穩定,整體的秩序感則優于局部的個性。可一旦權威消逝,向心的結構就會隨之松動,其結果往往是整體秩序的崩壞,進而使原生的、地域性的、個性的文化擺脫束縛,解放和凸顯出來。文字與書法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也是一種富于象征意味的文化符號,任何文化上的變革,都會在其上打下烙印。
春秋以來的書體革新大致分為以楚國為代表的東南諸國的裝飾性文字和以秦國為代表的實用性文字兩個方向。秦系金文與東南諸國金文的最大區別是它始終以《史籀篇》為基礎,保證了周秦文字的連續性發展,也為后來小篆的創立奠定了基礎,這是中國文字與書法——周(前1046-前256)秦(前221-前207)漢(前202-220)唐(618-907)——一脈傳承發展的關鍵。《漢書·藝文志·小學》云,“《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前782)太史籀(生卒年不詳)作大篆。”西周末期,宣王中興,勵精圖治,作《史籀篇》統一規范文字為其貢獻之一。《史籀篇》的編纂施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的文字整理與規范,也使文字教育和書寫訓練有了固定范本,標志著“王者之風,化及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序而具體地落實在了文字上。秦國遠居西土,與東南各國來往甚少,且秦先君為周王室大夫,理所應當地奉行《史籀篇》,而后文化相對閉塞,使其文字在不受外來影響的情況下,平穩地延續《史籀篇》而發展。
春秋時期的附銘秦器發掘較少,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秦公鐘、秦公镈和秦公簋,其銘文之首均有“秦公”二字,故此得名。現藏于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秦公鐘和秦公镈(以下簡稱“鐘镈”)于1978年同時在陜西省寶雞縣太公廟出土。其中鐘五枚,銘文合兩鐘為一篇;镈三枚,銘文各自成篇。其主人均為秦武公(?-前678),作于春秋早期。鐘、镈同銘,結體、章法類似,筆法略有細微差異,可見銘文范本同為《史籀篇》。以二器之銘相較,鐘銘筆畫略粗,呈內斂之勢,筆力較為平實;镈銘筆畫瘦硬,呈放縱之勢,筆力略勝于前者。共同點是圖案化程度較高,筆畫的排疊轉曲均與宣王時期奉行《史籀篇》的虢季子白盤銘文類似。
秦公簋的斷代問題尚有爭議,計有成公(?-前660年)、穆公(?-前621年)、共公(?-前605年)、桓公(?-前577年)、景公(?-前537年)諸說,前后相差百余年。從書體革新的角度看,進一步圖案化、規范化是秦系金文發展的基本趨勢,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秦代小篆的出現。而秦公簋銘文的書體革新進程晚于鐘镈銘文,如圖2所示,“宅”字的“宀”部首筆畫的方圓變化;“靜”字結體的訛形與簡化;“余”字下半部件的完善;“壽”字“口”部首的移位和結體的整飭;“朙(明)”字“囧”部首部件的完善;“疆”字“弓”部首增加了“土”部件以區分疆、彊(強)二字。以上都是秦公簋銘文在《史籀篇》和鐘镈銘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圖案化、規范化的例證。虢季子白盤與鐘镈相隔百余年,變化并不十分顯著,依此進程再順延百年左右,則可推斷秦公簋作于共公、桓公、景公的可能性較大,時當春秋中末期之際。[2]

圖2 秦公簋銘文和鐘镈銘文的比較
二、秦公簋銘文小章法的設計性
小章法亦作結體,結體在字體設計中可以體現為對字面、結構比例、重心等的把握。秦公簋銘文結體的最大特點是在《史籀篇》和鐘镈銘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奉行規范化的書體革新法則。較之虢季子白盤銘文和鐘镈銘文,它的結體更為方正和規整;較之同時期的楚系金文,它的結體更加簡潔,更加注重“文質之爭”中“質”的因素。
如第一章所述,從虢季子白盤銘文到鐘镈銘文,再到秦公簋銘文,是秦系金文書體革新的一條時間軸。為了更加直觀地分析秦公簋銘文的結體特點,筆者分別選取虢季子白盤銘文全文78字、秦公镈銘文全文77字、秦公簋銘文全文82字(不含重復出現的字、殘缺嚴重的字以及“十”字[如圖1的4行1字和虢季子白盤銘文和秦公簋銘文中“十”字的橫畫都以圓形飾點代替,字面非常特殊,不具有普遍性])進行整理,將字面的縱橫比(AR)屬于(-∞,1)的文字定義為“寬扁”,AR屬于[1,1.25]的文字定義為“方正”,AR屬于(1.25,1.5]的文字定義為“較高”,AR屬于(1.5,2]的文字定義為“高”,AR屬于(2,+∞)的文字定義為“特高”,并以圖3進行數據匯總。[3]

圖3 虢季子白盤銘文、秦公镈銘文和秦公簋銘文結體的比較
根據圖3分析可知:①三篇銘文中方正、較高和高的文字最多,占比均達到了全文的80%以上,可見結體整體上較為修長是三篇銘文的共同點。從虢季子白盤銘文到秦公镈銘文,再到秦公簋銘文:②占比最多的文字從高、較高到高、方正,再到較高、方正(見圖3灰色區域,均達到各自全文的65%以上),秦公簋銘文中方正的文字更是高達47.6%,且AR的均值逐漸遞減,可見秦系金文的結體在整體上保持較為修長的基礎上有逐步向方正發展的趨勢。③寬扁和特高的結體比較特殊的文字占比從11.5%到7.8%再到4.9%,呈現遞減的趨勢;AR的方差(σ2)也呈現遞減的趨勢,其離散程度越來越小,也越來越穩定。可見秦系銘文的結體一直朝著規整的方向發展。
結合以上對于秦公簋銘結體的分析可以看出它與同時期楚系金文書體革新的代表作王子午鼎銘文的結體風格相去甚遠,前者結體較為方正,在《史籀篇》的基礎上或簡化、或訛形、或整飭文字部件,朝簡潔實用的圖案化的方向發展;后者則繼續拉長文字的結體,并將鳥書、鳳書、龍書、蟲書等的物象裝飾附加在文字上或寓于文字中,形成了神秘奇詭、極富裝飾性、頗具原始宗教意味的鳥蟲書。
春秋時期楚系金文和秦系金文在結體方面的書體革新的不同趨勢正對應了當時設計美學中“文”與“質”的關系,“文”指形式與裝飾,“質”指內容與功能,即內容與形式、功能與裝飾的關系。當時的文質論主要表現為兩種思想傾向:一是以儒家為代表,主張文質統一,即既有“文”,又有“質”,以“文質彬彬”為最高理想;二是以道家、墨家為代表,主張“重質輕文”,但道家的“重質輕文”是注重物質本有的天然之美,崇尚質樸,追求自然的審美傾向,墨家的“重質輕文”也不是排斥美,而是始終把“質”放在首要地位。顯然,以王子午鼎銘文為代表的楚系金文受到了儒家“文質彬彬”思想的影響,既注重文字的外部裝飾,也賦予了文字歌功頌德、宗教祭祀的功能,但沒有沖破禮樂制度的束縛,沒能將文字的功能從階級中解放出來;以秦公簋銘文為代表的秦系金文受到了“重質輕文”思想的影響,注重文字的功能性,對于文字的整理規范以及第二章提到的注重功能、以人為本的觀念的萌芽也對應了墨家“非樂”(即反對禮樂制度)的主張,有將文字的使用對象從王公貴族推向普通民眾的傾向,也為秦建國后統一文字、創立小篆奠定基礎。同時,這種注重文字的識別性和規范性,不在原有的文字結體上附加裝飾元素的秦系金文也體現出道家重質樸、擯裝飾,認為裝飾是對自然本真的破壞,推崇自然之美的審美傾向。[4]
三、秦公簋銘文大章法的設計性
如圖4所示,金文的章法可分為無行無列、有行無列和有行有列三種形式。[5]殷商時期(前1600-前1046)的金文多為款識,此類金文多為無行無列,寥寥數字,章法巧妙奇絕,但不便于閱讀,[6]如木工冊作母甲觶銘文。殷商晚期的小子逢卣銘文突出表現了文字的行距,形成了便于閱讀的有行無列的章法樣式。西周中期出現了字距、行距均衡的有行有列的章法樣式,如孟簋銘文。西周中晚期界格的出現使得金文的章法更加嚴謹,界格類似于字體設計中假想框的設定,在約束字面大小的同時,使得大量結體各異的文字形成了統一的視覺效果,標志著金文的章法由自由逐步轉向理性,也為《史籀篇》的編纂奠定了基礎,如大克鼎銘文。春秋時期秦系金文與西周中期以來的金文章法區別不大,屬于有行有列。然而,隨著重復文字使用頻率的增加,整篇的文字模制作起來耗時費力,且不能重復使用,于是春秋中末期出現了活字印刷術的雛形。圖1中清晰可見活字模的痕跡,顯然秦公簋銘文通篇由一個個活字模拼組翻鑄而成,這種技術使得章法的布置有了全新的模式,方形的活字模相當于字體設計中的假想框,尺寸一致的假想框固定了銘文的字距和行距,使得秦公簋銘文的章法更加理性,視覺效果也更加整齊勻稱,順應了秦系金文規范化的書體革新法則。[7]

圖4 金文章法的三種形式
秦公簋銘文的章法體現出設計中技術和藝術的互動關系。技術和藝術說起來好像是兩種不同的人工創造,實際只是同一精神活動的兩面,最高的技術成就也代表了最高的藝術境界。[8]青銅鑄造業中技術方面的實驗與改進,大部分都反映在器形、紋樣和銘文的設計與安排上。相反,很多器形、紋樣和銘文的造意和形成,都是被新技術所啟迪或被舊技術所限制的。首先,活字模的技術直接影響了秦公簋銘文章法的革新形式;其次,金文章法革新的新需求又會推動鑄銘技術的進步;最后,鑄銘技術的演進與書體革新的進程也并非完全同步,兩者分別具有相對的獨立性,這也解釋了從目前出土的春秋時期的青銅器來看,運用活字模技術鑄銘的只此秦公簋一器的原因。
結語
文章從春秋時期的歷史文化背景入手,分析了秦系金文的發展過程,從章法的角度探尋秦公簋銘文的設計性。結體方正,注重文字的識別性,弱化裝飾性。此外,活字模的出現類似于現代字體設計中假想框的設定,使得文字的章法布置更加規范整齊。筆者通過分析秦公簋銘文章法的設計性,發現書法和字體設計之間存在關聯性,關聯性決定了將其應用到當代字體設計具備可行性。這樣的應用不僅是對傳統書法藝術的傳承,也給予了當代字體設計厚重的歷史文化氣息。
這次的研究是基于大量文獻、圖片以及實地考察的資料,通過比較、歸納等方法所做的理論性研究。在今后的課題中,筆者計劃將這一研究成果運用于設計實踐中,制作出一套名為“古韻秦公體”的字體設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