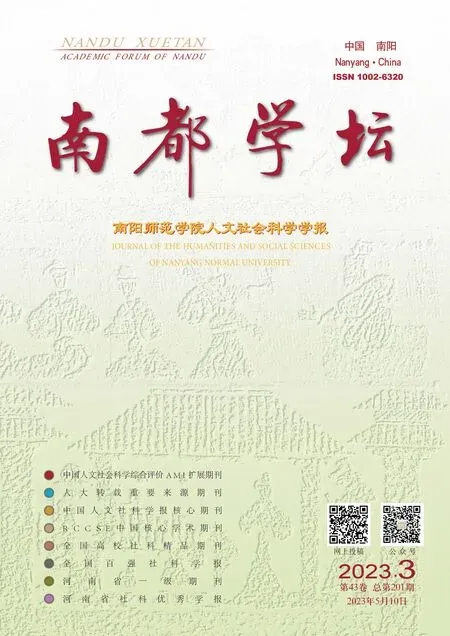先秦兩漢時期感生神話書寫的演變
田 藝 景
(山東師范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山東 濟(jì)南 250014)
感生一詞,始源于《易經(jīng)》,“天地感而萬物化生”[1]95。《禮記》:“王者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2]902鄭玄注:“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2]903“感生”強(qiáng)調(diào)始祖出生與神明帝靈密切相關(guān),以突出家族的神圣性。先秦時期,夏商周三代始祖都有感生神話,這些感生神話,特別是商周的始祖神話,成為王朝宣揚(yáng)天命,凝聚家族的重要力量。漢代的皇帝則以感生夢神化皇權(quán),提高權(quán)威。隨著經(jīng)濟(jì)、社會、文化背景的變遷及史學(xué)的發(fā)展,先秦兩漢時期的感生神話書寫呈現(xiàn)出不同特點(diǎn)。對于先秦兩漢時期的感生神話,前賢已取得較多學(xué)術(shù)成果,本文著眼于先秦兩漢時期感生神話的文本性特征,對神話文本的演變及特點(diǎn)進(jìn)行總結(jié)和剖析,以期推動相關(guān)研究的發(fā)展。
一、先秦時期感生神話的生成及其文本的書寫特征
兩漢之前的部分典籍中就已出現(xiàn)過對始祖感生事件的記載。本文將先秦時期傳世文獻(xiàn)與出土文獻(xiàn)中感生材料加以整理制成表1。
(一)《玄鳥》《生民》與始祖感生神話的起源與故事定型
除鄭穆公與褒姒以外,禹、契、棄分別是夏、商、周三代的始祖,這些神話可以稱為始祖神話。這些材料的文本性質(zhì)頗有不同之處。《玄鳥》《生民》分別是商族、周族稱頌祖先功德的詩篇,用于祭祀等情形,反映了商(宋)、周貴族對其族群起源的認(rèn)知。由于詩體所限,《玄鳥》的記述較為簡略,但仍突出了感生神話中具有神圣性的“天”以及感生物“玄鳥”,說明天命以及感生物是始祖神話的最重要的構(gòu)成要素。《生民》的記述較為詳細(xì),記載了姜嫄履帝武而生后稷,以及后稷出生以后的種種神跡,與《玄鳥》相比,《生民》突出了后稷之母在感生過程中的作用。《天問》則是戰(zhàn)國后期屈原所作詩歌,“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何喜”,是其對商祖感生神話的追問,簡狄是契之母,是嚳之妃,也就意味著嚳是名義上的契之父,“臺”是感生之地,到戰(zhàn)國后期,商的感生神話已經(jīng)具備天(上帝)、感生物、感生地、父、母等神話構(gòu)成要素。

表1 先秦文獻(xiàn)中的感生神話
從這些神話的內(nèi)容上看,先秦時期的始祖神話反映了遠(yuǎn)古先民的圖騰崇拜、英雄崇拜,產(chǎn)生的年代很早,但從神話起源——故事成型——形成文本需要一個較長期的過程,隨著社會發(fā)展,文本還有進(jìn)一步演變的可能性。就始祖神話起源來看,根據(jù)“神話歷史”理論,史學(xué)是一種以史家主觀闡釋和敘述為主的哲學(xué)或詩學(xué),我們所看到的歷史并不是完全真實(shí)的,而是真實(shí)與虛構(gòu)的混合體。對感生神話而言,事件的虛構(gòu)主要在于此事件要素的強(qiáng)烈因果性。如在遠(yuǎn)古時期的感生神話中,女性吞鳥卵并非奇事,女子懷孕生子更為常見,因此其事件要素真實(shí)存在并不足為奇。然而將事件的各個要素以因果關(guān)系相聯(lián)系,就成了神話——如簡狄因吞玄鳥之卵而孕契。在此事件中,簡狄吞鳥卵為真實(shí),而因此有孕生契的因果聯(lián)系為虛構(gòu),最終真實(shí)與虛構(gòu)的各要素混合形成了我們所看到的“神話歷史”。因此,從現(xiàn)代科學(xué)的視角看起始階段的感生神話,或許其存在是真實(shí)與虛構(gòu)的事件要素并存的結(jié)果,亦或是在遠(yuǎn)古時期人類對某些未知事物的虛構(gòu)性聯(lián)系而造成的。
中國遠(yuǎn)古時期的神話,更傾向于人事的神話化,而非神話的擬人化,神話事件的存在,并非為突出其逃離于社會的神性,而是有其存在的需求,也可以稱之為存在的意義。在原始神話產(chǎn)生的遠(yuǎn)古時代,神話被人們所信仰,神話所講述的內(nèi)容將被民眾無條件地接受,這使得神話與權(quán)力的歸屬有著十分密切的聯(lián)系。掌握神話的創(chuàng)作、傳播權(quán)力就等于掌握了與天交流、代天下達(dá)命令的權(quán)力,控制了神話的講述體系也等于控制了權(quán)力的主體,于是知識的擁有者在控制神話的創(chuàng)作、講述、保存和傳播的過程中,無不刻上代表他們的權(quán)力烙印。絕對意義上的客觀與歷史書寫的真實(shí),無論在歷史或未來中都不會出現(xiàn)[7]16。筆者認(rèn)為,在感生神話中對女性人物的著重描述,并使其成為感生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反映了其人物原型產(chǎn)生于母系氏族社會的史實(shí),但故事成型許是在父權(quán)制社會下完成的。又或許感生神話產(chǎn)生的時代正處于母系氏族社會向父權(quán)制社會過渡的階段,男性的地位已經(jīng)確立,因此感生神話中存在著父權(quán)制社會的因素,但也難免受到過去社會生活的影響,還帶有母系社會的遺風(fēng)。在古代的創(chuàng)世神話中,女媧是被崇拜的女始祖,古文獻(xiàn)中的感生神話“其特點(diǎn)是把部族的英雄始祖說成是女性與某種神物交感而誕生出來的。這一方面表現(xiàn)出古人的圖騰意識;另一方面也能表現(xiàn)出古人的女始祖崇拜,因?yàn)檫@些感生神話都崇拜女始祖,是她們生下了部族的男性英雄”[8]。
(二)《子羔》與始祖感生神話文本書寫的模式化
《子羔》對禹、契、棄的感生神話的記述不僅反映了戰(zhàn)國時人對先祖感生現(xiàn)象的認(rèn)識,而且是始祖神話文本模式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重要階段。《子羔》:
子羔問于孔子曰: “三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賤而不足稱也輿? 亦誠天子也輿?”孔子曰: “……女也,觀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劃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皕氏之女也,于央臺之上,有燕銜卵而措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劃于膺,生乃呼曰,‘欽’,是契也。后稷之母,有邰氏之女也,游于玄咎之內(nèi),冬見芙,乃薦之,乃見人武,履以祈禱,曰: 帝之武,尚使……是后稷之母也。三王者之作也如是……孔子曰: “舜其可謂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有虞氏之樂正苫卉之子也。”子羔曰: “何故以得為帝?”孔子曰: “……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3]193
《子羔》對三王感生神話的記錄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模式化。
筆者將禹、契、棄三人感生神話要素進(jìn)行提取并整理成表格如表2。

表2 《子羔》始祖感生神話要素
子羔問孔子三王者禹、契、后稷到底是人的兒子,但是其父親卑賤而不足稱道,還是確實(shí)是天的兒子。孔子則為子羔講述三王的感生神話,孔子認(rèn)為三王是天子。在《子羔》篇中記錄的夏商周三代始祖禹、契、后稷感生神話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固定的記述模式,感生神話的記錄要素也是相對整齊劃一的,包括其母系氏族、感生的地點(diǎn)、感生的經(jīng)歷等部分構(gòu)成,除缺失部分外,只有對棄的孕育時間未曾提及。對比《詩經(jīng)·大雅·生民》《詩經(jīng)·商頌·玄鳥》所載神話,《子羔》所載的神話細(xì)節(jié)顯然更多,更加整齊。在缺簡部分,子羔應(yīng)該還問了舜的情況,孔子認(rèn)為舜是受命之民,是人的兒子。子羔接著問孔子舜不是天子為何能夠成為帝,孔子認(rèn)為這是因?yàn)樗吹沦t。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上博簡之《子羔》篇中所記載的孔子對子羔問題的回答,主要為了突出舜的受禪為王因其有德,并非因其感天而生,從而強(qiáng)調(diào)“德”的重要性[9]。
始祖神話的模式化書寫的形成與發(fā)展,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在遠(yuǎn)古時期各種神話與傳說在各部落之間互相流傳,其各要素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借鑒,因此出現(xiàn)了主要要素較為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隨著部族間交流的擴(kuò)大乃至民族融合的加劇,各部族自發(fā)生成的感生神話,也在彼此協(xié)調(diào)借鑒,從而在更大的人群共同體范圍內(nèi),建構(gòu)著某種結(jié)構(gòu)性的知識。”[10]80各部族之間各個獨(dú)立的神話要素之間的互相影響,從很早之前就開始了,甚至從各部族的神話相互流傳、接觸時就一直存在著,但其共同發(fā)展成為較為統(tǒng)一的模式,有著共同書寫的要素,則要到各部族深入融合甚至成為統(tǒng)一的政權(quán)后才得以實(shí)現(xiàn)。就現(xiàn)有史料典籍看,大概直至戰(zhàn)國時期,感生神話在同一史料中以體系化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總體而言,雖然在兩漢以前還并未形成所有史籍都達(dá)成并遵守的固定、統(tǒng)一的關(guān)于始祖人物感生神話的記述方式,但關(guān)于禹、契、棄三王的感生神話書寫則較為固定,這對后代感生神話的發(fā)展和記述方式的最終固定,提供了素材。
(三)鄭穆公、褒姒感生故事與感生神話敘事的發(fā)展
《國語》《左傳》是記載春秋史事的重要典籍,具有某些相似的史料來源,在漢代分別被稱為春秋經(jīng)的內(nèi)傳和外傳。他們記載的鄭穆公、褒姒感生故事細(xì)節(jié)豐富,語言生動,具有很強(qiáng)的文學(xué)性。隨著史學(xué)、文學(xué)的發(fā)展,感生神話的文本從內(nèi)容、形式兩個方面都更加豐富起來。
戰(zhàn)國時期開始出現(xiàn)了感生夢這一感生神話的新形式。關(guān)于鄭穆公感生經(jīng)歷的背景為燕姞之夢,燕姞夢到天使給予其蘭花,并對她說以蘭花為其子,而后燕姞孕而生子,是為穆公。女性于夢中受到神明或祥瑞的感召,這是比較標(biāo)準(zhǔn)的感生夢,是筆者所見的先秦成書的材料中,唯一關(guān)于感生夢的記載,而且,鄭穆公的身份也與其他出現(xiàn)在先秦感生神話中的人物有很大不同。其他諸如禹、契、棄,都是始祖人物,而鄭穆公則是鄭文公與其妾之子,不僅有明確的父母記錄,而且僅為國君庶子。感生物為蘭,蘭成為一種象征,不具有圖騰的意義。袁珂認(rèn)為從神話的廣義來看,神話是存在于各個時期的,原始社會有神話,奴隸制社會也有其自己的神話,甚至封建社會等進(jìn)入階級社會以后每個歷史時期都有神話。但是每個時期的神話卻也各有不同,在神話的內(nèi)容、形式等方面表現(xiàn)出來。舊的神話在歷史的進(jìn)程中不斷發(fā)展、演變,逐漸變成新的神話,或被新的神話所代替;而與此同時,新的神話也隨著歷史的進(jìn)展在不斷地產(chǎn)生,或者從舊的神話轉(zhuǎn)變過來。無論何時,舊的神話都沒有完全消失,新的神話也在不斷產(chǎn)生[11]。感生夢或具有一定的事實(shí)基礎(chǔ),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感生夢這一神話形式,是以女性在孕期所做的胎夢為事實(shí)基礎(chǔ)記錄的[12]。自漢代及后世對新出現(xiàn)的感生經(jīng)歷的記載都轉(zhuǎn)變?yōu)楦猩鷫舻男问?則是感生神話形式發(fā)生變化的必然表現(xiàn)。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鐵器牛耕的出現(xiàn)與應(yīng)用,以及各諸侯國之間的不斷爭霸與戰(zhàn)爭迫使各國變革圖強(qiáng),使自身國力強(qiáng)大,從而令生產(chǎn)關(guān)系與生產(chǎn)力相適應(yīng),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同時,各國的紛爭、社會的變革以及私學(xué)的興盛又極大地促進(jìn)了一批批有知識的思想家的誕生。隨著人類經(jīng)濟(jì)、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迅速發(fā)展,對某些自然現(xiàn)象的認(rèn)識也有了較大提升,人類已經(jīng)可以用較科學(xué)的眼光和認(rèn)知看待嬰孩的孕育與誕生,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的感生神話已經(jīng)不能夠滿足時人的認(rèn)知,因而亟需用一種新的方式來替代神話,承擔(dān)感生的各種宗教、社會及政治功用。因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與天及神明聯(lián)系密切的夢成為了合適的選擇。
做夢是普遍的生理現(xiàn)象。泰勒認(rèn)為遠(yuǎn)古時期初步發(fā)展的人類更愿意探究生與死、醒與夢之間的關(guān)系[13]351。原始哲學(xué)用靈魂的概念來解釋這些問題。如甲骨卜辭中有很多對夢的記載,泰勒認(rèn)為商人就是因?yàn)閷ψ晕覊糁械木跋蟛荒芎侠斫忉?視夢因乃出自鬼魂所致[13]66。將夢與靈魂相聯(lián)系的觀念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商人也不例外。商人將夢看成一種鬼魂給做夢者的預(yù)兆,并通過占夢來預(yù)測兇吉,有時還會通過儀式來禳除噩夢,占夢、禳夢的習(xí)俗為后代所沿用。榮格則認(rèn)為:“個人無意識主要是由各種情結(jié)構(gòu)成,集體無意識的內(nèi)容則主要是‘原型’構(gòu)成。”[14]原型在三代時期甚至更久遠(yuǎn)的時代里,則常常表現(xiàn)為宗教中的某些形象,如神話中的人物、圖騰等,而后逐漸發(fā)展為三類,即天、自然神、祖先神。西周以后至春秋時期,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對天、神、巫的信仰氛圍依舊濃厚,而人與神明溝通的方式便是夢,在夢中、神明可以 預(yù)示未來的發(fā)展,并對人們的行為進(jìn)行指導(dǎo)。這與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提出的對夢解釋——“(夢)主要是預(yù)見未來,是與精靈、靈魂、神的交往”相契合[15]。清華簡《程寤》記載周武王母親夢見商王的朝廷長了很多的荊棘,姬發(fā)把周朝廷的梓樹種在其外,化成松柏棫柞等堅固的樹木。太姒醒了以后,周文王不敢占夢,舉行一系列禳夢的儀式,最后“占于明堂,王及太子發(fā)并拜吉夢,受商命于皇上帝”[16]。該篇將太娰之夢與上帝受命聯(lián)系在一起。《周禮·春官宗伯》有記載通過日月星辰的變動和運(yùn)行占夢之吉兇。《周禮》將夢與天地之會、陰陽之氣、日月星辰聯(lián)系在一起,并將夢根據(jù)反映情緒加以分類,反映出戰(zhàn)國時期隨著天文歷法等知識的增長,對夢理性化的思考及占夢術(shù)的發(fā)展。《左傳·昭公三十一年》記載日食:“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zhuǎn)以歌,史墨為其占卜”[1]4618,可看做“以日月星辰占夢”的實(shí)例。《列子》亦將夢與天地、陰陽聯(lián)系在一起,認(rèn)為“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yīng)于物類”是夢產(chǎn)生的原因[17]。《左傳》岳麓秦簡中有占夢書,“對于做夢日期與夢中景象的聯(lián)系,秦簡《占夢書》主要采用了五行學(xué)說進(jìn)行解釋”[18]。天地陰陽五行與夢的結(jié)合,反映了古代人民對天人關(guān)系的思索。正如燕姞之夢,在這個故事中,伯鯈是燕姞之祖,反映了靈魂概念,他的身份又是天使,將夢與天、上帝聯(lián)系在一起,與《程寤》反映的觀念相似。燕姞因夢而生子,雖與后來的感生夢仍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兩者所反映的上帝通過夢以一個象征物(蘭、日、月等)而使女子生子,該子最終成為后嗣的上天授命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見,在戰(zhàn)國時期,夢已經(jīng)成為公認(rèn)的神明傳達(dá)命令的介質(zhì),由此,它成了在過去感生神話之中表達(dá)神明感召行為的載體,實(shí)現(xiàn)了感生神話向感生夢的感生方式轉(zhuǎn)變的第一步。
褒姒感生神話是目前所見第一個以女性為感生人物的感生神話,在傳統(tǒng)歷史敘述中,西周的亡國與褒姒有莫大關(guān)系。如果說始祖感生是為了突出始祖的神圣性,那么褒姒感生則是為了妖魔化褒姒,為周失天命作了注腳。鄭穆公的感生神話頗具中性色彩,其創(chuàng)作目的固然要解釋其何以以庶子而為諸侯,但同時亦聚焦于穆公的個人生命的盛衰。褒姒的感生神話則完全是負(fù)面性的,感生神話的作用從塑造祖先的神圣性進(jìn)一步擴(kuò)展了。
總之,先秦時期的始祖感生神話起源于母系社會時期,故事定型于父系社會時期。在戰(zhàn)國時期,夏商周三代始祖感生神話文本已經(jīng)具有模式化特征,故事包括始祖之母,感生地點(diǎn),感生物,感生過程,孕期,出生后的神跡等多種要素。感生的主體擴(kuò)展到諸侯國君、女性,出現(xiàn)了感生夢的敘述方式。
二、兩漢時期對先秦感生神話的采用與創(chuàng)造
“感生夢”在兩漢時期逐漸發(fā)展,并成為眾多感生神話的主流書寫方式。筆者將兩漢時期的史料、典籍等文獻(xiàn)中關(guān)于感生事件描述的材料整理總結(jié)如表3。

表3 兩漢典籍中的感生神話

續(xù)表3 兩漢典籍中的感生神話
表3中共有21條相關(guān)材料,涉及11個人,除在先秦史料中已出現(xiàn)的禹、契、棄、鄭穆公、褒姒的感生神話,又增加了秦大業(yè)、漢高祖、漢文帝、漢武帝、劉協(xié)和王政君的感生事件。其中,秦大業(yè)的感生神話同過去夏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話類型相同,而從漢高祖劉邦開始,新增的感生神話則都以感生夢的形式出現(xiàn)。
在上表梳理的21條材料中,依據(jù)先秦時期關(guān)于感生神話的書寫內(nèi)容和記錄的時代,筆者認(rèn)為兩漢時期對感生神話與感生夢的記錄與書寫,主要有三種不同的形式。其一,對先秦時期已有記錄的始祖感生神話采取基本采納、保持原型的方法,如此二十余條記錄中對禹、契、棄三人的感生神話都基本保持其原貌。其二,對存在時代為兩漢以前,但卻沒有相對應(yīng)感生神話的部分祖先,則采用仿照禹等三人感生神話的經(jīng)歷,仿寫其感生神話。先秦西漢時期,將當(dāng)時的文獻(xiàn)、材料進(jìn)行抄錄或修改,直接或間接地用于文作中,是普遍現(xiàn)象[27]9。其三,對漢代以來的對于時人而言較近的朝代帝王,則采用創(chuàng)新感生神話的方式,以感生夢的形式描述其感生經(jīng)歷。
(一)沿用
先秦時期已有的關(guān)于感生神話的記載主要有禹、契、棄、鄭穆公、褒姒五人,筆者摘錄兩漢時期關(guān)于此五人感生神話的內(nèi)容以表格的形式對比于如表4。
在對禹的感生神話描寫中,《吳越春秋》《蜀王本紀(jì)》都基本保存了《世本》中所見的大禹感生事件要素,如“吞薏苡,胸拆而生禹”,但又加入了關(guān)于禹出生地的信息,如“嬉于砥山”“生于石紐”等;在對契與棄的感生神話描寫中,《列女傳》《史記》等史籍則加入了部分故事細(xì)節(jié),使得事件的發(fā)生更加合理,情節(jié)更豐富。在對鄭穆公、褒姒感生神話的描寫中,《史記》則完全遵循了原有史料,只是對文字進(jìn)行凝練,使其更簡潔、清晰、順暢。由此對比可見,在漢代成書的史料典籍中,對于過去已經(jīng)存在的史料記載,后代史家們基本采用采納、整理、擴(kuò)充的方式,或通過對原有事件的解釋與完善,在原神話情節(jié)主體不變的基礎(chǔ)上,使其內(nèi)容更有邏輯性,體系更加完整。
中國史學(xué)家自古就有著“秉筆直書、撰成信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將撰成“實(shí)錄”式著作作為自己寫史的終身要求。孔子提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觀點(diǎn),將“信”的要求加以明確。史家在面對前代已有的對事件的記述時,往往會采用其事件主體,或者在不改變原有事件主體的情況下進(jìn)行修飾。于是,在兩漢時期所見的史書中,對先秦時期已存在的感生神話,都保持了其基本原貌。
(二)仿照
在感生神話中,其人物時代存在于兩漢之前,但在先秦時期沒有相關(guān)感生神話且感生形式類似于禹等始祖的僅有一則,材料出于《史記》: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yè)。[21]476
一般認(rèn)為,秦大業(yè)的感生神話向來被學(xué)界認(rèn)為是司馬遷對商代“玄鳥生商”感生神話的仿寫。《史記》中此條對秦大業(yè)感生神話的記錄是目前可考的最早的關(guān)于秦始祖的感生記載,且其要素構(gòu)成也與契的感生神話極為相似,都記述其祖先為女性吞玄鳥之卵而生。根據(jù)《左傳》的記載,嬴姓諸侯國郯國的國君郯子,談到他的祖先少皞繼位時,“鳳鳥適至”,因此用各種鳥的名稱來命名官員,如管天時的官叫鳳鳥氏,管春分秋分的官叫玄鳥氏等。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少皞是東夷部落的首領(lǐng),東夷部落以鳥作為圖騰。秦人姓嬴,雖然周代分布于今天的甘肅、陜西等西部地區(qū),但他們與郯國都是嬴姓,并且同祭祀少皞,雖然位于西部,但他們的祖先同屬于一個部落,以鳥作為圖騰。商人、秦人都認(rèn)同鳥是自己的祖先,因此司馬遷在撰寫秦始祖的感生神話時參考了商契的感生經(jīng)歷。

表4 先秦西漢感生神話要素對比

續(xù)表4 先秦西漢感生神話要素對比
(三)創(chuàng)新
在漢代史傳中所記載的感生事件中,除上述所論的沿用與仿寫的兩種感生神話記載外,剩余的八條感生經(jīng)歷都記載了兩漢時期的人物,共涉及五人,除王政君、劉協(xié)的感生夢記錄出于《漢書》《后漢書》外,其余對漢高祖、漢文帝、漢武帝的感生夢記述同時存在于《史記》與《漢書》中。這七條感生經(jīng)歷的記載與秦及以前的感生事件記載有明顯的區(qū)別,主要表現(xiàn)為:感生方式由現(xiàn)實(shí)感生變?yōu)橛蓧舾猩?在感生事件記錄中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父親的信息,擁有感生神話的人物不再僅僅局限于始祖人物,而是出現(xiàn)了普通帝王,甚至皇后。根據(jù)材料,關(guān)于漢高祖、漢文帝、漢武帝三人的感生神話都是在《史記》中首次出現(xiàn)。《史記》作為漢代眾多史傳中成書相對較早的一部史學(xué)著作,司馬遷根據(jù)其所處時代的認(rèn)識及需求,改變了原有感生神話的書寫方式,一定程度上創(chuàng)新了他們的感生夢,這也是《史記》及其后代史傳中感生夢逐漸成為感生神話書寫主流的開端。
三、兩漢時期感生神話書寫模式的新特點(diǎn)
在兩漢時期對先秦史料的采用與完善中,基本確立了感生夢作為感生經(jīng)歷的主要描述方式,并逐漸形成固定模式。從具體的事例看,史傳中對人物感生經(jīng)歷以感生夢的形式呈現(xiàn),基本始于司馬遷之《史記》,其對漢高祖、漢文帝等人的感生夢事例描述,開啟了后世以感生夢描述近代帝王的先河。除了感生夢敘述模式,與先秦時期相比,兩漢時期感生神話書寫模式還具有以下新特點(diǎn)。
(一)父親的角色的出現(xiàn)
中國遠(yuǎn)古時期以神論體系為主,先民認(rèn)為在強(qiáng)大的自然界面前人力渺小,因此祈求神靈保佑、順應(yīng)天命所為才可以順?biāo)彀捕?特別是殷商時期,敬鬼事神,無事不卜,以天為治,然而殷商最終并沒有逃脫滅亡的命運(yùn)。因而周滅商后,統(tǒng)治者吸收殷商滅亡的教訓(xùn),認(rèn)識到殷商之亡不在于鬼神,而在于“民”,由此認(rèn)識到人民的作用,進(jìn)而奠定了“敬天保民”的天命觀。周公后人周祭公謀父論及此,認(rèn)為殷商因?yàn)椤按髳河诿瘛薄⑴c民為惡而最終走向滅亡,而周則因?yàn)椤笆律癖C瘛薄扒谛裘耠[而除其害”順應(yīng)民意而從天之愿,得以受命[6]6,正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1)此言出于《尚書·泰誓》,為古文尚書,而不見與今文《尚書》,而古文尚書學(xué)界基本統(tǒng)一其為漢代偽造,但此言亦為《左傳》《國語》所引,《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和昭公元年,《國語周語》中及《國語鄭語》皆有引,因此此言當(dāng)為古本《泰誓》之語,可以視為西周春秋時人的理念。即天從民之所欲,可以通過民意而知天意。雖然周朝已經(jīng)提出了“民本”的觀點(diǎn),但并沒有完全摒棄鬼神之說,雖然講“保民”,但同時提及“敬天”。《尚書·康誥》中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1]432認(rèn)為天威難測,但民意卻可見。在時人觀念認(rèn)同中,民意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天意,從民意的根本更是為了順從天意。在此時,天是最高的意志存在,尊天敬神的神權(quán)思想仍然是西周時期的主流思想。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禮崩樂壞,隨著各諸侯國的強(qiáng)大及發(fā)展,宗周原有的禮樂制度名存實(shí)亡,宗法制度的約束力也隨之衰減殆盡,以人為本的思想開始逐漸沖破神本思想發(fā)展開來。子產(chǎn)提出“天道遠(yuǎn),人道邇”[1]4529的觀點(diǎn),《管子》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28]以人為本的觀點(diǎn)被正式提出。此后,人重于神、民重于天的觀念不斷發(fā)展,“人者,天地之心也”[1]3083、“天生萬物,唯人為貴”[1]3800的言論被傳播,開始確立并鞏固了人的地位,而不再唯天命是從。
感生神話的書寫中,女性所感之物往往是現(xiàn)實(shí)存在的,是部族圖騰或神奇事物,如殷商之玄鳥、周始祖與巨人足跡,其結(jié)果是圖騰扮演了父親的角色,嬰兒沒有實(shí)質(zhì)上的父親。但隨著人的地位被確立以及父權(quán)社會對帝系明確、父親身份清晰的要求,感生神話的書寫轉(zhuǎn)化為感生夢。在此類事件記述中,胎兒有明確的父親,而神明只扮演著天意的授權(quán)者,“因此感生所誕之人不再是天神之子,而是被天神賜予神圣特質(zhì)的凡人之子”[29]。
(二)感生神話政治性的增強(qiáng)與感生范圍的擴(kuò)大
在先秦時期感生神話的擁有者,往往都是部落始祖型人物,但至兩漢之際,感生范圍進(jìn)一步擴(kuò)大,不僅朝代的開創(chuàng)者如漢高祖劉邦擁有感生神話,其他皇位不甚穩(wěn)定的帝王如漢獻(xiàn)帝,甚至女性,如皇后王政君也擁有感生夢。感生夢涉及范圍的擴(kuò)大,是兩漢時期感生經(jīng)歷書寫形式較之先秦時期的一大改變。兩漢時期擁有感生夢記述的帝王有漢高祖、漢文帝、漢武帝、王政君、漢獻(xiàn)帝五人。詳細(xì)分析他們的特質(zhì),可發(fā)現(xiàn)他們擁有感生夢的出發(fā)點(diǎn)可能不一,但殊途同歸,最終都是使用感生夢的形式神化其出身,明確其天命所屬。這些神話產(chǎn)生都有政治性需求,各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自身的統(tǒng)治地位,以輿論的形式證明其政權(quán)合法性,以天命的方式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抬高自己的威信。除了加強(qiáng)在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軍事等領(lǐng)域的統(tǒng)治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加強(qiáng)在文化上的統(tǒng)治力,即文化上的認(rèn)同感與歸屬感,而感生夢即是其采取的手段之一。
陳勝吳廣起義開啟起兵反抗暴政之始。劉邦作為萬千起義人之一,并沒有顯赫的出身與血統(tǒng),即使以武力獲得天下的統(tǒng)治權(quán),其仍舊沒有擁有名正言順的統(tǒng)治者地位,這就亟需以傳統(tǒng)的天命觀,以君權(quán)神授的形式對其擁有政權(quán)的合法性進(jìn)行粉飾,而“感天而生”便是必然且必要的選擇。正如呂宗力所言,感生神話是“漢代人為論證漢皇室統(tǒng)治正當(dāng)性而推出的政治神話。”[30]感生夢成為漢高祖塑造其神圣血統(tǒng)、明確其神圣地位的重要方式。當(dāng)然,僅有感生夢的輿論鋪墊是不足的,因此史傳中我們可見,對劉邦天命地位的塑造,除了感生夢外,還有對其異貌、異行、祥瑞等各方面的記述,如司馬遷記載劉邦左腿上有七十二顆黑痣,又言其醉酒斬白蛇,并有“五行聚于東井”的大吉之兆。感天而生是其出身的象征,而異貌、異行等則是天意的證明,這就使其受命于天的身份更加明確和突出。無論是感生夢的形式,還是對其異貌、異行的描述,其本質(zhì)都離不開政治上的需求。一般而言,開國之君名正言順的繼任者不僅可以繼承其權(quán)位,亦可以繼承其天命與神圣的血統(tǒng),因此不再需要以“感天而生”的形式獲取人民對其統(tǒng)治地位的認(rèn)可。但是如若繼任者獲得皇位歷經(jīng)曲折,或者其本身并非皇位的首選繼承者,便需要進(jìn)一步借天命之名為自己的繼位打造輿論陣地。如漢文帝、漢獻(xiàn)帝等皆是如此。漢獻(xiàn)帝其作為兩漢時期的最后一位皇帝,其正出于宦官與朝臣爭權(quán)而皇室卻極度衰弱的時期,其繼位實(shí)為董卓廢漢少帝而立,并非名正言順地對皇位的繼承。因此漢獻(xiàn)帝的感生夢可以以天命的形式對其繼位加以解釋,“感天而生”是上天的安排,是天意的表達(dá),是人力不可相抗的力量,漢獻(xiàn)帝的感生夢明確佐證了其天命所至的地位。如漢文帝,其登基為帝也是克服了重重阻礙,但為其構(gòu)建感生夢的經(jīng)歷后,則成了他是天選之子,是上天早已注定的統(tǒng)治者,而其所受的阻礙則成為磨礪他的一部分,因此,無論他遇到何種問題,皆能沖破重重障礙,最終成為名正言順的帝王。帝王感生夢這一形式的構(gòu)建,成為明確其統(tǒng)治與政權(quán)合理性的重要方式。袁珂指出:“統(tǒng)治階級不但借感生神話宣揚(yáng)天命思想,并且自己也創(chuàng)造感生神話。”[10]94本質(zhì)上說,帝王的感生神話是晚起的政治神話,是統(tǒng)治者應(yīng)現(xiàn)實(shí)要求而授命史官創(chuàng)造的神話。
在原始社會部落制的社會形態(tài)下,部落聯(lián)盟的首領(lǐng)采用禪讓制的形式,其權(quán)力和地位不能世襲罔替。但自夏朝進(jìn)入階級社會始,有了家天下的觀念,并采用世襲制代替過去的禪讓制,逐漸形成了政治權(quán)力相對集中的君主專制制度。因此秦統(tǒng)一前的夏、商、周三代都相對應(yīng)的有其始祖感生神話。而感生神話這一神化出身的描述形式在兩漢時期轉(zhuǎn)變?yōu)楦猩鷫舻男问?正是其由最初的遠(yuǎn)古時期人類對自然、圖騰的信仰與崇拜轉(zhuǎn)變?yōu)樘烀^與君權(quán)神授思想成為社會主導(dǎo)思想的標(biāo)志。感生夢在本質(zhì)上繼承了感生神話核心,使感生者擁有被上天賦予的神圣地位和血統(tǒng),是天意之下的皇位擁有者,其子孫亦是名正言順的繼任者,從而保證對國家治理權(quán)的把控。如若一旦其失去天命至血統(tǒng)和地位,其自身甚至后代也將失去擁有皇位的正統(tǒng)性,失去統(tǒng)治國家的合法性,感生夢在輿論層面所具有的塑造與鞏固作用,是其他的任何真實(shí)性敘事所無法企及的,因此自漢代以后,歷代王朝開國之君或繼位之君多以感生夢的形式強(qiáng)調(diào)自身血統(tǒng)與天命的地位,這實(shí)際也成為史家撰寫帝王的固定形式。筆者對我國古代帝王的感生神話與感生夢記述進(jìn)行統(tǒng)計,最終得出,五胡十六國時期感生神話最多,而宋及以后則相對較少,這與五胡十六國時期各國戰(zhàn)亂紛爭、政權(quán)更迭、皇位常常易主不無關(guān)系。
總體而言,漢代史傳所載的感生神話表現(xiàn)出了新的特點(diǎn),一方面,對于先秦時期已有的感生神話,漢代史傳基本采納,保持其原有的記述主體不變,至多加以簡單梳理或細(xì)節(jié)修飾使其更具邏輯性;另一方面,對于過去史料沒有感生神話記述的人物,則依據(jù)時間分段,分別采用仿照和創(chuàng)新的手法書寫其感生經(jīng)歷。即人物存在于兩漢以前的、屬于始祖人物或地位尊崇甚至重于始祖人物的,采用仿寫的方式,將其感生神話記述為類似于先秦時期史料已有的人物感生神話,而對于兩漢時期的人物,則遵從時人的已提高的認(rèn)識,廢棄以神話、母系氏族、圖騰等因素為主的書寫模式。采用感生夢的方式,明確對父親的記述,并一定程度上擴(kuò)大了感生經(jīng)歷的記述范圍,不僅始祖人物,甚至優(yōu)秀帝王甚至皇后都成為可以擁有感生經(jīng)歷的人物。漢代對于感生夢的記述仍處于變動和發(fā)展的階段,還未完全形成固定的書寫方式,也未形成完整的體系,但其對先秦時期感生神話的改變和發(fā)展,對魏晉及后世感生神話的書寫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是史傳中關(guān)于感生神話書寫形成的重要一筆。
四、結(jié)語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由于遠(yuǎn)古時期產(chǎn)生的受到圖騰崇拜、英雄崇拜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族群的始祖感生神話逐漸成型,并參與到祭祀祖先過程中,成為稱頌祖先的工具。當(dāng)商周王朝建立以后,最終,形成了以《生民》《玄鳥》等詩歌形式的文本,并在國家祭祀過程中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夏商周三代始祖被視為圣人,在士人馳騖爭鳴的過程中,三代的始祖的感生神話被當(dāng)作論據(jù)進(jìn)行使用,在此過程中,始祖神話逐漸模式化,母族、感生地、感生經(jīng)歷、受孕時間、生產(chǎn)時神跡等諸多要素被組合在一起,一方面增加了三代始祖的神圣感;另一方面也便于記憶。隨著史學(xué)、文學(xué)的發(fā)展,《國語》《左傳》等史籍的出現(xiàn),感生神話主體擴(kuò)大到女性、諸侯國君,其文本更加生動具有故事性。感生夢這一模式開始出現(xiàn)。
漢朝的史學(xué)家對于前代流傳的感生神話,通過沿用、仿寫、創(chuàng)造等方式進(jìn)行利用,三代始祖神話更加生動,對于本朝的帝王則運(yùn)用了感生夢這一模式進(jìn)行神話,塑造其神圣性。在感生神話中父親的角色開始鞏固,感生神話的政治性更加明顯,對君主的神化也從始祖擴(kuò)展到普通帝王。感生夢這一寫作模式對后世影響深遠(yu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