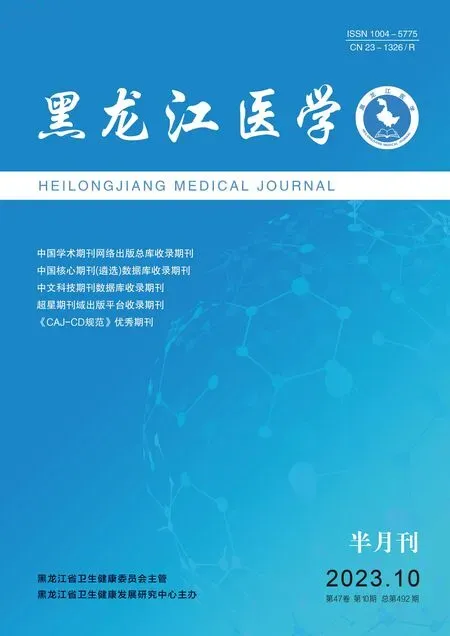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與膿毒癥患者預后關系的研究分析
宋躍飛,梁偉智,于海建
廣州市花都區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廣東 廣州 510800
膿毒癥在重癥監護室中是一種病死率高的嚴重疾病。早期識別高危膿毒癥患者對于提高膿毒癥患者生存率是十分重要的。膿毒癥第三次國際共識[1]中,膿毒癥定義為宿主因嚴重感染而導致患者器官功能衰竭的一種嚴重疾病。目前,臨床上缺乏早期識別高風險膿毒癥的生物標記。近期的研究[2-5]表明,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在重癥及晚期腫瘤患者中有較好的預測、預后價值,而外周血NLR 具有容易快速獲取、技術成熟、結果可靠等特點。因此,本研究探討膿毒癥患者外周血NLR及其變化與膿毒癥患者預后的關系,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6年5月—2020年1月廣州市花都區人民醫院收治的301例膿毒癥患者的臨床資料。(1)納入標準:①符合Sepsis-3診斷標準為由感染導致的宿主嚴重器官功能障礙且SOFA 評分≥2 分。②住院時長≥4 d。(2)排除標準:①年齡<18 歲。②懷孕和圍產期婦女。③合并影響患者血常規白細胞、中性粒細胞等指標的血液系統疾病或腫瘤。④放化療期間的腫瘤患者。⑤先天性或后天獲得性自身免疫缺陷性疾病。⑥口服或靜脈使用糖皮質激素≥1個月。本研究為回顧性分析患者的臨床資料,在研究過程中,不會泄露患者住院、住址等識別身份的信息。本研究不會對患者做出任何臨床干預措施,不會對患者診治造成任何影響,屬于可免除知情同意書的范圍條件,并通過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受理號:2020010)。
1.2 研究方法
收集確診后膿毒癥患者的年齡、性別、基礎疾病、確診后第1天的血肌酐(SCr)、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B 型腦鈉肽(BNP)、紅細胞沉降率(ESR)、血乳酸(Lac);收集確診后第1天及第4天患者血常規中的白細胞計數(WBC)、中性粒細胞(NEU)、血小板(PLT)、淋巴細胞(LYM)和降鈣素原(PCT)、C反應蛋白(CRP);分別計算患者第1天和第4天的NLR、序貫器官衰竭評分(SOFA)、急性生理學與慢性健康狀況評分Ⅱ(APACHE Ⅱ)以及計算它們第4 天與第1 天的差值(NLR=第4天NLR-第1天NLR,SOFA=第4天SOFA-第1天SOFA,APACHE Ⅱ=第4 天APACHE Ⅱ-第1 天APACHEⅡ);根據患者28 d 預后結局分為存活組和死亡組,根據NLR是否>0分為NLR升高組和NLR非升高組。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M(QL,QU)]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 檢驗方法。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ROC曲線下面積(AUC)評價NLR對膿毒癥患者28 d死亡風險的預測能力,均采用雙側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301 例膿毒癥患者中,28 d 內死亡123 例(40.86%),存活178 例(59.14%)。其中,男212 例(70.43%),女89例(29.57%),平均年齡(73.81±13.41)歲;感染部位:下呼吸道感染254 例(84.39%),腹腔感染17 例(5.56%),皮膚軟組織感染13 例(4.32%),頭頸部感染1例(0.33%),泌尿道感染16 例(5.32%);致病菌結果:銅綠假單胞菌36 例(11.96%),嗜麥芽窄食單胞菌3 例(0.99%),大腸埃希菌22例(7.31%),鮑曼不動桿菌14例(4.65%),肺炎克雷伯桿菌12例(3.99%),金黃色葡萄球菌11例(3.65%),肺炎鏈球菌2例(0.66%),奇異變形桿菌1 例(0.33%),陰溝腸桿菌1 例(0.33%),未有明確病原菌回報199例(66.11%)。
2.2 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情況
與存活組對比,死亡組第1 天及第4 天的SOFA、APACHE Ⅱ、PCT 均高于存活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死亡組第4天的WBC、NEU、NLR、CRP均高于存活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LYM、PLT均比存活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年齡、性別、基礎疾病、AST、ALT、Lac、BNP、ESR 和第1天白細胞、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血小板、NLR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死亡組第4 天的NLR、SOFA、APACHE Ⅱ均較第1 天升高,而存活組第4天的NLR、SOFA、APACHE Ⅱ均較第1天下降,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情況

表1(續)
2.3 NLR升高組與NLR非升高組資料情況
NLR 升高組與NLR 非升高組患者相比,第1 天和第4天的SOFA 評分、APACHE Ⅱ評分、PCT 和第4 天的WBC、NEU、NLR、CRP 均顯著升高,第4 天的血小板、淋巴細胞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NLR升高組患者28 d病死率比NLR非升高組顯著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年齡、性別、基礎疾病、AST、ALT、Lac、BNP、ESR 和第1 天白細胞、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血小板、CRP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NLR升高組與NLR非升高組資料情況

表2(續)
2.4 NLR、SOFA、ANPACHE Ⅱ及其變化、LYM、PCT在預測膿毒癥患者28 d預后價值結果
ROC 曲線顯示,第4 天的NLR、SOFA、淋巴細胞、PCT、APACHE Ⅱ均比第1天有更好的預后預測價值(ROC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929、0.950、0.904、0.734、0.969),且ΔNLR、ΔSOFA、ΔAPACHE Ⅱ也有良好的預后預測價值(ROC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868、0.935、0.947);以第4天ΔNLR>14.51 為預測28 d 死亡臨界點時,其敏感度為74.8%,特異度為98.9%,陽性似然比值為68.000,陰性似然比值為0.255;以ΔNLR>0.07 為預測28 d 死亡臨界點時,其敏感度為73.2%,特異度為93.8%,陽性似然比值為11.806,陰性似然比值為0.285,見表3。

表3 NLR、SOFA、ANPACHE II及其變化、LAM、PCT在預測膿毒癥患者28 d預后價值結果
3 討論
研究[6]表明,相對于早期膿毒癥患者持續的“炎癥風暴”,后期膿毒癥患者多處于持續的免疫抑制狀態。這提示膿毒癥患者機體的免疫狀態是動態變化的[7-9],而且免疫功能的變化影響膿毒癥患者的預后,淋巴細胞計數變化與膿毒癥患者預后相關,這已在早期研究[10]中被證實。
機體在受到感染時,循環血中性粒細胞被激活并釋放炎癥介質,以協助清除病原菌。但是過度激活的中性粒細胞會釋放過多的炎癥介質,如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等,對宿主器官產生損害,持續、嚴重的損害會引起宿主器官功能衰竭[11]。淋巴細胞作為人體的免疫細胞,其功能和數量是保證機體正常的免疫反應正常運行的基礎。研究[12]發現,膿毒癥患者由于機體內的炎癥反應,T 淋巴細胞功能低下,程序死亡受體—1(PD-1)表達升高,進而促使淋巴細胞凋亡增加、大量的淋巴細胞凋亡及功能喪失[13],促進免疫功能抑制的發生。研究[14]表明,NLR不但能反應患者機體的免疫功能狀況,而且對預測危重癥和腫瘤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價值[2-3,15-16]。機體大量淋巴細胞凋亡導致淋巴細胞數量持續低下,提示患者處于免疫抑制狀態[17]。Drewry 等[18]也證實,當重癥患者出現持續淋巴細胞低下時,患者預后較差。在本研究中,NLR變化主要為死亡組的淋巴細胞計數變化,死亡組與存活組的NLR、LYM、NEU 在確診后第1 天均無顯著差異,但死亡組患者第4 天的NLR、NEU 較存活組均顯著升高,而淋巴細胞顯著降低,提示死亡組患者淋巴細胞仍然處于低下水平,機體存在免疫抑制。相反,存活組患者第4天的淋巴細胞較第1天升高,提示存活組患者免疫功能恢復正常。臨床中,早期識別高危膿毒癥患者以及患者的免疫功能狀態對于診治膿毒癥十分重要。NLR能反應膿毒癥患者免疫功能,因此,動態監測NLR在膿毒癥患者病程中的變化有助于識別高危患者。楊萌等[3]研究發現,動態監測NLR 對血流感染膿毒癥患者有較好的預測價值。Choi等[19]研究也證實,在腫瘤的輔助治療中,NLR 的變化與晚期乳腺癌患者預后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NLR升高組第1天、第4天的SOFA、APACHE Ⅱ評分、PCT、病死率均高于非升高組,提示NLR 升高組病情更危重、預后更差。本研究結果顯示,NLR的變化對于膿毒癥患者28 d預后有良好的預測價值。
綜上所述,膿毒癥患者外周血NLR與膿毒癥患者28 d預后結局密切相關,及時通過NLR發現高危膿毒癥患者以及動態監測NLR變化,有助于評估患者28 d死亡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