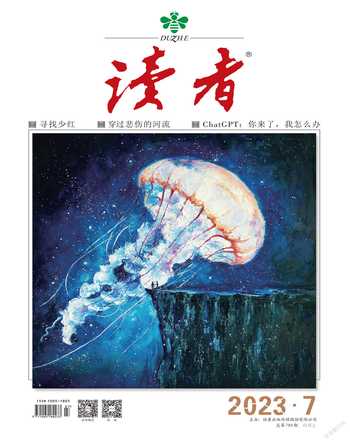一個名為“表演”的殘酷游戲
林秋銘

張頌文
置換
在開始學習表演之前,張頌文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導游。在家鄉廣東韶關帶團時,常常會去南華寺,他會帶著一群游客走一段長長的路,走到寺廟的后山,那里有一眼泉。他會這樣介紹這眼泉,泉水可以治病,洗一下眼睛,一生都能看懂人。
“其實這段話并不是指定的講解詞,我是在重復我媽的話。”他說。
張頌文13歲那年,母親被確診為肝癌晚期。某一天下午,她牽著張頌文,坐著搖搖晃晃的公交車去了南華寺,走的就是那條路。那是張頌文第一次看到那眼泉,他們用礦泉水瓶灌了很多泉水,母親說這是神泉,能治好她的癌癥。
好多次,他上著上著學,就會突然冒出母親去世的念頭,便猛地從學校跑去醫院確認她還在不在。13歲是一個少年躁動的年紀,醫院卻像個牢籠。
一次又一次的虛驚讓張頌文感到疲乏,生離死別的概念變得模糊。他開始想,這樣的日子,什么時候才能結束——這樣的想法讓他在母親去世后的十年里,常常感到內疚,“我一聽到別人提起媽媽就會止不住痛哭,我總覺得內心愧疚……沒有在來得及的時光里讓她得到安慰。”
后來,他一次又一次地帶著游客走過那條長長的路,去看那眼泉,復述著母親的話,“我一到那個地方,就會很想她。”
年少喪母,給張頌文的心里制造了巨大空洞,而命運的愈加殘忍之處則在于,他似乎無法逃避這種傷痛。無論是做導游,還是后來做演員——每次演到與別離、死亡相關的情節,他都會調出這段記憶,因為只有這樣,那種痛苦才是真的。
張頌文并非天賦型演員,入行晚,快25歲時才去北京電影學院學表演。他外形條件沒有那么優秀,普通話也不標準。因此,關于張頌文的表演經歷,最初的故事都與勤奮刻苦有關。負責他們班級的主任教員張華記得,那時,張頌文會洗幾顆石子含在嘴里,給舌根和舌尖增加壓力。和同學、老師講話,張頌文也不會把石子放下,那幾顆小石子就在他嘴里翻滾。半夜12點,電影學院的操場上,總有兩個同學在高聲念臺詞,一個是海清,另一個就是張頌文。
周一圍是張頌文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在他早年間的博客中,還留著張頌文勤奮的印記。學表演,也需要像戲曲演員那樣出晨功,每天早晨6點到7點,去操場上吊嗓子,兩年,4個學期,每一天,作為班長的張頌文都會帶著同學們去出晨功,風雨無阻。
若干年后,他終于成了一名擁有“教科書般演技”的演員,經典的表演片段一個又一個,每一個都細膩到令人驚嘆——這也正是演員這個職業之于張頌文的殘酷之處——這些所謂的表演質感,都是他用過往人生中真實經歷的難堪、窘迫、掙扎、苦痛置換來的。
成為演員
在做演員之前,張頌文擁有太多不同的職業經歷。
母親去世兩年后,16歲的張頌文開始了打工生涯,在各個工廠之間流轉,一個接著一個工種地換。他干過安裝空調的活兒,去日歷廠糊過日歷,在“亞洲汽水廠”洗汽水瓶。他還要在流水線給瓶子貼上標簽,傳送帶如果快一些,就得追著瓶子跑。“亞洲汽水”四個大字天天在他眼前晃,亞洲,多么宏大的詞,再對比自己的工作,他覺得有點諷刺。
后來,他又去做了幾年導游,這份職業讓他變得愈加敏銳。他得靠著這個技能生存——旅游大巴上,他需要快速判斷每個人的家庭背景、情緒和興趣,及時做出反應。他干得不錯,連續多年榮膺“廣東省優秀導游”。
因為喜歡看電影,張頌文準備嘗試考北影的導演系。1999年,北影導演系不招生,他陰差陽錯地學了表演。
好友林家川記得,在北影念書期間,班長張頌文一副文質彬彬的模樣,熱愛洗澡,喜歡讀報紙。他是班上年齡最大的學生。他好像在追趕什么,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25歲考電影學院,我知道這應該是我終身的職業了,我已經沒有時間了,我得拼命。”
但畢業后,他四處碰壁。好友周一圍的蟄伏期比他短得多,在畢業后的第三年,接戲的節奏漸漸走上正軌。周一圍開始向各個劇組推薦張頌文:“我有個哥們兒叫張頌文,他是個好演員。”但每次都沒能成功。
跑龍套的日子,收入也不穩定。有一年,張頌文全年的收入就3萬多元,后來才變成7萬多元。很多合作過的人都說,張頌文絕對是一把好手,可每次談價錢時,對方又說:“張老師,你是藝術家,但是你出演這個角色,你沒有流量,你懂嗎?”
周一圍記得,在張頌文等待的日子里,他們會去潮白河上劃皮劃艇,或者騎個小摩托,去河對面的某一個小區散步,一人買一支冰淇淋,坐在長椅上觀察小區里的人走來走去。通常都是張頌文說話,他聽。兩個人看著湖面,聊河邊住著的老年人會怎么打發接下來的時光,聊如何與形形色色的人相處。冰淇淋吃完了,再騎著摩托車回家。
寒冷
2009年11月,因為市區的房租太貴,張頌文正式搬到北京郊外的院子。搬進去的那天,暴雪來臨,到了晚上,郊區的氣溫降到了零下21攝氏度,室內只比室外高了3攝氏度,倒出來的水瞬間結冰。因為沒有關好水閥,第二天,張頌文家的水管被凍裂了,水流了一院子,結成了一層亮晶晶的厚冰。后來很長一段日子里,他都需要面對“寒冷”——這是他的生活處境,也是他的職業環境。
當然,如果能去劇組,就沒那么冷了。2010年,他前后演了5部戲,但是戲份很少,在劇組的天數加起來也只有10天。原本只有一天的戲,他硬是和導演拖了4天。原因是酒店暖和,還能吃上盒飯。
回到家,最冷的一段日子,張頌文會在中午12點拉來椅子坐在院子里曬太陽,然后想起母親。母親早年間是下鄉的赤腳醫生,村民們常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疑難雜癥,赤腳醫生的專業能力有限,但總會想很多方法來解決問題。母親最喜歡給人支的招是曬太陽,她告訴張頌文,曬太陽會讓一個人開心,因為,在她看來,很多病的根源是沮喪。她告訴張頌文:“文仔,一切都會有辦法,只要你清楚你的目的,就一定能找到。”
奇妙一夜
也就是在張頌文搬去郊區的那一年,他偶然結識了經紀人趙玉德。趙玉德曾經擔任許多香港演員的經紀人,帶過張家輝、舒淇、余文樂等,但因為欣賞張頌文,他專門從香港搬來北京,只負責張頌文一個人。
張頌文說,趙玉德“縱容”了他8年。他從不逼迫張頌文接戲,將選擇權交給他。張頌文也就那樣等著。
直到2016年,有一天聊天,趙玉德慢悠悠地說:“頌文,能不能積極一點,其實你有機會的,很多人欣賞你。你總是看到人家的劇本說,那個戲不行,不拍,但是后來人家拍出來也很合理。是不是有些不行的東西,可以在現場通過努力把它變好?”他還強調了一句,“你40歲了。”張頌文搖搖頭:“哎呀,無所謂。”
趙玉德攤了牌:“你能不能為我努努力,我現在連房租都交不起了,還這樣陪你熬,你能不能做些改變?”那是趙玉德第一次向張頌文坦白自己的窘境。張頌文愣了,答應趙玉德“今年多接幾部戲”。那一年是張頌文最拼命的一年,一口氣拍了四部戲,包括電影《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和《西小河的夏天》。但也是在那一年,趙玉德因為心肌梗死突然去世,倒在了張頌文的家里。
張頌文在北京八寶山為趙玉德辦了葬禮。那天來了很多人,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前后有4家經紀公司派人前來悼念,他們和張頌文握手、擁抱,安撫的話沒講幾句,便直接表達了要和他簽約的意愿。他回絕了所有邀約,把自己藏起來,那之后足足有兩年沒有拍戲,“我經紀人剛去世,我就馬上簽約別的經紀公司,我會覺得很對不起他,像背叛了他。那8年,最苦的時候,他和我在一起。”
他回憶起為了拍《西小河的夏天》,他和趙玉德提前到拍攝地浙江紹興踩點。夏天快來了,他們倆在西小河的溪邊散步,閑聊著。趙玉德提議:“咱倆合張影好不好?”他們請路人幫忙拍了一張。
趙玉德去世兩年后,張頌文因為電影路演在紹興停留,他又獨自回到那個舊地。張頌文依然請經過的人拍了一張同樣角度的照片。張頌文抬起手臂,做出了搭肩的動作。拍照姿勢和兩年前一樣,只是,趙玉德不在了。

張頌文
后來,綜藝節目《演技派》里,排演了一個類似的故事。故事主角的兒子去世了。起初,他不愿意相信這個事實,在朋友的勸說下逐漸接受。故事的結尾,喪子的父親和兒子的朋友合影時,父親喊“等一下”,然后突然抬起手,搭在空中。這個動作正是表演老師張頌文建議的。那場表演后,在場很多人因為抬手的動作哭了。他們問張頌文:“你怎么會想到這個點?”他沒有跟他們講與趙玉德的故事。“我不知道別人演戲用什么辦法,我的方法就是用真實的生命體驗。”
他想起在北影那幾年,老師問他們覺得表演是什么?班上的同學給了各種各樣的答案,老師都不滿意。誰也不知道,老師的那個答案是什么。
張頌文回去查百科全書,找到那個關于表演的字面解釋——“表演是演員利用自身的材料塑造人物的心理變化過程。”“自身的材料”,對于張頌文,這就是他經歷的所有生活,而表達這一切的工具,就是他的肉身。“你生活中一定有難堪的地方,你不會像講段子一樣,說自己的不堪,講的時候會讓你難過。但演員不可以,演員就得不停地挖出來,要回憶所有的悲傷,回憶我的不堪,我的窘迫。我不能忘記它,甚至要不停地、反復地去回憶親人離開的時候,我的反應是什么樣。你知道嗎,每一次回憶對我都是一次傷害,所以方法派表演是很傷身體的,我不能來假的。”張頌文說,“我要允許很多人進入我的體內,侵蝕我的心,這是對演員最殘酷的地方。”
他至今仍留著趙玉德的一件黃色皮夾克,在一些榮耀的時刻,他會穿上。他還在家里為趙玉德掛上一串風鈴,風吹過的時候,會發出好聽的聲音。
而這個故事的更殘酷之處在于——后來,《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公映了,趙玉德相信了8年的事情,終于發生了,但他沒有看到。
提著那口氣
寒冷的日子終于過去了。
張頌文開始變得忙碌。他已經忙得很少回到北京的家,每次回去,停留時間都很短。但他還是會盡力保持自己和生活的距離。
編劇史航對一個畫面記憶很深。今年春天,演員王悅伊去橫店看望正在拍戲的張頌文,結束后,他們一塊兒去菜市場買菜。菜攤的老板娘舉著手機,聲音放得很大。一般人可能要么請她聲音小一點兒,要么趕緊買完菜離開。但是張頌文接過菜停住了:“大姐,你在跟誰說話啊?跟你的小學同學啊?你們現在60歲,這么多年一直都有聯系,真是個很幸福的人呢。”
“這種對人的留意和解讀特別好,我偶爾想起來也覺得倍受鼓舞。”史航說,“我只覺得他是好好地吃每一粒米,最后能夠讓自己不會挨餓、不會腹中空空的那種人。廣東人愛說一個詞,叫‘一碗安樂茶飯,我覺得頌文不管怎么大紅大紫,他還是他要的那種安樂茶飯。”
曾經采訪過張頌文的作者呂彥妮見證了他從冷到熱的過程。“我覺得他這么敏感的人,一路走來一定好辛苦。他經歷過很多不好的東西。他都沒有因此變成一個多么市儈的、圓滑的人,他還在以最大的熱忱待人和處事。”她也為張頌文擔心,這是一個充滿人設的時代,面對熱度,“輿論需要造一個人”。而這個被制造的人,或許會將張頌文身上的一點無限放大,但這樣一來,這個人也會離張頌文越來越遠。
去年,一篇《張頌文買不起房》的報道登出,惹得張頌文微博的私信箱塞滿了安慰的話語。一個人因為熱愛而堅守,他買不起房,忍耐著貧窮在繼續行走——這是人們期待的敘事。但這讓張頌文本人感到苦惱。張頌文厭煩外界為他貼上“貧苦”的標簽。事實上,在進入表演行業的后一個十年,他的待遇已經好轉,但大家不愛聽這個了。
后來,他不得不在微博上做出澄清——“來過我家的朋友都知道,我租的平房宅子雖然質樸,但被我收拾得非常舒適,滿園都是我種的花花草草,周圍的集市各種蔬菜瓜果也很劃算,很多朋友愛來我家小院做客,我猜他們是真心喜歡的,這樣的生活氣息給了我很大的安撫……”
這是這個殘酷故事的下一環——人到中年,終于守得云開,得到聲名,但此時,無論是年紀還是環境,都決定了他無法再享受年少時對成名的渴求和恣意。如今,他謹慎地伴著這些聲名生活,心里想的是,怎么平穩地站在水中央。
林家川去張頌文家里做客,即使屋里已經有了取暖設備,依然感覺很冷。張頌文說,自己想保持這種“冷”,這會使他清醒,“他害怕自己不平靜。這么多年看著身邊的人大紅大紫,也有失敗的,火了以后,是不是應該先等一等,冷靜一下”。
這一切并不難理解,在人生的前40多年中,張頌文一路沉浮,始終提著一口氣,一個人面對生活所有的難,然后一個人去解決。而當變化終于到來時,他或許會松口氣,但也只是松一下而已,因為,在他的意識,甚至習慣里,他還需要提著那口氣,自己去守住眼前來之不易的一切。
(千百度摘自微信公眾號“人物”,本刊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