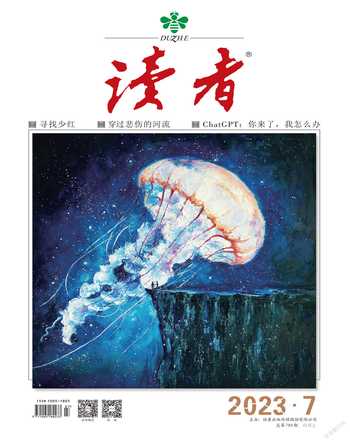有月光的生命
連中國(guó)

人的長(zhǎng)大,或許就是一個(gè)離精神故鄉(xiāng)越來(lái)越遠(yuǎn)的過(guò)程。看到現(xiàn)實(shí)里我們的那些窘態(tài),我想,教育最大的一個(gè)功能或許就是呵護(hù)生命。其實(shí),生命是嬌弱的,易破碎、易固化、易無(wú)聊、易盲從、易臣服、易為現(xiàn)實(shí)徹底所擒……而一年年、一屆屆,師生共浴在朗朗的月華里,至此生命里總有一捧清輝,遇澀滯以清明,遇枯癟以澤潤(rùn),遇黑沉以皎白,遇絕境以再升。
有月光的生命里,存有美。美,是一種在自由與柔軟中認(rèn)同了的方向。南宋詩(shī)人楊萬(wàn)里有幾句寫(xiě)月的詩(shī)頗妙:“溪邊小立苦待月,月知人意偏遲出。歸來(lái)閉戶悶不看,忽然飛上千峰端。”這活潑調(diào)皮的月色似乎支持了他的一生。他一生寫(xiě)下許多清新明快的小詩(shī),對(duì)大自然觀察領(lǐng)悟得既精妙又有趣。他目光新巧,美的每一個(gè)細(xì)小微妙的瞬間似乎都可以被他準(zhǔn)確地捕獲。中國(guó)歷史上,風(fēng)起云涌的大人物不少,生命里有純正的趣味、有意思的人有限,而楊萬(wàn)里是一個(gè)。
有月光的生命里,有自己的“境”,不容易被現(xiàn)實(shí)輕易征服。張孝祥在北歸途中,過(guò)洞庭湖,他說(shuō):“盡挹西江,細(xì)斟北斗,萬(wàn)象為賓客。”在滿月的輝光里,生命的筵席多么遼闊!他進(jìn)而更加疏放,不為現(xiàn)實(shí)所限。
有月光的生命很干凈,有一種皎潔的力量。我常常驚訝孫犁其人,他所生長(zhǎng)的環(huán)境,他所經(jīng)歷的社會(huì),他所面對(duì)的現(xiàn)實(shí),都不會(huì)促成、支持他變成那個(gè)樣子。我們驚訝于孫犁的那片世界:再艱苦貧窮的處境,水生的小褂也總是“潔白”的;再嚴(yán)峻壓抑的現(xiàn)實(shí),“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fēng)吹過(guò)來(lái),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再殘酷激烈的戰(zhàn)斗,我們也能看到“那一望無(wú)際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著陽(yáng)光舒展開(kāi),就像銅墻鐵壁一樣”……而水生嫂編席,必要的環(huán)境一定是:“月亮升起來(lái),院子里涼爽得很,干凈得很”。月色、荷香、浩渺的煙波、俏麗多情的白洋淀婦女構(gòu)成了孫犁文章特有的境界。隨著自己的年歲漸長(zhǎng),從孫犁先生潔凈的作品中,我甚至讀到了一種高貴的抵抗。莫言說(shuō):“按照孫犁的革命資歷,他如果稍能入世一點(diǎn),早就是個(gè)大文官了;不,他后半生偏偏遠(yuǎn)離官場(chǎng),恪守文人的清高與清貧。這是文壇上的一聲絕響,讓后來(lái)人高山仰止。”
說(shuō)起有月光的生命,在現(xiàn)實(shí)里會(huì)遭遇較嚴(yán)重的隔膜。從小學(xué)一直講到高考的簡(jiǎn)單的模式化的答題方法與泥沙俱下的大量練習(xí),壓住了生命的月華躍出黑黢黢山脊的可能性。如若我們生活在一個(gè)由青少年時(shí)代唯分?jǐn)?shù)論的“人”構(gòu)建而成的社會(huì)里,恐怕還不如生活在叢林之中吧。
我渴盼,也一直在努力,在我們的校園里,有健康爽朗的分?jǐn)?shù)。我這樣想,在現(xiàn)實(shí)中也這樣做,并且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月光與分?jǐn)?shù)可以不對(duì)抗,在月光里可以釀造出“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一般的分?jǐn)?shù)呢。釀造的過(guò)程里,師生都享有現(xiàn)實(shí)里的美好與幸福,也獲得了彼此最純摯的可以一生懷想的感情。
(舒 窈摘自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語(yǔ)文課Ⅱ》一書(shū),曾 儀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