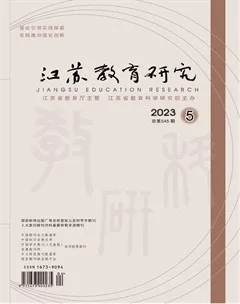“雙減”時代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的缺失與應對
陸韻?傅安妮?楊玥
摘要:“雙減”時代凸顯高質量家庭教養的必要性,但農村留守兒童家長因“身體離場”“學歷不足”“主體缺席”造成的文化資本缺失將加劇教育不公平。為推進“雙減”有效落實并實現政策公平,需沿著家庭文化資本的外在補償、內在激活與賦能創生三條理路展開如下舉措:以貫通課堂內外的優質服務補償家庭教育資源,以鼓勵多元發展的制度情境激活家庭精神財富,以開放合作共享的關系網絡創生家庭文化資本。
關鍵詞:家庭文化資本;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公平;“雙減”政策
中圖分類號:G6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23)05-0091-06
“雙減”政策回應了21世紀以來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重負、教育內卷、家長焦慮等系列問題,背后隱含著以優化公共教育服務和規范教育市場運行促進教育公平的深層邏輯,然而群體固有差異下的結構性矛盾對政策公平意圖的實現構成挑戰。截至“十三五”末,我國共有643.6萬農村留守兒童[1],他們面臨親情缺位、家庭教育薄弱的困境,更因家庭文化資本不足而處于學業競爭劣勢。家庭文化資本作為內化于家庭成員之中的知性與情感體系,較少受到外界社會力量干預,其不平等效應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2]。“雙減”時代學生課外時間的增加凸顯高質量家庭教養的必要性,闡明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缺失的隱憂并探尋應對舉措,不僅是有效落實“雙減”政策所需,也有利于促進城鄉教育公平。
一、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缺失的隱憂
家庭文化資本是家庭及其成員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氣質以及文化背景等資源總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發現出身于不同階級的孩子在學術市場中獲得的成就與文化資本分布狀況相對應[3]193。家庭文化資本與教育獲得之間的正向關聯也得到我國學界印證。城鄉家庭文化資本差距是形成學生學業成就差異的關鍵因素[4],家庭文化資本擁有量多少是影響農村留守兒童學業成就高低的重要原因[5]。“雙減”政策下家庭教育空間大大拓展,但對親子分離狀態中的農村留守兒童來說,家庭文化資本缺失會擴大成長空間差異。
(一)家長“身體離場”難以實現優質親子陪伴
“雙減”政策為高質量親子陪伴提供現實條件并激活了家庭教育的內生動力。文化資本的基本狀態是與身體相聯系的,其作用發揮需要行動者的親力親為[3]194。家庭教育中的身體化資本表現為父母在語言交流、情感互動和行為示范中向子代傳遞文化與修養。城市高學歷家長可在工作之余充分關注子女學習生活,給予子女細致的引導監督與鼓勵,與之進行深入情感交流并組織運動、旅行等豐富的親子活動。相比之下,農村留守兒童與家長之間缺乏長時間親密接觸,約40%的留守兒童一年與父親或母親見面次數不超過2次,約20%的留守兒童一年與父親或母親聯系次數不超過4次[6]。在家長“身體離場”的情形下,親子互動時空碎片化導致文化資本傳承機制斷裂[7]。父母無法及時觀測把握子女的學習狀態、習慣養成,更難身體力行地傳遞積極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雖然隔代教養方式解決了“溫飽照料”的問題,但仍存在重養輕教的弊端。因此,“雙減”時代學生自主安排時間增加使父母言傳身教顯得尤為重要,城市家庭陪伴潛力的激活與農村留守兒童家長身體化文化資本的缺失共同導致城鄉之間親子陪伴鴻溝擴大,形成生活教育、價值養成和情緒培養等方面的更大差距。
(二)家長“學歷不足”難以提供課后輔導資源
制度具有穩定性,新舊規則的更替存在遲滯效應[8],校外學科類補習班受到嚴格監管,但中高考競爭與篩選機制依舊存在,部分家長和學生戲稱“拼家長”時代已到來,家庭教育焦慮愈發凸顯。城市家長不僅會運用自身知識親自參與輔導,還可能會為子女鑒別選擇適宜的家教,盡力尋找替代性方式。學歷水平較高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更重視子女綜合素質養成,注重知識所轉化的見識、趣味、辨別力和判斷力,以及潛移默化中形成的認知圖式、審美趣味和性情傾向[9]。相比之下,雖然農村留守兒童家長并沒有因外出務工而放任對孩子的管教[10],但是由于自身文化學歷水平的限制,他們缺乏恰當的教育理念與方法,無力承擔課業輔導任務,更多地關注子女成績結論而忽視對學習過程的關心指導。因此,“雙減”時代家長文化學歷資本作用發揮空間放大,進城務工者文化知識局限與農村課外資源匱乏,將導致城鄉之間產生新型課外學習鴻溝[11],使得農村留守兒童在獲取課后輔導資源方面處于不利地位,拉大應試競爭差距。
(三)家長“主體缺席”難以融入家校社協同共育
“雙減”帶有重構家校社關系、形成高質量協同育人體系的深層指向。家長在不同組織機構之間的互動溝通能力屬于動態文化資本,是關聯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兒童學習品質的重要機制[12]。西方學者發現中產階層家長會與很多不同的組織機構發生互動[13],通過密切監測、積極協調來為子女尋找契機,幫助他們獲得有利于實現自我價值的經歷。類似的“母職經濟人化”現象存在于我國基礎教育階段,教育競爭與家長主義泛濫背景之下,部分城市高收入高學歷家長為提升子女學業成就與學校、校外機構展開積極互動。相比之下,農村留守兒童家長作為協作主體之一時常缺席家校社聯動。“雙減”落實后學校逐步優化作業內容并加強課后服務質量,然而學生學習基礎、學習能力上的差異客觀存在,農村留守兒童家長無法及時把握子女在課后服務中的學習體驗與反饋,較少與各類組織機構溝通子女的個性化學習需求。因此,農村留守兒童家長“主體缺席”使家校社之間出現溝通障礙,影響多方教育資源的整合作用發揮,形成協同合作方面的鴻溝,繼而引發學生學習能力發展方面的更大差距。
二、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缺失的應對理路
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缺失有著難以避免的客觀因素,既受到城鄉二元結構下社會福利不盡完善的影響,也與留守兒童家庭中繼承性文化資本的局限性有關,表現為存量不足與傳遞斷裂的雙重困境。但文化資本同時也與行動者的能動性緊密相關,站在教育公平立場上優化“雙減”政策效應,可依據文化資本產生與傳遞的規律,從補償、激活與創生三方面探尋應對理路。
(一)家庭文化資本的外在補償
學校的教育內容具有一定的文化偏向,這種偏向表現在一種城市生活的價值取向上[14]。農村子弟的家庭成長環境缺乏這類文化資本,從而面臨學習難度增加且學業成功概率降低的困境。因此,補償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的邏輯前提在于將該群體歸為“主流文化缺失”一方,他們并不具備提升子代學業成就的足夠文化資本,所以需要由外至內加以增補。補償邏輯假定當留守兒童擁有了與主流文化相契合的習慣、態度和價值觀等,就會改變文化資本相對弱勢的處境。“雙減”政策旨在回歸育人根本,強調通過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促進學生綜合素養提升。理想的家庭文化資本涵蓋助力子女個性化成長與全面發展的資源與氛圍。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的外在補償,意味著調動學校、社區與公益機構等多方力量,向留守兒童補充其家庭中缺乏的文化資源,包括個性化學業輔導資源與興趣愛好發展資源;同時,創造有利于創新思維訓練、核心素養培育及身心健康發展的空間與機會,使農村留守兒童能夠享受到與城市兒童或非留守兒童相近的課余生活。
(二)家庭文化資本的內在激活
有學者打破底層子弟學業困境的宿命論循環,提出包含先賦性動力、道德化思維和學校化心性品質在內的“底層文化資本”[15]。正是農家子弟發奮向上的精神動力和堅忍懂事的性情品格使他們能在學業競爭中攻克難關。因此,激活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的邏輯前提在于肯定留守家庭中存在有待開發的資源,所以需要從內部加以喚醒與激發。激活邏輯假定當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特有的文化資本被挖掘出來后,就會生成助力性因素彌補親子分離造成的文化資本缺失。“雙減”政策通過提升校內教育質量,為家庭教育與親子互動留出了更多時間空間。農村留守兒童家庭除了擁有勤奮樸素的生活觀念、本分務實的處事習慣,父母外出務工的積極行動還有利于彰顯“肯吃苦、輕享樂”的人生奮斗理念。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的內在激活,意味著從家庭本身發現有利于子女學習成長的文化資本,包括自立自強的生活態度與勞動技能、堅毅勇敢的精神意志等;同時,通過一定的制度條件與活動情境,促進這類家庭中已有文化資本的作用發揮,使農村留守兒童獲得學業發展的內生動力。
(三)家庭文化資本的賦能創生
社會學者迪馬吉奧開始用“文化流動”挑戰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文化流動更為強調行動者自身的能動性,認為家庭文化資本差劇并非固定,而是會通過后天努力逐漸拉平。為彌補自身文化資本的不足,行動者既能夠從學校等公共機構中汲取文化資源,也能夠開拓新的文化資源。因此,創生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的邏輯前提在于肯定留守兒童自身及其家庭成員有著創造文化資本的能動性,所以需要給予他們積極的肯定與助力。創生邏輯假定農村留守兒童家庭中自發生成的文化資本縱使不與社會主流文化和優勢家庭背景相關,也能夠成功轉化為現實的學業成就。“雙減”政策突出家庭教育主體責任,強調家校社協同的良好教育生態構建。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不再是一件“私事”,而是處于社會網絡之中且頗受公眾關注。因此,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的賦能創生,意味著維持文化資本的流動性并拓寬其邊界,形成一套協作干預和激勵反饋的賦能機制,通過啟發、鼓舞與牽引使留守兒童家庭發揮能動性,結合家庭實際創生出對子代學業發展有積極效應的文化資本。
三、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缺失的應對策略
任何一項教育改革政策的細化推進都需充分考慮不同社會群體的生存境遇和發展需求,應對“雙減”政策背景下農村留守兒童家長因“身體離場”“學歷不足”“主體缺席”造成的文化資本缺失及其連帶的教育不公平現象,需充分發揮家校社多方的能動性與協作性,沿著家庭文化資本的外在補償、內在激活與賦能創生三條理路建構如下實踐舉措。
(一)以貫通課堂內外的優質服務補償家庭教育資源
家庭文化資本補償的重點在于將優質的教育教學服務、素質養成服務和價值培育服務拓展至農村留守兒童的課外時空,彌補其家庭教育人力智力的多重匱乏。
1.建立留守兒童課后服務跟蹤體系。為實現教育公共性目標,農村學校需兼顧普惠性服務與個性化服務,在保障全體學生底線需求的基礎上為留守兒童建立個性化的課后服務跟蹤體系,全面把握他們的學習反饋與發展需求,彌補家長不便參與子女學業監管與家校溝通的局限。一方面,實施動態監測,對留守兒童在課后項目中的出勤情況、作業表現、學習習慣、參與程度等情況加強評估,發現他們的學習困境與興趣轉向并及時提供針對性指導;另一方面,加強全程跟蹤,關注留守兒童在學校課后活動與校外自主學習活動之間的銜接性,與留守兒童家長保持聯絡溝通并給家庭中的監護人提供適宜的教養建議。
2.增設農村地區素質拓展公共平臺。在校外培訓資源本就欠缺的農村地區,需發動政府、學校、公益機構和志愿者的力量,建立藝體類培訓機構、增加相關專業師資,彌補家長無法幫助子女獲取有效課外培訓資源的局限。一方面,為留守兒童參與綜合素質培訓開辟綠色通道,減免其培訓費用,從而減少留守兒童家庭的教育支出;另一方面,保障素質拓展公共平臺的常態化有效運行,避免形式化、運動式的短期活動效應,因地制宜地設立培訓項目,吸納公益經費補充場地、設備、工具之需,嚴格審核教員上崗資質,充分保障培訓質量。
3.形成社會情感能力培育共同體。“雙減”背景強化學生學習認知能力與社會情感能力同步發展的必要性。個體生活經歷影響社會情感能力的發展,在農村留守兒童人格養成關鍵期,學校應聯合社會多方力量形成社會情感能力培育共同體,彌補家庭中親子分離的局限。一方面,在學校課程教學中貫穿社會情感能力培育,設計交互式、協作式、游戲化教學活動,使留守兒童在學習知識的同時養成德性與情感;另一方面,加強學校、社區與留守兒童家庭的聯結,通過構建常態化的積極互動關系,提供人際交往機會與必要的情感支持與情緒疏導。
(二)以鼓勵多元發展的制度情境激活家庭精神財富
家庭文化資本激活的重點在于通過構建有利于不同家庭背景學生多元成長的制度情境,賦予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的精神財富以獨特價值,并促其轉化為留守兒童學業發展與個性成長的有效助力因素。
1.完善學生學業成長多元評價制度。轉變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缺陷論”的慣常思路,會發現留守家庭也有對子女學業成就的期待,父母的外出拼搏經歷和勤勉努力精神為子女學業成長提供先賦性動力,不乏留守兒童具備刻苦自強的學習品格。針對留守兒童學業成長的多元評價,需擺脫學業成績的單一結論性指標,增加對積極學習品質的持續性激勵。一方面為留守兒童建立動態檔案,充分關注學生在學習方面的思想態度、行為習慣、成長軌跡;另一方面在留守兒童中樹立品學兼優、勇敢奮進的典型,表彰他們的努力付出與堅持進步,從而激發學生本人的學習信心與家長的教育期待。
2.建立留守家庭文化實踐激勵制度。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的物理阻隔并不完全割裂親子之間的情感紐帶,親子分離與隔代教養的生活實踐里孕育著獨立精神、家庭韌性與奮斗品格等文化資本。學校需通過系列激勵制度保障留守家庭文化實踐的價值并促其轉化為學生學業成就。一方面使作業內容布置與課外實踐安排緊密關聯不同類型家庭的生活經驗,例如學會一種家務勞動、了解父母工作、獨立完成假日規劃等,讓留守兒童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獲受到關注與價值認可;另一方面打破家校活動和親子互動的限制,邀請留守兒童監護人參與家校活動、交流教養經驗、分享家庭故事,重視留守兒童家庭在子女教養中的付出。
3.構建家校遠程聯動協作共育制度。留守兒童父母穿梭于城鄉之間,有機會打破文化水平局限、形成新的見識與視野,能夠對子女帶來正向動力和榜樣力量。通過遠程聯動,學校一方面應向在外務工家長傳達子女在校學業情況與身心發展狀況,鼓勵家長加強與子女的遠程溝通與情感交流,分享城市生活與工作見聞;另一方面需向家長遠程提供家庭教育能力提升相關培訓,指導家長充分汲取務工所在地的科普藝體等方面公共文化資源,利用假期時間合理安排親子活動,陪伴子女閱讀、游覽、觀影和參與社會實踐。
(三)以開放合作共享的關系網絡創生家庭文化資本
家庭文化資本創生的重點在于將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納入開放合作共享的交往關系之中,使他們在多種社會力量的賦能支持下發揮主觀能動性,吸收與融合關系網絡里的文化資本并結合自身潛力創生出新的家庭文化資本。
1.通過異質關系網絡提供外在指引。用“授人以漁”的方式培育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生產文化資本的意識和能力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異質型社會關系互動為弱勢者改變不利處境提供通路,學校或教育行政部門需借助政策安排,在公益機構與留守家庭之間、城市高學歷家庭與農村留守家庭之間建立幫扶關系。一方面,通過異質關系的建立向留守家庭呈現家庭教育方式理念的多種樣態,激發家長尋求各方資源,提升子代教育成就的動機;另一方面,借助異質社會關系協作互助的持續運行,形成家庭文化氛圍營造、子女教育資源汲取和學習習慣培養方面的切實舉措。
2.通過同質關系網絡提供內生動力。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在農村留守兒童家庭中普遍存在,同質關系網絡的建立有利于相似境遇者之間的共情交流與經歷分享。因此,無論是公共機構還是留守家庭本身,都需注重農村留守兒童家長群體的同質關系網絡搭建。一方面通過典型案例展示,發揮留守兒童中學業表現優異者的示范引領作用,增強留守家庭父母的信心與動力,提高他們對子女學業成就的期待;另一方面通過增進交流,使相同境遇者之間的經歷分享成為家庭文化資本創生的途徑,緩解留守家庭父母的焦慮無奈情緒,并推進家庭教養經驗的傳播與實踐。
“雙減”政策的有效落實呼喚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同步提升、協同配合,農村留守兒童親子分離狀態下的家庭文化資本缺失將擴大城鄉教育差異,引發愈加嚴重的不公平問題。突破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特殊境遇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制約,需擺脫“社會結構-行動者”二元對立的僵硬框架,從單純的決定論走向靈活的互構論,將家庭文化資本看作可變的、流動的、生成的,充分發揮多方行動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通過家庭文化資本的補償、激活與創生,從“扶貧補給”式的幫扶逐步轉向“助人自助”式的引領,不僅有利于破解農村留守兒童學業困境的循環,而且能夠彰顯多樣化家庭中獨特文化資本的豐富表象與教育意涵,使農村留守兒童在“雙減”時代實現更好的學業發展與個性成長。
參考文獻:
[1]郁靜嫻.重塑鄉村活力,給留守兒童更多關愛[N].人民日報,2021-07-09(19).
[2]劉精明.中國基礎教育領域中的機會不平等及其變化[J].中國社會科學,2008(5):105.
[3]皮埃爾·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蔣國河,閆廣芬.家庭資本與城鄉學業成就差異——基于實證調查基礎上的相關分析[J].青年研究,2006(6):28.
[5]李亞琴.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的關系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9:82.
[6]桂杰.2018《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約40%的留守兒童一年與父母見面不超過兩次[EB/OL].(2018-10-16)[2022-08-05].news.cyol.com/yuanchuang/2018-10/16/content_17690554.htm.
[7]陳昕苗,衛甜甜.鄉村文化傳承中的留守兒童成長困境解讀——基于文化資本視角[J].青少年研究與實踐,2019(4):8.
[8]馬奇,奧爾森.重新發現制度:政治的組織基礎[M].張偉,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54.
[9]張和平,張青根,尹霞.家庭資本、校外培訓與教育機會公平[J].教育學術月刊,2021(2):10.
[10]2020年度《留守兒童藍皮書》暨中國留守兒童心理發展報告發布[J].新西部,2021(1):128.
[11]余輝.“雙減”時代基礎教育的公共性回歸與公平性隱憂[J].南京社會科學,2021(12):151.
[12]王元.家庭資本與教育代際流動:基于學習品質的研究[J].基礎教育,2020(10):108.
[13]安妮特·拉魯.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M].宋爽,張旭,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95.
[14]俎媛媛.我國教育的城鄉差異研究——一種文化再生產的視角[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6(2):24.
[15]程猛,康永久.“物或損之而益”——關于底層文化資本的另一種言說[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6(4):83.
責任編輯:石萍
*本文系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年度課題“‘制度-行動互構視角下浙江省義務教育‘公民同招政策實施跟蹤研究”(22NDQN275YB)、浙江省教育廳一般科研項目“教育公平視野下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文化資本補償機制研究”(Y202044097)、浙江省教育科學規劃重點課題“高校農村寒門學子的文化資本‘逆襲與教育引導策略研究”(2021SB026)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2-12-02
作者簡介:陸韻,湖州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講師,浙江省鄉村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社會學;傅安妮,湖州師范學院碩士研究生;楊玥,湖州師范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