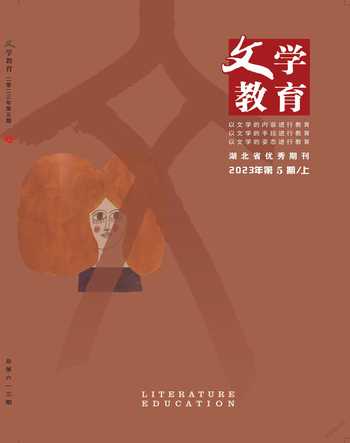魯迅《野草》中的情感撕裂與重建
閆賢
內容摘要:《野草》的創作是魯迅情緒激蕩下冷靜思考的產物,是自己親手解剖自己的過程,其中表現出來的怪誕、跳躍的語言文字正是魯迅以夢境的方式審視自己精神世界的結果。清醒認識到自己本質的自我意識讓魯迅負面情緒長期積壓,所以碰到兄弟失和、愛情糾結等生活工作失意的導火索之后讓魯迅有了情感宣泄和精神重構的迫切需求,《野草》正是承擔了這樣的作用,其中不同人格的撕裂、拉扯是魯迅探究自我、宣泄情感的過程,同時也是重建精神自我療救的過程。
關鍵詞:魯迅 《野草》 自我分裂 自我療救
《野草》作為魯迅唯一的散文詩集,一直以來備受學界的關注,不止一個學者把《野草》比作魯迅的“自畫像”。有學者說過魯迅的偉大之處在于敢于審視自己,他看穿國民性的同時也看到了自己的本質,這是他一直以來苦悶彷徨的根源,當自我意識占據主導地位即主體不斷進行自我反省的時候,內心的“自我”概念就會被模糊化,而不斷把自己當作旁觀者和被審視者,而一個人頻繁與自己曾經有意、無意產生的思想進行辯論并不斷否定自己的過程無疑是痛苦的,這樣的心態讓魯迅的情緒徘徊在崩潰的邊緣,巨大的心理壓力讓魯迅急需一個發泄的中介,《野草》中“自我分裂”的寫作手段正是通過夢境和自我分裂式的對話紓解內心的孤獨與煩悶。
一.《野草》中表現出的自我分裂
從醫學的角度來看,精神分裂是“患者認知、情感、意志和行為等精神活動與周圍環境的不協調,與現實脫離”[1]2而“精神分裂最主要的癥狀就是自我分裂”[2]9。從醫學的癥狀來看自我分裂會“產生一個或多個幻聽不斷批評自我或者會產生兩種幻聽不停地互相批評、咒罵”[2]9,而造成自我分裂這種精神病的外在力量則被認為與弗洛伊德所說的超我、本我和本能形成的矛盾有相似之處,也就是說自我分裂大都是由心理情緒積壓和變化造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野草》中表現出來的自我分裂也只是他表現內心矛盾和壓力的一種寫作手段。所以分析《野草》要更偏向于感受魯迅賦予文字的情緒變化以及文本中的話語蘊藉。
當時初入文壇還帶有些許希望想要療救中國人精神的魯迅正如他在《秋夜》中描繪出的弱小但擁有美夢的小粉紅花,而棗樹則是已經失去希望而依舊樣反抗絕望的那個孤獨的魯迅。“我”意識到笑聲是從“我”自己的嘴里發出來的,“我”在審視“我”自己無意識的行為,否則就可以直接表達“我發出了笑聲”而不是“我聽到這聲音就在我嘴里”,“我”在有意識地審視自己無意識的行為(夜半的笑聲),它雖然潛藏于內心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個人最真實的內心世界,而“我”意識到自己無意識的行為之后“我”的第一反應是“趕緊砍斷我的心緒”,也就是“我”在否定“我”之前的思想以及這種思想下產生的行為,這里“我”已經發生了人格上的分裂。不過這種自我分裂式的創作在同時期的《彷徨》里也有所表現,《弟兄》中沛君以為弟弟得了猩紅熱之后夢到弟弟死后他們一家的生活場景“他看見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鐵鑄似的,向荷生的臉上一掌批過去……”[3]491,沛君對夢中自己的行為感到害怕并且無法控制,兄友弟恭的外表和自私自利的內心都是沛君自己,但卻通過夢的方式表現出他和平時完全不一樣的心理,這正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典型的本我和超我的矛盾,沛君在批判自己心中維護自我利益的最真實的想法,就是因為是真實存在的所以才會產生恐懼,這里的自我分裂是沛君自己不曾意識到的,但卻是魯迅有意而為的寫作手段。除此之外《影的告別》更是公認的對話式的創作,甚至有學者提出“《影的告別》是自我分裂與沖突的典型,從標題即可看出”[4]37,李歐梵也在《鐵屋中的吶喊》中寫道“‘影的形象顯然是代表著詩人的另一自我”[5]112,影與本體“我”告別,選擇獨自遠行,正常情況下,“我”與影子本是一體,但文中卻要把二者分離,而且是“我”的附屬品——影子主動提出的,影子提出的三個“不愿”是對“我”的否定。《求乞者》雖然不像《影的告別》那樣直白,但“求乞”和“布施”兩個對立的詞同時出現在“我”的思緒當中,也就是“我”在求乞者和布施者兩個身份中轉換,當“我”成為求乞者時得到的答案是被布施者厭惡,也就是被“我”厭惡,原文中這樣說到“我將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6]7而“煩膩、疑心、憎惡”這三個詞語正是前文中“我”是布施者時給予求乞者的答案,也就是布施者的“我”否定了作為求乞者的自己。《過客》也是這種身份的自我糾結與否定,女孩和老翁一個充滿希望一個滿眼絕望,《希望》認為無論是希望還是絕望都是虛無的,所以女孩和老翁的存在也是值得質疑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兩種聲音互相否定的過程是“過客”內心最真實的存在,所以他才會有一瞬間想要停下來的猶豫,甚至不斷提醒自己“不能停下”,可以說過客的堅定是在自我否定的基礎上完成的。《過客》完成后與許廣平的通信中,魯迅這樣說“同我有關的活著,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這意思也在《過客》中說過”[7]62,還原到《過客》中“同我有關的”這種話的主語只能是“過客”,那就可以表明“過客”是魯迅自己的一個影射,而女孩和老翁是“過客”思想里的兩種聲音,所以《過客》里的三個人物就是魯迅內心的三種聲音,其中“過客”產生的猶豫其實是魯迅自己的猶豫,《過客》的創作就是為了逼迫“過客”也就是魯迅自己的第三種聲音堅定“行走”的選擇。精神分析法提出三重人格結構學說——伊德、自我和超我,簡單來說,“伊德”是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意識不到但是卻在意識中起重要作用的“無意識”;可以把它理解為“最想做的事”,“自我”則受到現實世界的影響,在現實的基礎上滿足本能的需求;“超我”是社會道德的高標準,通過社會的期望來壓抑自己的本能。最能表現魯迅自我剖析過程的是《墓碣文》,“我”夢到自己與墓碣的對立,正是“我”直擊自己內心的過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夢的理論表明“由于人的欲望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滿足,便采取一種迂回的方式表現在睡夢中”[8]47,所以“我”夢到死尸在抉心自食,其實是“我”在探尋自己的內心,而死尸被壓抑的“我”,有學者提出“魯迅用夢中的 ‘我竭力逃避著死尸的追隨做結尾,意味著這個‘我在竭力的逃避著另一個‘我的追隨”[9]103。同時也說明這種逃避正是“我”在盡力否定那個解剖自己的“我”,自己對自己的否定與恐懼正是自我分裂的有力證明。錢理群在分析《死火》時表示“任何人都逃脫不了死亡的宿命,人只能在這個大前提下做出極其有限的選擇”[10]284,所以“我”看似在問死火,實則是在問自己,而魯迅看似讓“我”與死火相遇,實則是在看清死亡的本質之后對自己內心的探尋,最后“我”與死火都逃不開滅亡的命運并不是魯迅的悲觀,而是一開始魯迅就已經想明白“我”最終的歸路,那是“我”乃至任何人都逃不開的大前提。
以自我分裂為方法進行寫作,即使作家自己不是精神病患者,但也一定會有自己內心的矛盾與掙扎,這些批判與否定一定會不自覺地滲透到文本當中,更何況魯迅有意識地進行自我分裂和夢境相結合的創作就是在理清內心的矛盾。
二.《野草》的自我療救功能
《野草》中表現出的自我分裂式書寫以及以夢境為底色的創作使得文中充滿了荒誕的描寫,雖然以夢境為依托使得一切荒誕的表述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但夢境并不僅僅是為了給荒誕矛盾的現象一個合理的安排,同時也蘊藏著魯迅自我療救的深層內蘊。
《野草》中表現出來的自我分裂是魯迅有意為之的寫作手法,但同時也是魯迅自己心理壓力過大造成的結果。《野草》創作于1924年到1926年間,這三年間魯迅先后經歷了兄弟失和、愛情初遇、女師大風潮以及三一八慘案等生活工作方面的重重事件,這些沉重的枷鎖不斷堆積在魯迅的內心,以至于魯迅彷徨低落的情緒急需宣泄。1923年8月2日魯迅搬出了他一直以來用心維系的大家庭,家庭的離散給魯迅帶來了沉重的打擊,黃喬生說“在事發之后一段時間里,兄弟倆各自內心都翻騰著失望、憤怒的波濤,甚至其后的許多年,乃至終身,也難以忘懷,魯迅寫了《頹敗線的顫動》等文章,宣泄心中的郁悶”[11]153。經歷了幼年喪父的魯迅,早早就擔起了“長兄如父”的責任,在物質和精神上都給予弟弟們扶持,但兄弟失和讓苦心經營的大家庭一夜之間傾覆,內心的郁悶可想而知。同時在創作期間魯迅也遇到了他的愛情,有學者也提出《野草》是魯迅獻給許廣平的愛情詩,這種說法太過絕對,但不能說完全沒有愛情因素的影響。1906年26歲的魯迅就被迫迎娶了沒見過面的朱安,黃喬生這樣描寫魯迅結婚那天的場景——“王鶴照(從13歲起在周家當傭工)看到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魯迅的臉——感覺自己受騙的新郎晚上把頭埋在被子里哭了”[11]23。魯迅是孝順的,他在1925年寫給趙其文的信中說“我有時很想冒險、破壞,幾乎忍不住,而我又一個母親,還有些愛我,愿我平安,我因為感激他的愛,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11]31。魯迅認為朱安是母親給他的禮物,他除了好好接受別無他法,朱安的存在一直提醒著魯迅自己是封建禮教的一部分,但這種壓抑的情緒不能發泄在母親身上甚至不能發泄在朱安身上。直到遇到許廣平,這種情緒不但沒有消解反而更加濃烈,因為“愛情雖然能點燃他生命的火花,但在新舊文化與新舊道德的雙重夾擊下,魯迅無論作出何種選擇,一時都無法解決現實生活中道德責任與愛情自由的兩難問題”[12]27。初遇愛情的魯迅在面對朱安以及與許廣平師生身份阻隔的情況下內心不斷猶豫,一邊是愛情一邊是名分,這樣道德和情感的拉扯讓魯迅感到窒息,這不是簡單的因為愛情的出現帶來的問題,而是封建禮教和現實問題的碰撞必然會擦出的火花,同樣其他家庭、工作的苦悶也不是表面看到的一件事,而是一直以來積累的心理壓力,這種“厚積薄發”的情緒壓力折磨著魯迅,因此《野草》在滿足魯迅宣泄情緒的同時也承擔起魯迅自我療救的責任。
一位老生理學家布達赫謹慎的論述“夢的唯一目的是讓我們從中得到解脫”[13]23,簡單來說,弗洛伊德贊同這種說法,他認為夢擁有清洗心靈的作用,作為醫生的弗洛伊德用“談話法”治療病患并取得了一定意義上的成功。《苦悶的象征》這樣說“用了巧妙地問答法,使他極自由極開放地說完苦悶的原因,總之是因為知道現在還夾著壓抑的便是病源,所以要去掉這壓抑,使他將欲望搬到現在的意識世界來。這樣的出去了壓抑的時候,那病也就一起醫好了”[14]19,因此可以看出自言自語式的《野草》正是魯迅自己給自己搭建的平臺。
所以《野草》以夢為依托就不僅是在描寫表面現象,以夢境搭建框架的描寫更多的是魯迅在用這種書寫緩解自己內心的壓力甚至精神的危機。
《野草》中自我分裂式的寫作是魯迅在與自己內心的多種聲音對話,但“我”的清醒認識精神世界需要依附于“我”這個物質世界,所以這里的對話更是魯迅對自己的開導,他要從多種聲音的糾結中掙扎出來,《失掉的好地獄》“我”在夢中見識了人比魔鬼更兇殘的一面,揭示了無休止的殺戮,戰爭不會隨著文字的結束而結束,人的苦難只會隨著戰爭的繼續而加深,這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阻止的;《墓碣文》中“我”在否定那個一直解剖內心的自己,魯迅以夢為底在深夜用文字看到了血淋淋的自己——那個正在剖析自己的自己,羅伯特認為“夢來源于心靈本身在于它超負荷而需釋放出一些東西的事實”[13]66,所以“我”夢見自己在與死尸對峙的過程是抒發真實感受也就是釋放的過程;這也就不難解釋《頹敗線的顫動》《立論》《死后》等也都用夢境來托底,把平時在實現生活中不方便直接說出來的話借用夢的角度抒發出來,心中的苦悶、彷徨也就隨著文字排解出來了。這是魯迅賦予“我”的體驗,也是在“夢”中重塑自己的思緒和精神的過程。所以魯迅在《題辭》中說“去罷,野草,連著我的題辭!”[7]這是魯迅對野草給予的厚望,同時也是魯迅對野草式創作的告別,因為清醒的自我分裂無疑是痛苦的,沒有強大的內心怎能從夢中走出來,又怎能在清醒的分裂中達到自我療愈的目的。
夢和自我分裂式創作都是魯迅宣泄和重構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同樣也是自我療救的過程。魯迅自己向友人訴說過《野草》包含著他自己的人生哲學,所以魯迅不是在教給別人什么處事經驗,而是在說服自己或者說服和自己相似的仍然處在精神重壓下的同行者。
參考文獻
[1]徐勇,劉莎,王斌紅.精神分裂癥規范化診療及臨床路徑[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1-2.
[2]葉錦成等.自我分裂與自我整合:精神分裂個案的實踐與挑戰[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8-9.
[3]魯迅.吶喊[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107-497.
[4]富強.提燈尋影 燈到影滅——從《墓碣文》看《野草》[J].魯迅研究月刊,2000(6):36-42.
[5]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M].尹慧珉,譯.長沙:岳麓書社,1999:112.
[6]魯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5-41.
[7]魯迅,許廣平.兩地書[M].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20:284.
[8]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47.
[9]張少嬌.分裂與悖論——魯迅《野草〈墓碣文〉》的修辭形象之悖論[J].哈爾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6):102-106.
[10]錢理群.與魯迅相遇[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284.
[11]黃喬生.八道灣十一號[M].北京: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23-153.
[12]任毅,陳國恩.從生命體驗到反抗哲學——論魯迅《野草》哲理內涵的實現方式[J].湖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8):24-29.
[13](奧)弗洛伊德.釋夢[M].車文博,譯.長春:長春出版社,2004:23-66.
[14](日)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M].魯迅,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19-37.
(作者單位:陜西理工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