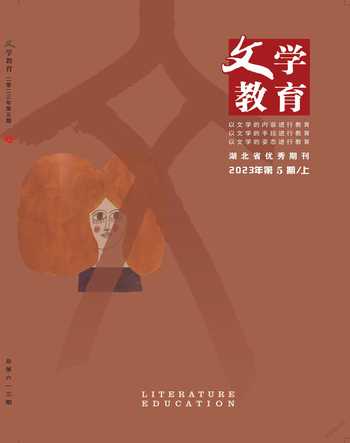《半生緣》相較于《普漢先生》的藝術獨創性
王小博
內容摘要:《半生緣》作為張愛玲創作的重要的長篇小說之一,一直以來在文壇廣受關注,并且還被翻拍成電影在國內上映,但在被大家討論熱議的過程中,人們發現張愛玲的《半生緣》和美國作家馬寬德的長篇小說《普漢先生》在敘事結構和故事內容上存在高度的相似性,這引發了人們的熱議。張愛玲的小說創作是抄襲還是借用?她對原作《普漢先生》做了哪些精妙入神的改編,從而表現出自己的個人才情。本文對照兩本小說,試圖探討張愛玲的創作意圖以及如何看待這種文學創作現象。
關鍵詞:張愛玲 《半生緣》 馬寬德 《普漢先生》 藝術獨創性
《半生緣》是張愛玲中年時期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以顧曼楨、沈世鈞為中心,描寫了沈世鈞、顧曼楨、許叔惠、石翠芝等青春飛揚的青年在亂世都市中陰差陽錯,愛而不得的愛情悲劇,從中體現了作者對于青年男女,尤其是青年女性在困境中對生命生存狀態、個人情感意志的思考和深切關照。
小說初載于1950年,張愛玲在《亦報》上連載小說《十八春》。1952年,張愛玲離開大陸,旅居香港,其間她改寫了《十八春》,并且起名為《惘然記》在《皇冠》月刊上重新連載。直到1969年,臺灣皇冠出版社發行了小說的單行本,出版時名稱為《半生緣》。小說一經出版,就在大陸、海外等地引起轟動,產生巨大影響,由此大陸也開始了對《半生緣》的影視化改編。目前共有三個影視化版本:一是1997年上映的同名電影,由黎明、吳倩蓮主演;二是2003年上映的同名電視劇,由林心如、蔣勤勤主演;三是2020年上映的電視劇,改名為《情深緣起》,由劉嘉玲和蔣欣主演。三次不同的影視化改編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座率爆棚,叫好聲不斷,許多讀者尤其是熱愛張味寫作的書迷們,都將其視為張氏寫作的范本。
然而隨著《半生緣》逐漸取得越來越大的影響,人們開始普遍關注到一個問題,《半生緣》是否涉及抄襲?關于這個問題,張愛玲在給宋淇的信中寫道:我在創作《半生緣》的時候,很大程度上參照了美國作家馬寬德的《普漢先生》。這讓許多讀者不禁疑惑,普漢先生是誰?《普漢先生》是普利策獎獲獎作家馬寬德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主要敘寫了以普漢和瑪文為中心的青澀愛戀,描寫了普漢、瑪文、凱、比爾四人之間陰差陽錯的婚姻悲劇,表現了命運無常對人生的無情捉弄,文章透露出一種淡淡的憂傷和迷惘。兩部小說在行文風格、人物塑造、小說情節、臺詞設置等方面都具有極高的相似性,但是大陸學者往往在對張愛玲創作《半生緣》的研究中對于這方面避而不談,對兩部小說客觀存在的親屬關系鮮有提及。筆者在細讀兩部小說后,比較了二者的相同和相異,算是拋磚引玉,也是對張愛玲抄襲問題的回應,希望引起關注。
一.《半生緣》和《普漢先生》的共同點
1.人物情節的相通
兩部小說都采用了“四角戀愛”的設置,兩位男主,世鈞和普漢,都來自于當時社會的中上層階級,舊社會的世族家庭。他們身邊有一個自小便認識的青梅竹馬,也就是他們各自后來的妻子——石翠芝和凱。但是他們從小相識,又從來沒有超出朋友的界限,或者說,在之前,他們從未將對方納入自己未來結合的人選的考慮范圍內。
故事發生在冬季,世鈞為了擺脫家庭父母的束縛來到上海工作,在叔惠的引薦下,他認識了叔惠的同事——曼楨;而普漢也在一戰結束后留在紐約從而結識了女主人公瑪文。兩個女孩子都出身貧寒但是性格堅強,對待工作一絲不茍,對待生活積極進取,富有激情和熱血。與其他之前接觸的女孩子相比,她們無疑是特別的。瑪文和曼楨的生命鮮活而真誠,她們身上對于生命無限熱愛的品質深深地吸引著兩位男主角,不久二人便陷入愛河。然而他們都沒有把這段戀情告訴彼此的好友。由于父親病逝的緣故,普漢和比爾趕回波士頓,世鈞和叔惠返回南京,在這里,比爾和凱,叔惠和翠芝相識相愛,但是由于二人社會階級及家庭背景的巨大差異,以及兩位男生沒有回應的表現,使得這份不為人知的感情最終走向不了了之。與此同時,男女主也因為彼此之間的隔閡與誤會產生了感情裂痕,最后無疾而終。在普漢和世鈞雙雙經歷感情的變故后,反而和以前的青梅竹馬越走越近,彼此在朝夕相處之間產生了一種惺惺相惜的情感,并最終結為夫妻。然而兩場門當戶對的婚姻終究不是以愛情為基礎的,時隔多年后,兩對曾經的戀人彼此重逢,在經歷了各自情感和道德上的波動與掙扎后,最終四對情侶,八個人還是選擇了各歸各位,回到了原本熟悉的生活中去,對于曾經那份年少的悸動,只能留下“Darling,we cant go back”的無限迷惘與憂傷。
經過對兩部小說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張愛玲幾乎完全照搬了馬寬德創作的主要人物的人設以及他們之間的情感關系。幾位主角的對應關系如下:世鈞——普漢、叔惠——比爾、曼楨——瑪文、翠芝——凱。不僅主要人物,就連其中幾位重要配角的人物設置上也有參考。曾與石翠芝訂親的方一鵬和他的妻子竇文嫻也仿照了《普漢先生》中喬伊·賓漢姆夫婦。方一鵬和石翠芝做媒,喬伊賓漢姆和凱·蒙特福德訂婚的時候,普漢和世鈞都認為“好極了,再好不過了,這樣家里就再也不會催他結婚。”而最后,喬伊和瑪德琳訂婚,方一鵬和竇小姐結合,比起之前訂親的一方,他們更愛他們的妻子。這里對應了普漢的父親曾說過的考慮一個合適的女孩的重要性:“你看,我還年輕的時候就和你母親結婚了,我從來沒有后悔過,關鍵是要找到一個跟你同一類的人。”在《普漢先生》中,哈里母親曾講過一個故事,故事中蘭斯洛特爵士愛上了貴尼微皇后(亞瑟王的妻子),導致騎士和國王的關系破裂,所以蘭斯洛特騎士被認為是不道德的,這個故事也為后來哈里最終返回家鄉,比爾放棄戀人凱埋下了伏筆。而張愛玲在書中設置如此的人物關系,也在隱隱對應著小說的結局。
其次就是兩部小說都有相同的兩地時空轉換設置。紐約對應上海,波士頓對應南京。時空的相互轉換為小說的敘事增添了一抹層次感。同時小說中許多小物件也起到了穿針引線的功能和作用,玻璃寶石戒指、紅絨絨手套、男女主來往的信件等,都見證了那段“此情可待成追憶”的悠長記憶和青春悸動。
由此可以推斷,《半生緣》的故事發展線索和情節設置都和《普漢先生》保持著極高的相通性。
2.細節臺詞的移植
除了人物情節的借鑒,《半生緣》中不少臺詞和細節也都存在移植現象。
第一處,兩位女主人公莫名地都不喜歡叔惠/比爾的角色。《半生緣》中,曼楨和世鈞說到:“其實我一直都想告訴他的,但不知道怎么的,就一直沒有說。叔惠這人不壞,不過有時候我真的簡直恨他,因為他給你一種自卑心理。”而在《普漢先生》中,瑪文也說過類似的話“親愛的,我不希望你什么都聽比爾·金的,他很好,你也不壞,你比他還要好。”可以看出,張愛玲在創作曼楨一角時,著重復制了瑪文的性格,她們同樣熱情剛烈、敢愛敢恨。
第二處,在世鈞因為家里的事情,準備返回故鄉時候,和女主進行了告別。曼楨問道:“你禮拜一一定可以回來嗎?”世鈞說到,“禮拜一一定回來,沒有什么必要的事情,我不想請假。”在另一文中,“哈里,你還會回來的,是嘛?”瑪文問道。“我一定會回來,周一我會到辦公室。”普漢先生回答道。在這個告別的節點,兩位女生都有隱隱感受到戀人離去帶來的危機感,“你一定會回來嗎?”“你一定會回來嗎?”反復的提問能看出來熱戀中的情侶彼此之間惺惺相惜,不舍分別的感情。
第三處,兩位男生都曾向女主表達過想要結婚的想法。世鈞道:“曼楨,我們什么時候結婚呢。”普漢說到,“瑪文,我們結婚吧。”但是兩個女生卻拒絕了提議。世鈞是上流社會階層,而曼楨只是中下階層的普通職員,因為“門不當戶不對”的社會觀念,內心深處的它一直抗拒這段感情,所以當男主幾次向曼楨求婚的時候,曼楨都沉默不語。
第四處,男主邀請女主來故鄉做客的信件內容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世鈞的信:我真想再見到你,但是我剛來過,這幾天內實在找不到一個借口再到上海來一趟。這樣的好不好,你和叔惠一同到南京來度一個周末。你還沒有到過南京來過呢。你一定要來的。叔惠我另外寫信給他。
普漢的信:給你寫信,很有意思,因為你好像就跟我在一起,就在桌旁,所有的收報機都在響,瓦爾丁現在一邊喝著一杯牛奶一邊看著我。見不到你我有些受不了,但總是有事讓我不能離開這里,一天都不行,所以我想請你為我做點事情,我總想讓你到這里來看看,我們說過很多次了,你和比爾下周末一起過來怎么樣?這兒有很多房間,我可以帶你去看所有的東西。
兩位男主人公在邀請自己的戀人時,都讓女主叫上男二一起出現,他明白讓他的朋友一起來,會讓事情顯得更輕松自然,同時也為小說中第二男主角和第二女主角的相戀奠定基礎。
第五處,兩位女主角正式的第一次見面也存在著相似點。兩個女人的初次見面都讓男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顫顫巍巍,緊張過度。不過他們的見面的地點不同,一個是去紐黑文看比賽,一個則發生在曼楨和叔惠到南京看望世鈞的時候。從時間跨度來看,顯然《半生緣》更晚。不過也能解釋,石翠芝的性格在前文提到過,“她好像除了對狗和劃船便沒有什么感興趣的了”,而曼楨在之前也是一直拒絕和世鈞的父母見面,所以兩位女主角的會晤自然而然地被推遲到了后面。
第六處,男主人公邀請男二做自己婚禮伴郎時二人的對話。叔惠說道,“跟石翠芝界結合,你就完全泥足了,只好一輩子安分守己,做個闊少奶奶的丈夫。”而比爾說,“你要和凱訂婚?對,那你真的是把自己系牢了。”
第七處,婚禮過后,在新房新娘子對這場看似完美的婚禮都向愛人袒露了內心的焦慮與后悔。
翠芝:“世鈞,怎么辦,你也不喜歡我,我想過多少回了,要不是從前已經鬧過一次,——待會人家說,怎么老是退婚,成什么話?現在來不及了吧,你說是不是來不及了?”
凱:“哈里,我不確定我們是否彼此相愛,我不確定,如果我們以為彼此相愛卻實際上并非如此,是不是很可怕?我的意思是——要是我們只是因為結婚而結婚。”她想的正是我想的,而她并不害怕說出來。而普漢先生也在安慰他的新娘:“凱,也許所有人都這樣,也許千百萬的人都這樣。別擔心,一切都會好的,凱。”
第八處,兩位男主在步入婚姻后,毀掉了那些帶有回憶的物品,唯獨留下了戀人的信件。給翠芝和凱發現女主自訴衷腸的寄托提供了契機,信件的大致內容如下:
曼楨的信:你這次走的匆忙,冬天的衣服一定沒有帶去吧?我想你對這些事情向來馬馬虎虎,冷了也不會想到添加衣裳的。我也不知怎么老是惦記這些。隨便看見什么,或是聽見人家說一句什么,完全不相干的,我腦子里會馬上轉幾個彎,立刻想到你。因為你走了有些時候了,我就有點恐懼起來了,無緣無故的。世鈞,我要你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永遠等著你的,不管是什么時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總有這么一個人。
瑪文的信:我最親愛的人,最最親愛的人,我一整個白天都在想你,我整個晚上都在想你。我一直在想你會是什么樣子,會說什么,有沒有穿套鞋,我一直在想我能為你做的小事情。我從來沒想過你會如此進入我的世界——似乎我已經不再是一個人——而是有部分的我跟你在一起。你知道的,我這樣絮絮叨叨,是因為我愛你,不是嗎?要是你愛上某個人,卻又什么都不能做,你會很無助。我要你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一個人在等你,無論你在什么地方,無論是什么時候,反正總有那么一個人。
第九處,男女主闊別多年的重逢更是一摸一樣。
《半生緣》:那時候她一脫掉外套我就會吻她,世鈞想到……但是吻了又怎么樣?前幾天想來想去還是不去找她,現在不也還是一樣的情形?所謂鐵打的事實就像鐵案如山。他的眼睛里一陣刺痛,是有眼淚,喉嚨也堵住了。他不由自主地盯著她看,她的嘴唇在顫抖。曼楨半晌道,“世鈞,我們回不去了。”他知道這是真話,聽見了還是一樣震動。她的頭已經在他的肩上。他抱著她。她問道,“世鈞,你幸福嗎?”
而《普漢先生》中關于這段的描寫是這樣的:那時候她一脫掉外套我就會吻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記得,我希望我能說點什么讓我從中擺脫出來,或者她能說些什么,可她沒有開口,我們就只是站著,看著彼此。我的眼睛有點酸痛,喉子發干。我無法把眼睛從她身上移開。她的嘴唇在顫抖。“哈里,”我等著她往下說,我都不想回答她,我又聽到了她的聲音,緩慢而堅定。“哈里,親愛的,你幸福嗎?”“親愛的,我們再也回不去了” 這就是答案。這就是我們一直想要說的話——真相,絕對而完整。或許在我的內心深處我一直有這個念頭,我們可以,如果一切是可怕的,我們可以回去——可是現在這個念頭結束了。
提筆至此,不禁感嘆,青春就像一頂舊氈帽,由于某些原因沒有人會經常再穿它,可是又保存的很好不舍丟棄。你總會在壁櫥的某個角落遇見它,要是遇見了,有時候你會感到一陣刺痛,然后你還是不得不把它從心里清理掉,所以你越過了它。故事的結局是世鈞夫婦和亨利夫婦一起造就的,因為在他們心里,最重要的是自己,他們合力把事情變成了這樣,不管他們想或是不想。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時隔多年后,兩位男主在得到女主人公的消息時,沒有立馬去見她們,而是在內心經歷反復的掙扎和痛苦,還是選擇放棄見面。
盡管由于篇幅的限制,筆者不能將兩部小說之間全部的細節相通之處一一列舉出來,但是不難看出,張愛玲對馬寬德的創作絕非只是簡單的借鑒,而是從人物、情節到細節等多方面的模仿和化用。
二.《半生緣》對《普漢先生》的改編
張愛玲如此大范圍的借用和模仿,從今天的視角來看,或許通過知網、維普等文獻查重平臺的檢測,一頂“抄襲”的帽子必然要扣到張氏的頭上了。但是,《半生緣》究竟是抄襲還是借用,取決于社會文藝如何定義“抄襲”,這是一個彼亦是非,此亦是非的問題。筆者在這里絕非是為了指責或是控訴張愛玲“抄襲”。正如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論指出的那樣:藝術是對于實物的模仿,但模仿的對象、方式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種類的藝術。他還認為模仿是人的本性,模仿的藝術不僅可以給人帶來快感,還可以幫助人們求知。文學作品的抄襲和借用本來就是一個灰色地帶,而藝術的本質就是為了解釋事物的本真和規律,或許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待為什么國內讀者對張愛玲的創作持有一個如此寬容的態度。
撇開兩部小說的共通性不談,張愛玲在創作改編中更表達了自己獨有的想法和思考,使小說,尤其是后來改寫的《半生緣》帶上了一股子獨有的張氏悲傷。首先從技術層面上,張愛玲改變了敘事的角度,《普漢先生》是第一人稱敘述,《半生緣》則是第三人稱,小說以一種近乎全知全能的視角對其中的愛戀故事進行了描述。其次,張愛玲對原作進行了人物情節的增刪,《半生緣》中,曼楨的姐姐曼璐,隱隱對應著《普漢先生》中普漢的妹妹瑪麗,但又有位移,體現了張氏特有的塑造女性形象的筆觸。而祝鴻才的形象又是一個完全上海式的,舊道德式的人物,是完完全全屬于張愛玲的。曼楨被祝鴻才強奸并囚禁是張愛玲增設的情節,也是小說最為重要的轉折點。此外,她還改寫了故事的講述結構,到《半生緣》的后期故事,男女主雙線發展,平分秋色,單線敘述和雙線并行,交叉但獨立的故事線發展使得《半生緣》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更加豐滿。《普漢先生》中,瑪文第一次出現是二十五年后的哈佛大學同學會,但是普漢拒絕了她的見面邀請,之后在第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瑪文正式出現,從相識相愛相離,作者只用了短短十章的內容便對男女主角的戀愛全過程做了完整的敘述,后面用了大量的篇幅講述普漢和凱的婚后生活,對女主角的刻畫著墨不多,因此小說重點表達的第一主角永遠是普漢先生。
從情感濃度看,《普漢先生》更平常淡雅,《半生緣》更蒼涼幽怨。《半生緣》的重點在曼楨的人生苦難和愛情理想的破滅,表達了苦難的力量和面對苦難體現出來的堅強人性的閃光一面。《普漢先生》則重點描述哈里作為美國上層階級社會生活的拘束性,瑪文僅作為一個男主想要擺脫束縛的象征性的符號,《普漢先生》沒有涉及到生命和苦難的這一話題,它更多地是以溫和的諷刺手法大力渲染被現代都市不成文的規矩束縛住的人們,從而表達他們的愿望與訴求。
同時,《半生緣》的成功之處關鍵在于其中對于女性力量和女性價值的抒寫。張愛玲首次在小說中賦予女性非性格悲劇的命運。顧曼楨算得上是張愛玲筆下為數不多的正面的女性形象之一。這點從她委身嫁給祝鴻才,物質生活一步步變好的時候,決心與祝鴻才離婚,獨自撫養榮寶也可窺見一斑。而曼璐的悲劇也是由于時代的原因,從她身上,讀者不難體會到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束縛。張愛玲借曼楨之口,發出來振聾發聵的控訴“我覺得我姊姊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地方,是這個不道德的社會逼得她這樣的,要說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和妓女是誰更不道德。”曼楨在經歷了愛情和親情的雙重背叛后仍能樂觀地面對生活,曼璐壞事做盡最后孤獨終老,翠芝禁錮于封建傳統無法自由地追求愛情,顧太太的愚昧和沈夫人的固執害慘了自己的兒女,作品通過不同女性的命運悲劇表現了中國舊社會的封建倫理道德和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欺壓以及封建思想的枷鎖。而曼楨,就是戴著鎖鏈跳舞的女戰士,小說中的女性悲劇揭示了女性的現實命運的悲慘和抗爭的無力。
張愛玲的女性思維以敏銳的感情捕捉到戀人之間細膩的心理變化,符合張氏寫作的通俗風格,更賦予了作品更深厚的時代記憶和文化印跡。張愛玲擅于描寫那種舊的空氣下的悲劇性的人物,描述小人物的悲歡離合,體現了張氏獨有的審美視野以及對舊中國的蒼涼思考,在賡續了張味書寫的同時表現了悲憫的人文情懷。這些是張氏獨有的筆觸,是只有敏感的女性思維才能想到的,是馬寬德以一個男性思維的寫作態度絕對無法在小說中表現出來的。小說將社會對于女性自我價值的物化和凝視的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從這個角度看,不妨說,張氏的《半生緣》是對馬寬德《普漢先生》主題的逆寫。
一世沉重,千鈞一發。張愛玲早已經作古,如今再去追究她是不是“抄襲”這個問題意義已經不大。逝者為尊,死者為大,自古以來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古老傳統,對張氏寫作的寬容和保護是在我們民族心理的作用機制下起作用的。蘇友貞在《張愛玲怕誰?》中寫道,“張愛玲沒有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她誰也不怕地借用與改寫她認為可用的素材,不管是西方的、中國的、經典的、通俗的、古典的、現代的、甚至是她同時代并相識的作者。”《普漢先生》和《半生緣》,一個是“上流社會的婚戀挽歌”,一個是“夾層時代的蒼涼宿命”男女主之間難以忘懷的深厚情誼只是亨利不痛不癢的青春傷痛,卻是曼楨悲涼徹骨的生命體悟。我們之所以如此熱愛《半生緣》這部作品,也是因為它真正寫出了中國社會的思維和情感,從中我們看到了一代才女的幽怨冷對,更能在文字中聆聽那個時代的潮起潮落。這和《普漢先生》冷靜客觀的敘事方法截然不同。
馬寬德和張愛玲曾經在香港有過一面之緣,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向張愛玲本人去追問她當時創作《半生緣》的契機和用意,但是我們可以通過這兩部作品,去思考一些問題。一是在近現代文壇中,一些著名的文學作品有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又有在多大程度上出自作家本人的藝術原創?其作品藝術獨創性和作家自身的創造力體現在哪些地方?又或者我們是如何影響一些外國作品?比如我國藏族流傳的民間故事《斑竹姑娘》,被改編到日本,取名為《竹取物語》,對日本物語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意義。二是馬寬德雖然獲得了普利策獎,但在美國文壇中一向不受重視,透過《半生緣》的文本重新審視這位值得被再發現的美國文學家應該引起思考。同時張愛玲也為我們如何借鑒和學習模仿優秀作品,又能在其中表現出個人特色提供了范例,能夠產生深遠影響,這些都值得之后的學者進行更加深入和系統的研究。
參考文獻
[1]《普漢先生》馬寬德著,鄺明艷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
[2《半生緣》張愛玲著.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3.10
[3]蘇有貞.禁錮在德黑蘭的洛麗塔.北京:三聯書店.2006.第43、44頁
[4]卜杭賓.張愛玲的創造性改寫:從《普漢先生》到《半生緣》.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7.1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