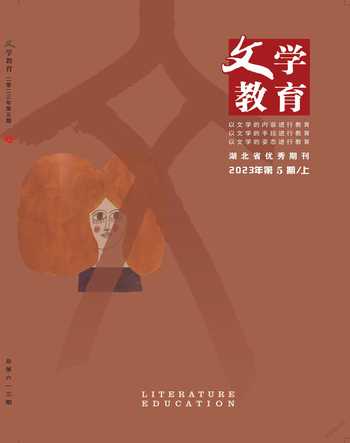梁宗岱的西方詩學特征
梁思域
內容摘要:梁宗岱為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既在詩歌上進行創新實踐,又推出了詩歌創作的理論。中國現代新詩本來就是受到西方現代性的影響,所以有必要去系統地梳理梁宗岱的西方詩學特征,以更好地理解中國新詩的發展,而這些西方源淵又有助于推進梁宗岱詩學的本體研究。
關鍵詞:梁宗岱 《晚禱》 《蘆笛風》 象征主義
梁宗岱(1903-1983)是一位天才詩人、杰出翻譯家和理論家。1925年發表第一本詩集《晚禱》,1944年發表最后第二本詩集《蘆笛風》。他在中國現代詩壇頗有名氣和影響。他的文學鑒賞力和詩學理論尤其受人尊敬,并對中國新詩作出了貢獻。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對梁宗岱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但在他去世后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學界對梁宗岱的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的著作一直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根據知網的數據,60%以上的研究集中在他的詩學上,25%的研究集中在他的生平故事上,15%的研究集中在他的翻譯上。例如,許多學者,如劉金華闡述了梁宗岱的純詩理論。但總體上只有四篇文章集中介紹了他的詩歌。
本文旨在探討西方詩學對梁宗岱詩歌的影響,以期完善和深化梁宗岱的本體論研究。由于新詩本身受到西方的影響,我們有必要在細讀梁宗岱詩歌的基礎上,全面考察梁宗岱西方詩學特征的淵源,從而更好地了解中國新詩的發展。西方詩學的特點,反過來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他的詩歌。
一.宗教意象和意識
文學理論家勒內·韋勒克(Rene Wellek)和奧斯汀·沃倫(Austin Warren)在他們的著作《文學理論》中講到,“我們可以把傳記看作是對詩人心理和詩歌創作過程進行系統研究的材料[1]。”所以,除了單純的內部研究,或許我們暫時可以借助梁宗岱的人生經歷來分析和評價他詩歌中的西方特色。
梁宗岱于1903年11月5日出生,廣西百色人。1917年,他選擇在廣州培正中學學習。然而,他根本不懂英語,所以他得花費一年的時間學習英語,以進入學校。然而他只用了半年時間便完成了語言的學習,可見語言能力不容小覷。1919年,他終于被培正中學錄取了[2]。正是在這段時期,他的詩歌受到了宗教的影響。
培正中學由中華浸信會于1889年創辦。它最初是為吸引更多教徒而開設的教會學校,主要是那些不了解基督教福音卻又想接受教育的人,也為了培養基督教徒美好的品德[3]。這就是為什么它被命名為培正,意味著“培養正直人才”,培養一個具有健全的人格,科學和人文以及國際視野的學生。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學生們必須參加宗教課程,并參加校園里所有的宗教儀式和晚宴。學校還會邀請校外的福音傳道者舉行復興會,吸引更多的學生加入教會[4]。在培正中學學習了近四年后,梁宗岱被嶺南大學免試錄取,并獲得全額獎學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嶺南大學最初也是一所教會學校,采用的是美國式的教育模式。學生們被要求每年至少上一門宗教課程,每天參加一到兩次宗教儀式,并在一周的中間進行祈禱。更重要的是,星期天要花一整天的時間去禮拜[5]。“宗岱,”他的同學回憶說,“是個基督徒。他有時自己唱基督教贊美詩,并將一些英文贊美詩翻譯成中文[6]。”他的同學的說法顯現著一種敏銳的直覺,即梁宗岱已經受到了基督教潛移默化的影響,盡管梁堅持說他違背自己的意愿皈依基督教,只是因為他的女朋友,為了求得她的愛[7]。
他僅在22歲就發表了第一本詩集《晚禱》。從這本詩集的標題可以看到,祈禱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對上帝的精神獻祭[8],給全本詩集奠定了一個宗教基調。全二十首詩中,超過四分之一與宗教有關。很明顯,祈禱是一種宗教儀式,是詩人主動與超自然力量交流的方式,以贊美、祈禱、懺悔,或簡單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或欲望。董強在他的書中評論到,“梁宗岱的詩歌有一種很強大的精神氛圍[9]。”實際上,這種氣氛源于基督教的意象,如祈禱、懺悔、恩典、贊美、憐憫等。梁宗岱的第一首詩《晚禱》以描寫莊嚴寧靜的環境開篇,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彈也罷,
雖然這清婉潺湲
微颶蕩著的
蘭香一般飄渺的琴兒。
一切憂傷與煩悶
都消融在這安靜的曠野。
無邊的黑暗,
與雍穆的愛幕下了。
讓心靈恬謐的微跳
深深的頌贊
造物主溫嚴的慈愛。
《晚禱》這首詩有《創世紀》的影子。《創世紀》講述了創世的故事,諾亞方舟,以及解釋世界和人類是如何被創造的故事[10]。這首詩描繪了“晚禱”的神圣經歷。第一節以樂器、溪流、寧靜的荒野等意象構成了一種莊嚴的氣氛。蘭花的芬芳,象征著上帝的慈悲,彌漫在黑暗的每一個角落。悲傷和恐懼都被遺忘在天地之間。在贊美上帝的恩典中,“造物主的愛”在詩人的思想和靈魂中涌動。在擺脫世俗的煩惱之后,他達到了一種寧靜、和諧和虔誠的狀態。這些意象讓人回想起宇宙的起源。當我們讀這首詩時,我們的自我精神在翱翔,我們與詩人一起感受到優雅和超自然的力量。此外,造物主的愛和憐憫在黑暗和寂靜的背景下突出,這反映了他對宇宙的愛。
此外,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聲稱,自我探索是耶穌會士和清教徒紀律的一部分[11]。在《晚禱二》這首詩中,梁宗岱真誠地“在悔恨中反思自己瘋狂的過去”,并“在黃昏星的溫柔光芒中懺悔自己的罪惡”。黎志敏教授認為,在原罪和“否定自我”的文化信仰的影響下,基督徒相信一個微不足道的有罪的自我,贊美神的強大和驚人[12]。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和中國世界之間的鮮明對比。因為在傳統中國文學中,人們傾向于認為,一個人的不幸必須歸咎于宇宙或時代,是時代和社會的捉弄導致個人的失敗,原因不在于個人[13]。
在這首詩可以看到,梁宗岱雖然是中國人,但他受到的卻是西方的教育,并且時常接受教會的洗禮。他已經學會了反省,反思自己的年少時犯下的錯誤, 期待通過懺悔來獲得一種神圣的情感,在此期間他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由此可見,梁宗岱的自省是基督教傳統的一部分。
除了“上帝”,他還多次贊頌了“主”和“造物主”。在《夜露》這首詩,泛神化現象也很明顯,讀者能遇到很不少由自然化身的身,諸如“夜神”、“地母”、“天神”等等。事實上,這些自然神的意象,都是一個中心主題的變體:對愛之源的頌贊。
宗教環境對他的詩學和美學理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14]。然而,最令人驚訝的是,梁宗岱的宗教意識卻與虔誠的教徒對某一宗教的虔敬截然不同。與冰心虔誠的皈依基督教相比,梁宗岱所表達的更多是宗教和崇高的體驗以及信仰哲學。這種內在的升華恰恰與他的象征主義宇宙意識相應和。
二.象征主義和宇宙意識
在嶺南大學學習一年后,梁宗岱前往歐洲深造。1924年,他進入瑞士日內瓦大學學習法語。1925年,他被巴黎大學錄取。接著在后幾年中到意大利等地游學 [15]。幸運的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象征主義這一歐洲文學運動在法國盛行。波德萊爾,馬拉美和瓦萊里分別代表了詩歌中這一特殊傳統的開始,中間和結尾[16]。
20世紀初,白話文學運動在中國進行得熱火朝天,由此胡適更是提出了“詩體大解放”的主張。可以看到,為了拯救瀕死的民族,語言乃至詩歌逐漸成為功利的工具,背離了詩歌的本質。一些詩人,如穆木天和王獨清,批評了這一功利性現象,并且批判了胡適的提倡。基于他們的論證和梁宗岱對生命和宇宙的理解,他認為完全推翻中國傳統文化是不可能的,完全照搬不加修改和吸收的西方文化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因為這兩種方法都會讓人失去思考的能力。因此,他在演講中闡述了“象征主義”和對應論,以幫助改變這種狀況。如果說穆木天和王獨清的早期詩學是中國象征主義興起的標志,那么梁宗岱的詩學則是其成熟的標志[17]。
象征主義,從廣義上而言,是使用語言作為一種手段,以重新發現存在于想象和精神領域的所有存在的統一[18]。這就是梁宗岱宇宙意識的起源,是他詩歌的核心,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體現。對他來說,宇宙意識是詩歌中體現的一種獨特的、以哲學的方式看待宇宙或自然的感覺。它是我與相關對象之間的一種深入的、共情的交流[19](p.130)。
據數據統計,他的詩歌中有大量的宇宙意象,如各種各樣的星星和天空,其中以各種形式出現的“月亮”最為頻繁。“黃昏”、“晨”等時間維度的意象是宇宙的隱喻。在多樣的語境中,出現了二十多次的“月亮”,又象征著不同的神秘事物。有時指詩人內心的平靜。有時,“月光”被證明是使詩人悲傷的原因。用不同的哲學方式來理解月亮,就是使用來自“象征森林”的意象。
在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詩歌“應和”中,他描述到,“ 大自然是一座廟宇,那里的活柱子有時會發出令人困惑的話語。人們穿過象征的森林,用熟悉的目光觀察它們[20]。”也就是說,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可以與自然界中的物體進行交流。要達到這種超然境界,梁宗岱主張:“詩人要用最生動、最具體的意象來表現最神秘、最飄渺的精神境界。”這在他的詩《水調歌頭》中有很好的說明:
人生豈局促,
與子且高歌。
浩然一曲沖破,
地網與天羅。
給我一枝蘆笛,
為汝星回斗轉,
冰海變柔波。
哀樂等閑耳,
生死復如何。
浮與沉,
明或暗,
任予和。
鈞天一笑相視,
認我與同科。
著取沙中世界,
更見花中天國,
同異盡消磨。
君掌握無限,
千古即剎那。
第一節為整首詩設定了一個哲學主題:生命短暫,我們應該珍惜時光。下面的詩句則用他的美學情感告訴我們如何達到這一境界,這是受到了瓦萊里的鼓勵。在他的散文《憶羅曼·羅蘭》中,梁宗岱回憶道,“因為稟性和氣質的關系,無疑地,梵樂希(即瓦萊里)影響我的思想和藝術之深是超出一切比較之外的[22]。”瓦萊里確實給了他藝術創作的力量,并鼓勵他要在藝術界繼續發揚光大。
從第一詩節可以看到,“一曲”和“蘆笛”都象征著音樂,而梁宗岱認為一首純詩本來據應該屬于音樂,所以這兩個意象也指的是“詩歌”。“地網”和“天羅”象征著生活的難關和敵人,“冰海”指的是受到的苦難,而“柔波”是愛情的象征。第一節的意思是,于詩人而言,有音樂和詩歌,他就可以克服萬難,將所有的痛苦化作為愛情的美好。這些意象和情感的關聯,就像瓦萊里所倡導的那樣,“詩之所以成為藝術,是由于詩人的審美情感。它本質上是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交流,是內在精神的共鳴[23]。”梁宗岱的審美情感,于他而言即是宇宙精神,在這首詩里表現得淋漓盡致。
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節詩,梁宗岱借鑒了著名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天真的預示》的頭幾句。梁宗岱將《天真的預示》的前四行翻譯成中文,然后放到了自己的詩里。對上與下、光明與黑暗、有限與無限的二元對立進行了解構,這也體現了他的宇宙意識。因為在他看來,生活不過是一個偉大的和諧。而且這對于時間和空間界限的打破,也是源于這種宇宙精神。
三.自由
法國自啟蒙運動以來,就有著追求自由的的優良傳統。自由、平等、博愛詩法國的的箴言。法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曼·羅蘭(Romian Rolland),將其一生奉獻給了反法西斯,支持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爭取自己的自由和權利。當梁宗岱他的小說《讓-克里斯托夫》(Jean-Christophe)時,他被克里斯托夫對自由平等的追求所深深震撼。毫無疑問,羅曼·羅蘭對他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無論是精神上還是道德上。后來,梁宗岱結交了許多優秀的法國作家,其中包括:保羅·魏爾倫(Paul Verlaine)、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保羅·瓦萊里(Paul Valery)、羅曼·羅蘭等人。與他們的頻繁接觸塑造了梁啟超對自由的信仰,這后來成為他性格和詩學的主要特征。
包辦婚姻,在中國舊社會,是人們生活的準則。新郎和新娘沒有沒選擇愛人的權利,甚至有許多人在結婚儀式那一刻,才知道與他們一同行禮的人是誰。也有很多人的婚姻是在一出生,就已經被選好了的。毫無意外,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還沒有擺脫這種封建集權,自然而然,梁宗岱也無法避免這種遭遇。梁宗岱還在廣州讀書的時候就被父母欺騙回家,讓他與何氏成親。那他當然是不愿意了,寧愿在大街上裸奔也不愿意將自己的幸福斷送在權威的手里,所以他違抗了父母之命,像這種據對的權威發起挑戰,就像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的一樣,“我們須擁有心靈上的自由。所謂心靈上的自由,就是無論對于任何文藝,任何原理,都不要囿于成見,不惑于權威,不盲從,不迷信,而一以躬自耐心精細檢討得來的認識為皈依[25]。這個心靈的自由被記錄在了《夜梟》這首詩里。
“嗚唔,嗚唔,”夜梟的聲音,
人生的詛咒者的聲音,
像凄切的莽鐘一樣,
把我從亂藤般的惡夢當中,
兀地驚醒了。
......
連我的游魂都一并招去罷。
我怎能夠也“嗚唔,嗚唔,”的
把人生努力地詛咒呢?
盡管包辦婚姻詛咒著他的生活,但他會找到擺脫詛咒的方法。盡管何氏在梁宗岱的父母和好友胡適的支持下將他告上法庭,但他還是還是決定與何小姐離婚。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梁宗岱就像他的朋友徐志摩一樣,一直在追求自由戀愛,盡管會受到許多批評。最終,他被一個貧窮的戲曲演員甘少蘇深深吸引住。她只是一個不知名的、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戲曲演員,負債累累,過著悲慘的生活。梁宗岱花了很多錢才把她從惡魔手里救出來。無論他必須犧牲多少,梁宗岱還是選擇了他的真愛與自由。這種逃離世俗桎梏的愛,在《金縷曲四》這首詩中得到了體現。
世情我亦深嘗慣,
笑俗人吠聲射影,
頻翻白眼。
榮辱等閑事。
但得心魂相伴。
更何必淚光偷泫?
萬劫沉淪都不悔,
任柔絲自縛春蠶繭:
將愁苦
為繾綣!
對于梁宗岱而言,他壓根不在乎他人的“吠聲”和“白眼”,因為這些蠶繭的束縛只能束縛到他人,但禁錮不了梁宗岱。盡管他和甘少蘇之間的社會地位有一條鴻溝的差別,盡管他的名聲會受到損害,但他還是選擇打破所有桎梏和枷鎖,選擇了甘少蘇,這或許是因為出于同情,或者是內心的英雄主義在吶喊,無論怎樣,他都選擇了自由。他也絲毫不后悔,并和甘少蘇在余生幸福地生活下去。
不計較名利,是梁宗岱在法國學到的自由精神的另一個體現。回國后,由于他的個性和在知識界的影響力,蔣介石邀請他加入國民黨,為國民黨效力,并向他提供了優厚的待遇。但是梁宗岱不想自己背負上正直的負擔,多次拒絕了蔣介石。最后為了避免迫害,他最終辭去了教授的工作,回到家鄉,假名從事翻譯和草藥研究,自由地度過了余生。
通過文本細讀,結合他的創作理論和生平事跡,我們發現我們發現,他的基督教意象、宇宙意識以及自由精神使他的詩歌顯得相創新和富有想象力,有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采取了西方的詩歌措辭和技巧。但是梁宗岱并沒有完全移植西方詩學,而是以中西和諧的結合促進了中國象征主義的發展。梁宗岱的詩歌和詩學表現了他對詩歌創作新實驗的批判洞察力,對中國新詩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
參考文獻
[1]Wellek,Rene & Warren, Austin. Theory of Literature[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Inc,1956:75.
[2]黃建華.《宗岱的世界·生平》[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2.
[3]冼子恩.《六十年間私立廣州培正中學的變遷》[A].《廣東文史資料》[C].第45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261.
[4]李興韻.二十年代廣東國民政府對教會學校的“收回”——以廣州私立培正中學為例的研究[J].開放時代,2004(05):5-14.
[5]張新標.從格致書院到嶺南大學:近代教會大學“中國化”的嶺南樣本[J].高教探索,2021(12):123-128.
[6]劉志俠,盧嵐.《青年梁宗岱》[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4.
[7]黃建華,趙守仁.《梁宗岱傳》[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8]王本朝.中國現代詩歌中的上帝意象[J].文學評論,2006(06):181-185.
[9]董強.《梁宗岱穿越象征主義》[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10]馬利安·高立克,胡宗鋒,艾福旗. 以圣經為源泉的中國現代詩歌:從周作人到海子[J].人文雜志,2007,(05):107-118.
[11]Taylor,Charles.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184.
[12]黎志敏.“理性的情感”:論中西詩歌主體的“自美”與“內省”——基于陸建德相關思想的辨析與拓展[J].文學理論前沿,2017(01):191-216.
[13]Lu Jiande.“ ‘Self- in F. R.Leavi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Literature”[J],The Cambridge Quarterly,2021(41):128-145.
[14]張仁香,趙曉華.梁宗岱早期詩歌創作中的宗教意識[J].學術交流,2010(04):178-180.
[15]張棗,亞思明.梁宗岱與象征主義詩學[J].學術月刊,2019,51(01):135-149.
[16]Eliot,T.S.“FromPoeto Valéry.” [J].The Hudson Review,1949(02):327–342.
[17]廖四平.“純詩”說·“象征”說·“契合”說——梁宗岱的詩論[J].江蘇社會科學,2001,(02):110-115.
[18]De Man, Paul. “The Double Aspect of Symbolism.[J].Yale French Studies,1988:3–16.
[19]陳太勝.《梁宗岱與中國象征主義詩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2004.
[20]Baudelaire,Charles. Les Fleurs Du Mal[M].Boston:Godine,1982:9.
[21]梁宗岱.《談詩》[A]《宗岱的世界·詩文》[C].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156.
[22][24]梁宗岱.《憶羅曼·羅蘭》[A]《宗岱的世界·詩文》[C].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23]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13.
[25]梁宗岱.《詩與真續編》[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163.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