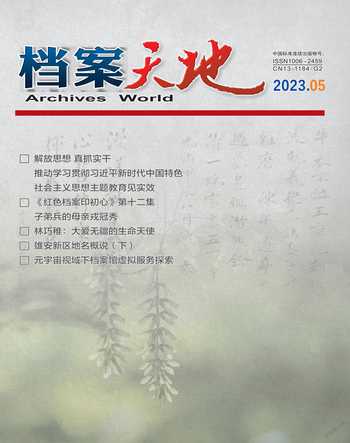雄安新區地名概說(下)
孫進柱
以自然地理實體命名的居民地地名共75個,其中帶有“河”字的村落26個,帶有“淀”字的村落7個,帶有“堤”字的村落9個,帶有“龍”字的村落13個,帶有“口”字的村落16個,充分反映了這一地域淀河密布、居民以水為伴的地理特點。安新縣南河、河西莊,容城縣大河、羅河,雄縣北淶河、岔河等村落,均為因古河道或地處古河道而得名;容城縣北河照、東河村是因北臨南拒河而得名,雄縣楊臨河、大臨河則是因臨趙王河而得名。以淀為名的村落主要集中在安新縣,其中有的地處白洋淀周邊,如大淀頭、西澇淀;有的坐落在白洋淀內,如光淀。以堤為名的村落,多是坐落在堤岸之上,如安新縣崔、王、高、朱公堤,原統稱公堤村,位于新安北堤邊。以龍命名的村落,多是取龍治水之意,期盼能夠減少水患,如容城縣白龍村[1]。雄縣龍灣原稱郝、郭二莊,因村莊坐落于大清河拐彎處,村名改稱龍灣[2]。以口名村的村落多是坐落于河口地帶,如安新縣趙北口,戰國時期為燕國、趙國交界處,又為白洋淀諸水東流之咽喉,故取名趙北口[3]。容城縣黑龍口,因古時此處為萍河渡口,傳說水中有一條黑龍,故名黑龍口。元末,在河岸邊修建一座龍王廟,部分居民遷至渡口附近定居建村,即以渡口名為村名[4]。一些村落的名稱給人以豐富的想象力,帶有水的意象,如安新縣漾堤口、采蒲臺,雄縣茫茫口、馬蹄灣等,體現出鮮明的地理和生態特色。“而雄安新區也將建成一座生態城市,這些都是可以歸納梳理的待保護地名”[5]。
以所在方位命名的居民地地名有63個。這一類地名以派生地名為主,多是圍繞縣城或某一區域核心地名而產生,相對縣城的方位命名,如安新縣南合街,容城縣東關,雄縣三鋪;相對某一區域核心地名命名,如安新縣南關、東角均是由古安州城而衍生的,容城縣仇小王、李小王是圍繞平王命名,雄縣米東大村、米西莊由米家務派生而來,城東、七里莊是因古鄚州城而命名。這一類地名與此區域原生地名連帶關系緊密,地理方位指向明確,易于為當地人所接受。
以某種寓意命名的居民地地名共52個。其命名多是蘊含著人們的某種希望,或是鄉愁、或是愿望、或是一種選擇,如安新縣山西村,明朝永樂年間,有幾戶人家由山西遷至此地定居,他們懷念故土,便將定居之地取名山西村[6]。雄縣樂善莊原名雙柳村。因清乾隆年間,村民張甲樂、張甲善兄弟二人與旗人打官司打贏了,村民為紀念張氏兄弟,改村名為樂善莊[7]。安新縣留村建于明永樂年間,原名劉村。后因遭水患,村莊僥幸留下,因此改稱留村[8]。容城縣留村始建年代不詳,原村名也不可知,元末明初時,此地發生兵災,人口傷亡嚴重,災后留存的居民重新建村,故取名留村[9]。容城縣崇明莊,是因為1941年中國共產黨抗日民主政權為便于領導,將駙馬莊、夏莊、新莊窠三個村合并為一個村,因當時人心向黨,相信前途光明,遂取村名為崇明莊[10]。雄縣東里長、西里長村建于明天啟年間(1621—1627年),因村莊低洼易澇,鄉里居民不斷在村中墊土,使村莊增高,故取村名為里長,后隨著人口的增長,分為東、西里長兩村[11]。此類村落地名不少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和這一地域特色地理元素。
除以上命名類型,還有以神話傳說或以居民職業命名的,共6個。如安新縣北龍化村,清雍正《高陽縣志》載:“其命名以豬化龍也[12]”。安新縣燒盆莊,是因清同治初年,一位擅長燒盆者到此地定居后建起盆窯,以燒盆為業,故取村名燒盆莊[13]。有些村落名稱,現在看起來與職業沒有關聯,但如追根溯源,即可發現其原始名稱與村民的職業聯系,如安新縣喇喇地村,建于明永樂年間,有山西遷民來此定居,因該地低洼積水,居民以打漁為生,遂取村名拉魚地,后來村民不再以打漁為業,村名也演變為喇喇地[14]。 此類村落地名多集中在安新縣,帶有明顯的白洋淀水鄉的特點。
地域特色鮮明的自然地理地名
雄安新區的自然地理地名以淀泊、河流為主體,而白洋淀則是其核心。白洋淀是雄安新區生態之眼,所以在《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中特別強調要做好白洋淀生態環境保護,“實施退耕還淀,淀區逐步恢復至360平方千米左右”“對現有葦田荷塘進行微地貌改造和調控,修復多元生境,展現白洋淀荷塘葦海自然景觀”“遠景規劃建設白洋淀國家公園”[15]。這是保持白洋淀生態底色的重要舉措。
歷史上白洋淀有“九十九淀”之說,包括白洋淀本淀在內的現存百畝以上淀泊有99個,每個淀泊都有名稱,命名方式多樣,或以歷史事件命名,如燒車淀、澇王淀;或以位置命名,如城北淀、留通淀;或以意象命名,如聚龍淀、泛魚淀;或以姓氏命名,如唐家淀、胡家淀;或以魚、鳥命名,如鴣丁淀、鰣鯸淀,或以水生植物命名,如藻苲淀、荷花淀;或以形狀命名,如半角淀、彎簍淀等。均各具形態。也有一些古代淀泊現已消失,如位于安新縣北部的古大渥淀,又稱大溵淀或大殷淀,清乾隆《新安縣志》載:“大殷淀在縣西北五里,即《水經》所謂大渥淀也,周圍四十里,白溝河溢出,由容城天溝蘆草灣水匯而為淀。”[16]此淀消失后,此處成為村落,諧音演化為大王淀,后簡稱大王村[17]。
白洋淀作為一個地理單元,是華北平原自然湖泊的典型代表,歷史上被稱為九河下梢,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的大部分河流匯集于此。其盈縮消長既與自然大氣候密不可分,又與人類活動形成的局部氣候有緊密聯系。在遙遠的地質年代主要是自然的影響,地質的變遷和氣候的變化決定著白洋淀水量和面積的大小。自有人類活動以來,在各個時代,出于各種目的,對于白洋淀的人為影響越來越突出,白洋淀的濕地面貌對于水生物種、濕地植被的變化,以及對于華北局地氣候的影響備受關注,所以才有白洋淀是“華北之腎”的說法。
白洋淀作為一個經濟單元,淀區百姓傍水而居,靠水生存,他們在與水的朝夕相處中,懂得了對水的取予關系,也在與水旱災害的拼搏中磨練出不屈的意志。水的消長,年景的好壞,承載著一代代人的喜怒哀樂,無論是魚葦菱藕等水生物種的自然繁育、產出和人工養殖及種植,還是墾殖種稻、水上航運,對水旱災害的抵御和救濟,都體現了白洋淀水鄉經濟與周邊旱作農業經濟不同的特色,依托水體景觀的現代旅游業更是賦予了白洋淀經濟新的內涵。
白洋淀作為一個歷史單元,歷史發展的每一頁上都寫有精彩篇章,無論是淀區民眾的生活史,還是古往今來淀水中映下的無數布衣百姓、墨客騷人、俠士武夫、帝王將相的面影,淀中凝聚的歷史事件更使白洋淀增添無窮魅力。從戰國時期的燕國南長城,宋遼時期眾多北宋守邊名將屯墾戍邊、以水為柵抵御遼兵,金章宗的渥城,月漾橋下明代的沉戟,趙北口、端村等地留下的清康熙、乾隆皇帝的行宮遺跡,趙北口的十二連橋,再到白洋淀雁翎隊紀念館、孫犁紀念館,都在展示著白洋淀的樁樁往事。
白洋淀作為一個文化單元,其文化意蘊耐人尋味。從渥城書院、三臺書院的設立可反映白洋淀地區人民崇文重教之風;從歷代文人墨客、帝王將相詠白洋淀的詩文中可品讀出白洋淀旖旎的風光、豐富的物產和淀區的風俗畫卷。孫犁的《荷花淀》寫出淀區人民的精神,在其筆下,白洋淀的一荷一葦都被賦予了性格,在詩情畫意中體現了不屈不撓的靈魂。
匯入白洋淀的河流有潴龍河、唐河、孝義河、府河、漕河、瀑河、萍河、白溝引河,歷史上這些河流源源不斷地將清水送入白洋淀,使這片華北最大的濕地始終有水的滋潤和循環,保證了白洋淀煥發出勃勃生機。同時白洋淀周邊的河流南拒馬河、白溝河、大清河、趙王河等也與白洋淀是共生的關系。要使其承載起“千年大計”的生態核心重任,則必須加強白洋淀的全流域綜合治理,全面改善生態環境,使各條河流常年清水流淌,讓白洋淀之水進入自然循環狀態。
體現地域特點的專業地名
雄安新區的專業地名,以堤防和水利樞紐工程為主,符合當地的地域特點。這里的堤防都很有歷史傳承,著名的千里堤,有的堤段有秦堤之稱,捍衛著潴龍河和白洋淀東南及下游的行洪安全;四門堤始修于北宋,保障著白洋淀西南上游村莊不受洪水的威脅;基本利用戰國時期燕南長城遺址形成的新安北堤,大致圈定了白洋淀的北部邊界。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這一地區興建了兩座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其中新蓋房水利樞紐控制著大清河向下游泄洪和通過白溝引河向白洋淀輸水,棗林莊樞紐控制著白洋淀向下游泄洪。這些水利工程都在防范洪澇災害、泄洪排瀝、引水灌溉中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
反映歷史變遷的行政區劃地名
雄安新區的行政區劃地名,反映了此區域行政區劃的歷史變遷。從戰國時期城邑的產生,到秦代在這里建立易縣,西漢容城縣建立,唐武昌縣的建立,五代時期雄州的產生,金代安州、渥城縣的出現,大部分具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容城、雄縣均為河北省千年古縣。歷史上,縣級行政區劃無論是其治理區域還是其名稱都是相對穩定的,縣級以下行政區劃,則隨著各個時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對基層社會的治理方式、人口的增減而不斷調整。
雄安新區在清代以前,基層治理單位有鄉、社、里、屯等,清末,縣以下開始有路的設置,如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雄縣分城關六鋪和東、西、南、北四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將全縣城鄉劃為東、西、南、北、中五區[18]。民國年間主要是區、鄉的設置。新中國成立后,縣以下分區、鄉(鎮)兩級。1958年實行人民公社體制后,縣以下由人民公社轄各生產大隊,一般一個行政村就是一個生產大隊。1983—1984年改變人民公社的行政體制,恢復鄉鎮建制。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交通的日趨便利,幾次全鄉并鎮,或撤鄉改鎮,形成21世紀以來的雄安新區鄉鎮行政區劃的格局。
截至2020年底,雄安新區三縣下轄行政建制鎮22個、鄉11個。一般鄉鎮的名稱是用其駐地村落命名,縣城駐地鎮以所在縣級行政區域命名,如容城鎮、安新鎮、雄州鎮,也有的鄉鎮開始設置時其駐地是個片村,以此片村的名稱命名,后來隨著發展分為若干個村落,其片村名稱已不作為村落名稱使用,但其鄉鎮名稱仍然使用原名稱,體現了歷史的延續性。如安新縣安州鎮、老河頭鎮、三臺鎮均為此類情況,其中安州鎮駐地歷史上曾是安州治所,安州裁撤后,其治所成為較大的片狀村落,分成7個自然村落,各有其名,安州便逐漸不再以自然村落的名稱出現,但安州鎮作為行政建制鎮的名稱則沒有改變。
通過解讀雄安新區地名,可以洞見雄安地區人文歷史和自然地理的基本肌理。這是世代繁衍生息在這里的人群,在與自然環境相適應,在與自然災害相博弈,在歷史發展的大浪淘沙中留下的智慧結晶,也是留給后人的一筆歷史文化遺產。這些地名,體現了名稱的穩定性、內涵的豐富性、通俗實用性和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特點。地名名稱比較穩定的有行政區劃地名中的縣級地名、居民地地名、自然地理地名,這幾類地名不少從產生之日起就一直沿用,如容城、唐河作為古老的地名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居民地地名中,產生于北宋及以前的有102個,其產生的時間距今都有一千余年。
地名不僅是一個稱呼,承載的是從產生之日起便開始積淀的人文歷史和自然特性,雄安地區的文物古跡幾乎都散布在各個村落,所有的非物質文化幾乎都賦存于村落之中,活化在村民的生活和習俗中,記憶著民間文化,體現了人與自然相依存的關系。這些地名絕大部分都很通俗,貼近百姓的生活習慣,是人們日常交流的依憑,易記好用,有的朗朗上口,有著鮮明的地域色彩。也有些地名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如行政區劃地名中的鄉鎮地名、專業地名中的文化教育和交通地名等具有較強的時代性。
在雄安新區大規模建設中,如何處理老地名與新地名之間的關系,已經是擺在眼前的課題。自雄安新區成立以來,已有幾十個村落整體征遷,這些村落地名也隨之消失,存在于這些村落中的故事也就無處棲身。保護和使用富有文化底蘊和地域特色的地名,延續當地的歷史文脈,體現特色文化,“讓尋根的人找到回家的路”“存續雄安新區的文化內涵,鏈接文化脈絡,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都是新區建設的文化底蘊和軟實力”[19]。應是雄安這座未來之城建設中應該給予重視的。
參考文獻:
[1]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03頁。
[2]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85頁。
[3]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5頁。
[4]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03頁。
[5]王勝三:《弘揚地名文化延續歷文脈——“五問”河北雄安新區地名保護與傳承》,載《雄安新區村落地名錄·代序》,人民出版社,2018年。
[6]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4頁。
[7]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88頁。
[8]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3頁。
[9]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04頁。
[10]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05頁。
[11]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687頁。
[12](清)清嚴宗嘉修,李其旋纂清雍正八年(1730年)《高陽縣志》卷一《輿地志·鄉社》。
[13]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7頁。
[14]河北省地名區劃檔案資料館:《河北政區聚落地名由來大典(下)》,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8頁。
[15]《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8頁。
[16](清)高景、孫孝芬纂,張鱗甲增纂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新安縣志》卷一《輿地志·山川》。
[17]河北省安新縣地名辦公室:《安新縣地名資料匯編》,1984年內部資料,第75頁。
[18]民國18年(1929年)劉崇本纂《雄縣新志·法制略·建置篇》。
[19]王勝三:《弘揚地名文化延續歷文脈——“五問”河北雄安新區地名保護與傳承》,載《雄安新區村落地名錄·代序》,人民出版社,2018年。
作者單位:保定市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