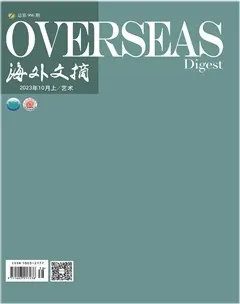《平原上的摩西》復調性敘事范式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進程中,雙雪濤是最耀眼的小說家之一。他創作的現實主義風格小說《平原上的摩西》一經面世,便備受關注,被奉為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在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小說創作中,復調性的敘事范式是典型的文學表達手法之一,構建了復雜多維的敘事結構,為讀者提供了更廣闊的解讀空間。本文主要從敘事主體、敘事時空、敘事意象等方面探討《平原上的摩西》的復調性敘事范式特質。
1 小說復調性概述
復調理論是巴赫金在研究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基礎上提出的。他借用了音樂學中的術語“復調”,說明小說創作中的“多聲部”。具體來說,“復調”手法表現為不同人物、情節和主題之間的交織與碰撞,強調文本中多個聲音或意識的共存與對話,多個人物在不同時空相互交融,他們的敘述相互交錯,以插敘的形式補足了其他人物的故事線。
《平原上的摩西》以懸疑命案為表現題材,借鑒了福克納《我彌留之際》的敘事手法,以敘事主體為核心進行單元架構,每個單元都是第一人稱,聚焦他們,展開敘事。小說的復調性體現為與傳統懸疑小說的敘事范式大相徑庭,它打破傳統線性敘事的限制,通過復調敘事使得文本呈現出多線條、多層次的特點。不同人物發出不同聲音,而這些聲音之間的對話和交鋒,使得作品具有更豐富的內涵和開放性,帶給讀者全新的閱讀體驗。
《平原上的摩西》的敘事時間跨度從1968年至2007年,長達近40年,敘事空間聚焦于“東北—沈陽—鐵西區”。敘事線索源于一件發生在1995年的襲警命案,這一件命案將文中所有人物的命運關聯了起來,也是他們各自命運的分岔口。敘事主體先后有莊德增、蔣不凡、李斐、傅東心、莊樹、孫天博、趙小東7人,7人共進行了14次第一人稱敘述,其核心人物是莊樹與李斐,雙方曾經是工人社區的鄰居,2007年再見時,關系轉變為執法者和涉案人。敘事意象涉及富有神性色彩的“摩西”“平原”“毛主席雕像”“太陽鳥”“火”等隱喻詞[1]。
2 小說復調性的敘事范式
2.1 敘事主體
小說《平原上的摩西》設置了7個第一人稱敘事主體。其中,以出場次數而言,李斐出場4次,莊樹出場3次,莊德增和傅東心各自出場2次,蔣不凡、孫天博、趙小東各自出場1次。每個敘事主體都是作者塑造出的人物,但與作者的思維并不融合。每個人都有個體獨立的思想,在文本中以獨白、對話等形式一點點敘述客觀事實,時時消解傳統小說作者創作的穩定視野和外在立場。每個敘事主體陸續出場,敘事人稱互相交叉,敘事視角自由切換,讓讀者自由穿梭于歷史與當下的時空隧道,根據閱讀的記憶,拼圖般找出分散在敘事主體各自領地的若干碎片化懸疑線索,最終拼湊出一個多聲部合奏的完整情節,領會到每個敘事主體的全貌,還原懸疑迷案的真相。
敘事主體中沒有設置李守廉這個人物,這或許是因為在各敘事主體的共同敘述之下,所形成的敘事視角上“眾聲喧嘩、多音齊鳴”的復調,也能補足李守廉的形象和故事。從作者為角色取名的角度分析,小說里的“父輩”李守廉與莊德增的名字互為對仗,但展現出迥然不同的人生軌跡。李守廉是小型拖拉機廠里技術過硬的鉗工,是東北城市工人集體下崗后迅速貧民化的典型代表。在敘事主體莊德增記憶中,李守廉身體很結實,雖在家排行最小,但卻是個狠角色,兩個哥哥都怕他。李守廉人物本身具有復調性,犟驢脾氣,“文革”期間為了搶郵票扎傷過人;愛女心切,為了女兒李斐一直未再娶;心存善良,1968年救過被紅衛兵毆打的傅東心的父親;1994年下崗那天,救過被城管驅趕的賣茶葉蛋的女人;1995年,女兒李斐因坐在警察蔣不凡為調查案件而開的出租車上被卡車追尾而再也不能站立,他憤怒之下重傷蔣不凡,自己的下巴也被打穿;拿走蔣不凡持有的槍支,槍殺過暴力執法、欺負賣苞米母女的城管。相對比,另一位父輩莊德增的命運則順遂很多,早期接父親的班在卷煙廠上班。身為供銷科長的莊德增是當時第一批下海經商、在國企私有化后發家致富的典型代表。他敢于走出舒適圈,適應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變革,煙草生意越做越大,后涉足房地產、餐飲、汽車美容、母嬰產品,甚至影視娛樂。但因其曾是紅衛兵,參與過毆打愛人傅東心的父親,與性格冷清的愛人傅東心看似生活和諧,卻始終在心理上橫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最終愛上環球旅行,在兒子莊樹從警校以優異成績畢業時,也不曾回國參加他的畢業典禮。
2.2 敘事時空
小說敘事主體的自由變換,呈現出敘述者可以自由穿越時空的共時狀態,形成多維復雜的立體化敘事空間。以敘事主體莊德增第一次出場部分為例,小說從1995年這個關鍵節點開始倒敘,引領讀者進入提前鋪設好的時空,首句夾雜著預敘“帶著一個會計和銷售員下云南”,為后來莊樹敘述父親人生軌跡走向打下充分的鋪墊,尾段寫李守廉的結實、扎傷過人的劣跡以及李斐不聽勸阻、執意玩火的執拗,暗示李守廉、李斐兩個人物的悲劇。在敘事主體李斐第二次出場部分,時間定格在父親李守廉下崗的那天,聚焦李斐和李守廉的對話,展開敘述,使讀者腦中閃現20世紀90年代因國企改革或企業重組等原因導致的工人集體下崗潮這一群體記憶,以及下崗潮后下崗工人群體的陣痛和迷茫。敘事主體相互交錯出場,時不時干預敘事鏈條,在敘述過程中,誤判誤傷李守廉的蔣不凡、暴力執法的城管雖然已經去世,但關于他們的敘事并沒有因此停止或中斷,反而繼續推動小說敘事持續前行。
小說時空的交疊穿插,使敘事始終在同一平面演繹,讓一切歷史皆成為當代史。小說時空映射著現實的痕跡,讓讀者既看到了東北父一輩的純善與隱忍,也看到了父一輩的沉淪與精神上的“營養不良”。小說以“鐵西區”為空間背景,鐵西區是全國聞名的重工業集聚區,工廠比比皆是,工人社區繁華熱鬧。作為“共和國長子”的東北有著完善的工業基礎,重工業發展繁盛,人人以進工廠上班為榮,享受著工廠所提供的優渥條件,如醫療、教育資源等。工廠建技術學校,接收子一輩進廠接班,端起了父一輩的“鐵飯碗”[2]。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東北地區重工業的龍頭地位減弱,在時代的巨輪碾壓之下,東北沈陽的鐵西區從極致的繁華跌落,淪為一片無盡的廢墟,無數工人家庭陷入絕境。小說中為五元錢劫殺他人、為實現再就業不惜與城管大打出手、九千元擇校費等情節皆來源于現實東北。時至今日,讀者從小說中依然能夠體會到以作者本人為代表的東北子一輩的成長歷程中不能言說的疼痛記憶和現實無奈[3]。
2.3 敘事意象
小說《平原上的摩西》中“摩西”“平原”“毛主席雕像”“太陽鳥”“火”等隱喻詞構成的多元意象形成復調敘事的重要一環,讓讀者從東北這一地志空間衍生出“救贖”“希望”“歷史”“革新”“光明”等主題詞。
小說名為《平原上的摩西》,全文三處出現“摩西”。敘事主體傅東心的第一次出場部分,在搬家前給李斐教《出埃及記》摩西分海的典故,囑咐李斐“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誠的,高山大海都會給你讓路,那些驅趕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會受到懲罰”。意味著兩人分別之后,李斐將獨自承受曲折的命運,直到開悟,終究踏上生命的救贖之路。在敘事主體孫天博的唯一一次出場部分,他去市圖書館幫李斐借書,借的十本書書單之首就是《摩西五經》。通過敘事主體交錯講述,此時的“摩西”象征著李斐殘疾后在孫家中醫診所茍藏隱忍、自我救贖的狀態。全文結尾,長大后的莊樹因追尋案件線索與李斐在湖上的小船重逢。李斐告訴莊樹小時候做鄰居時傅東心教的《出埃及記》故事,意味深長地告訴莊樹“如果你能讓這湖水分開,我就讓你到我的船上來,跟你走”,莊樹則回應“我不能把湖水分開,但是我能把這里變成平原,讓你走過去。”文中的“摩西”更多聚焦“救贖”的象征意義。傅東心父親、賣茶葉蛋的女人、賣苞米的女人得到李守廉的幫助。李守廉人性里的善良與罪惡在眾人的裹挾下交織輝映,亦正亦邪。小說中身為混世魔王的莊樹在遇到青年警察后逐漸頓悟走向自我救贖之路。李斐在遇到傅東心后打造了屬于自己的精神天地,一步步走向自我救贖之路。
小說中“平原”不僅是傅東心設計的煙草品牌名字,還意味著“將人生遇到的高山湖水分開兩邊,安穩抵達可以安放身心的舒適平原之地”的期望。莊德增雖是在“文革”期間毆打傅東心父親的人,但借著“平原”煙草事業騰飛。因李守廉曾救助自己遭到紅衛兵毆打的父親,傅東心對李斐有著母親對待子女般特殊的關愛,教她讀書,擴展人生厚度,幫她在貧困動蕩的生活中尋得一處精神的平原。她把李斐的形象畫到煙盒上,借著“平原”煙盒的設計,她也從原本封鎖身心的車間解脫。結尾莊樹所說“我不能把湖水分開,但是我能把這里變成平原,讓你走過去”意味著開放性結局中,莊樹可能會放下李斐父一輩的罪,放她回歸自由的精神平原。
在小說敘事主體莊德增第二次出場部分,紅旗廣場六米高的毛主席雕像被八米高的太陽鳥雕像替換,并強調太陽鳥是外國人設計的。“毛主席雕像”與“太陽鳥”兩個意象出現對立狀態,“毛主席雕像”象征著當時國家計劃經濟時期,“太陽鳥”象征著在全球化發展背景下,中國積極推動經濟轉型,面臨的新形勢、新變革。后來毛主席雕像又被重新換上,太陽鳥被安置到了別的地方,象征著中國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找到了一條遵循歷史基礎、本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之路,東北找到了重新振興的路徑。
小說中“火”的意象包含陰陽兩面,象征著人性的正與邪,以一條暗線索牽引著故事情節,使得敘事顯得跌宕起伏。李斐從小喜歡玩火,因火柴盒與莊樹第一次產生交集,因和傅東心有著一樣的玩火興趣,被傅東心預言“將來興許能干點啥”。李斐因承諾給莊樹在高粱地里放煙火,燒出一片圣誕樹,間接導致自己殘疾、父親受傷、蔣不凡死亡。直到最后兩人湖中再見,李斐才知道當時的約定是一場虛無的煙火,因為莊樹早已忘卻兩人之間的約定。“火”給李斐帶來希望,也毀滅了她的人生。
3 結語
《平原上的摩西》突破了傳統小說的固有模式,敘事結構具有開放性與多元性,運用復調式敘事,凸顯了敘事主體的人物形象,將他們塑造得更為立體而多面。作者對這些小人物有積極肯定、有悲憫、有共情、有愛莫能助的無奈。這些自由生命個體命運的聚集與交錯,以小見大,讓人能窺見東北地區在時代變遷的大背景下所經歷的歲月沉浮,由此讓讀者也能借助文本的橋梁,與人物一起感受人生百態、酸甜苦辣。■
引用
[1]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
[2] 鄧海燕.雙雪濤小說的敘事藝術研究[D].無錫:江南大學, 2021.
[3] 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J].文藝爭鳴,2019(7):35-39.
作者簡介:李艷菊(1985—),女,山東濟寧人,本科,講師,天津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在讀碩士,就職于西藏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