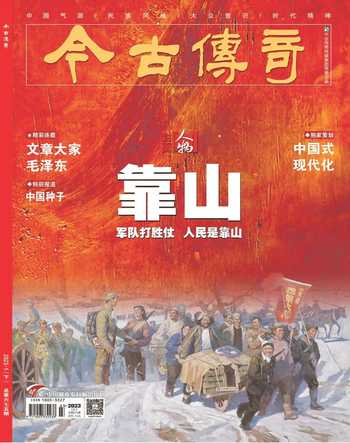種子功臣:自力更生,突破創新


寒來暑往,他們在田壟上勞作也在實驗室里奮斗他們愛種子,就像父母愛孩子
滿身泥塵、滿手老繭、滿頭白發,他們是日夜耕作的“農民”,是一群特殊的科學家。寒來暑往,他們在田壟上勞作,也在實驗室里奮斗,打響了一場場種子攻堅戰。他們愛種子就像父母愛孩子,因為他們深知,“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須把種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丁穎、黃耀祥、袁隆平:完成從吃“洋米”到“東方魔稻”的征途
水稻是中國第一大糧食作物,其產量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40%左右,但在20世紀初,我國一度過著吃“洋米”的日子。1928年,日本學者加藤茂苞等人撰文把栽培稻分為日本型和印度型兩個亞種,甚至認為中國的栽培稻部分來自印度,又稱在中國栽培了數千年的粳稻為日本型等。
糾正這一學術界錯誤認知的是“中國稻作學之父”——丁穎。
丁穎查閱了大量古農書,并結合自己20世紀20年代在我國華南熱帶地區發現有多年生野生稻的事實,經過多方研究最終認定:我國多年生普通野生稻是亞洲栽培稻種的祖先,而中國栽培稻種則起源于華南。丁穎認為,2100多年前,我國古籍中就已明確地從米質的“粘與不粘”出發,記載了粳、秈兩大類型稻種的地理分布和特征特性。他將日本人劃分的日本型和印度型改為粳亞種和秈亞種,這些結論后來都得到了國際公認。
1924年,在日本求學12年的丁穎畢業回國,他既掌握了扎實的現代農業科學理論知識,也因留學游行時遭日本軍警血腥鎮壓的經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民族自尊心,立志“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為提高我國糧食產量,結束吃“洋米”的歷史,丁穎積極開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規律的研究,對廣東糧食生產問題做了大量調查,寫下《改良廣東省稻作計劃書》和《救荒方法計劃書》等文章,還建議政府每年撥出1%的“洋米進口稅”作為稻作科研經費。
無奈民國政府不重視農業生產,生產力低下。丁穎意識到培育良種才是當時唯一可行的增產辦法。
1926年,丁穎在學校附近犀牛路尾的沼澤地里發現了一株野生水稻,他將這株野稻種子命名為“犀牛尾”。經過8年反復篩選,育成“中山一號”,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具有野生稻血緣的雜交水稻新品種。該嘗試很大程度緩解了當時的糧食荒年。
1927年,丁穎拿出部分工資積蓄來補充匱乏的科研經費,與同事、學生們一起走出校園,在廣東省茂名縣公館圩籌建了我國第一個稻作專業試驗基地——南路稻作育種場。
1936年,他又從華南水稻栽種品種“旱銀占”和印度野生稻種人工雜交的后代中,選育出每穗能多達千多粒的水稻雜交種,俗稱“千粒穗”。這一發現震驚中外,對發掘水稻高產潛力的研究大有啟迪。后來,他不斷嘗試更適合國民的新稻種,用系統育成品種與印度野生稻雜交,又在早熟、矮稈和比較大穗的品種間進行雜交育種,40多年持續不斷。
在此基礎上,半個多世紀以來,后輩水稻育種人致力于“中山一號”及其衍生品種研究,已發展出至少8輩95個品種,累計推廣面積達12369萬畝以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丁穎受到黨和政府的信任、關注和重視,他曾當選為第一屆、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3年,75歲高齡的丁穎親自帶隊考察西北稻區,后來病情急劇惡化,就算“用枕頭壓住肝痛部位,仍渾身冒汗”。他堅持在濟南做完了考察報告,才同意回北京醫院,經確診為肝癌晚期,住院僅20天就與世長辭了。
20世紀50年代,我國水稻品種大都是株高在1.5米左右的高稈品種,倒伏現象普遍。在較高水肥條件下越發嚴重,成為當時水稻高產的主要障礙。為此,水稻遺傳育種專家黃耀祥帶領團隊開始了矮化有種研究,將其降為保高八九十厘米的矮稈品種,具有耐肥、抗倒、產量高的特性,畝產從250公斤提高到350公斤以上。“這在世界水稻育種史上是一次重大突破,在世界農業發展史上被譽為‘第一次綠色革命’。”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萬建民評價說。
“第二次綠色革命”是常規稻向雜交稻的變革。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袁隆平為首的育種專家團隊開始雜交水稻研究,并在1973年培育成功,1976年在全國進行大面積推廣。水稻畝產由原來的350多公斤提高到400多公斤。
1964年,袁隆平和助手找到了天然雄性不育株。從選種、試驗、失敗,到再選種、再播種、再觀察……這一路并非坦途。“三系”配套的努力,前8年都失敗了,一直到1972年,也就是被視為研究突破口的“野敗”發現兩年后,還有人質疑甚至反對他的雜交水稻培育方案。
經歷近10年的探索,袁隆平和團隊終于在1973年攻克了“三系”配套難關,并于同年10月正式宣告中國秈型雜交水稻“三系”已經配套。雜交水稻的成果自1976年起在全國大面積推廣應用,使水稻的單產和總產得以大幅度提高。同時,袁隆平帶領團隊開展超級雜交稻攻關,分別于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實現了大面積示范每公頃10.5噸、12噸、13.5噸、15噸的目標。最新育成的第三代雜交稻“叁優一號”,2020年實現了周年畝產稻谷3000斤的攻關目標。從此,雜交水稻被西方專家稱為“東方魔稻”,比常規水稻增產20%以上。
目前,我國雜交水稻種植面積超過1700萬公頃,占全國水稻總面積的50%,僅每年增產的糧食就可養活7000萬人。除了產量上的不斷提高,水稻育種在抗病、抗蟲上也取得了一定進展,條紋葉枯病、白葉枯病靠自主研發的水稻品種完全控制住。
“麥癡”趙振東:中國人終于吃上了國產麥子做的面包
小麥是中國第二大糧食作物,是中國北方地區最重要的口糧作物。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小麥育種大致經歷了抗病穩產早熟、矮化抗倒高產和高產優質高效三個階段。從1949年到現在,小麥單產量增加了8倍。
1956年,黃河流域發生了大面積的“小麥條銹病”,小麥減產超過100億斤,相當于4000萬人口一年的口糧。“小麥條銹病”的病菌變異速度很快,平均5年半就能產生一個新的病種,而要培育一個優良抗病麥種至少需要8年。攻克“小麥條銹病”成了當時的世界性難題。
同年,為了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的號召,25歲的李振聲離開北京奔赴陜西楊陵。有著長久牧草研究經驗的李振聲產生了一種想法:農民精心栽增的小麥體弱多病,野草沒人管卻長得很好,是否可以把雜草基因轉入小麥中?這項研究國內沒有人嘗試過,當時普遍不被看好,李振聲心里也沒底。奔著這一目的,李振聲系統搜集、鑒定了800多種牧草,發現野生的長穗偃麥草等對條銹病有很好的抗性。經過20多年的努力,直到1979年,具有各種抗性的“小偃6號”終于研制成功。此后“小偃6號”成為中國小麥育種的重要骨干親本,其衍生品種近50個,全國累計推廣3億多畝,增產小麥逾150億斤。這種小偃麥的抗病性強、產量高、品質好,于是黃淮流域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謠:“要吃面,種小偃。”
1987年,我國糧食生產已經連續3年沒有增加,但人口增加了5000多萬。也就是在那一年,在西北扎根31年的李振聲臨危受命,深入黃淮海地區,改造當地的鹽堿地、沙荒地和澇洼地,力爭糧食增產。經過6年兩期的治理,全國糧食達到了9000億,黃淮海地區增加糧食504.8億斤。
雖然小麥總產量屢創新高,國產優質麥卻一片空白。“你能想象,上世紀90年代,國內還沒有能做出面包的面粉嗎?”當時在山東省農科院工作的趙振東敏銳地察覺到,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品工業的發展,對優質麥的需求將大大提高。于是,選育能夠替代進口的面包強筋小麥成為他要攻破的第一個目標。
面對國內品質育種這一全新領域,在“無經驗、無材料、無經費”的情況下,趙振東帶領兩名剛畢業的大學生,毅然決然地踏上萬里長征。引進國外的優質品種,用中國同緯度的優質材料進行農藝性狀改良,從成千份材料里尋找品質好產量高的材料用作父本和母本進行雜交……經過十幾年努力和無數次失敗,1999年,趙振東團隊終于成功地培育出優質強筋小麥“濟南17”,并很快實現了國產優質麥出口零的突破。“濟南17”的誕生,不僅攻克了“品質與產量難以協同提高”的世界性難題,還成為我國首個年推廣面積過千萬畝的面包強筋小麥。至此,中國人終于吃上了國產麥子做的面包。
趙振東有一個別名:“麥癡”院士。“每年小麥從種到收的8個月,趙振東不是在地里,就是在下地的路上,像照顧孩子一樣精心呵護試驗田里的麥子。”趙振東的同事回憶道,秋種夏收,趙振東早已養成與麥為伍的習慣。尤其冬季,天寒地凍,為了查看麥苗的長勢,趙振東經常走到田間,單腿跪地,用雙手刨開土,拔起麥苗,仔細觀察,經常一蹲就是半天。“麥品如人品。如果你怕熱,你育出來的麥子就不耐熱;如果你怕冷,你育出來的麥子就不抗寒。”在他看來,搞育種就要跟麥子一起經歷酷暑嚴寒的考驗,穩住心神,俯下身子,才能培育出高產優質廣適的好品種。
一次偶然,同事從趙振東家人口中得知,趙振東本人患有嚴重的蕁麻疹和關節炎。很難想象,一個對冷水、麥芒過敏的人,是如何幾十年如一日堅守麥田。在趙振東家的一個大抽屜里,裝滿了常備藥,每次下田地之前,他都要涂一層厚厚的藥膏。面對家人和同事的擔憂,趙振東沒當回事,他對麥子愛到了癡狂的程度,只要到了麥田,他總能忘掉疼痛。
程相文、趙久然:“必須探索出一個新的突破性品種,才有可能超過別人”
“你是學農的大學生,能不能讓地里多產糧食,我們好吃飽啊!”1963年,大學畢業到河南浚縣擔任農技員的程相文參與救災,老鄉眼淚汪汪的一番話,讓他至今難忘。彼時,當地玉米畝產只有百十斤,“種子差”是病根兒。“加快選育速度,早一點讓鄉親們用上良種!”第二年冬天,程相文一根扁擔挑著上百斤重的種子、行李和全縣人的希望,獨自一人來到海南崖縣(今三亞),開始第一次“南繁”育種。
開荒、建房、播種、施肥、育苗……熱帶蚊子多,他就在身上、頭上套個麻袋睡在田埂上,聽到響動,還要抄起鐵锨,驅趕啃食玉米的野豬、老鼠;青苗缺肥,他一天三四趟,往返幾十里地擔回肥料。花粉存活時間僅有6個小時,授粉必須在上午10時到下午4時進行。當時的海南,地表溫度可以達到40多攝氏度,當地老鄉都躲在家里不出門,可程相文依然往密不透風的玉米地里鉆。盡管條件艱苦,但在程相文眼中,這里是“育種天堂”。
這一年,程相文從海南帶回了自己培育的第一批玉米雜交種子,經過在浚縣當地種植,畝產從100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五六百斤。鄉親們都說:“小程帶回來的是‘金豆子’。”南繁大獲成功,倍受鼓舞的程相文在此后50多年里,始終堅持南繁北育,累計引進和選育了39個玉米新品種,推廣種植面積超億畝。他培育出的“浚單20”玉米新品種成為黃淮海夏玉米區種植面積第一、全國種植面積第二的大品種,帶來經濟效益上百億元,并榮獲2011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這輩子,干的是玉米、想的是玉米。”如今,已經87歲高齡的程相文依然參與南繁,經常一頭扎進玉米地里七八個小時不出來。他說:“這輩子不想其他,就搞玉米了!”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際種業巨頭紛紛參與中國市場競爭,世界500強美國杜邦先鋒公司的的玉米品種“先玉335”,迅速在中國市場搶占份額,播種面積越來越大,高峰時,在我國的種植面積達到2.8萬平方千米。“當時,國內很多育種人員模仿國外的品種進行培育。在我看來,模仿只能跟隨在別人后面,必須探索出一個雜優模式選育出新的突破性品種,才有可能超過別人。”趙久然說。
2001年,趙久然帶領的玉米團隊剛成立不久,僅有幾名科技人員和少量經費。“當時沒有固定的育種基地,我們就臨時租了一塊地。要將國外種質和國內種質兩方面的優勢相結合,即利用國外種質的‘高產優質’方面的優勢,再結合國內‘黃改系’玉米種質在‘多抗廣適’方面的優勢,形成新的雜交模式。”趙久然說。
從2001年選材培育,到2011年新品種正式通過國家審定,趙久然團隊選育的“京科968”雜交玉米品種利用“高密度、大群體、嚴選擇”的自交系選育新方法,經過多年南繁北育的選擇和測試,組配出“京科968”雜交種。據統計,20年來,趙久然團隊培育出100多個優良玉米新品種,累計推廣面積超過3億畝。“對于玉米來說,高產就是硬道理。”趙久然說。僅“京科968”一個品種就增產100多億公斤,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幫助農戶增產增收發揮了重要作用。
郭三堆、許勇:“核心專利絕不會給我們,所以必須自力更生”
改革開放初期,紡織品成為出口創匯的主要商品,棉花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國家863計劃將“棉花抗蟲基因工程研究”列為第一批啟動項目,郭三堆作為項目負責人,全程參與。
1992年至1996年,中國棉鈴蟲大規模爆發,農民噴灑農藥從兩三次增加到20多次也難以防治,棉農損失慘重。由于棉鈴蟲防治都在夏季高溫時節,農藥隨汗液進入人體,導致中毒事件大量發生,棉農大規模棄種。中國紡織業缺少原料,企業紛紛倒閉,工人紛紛下崗。這時,美國抗蟲棉技術研發成功,國家打算自美國引進抗蟲棉品種,但美國人提的條件非常苛刻。“讓人家來占領我們的市場、賺我們的錢,人家都不愿意,要的引進費,折合人民幣超過了1億多元,而且核心專利絕不會給我們,所以必須自力更生。”
1994年,郭三堆團隊取得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二個擁有抗蟲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抗蟲棉有沒有毒呢?這個問題最先由農民提出來。1994年,郭三堆到山東梁山做抗蟲棉新品種試驗。有農民提出質疑,棉鈴蟲農藥都殺不死,蟲子吃了抗蟲棉卻死了,你說抗蟲棉的毒性有多大?郭三堆回答,二者殺蟲機理不一樣,真有毒最先中毒的肯定是我們。
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郭三堆思慮再三,就在一畝農田上做種植示范:半畝種普通棉、噴農藥;半畝種抗蟲棉、不噴藥。到秋天一看,普通棉幾乎沒有棉鈴,絕產了;抗蟲棉則結滿棉鈴,白花花地吐著絮。農民一看說太好了,這個種子一定要給我們留下來。
自推廣種植20多年來,我國累計超過1億的農民種植過抗蟲棉,畝產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幾十公斤,提高到現在的150公斤左右,新疆更是高達350公斤,也再沒有發生過因防治棉鈴蟲而中毒的案例。1996年,我國的抗蟲棉開始推廣應用時,美國不再提任何條件,趕忙在河北、安徽等地成立種子公司搶占市場。2008年以后,中國育種家培育的抗蟲棉品種植棉率已經超過95%,成功奪回了曾被美國占領的棉花陣地。
我國西瓜年產量占全世界的67%,西瓜又是夏季時老百姓熱愛的解暑水果之一。在西瓜育種項目上,中國有了與美國談合作的話語權。
北京市農林科學院蔬菜中心主任、國家西甜瓜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許勇一直想破譯西瓜基因組圖譜,找到西瓜的基因鑰匙。2006年,最初因為傳統的測序技術尚存在缺陷,許勇主動聯絡“外援”——美國康奈爾大學等合作伙伴加盟,確保項目不因經費不足夭折。但雙方有約在先,中方必須延后兩年對外公布及發表相關學術論文,由外方先行獨享基因組圖譜知情權。許勇答應了,至少項目可以順利進行,而且他還留了個心眼,圖譜雖延緩,但基于基因序列的研究保持“中外同步”,且中方在這個過程中觀摩并學習了西方先進的數據管理方式與數據應用手段。“咱不吃虧。”許勇說道。在中外合力下,2011年,許勇主導完成的世界第一張西瓜基因組序列圖譜誕生了。基因組序列圖譜的意義遠不止于為西瓜尋根溯源。憑著這把基因鑰匙,許勇團隊獲得了西瓜抵抗枯萎病、炭疽病、白粉病與病毒病等病害的候選基因或基因標記。
“在西瓜由野生轉為人工栽培的馴化過程中,大量抗病基因丟失。而以往的傳統育種方式,是將病原菌像‘種痘’一樣在苗期接種到西瓜上,但如果我們可以直接從基因層面找到這些‘壞點’繼而在雜交后代的早期準確地予以剔除,那么就有可能高效地將全部優良性狀聚合在同一品種上,培育出體格倍兒壯,口感倍兒好的無敵西瓜。”“西瓜糖分高了,就可以榨糖、制作酒精,不再僅僅是水果,這是多么大的飛躍!”許勇認為,科研單位除了搞好育種,還要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服務西瓜生產發展。為此,全國的西瓜主產區是許勇每年的必去之地。據了解,近10年來,許勇團隊共推廣西瓜及砧木新品種829萬畝,畝增效466至2970元,總效益達60億元,累計為下屬種業企業創收逾1億元,成為了民族蔬菜種業阻擊跨國公司沖擊的中堅力量。同時,良種產業化規模連續多年在全國同行中居首位,成為我國優良西瓜品種的主要源頭之一。
中國種子從被肆意掠奪到有償轉讓給西方公司,是幾十年歲月幾代人的努力
近年來,中國采取進一步措施,通過增加獲得認證的育制種基地的數量來打破本國糧食生產的瓶頸,爭取實現種子自給自足。
自2013年以來,中國首次擴大了國家級育制種基地名單,在現有的100個區域性良種繁育基地基礎上增加了116個國家級制種大縣和區域性良種繁育基地,希望這些國家級制種基地到2025年的供種保障能力達到80%以上,較2016至2020年逾70%的水平有所提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說:“這是振興育種行業的具體舉措。”他說,這還將有助于滿足不同區域對種子的不同需求。李國祥說:“中國的(農業)資源是有限的……現在唯一能取得突破的領域是種子。要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立志打一場種業翻身仗。”
南繁基地就在這名單之中。北緯18度,氣候溫潤,光熱充沛,綠意盎然。從海南陵水過三亞到樂東,一方方農田繪就南繁耕作圖。20世紀50年代起,我國農業科研人員著手農作物種子異地選育工作,一路向南尋找繁育基地,終于發現被譽為“天然大溫室”的海南島南部地區這一不可多得的“育種天堂”。對新品種選育而言,這里是優良“孵化器”,甚至是“加速器”。“相比我國其他地區,種子在這里一年可繁育兩代甚至三代,極大縮短了育種周期。育種材料的抗病性及對濕、光的反應等也可同步完成鑒定,非常有利于新品種提升競爭力、擴大覆蓋規模。”中國科學院院士錢前這樣總結。
“把最好的土地騰給南繁。”為了保障國家育種大計,2014年以來,海南省專門成立南繁管理局,在三亞、陵水、樂東三地辟出占地26萬多畝的國家南繁科研育種保護區,輔以高標準農田和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來此工作的科研人員完全可以“拎包入住”,種植、采收、晾曬、脫粒、打包儲藏……所有育種環節順暢無阻。
每年冬春,數千名科研人員如候鳥般從全國各地來到南繁,開展育種制種研究。截至目前,已有累計超60萬人次科研工作者在南繁開展育種制種。據統計,我國已育成的農作物新品種中,七成以上都經過南繁培育。
2020年6月,崖州灣科技城在崖州灣畔掛牌,依托南繁育種傳統布局科研平臺,成為科技城重中之重的工作。次年5月,崖州灣種子實驗室正式亮相,創新力量得以在此進一步匯聚,生出更茁壯的根來。南繁管理局副局長唐浩說:“接下來我們要制定新的國家南繁硅谷建設規劃,拿出‘十年磨一劍’的勁頭,砌牢‘中國飯碗’的堅實底座,用中國種子保障中國糧食安全。”
“雜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勞應該歸功于南繁。”袁隆平曾這樣評價。據不完全統計,從南繁“走出去”的雜交水稻,累計種植面積已超過3億公頃。國人餐桌上的一碗米飯,種源超過八成來自南繁。可以說,南繁科研育種的工作,具有養育中華民族的戰略意義。60多年來,以袁隆平為代表的南繁人,為了中國人的飯碗,為了國家的糧食安全,付出了的巨大努力和心血。
中國在雜交水稻育種方面的成就,引起了西方的重視。1980年7月,我國首次將雜交水稻技術有償轉讓給美國西方石油公司,次年續轉讓給澳大利亞卡捷爾公司。
中國種子從被肆意掠奪到有償轉讓給西方公司,是幾十年歲月幾代人的努力。
幾代中國人自力更生,從無到有,突破創新,培育出高產種子,讓每一個中國人的飯碗里吃的是中國種子種出的大米、饅頭、玉米……有的甚至站在世界育種的前沿,讓中國在經濟作物的種子事業上不再受制于人。他們是和平年代的英雄,是人民的功臣。他們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推動民族種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責編/趙雪純 責校/李希萌、張超 來源/《大國種子》,楊采怡、鄧慧超著,光明日報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李振聲:中國人能養活自己》,佚名/文,新華社2021年5月13日;《“麥癡”院士趙振東談糧食安全:保證種源安全自主可控,14億人飯碗端牢端穩》,王迪/文,《民生周刊》2022年第13期;《田壟勞作雖辛苦 科學育種成果豐》,鞏育華、臧春蕾、張偉昊、鄧劍洋/文,《人民日報》2022年9月23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