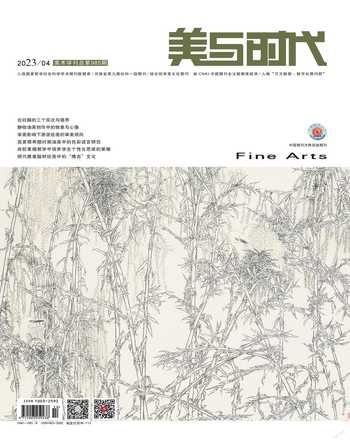米芾行書的美學風格探析
摘 要:米芾是“宋四家”中較具獨特性的一位,不僅是書法家,也是書畫理論家。在米芾的行書作品中,可以十分明顯地體會到他的感情流露,而這感情流露是他在書論中反復強調的觀點。米芾的行書作品有著較高的美學價值,其美學風格主要有四方面內容:一是用筆布局上更天真自然,更重視對感情的揮發;二是下筆時力求古雅脫俗,講究既要借鑒前人的技法,又要超越前人;三是技法上八面具備,從多個角度、多個方向呈現作品;四是作品中骨肉筋兼備,強調整幅作品要骨肉均勻,富有內涵。
關鍵詞:米芾;行書;美學風格
米芾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書法家之一,與蘇軾、黃庭堅、蔡襄并稱“宋四家”。他們四人的書法創作大致可以代表宋代的書法風格,米芾是其中較具個性的一位,世人常常稱其為“米顛”。米芾擅行書,受時代影響,其作品風格前后期差異明顯,前期好學古人,后期則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米芾在行書創作中,常常自覺追求創造性筆法,創作理念上重視“意”“趣”,其作品有著較高的審美價值,既反映出宋人共同的審美傾向,又體現出獨特的美學風格。
一、天真自然
天真自然本是形容兒童性格的詞,用以形容兒童性格純真,在文學藝術中多指作品不加雕琢,隨心而行,是文學藝術中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和精于雕琢推敲相對。米芾不僅是書法家,也是書畫理論家,他對書法理論有較深的研究,天真自然是他一直追求的書法狀態。關于書法中的自然思想,王羲之、蘇軾都有論述,但他們強調書法自然的背后還要學圣賢書、學道義。米芾并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書法應該隨心而行,重點在于書寫的過程,和圣賢書、道義并沒有關系。他強調書法超脫自然、率性而為,這一點在他的書法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像《珊瑚帖》就是一幅典型的自然之作。這幅作品起筆自然,運筆灑脫,書寫過程全憑米芾自己的心意,筆墨間盡顯自由瀟灑之感。
但是,天真自然并不是完全地憑借自己的性情,也不是完全地不思考落筆布局。米芾是一個極其認真的人,他在讀書和書法創作中都十分努力,將讀書寫字當作自己的習慣,“一日不書,便覺思澀”。也正因他長久的堅持,他的行書才能隨心而行。因此,米芾提倡的書法自然是建立在堅實的書寫基礎之上的,正如同畫竹子,胸中有竹才能夠隨心而行,如果沒有基礎,那么寫出來的只能是鬼畫符,稱不上書法作品。為了奠定堅實的基礎,米芾早期的作品以仿古為主,他精心研究書法大家的作品,模仿他們的筆法,然后再根據自己的理解,慢慢形成自己的行書風格,逐漸開始自成一家。因此,米芾行書風格的天真自然是建立在勤學苦練的基礎之上的,這也是天真自然的第一個表現。
除了堅實的基礎,自然的筆法也是十分重要的。米芾書法天真自然的第二個表現就是自由的筆法。在米芾的作品《珊瑚帖》中,一筆一畫盡是自由。這幅作品的字里行間都透露出作者欣喜若狂的心情,“珊瑚一枝”四個大字寫得蒼勁有力,對比周圍的字來說,字體大而筆畫粗,可見米芾寫到這里時的激動心情。這幾個字雖然和周圍的字大小不一,但并不破壞整體的和諧布局,反而更凸顯米芾寫這幅作品的盡情盡興。這樣灑脫的作品出自米芾精湛的筆法。米芾寫字一般輕輕拿筆,讓自己的掌心呈現虛空的狀態。這是因為拿筆太緊容易僵硬,不利于手腕轉動用力,所以輕輕拿筆可以保證筆完全隨著自己的心意而動。同時,在創作過程中,米芾一般不講究間距,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心意來安排,字的大小也不必追求整齊劃一,可以隨著心情產生變化。米芾認為如果一味拘泥于筆法和姿勢,心也會隨著受到禁錮,寫出來的書法作品便會古板僵硬,既喪失美感,也失去意趣。
天真自然是米芾行書作品重要的審美風格之一,也是米芾行書創作的重要指導思想。在天真自然思想的引導下,米芾的行書作品起筆落筆千變萬化,每一幅字都有不同之處,每一個字都有獨特的安排,一筆一畫都洋溢著自由灑脫的氣息。這種行筆風格讓他的作品和“宋四家”中的其他三家有了顯著區別,也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效果,豐富了行書作品的審美風格。
二、古雅脫俗
作為一個書畫理論家,米芾也多次強調要汲取古人的長處,在博采眾長的基礎上再自成一家。古雅脫俗的重點就是既“古”又“雅”,也就是說在學習古法的基礎上,還要增加自己的學識,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進行書法創作。米芾早年致力于學習古人,尤其愛學習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大部分閑暇時間都在臨摹這父子二人的書法,學習二人的書法技巧,力求自己的書法技巧在前人的基礎上能夠再上一層樓。在米芾的很多作品中,起筆和落筆、起承轉合都可以體現米芾個人的書法功力,他的一筆一畫流轉自然,絲毫沒有生澀之感,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用筆之老練。
想要做到古雅脫俗,不僅要效仿古人,還要避免流于庸俗。米芾在自己的行書作品中,常常自覺避開前人書法中的弊端,主張按照自己的審美理想進行書法創作。米芾后期作品往往不拘泥于一個字形,筆墨間變化多端,不再局限于前人的藩籬,表現出宋人審美上對意趣的崇尚之情。在米芾的代表作品《苕溪詩帖》中,下筆堅實,筆墨間盡顯雄渾磅礴,這是其早年學習顏真卿行書的結果。顏真卿的行書以剛健雄厚為主要特點,與其楷書一脈相承。米芾早年學習前人字體時,也極愛顏體,所以在他后來的行書作品中可經常窺見顏體的影子。除了筆墨間的雄渾之外,《苕溪詩帖》突出特點還有字體上的夸張恣意。這幅作品的字體多為豎長字體,結束時往往戛然而止,給人一種奇險的感覺,而且這幅作品中的字體都稍微帶著傾斜,更體現出和晉人風韻的不同之處,打破了晉人書法崇尚平穩嚴謹的風格傾向,表現出獨具一格的美學特色。
除了整體字形上不落俗套,米芾還力求在字的內在結構上不落俗套。在米芾的行書作品中,每一筆畫之間的銜接都千變萬化。以《苕溪詩帖》為例,在這幅書法作品中,橫和豎、撇和捺之間都有著多種銜接方式,像不同字體的三點水,三個點有完全相連的,也有徹底分開的,有重筆相連的,也有靠殘墨虛連的……不同的用墨方式可以反映出米芾在寫此字時的心情,也可以看出米芾對該字的理解。這是米芾在自己的書論中反復強調的創作理念,他認為書法創作既要復古,又要按照自己的審美感受進行肆意的創作,在創作過程中要不拘一格,不能拘泥于前人框架,要能夠形成自己的個性,多方面做到古雅脫俗。
三、八面具備
米芾的行書作品字形千變萬化,人們將其稱為“八面出鋒”。所謂“八面”,也不單是八個角度,也是指從不同方向、不同角度進行換筆和運筆。米芾行書作品的變化根植于他八面具備的換筆和運筆方法,可以說,八面具備是他作品獨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作品重要的美學特色。
米芾行書作品的八面具備特色的第一個表現是作品的方圓并用。在米芾的行書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字體的變化,在用筆的轉折和銜接的地方,米芾常常隨心而行,采用多種方式運筆,有時一個字中也存在方圓兩種銜接方式。以《吳江舟中詩》為例,“昨”字在運筆上,左半邊“日”上方的銜接以圓弧形為主,下方的封口則以有棱角的方形為主,整個字體上方較圓,下方較方,整體的筆畫下墨很重,讓人一眼就可以注意到這個字,給人一種時光雖然逝去,但仍濃墨重彩的感覺。這樣的例子在米芾的行書作品中有很多,這種方圓并用的結構也體現了米芾行書的瀟灑自然,增強了其行書作品的藝術效果。
米芾行書作品的八面具備特色的第二個表現是作品的輕重緩急兼施。米芾的行書創作下筆瀟灑隨性,作品中往往輕重緩急兼用,不但一個字的筆墨有輕有重,整幅作品中也講究輕重兼施。書法作品中最忌諱粗細相同、用墨均勻,即便是在楷書這種方正的作品中,下筆的輕重也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在相對更自由的行書中,輕重自然就是重要的落筆原則。米芾在行書作品中常常自覺尋求用筆的變化,在每幅作品中都追求輕重有度。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米芾的每一幅行書作品都可以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大大增強了作品的美學效果。米芾的《珊瑚帖》和《吳江舟中詩》的輕重感就完全不同。《珊瑚帖》布局上更偏輕一些,整幅作品肆意灑脫,用筆上隨心而行,不加收束,充斥著米芾的喜悅之情;《吳江舟中詩》這幅作品用筆則更重一些,整體上稍顯拘束,和顏真卿恢宏慷慨的風格還有些相似,相對于前幅作品來說,會給人一種沉穩的感覺。
米芾行書作品的八面具備特色的第三個表現是作品的墨色變化。書法作品的用墨一般頗為講究,該濃時則濃,該淡時則淡;該飽墨時則應該飽墨,該枯墨時就應該枯墨。墨色的變化不僅和作品的流暢度有關,也和作品的情感息息相關。米芾在行書創作中最喜歡用枯墨,有時在一篇作品中,會連著好幾個字都是枯墨,像《吳江舟中詩》中就有大量的字都使用了枯墨,在剛開篇的“昨風起”三個字上使用了濃墨,后面的五個字則都是枯墨,然后在兩個字的濃墨之后,連著的四個字又是枯墨,可以說,這幅作品的墨色就是以枯墨為主。在一幅書法作品中,枯墨一般更考驗筆者的功力,雖然用墨不多,但也要體現出字的風骨和感情,書法不精者多不能駕馭。但是米芾在作品中較多使用枯墨,可見其功底深厚。行書作品中,枯墨太多會讓觀者覺得太燥,濃墨太多則會讓觀者覺得太濕,所以一篇行書作品中墨色變化一定要安排妥當。米芾的《苕溪詩帖》中,濃淡安排相依,濃墨中摻雜著枯墨,讓整幅作品富有變化,不潤不燥,給觀者帶來了美的享受。
四、骨肉筋兼備
在繪畫領域,有“畫虎畫皮難畫骨”的說法,也就是說空有形象,毫無內涵。在書法領域也最忌諱筆下的字只有“形”,沒有“意”。米芾行書作品令人推崇的一個美學風格就是骨肉筋兼備,他筆下的每一個漢字都充滿了感情,蘊含了他的審美理想。也就是說,米芾的作品之所以為人稱道,原因在于其筆下的漢字形意兼備。
米芾早年間愛好“集古字”,尤其喜歡臨摹王羲之的作品。臨摹名家作品,是書法入門的第一步,也是較為驚險的一步。一般來說,書法初學者只有在大量臨摹夯實基礎之后,才能夠進入下一學習階段。但很多書法愛好者在之后的書法創作過程中往往會拘泥于臨摹過的大家技法,將自己困在大家作品的狹窄空間里。因此,很多人在書法創作的過程中,多醉心于臨摹名家作品的“形”,但難以達到名家作品的“意”,從而導致自己的書法作品始終難以得到突破。但是米芾雖然大量臨摹名家的字,卻從未將自己的思維局限在名家的作品中。他勇于突破,擅長學習名家技法的長處,創造性地將其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并逐步將其轉化成自己的長處,融入自己的審美理想。
在博采眾長之后,米芾的行書作品就開始形成自己的美學風格。米芾曾在自己的書論中提到骨肉筋的關系,在他看來,一幅作品中,如果肉太多則會讓漢字太肥,骨太多則會讓漢字太瘦,要準確把握骨肉筋的比例。也就是說,只有骨肉筋均勻兼備,才能稱得上是一幅好的書法作品。以米芾的《苕溪詩帖》為例,在每個字的字形結構上,頓挫分明,在變化無窮間又兼顧每個漢字的章法,重視法度,可見其作品的“骨”;在這幅作品中,筆墨十分豐富,可見其下筆的力道,這些豐富的筆墨構成了作品的“肉”;在字與字的起承轉合間,下筆時斷時連,行與行之間安排或緊湊或寬松,整個作品的安排力求和諧統一,可見其作品的“筋”。正是因為這幅作品在創作過程中力求骨肉筋均勻兼備,所以整幅作品看起來十分流暢,骨肉分明,讀來讓人賞心悅目,仿佛真的置身于小溪前聽流水潺潺一般,由此可見米芾在作品中的匠心獨運。
一幅優秀的書法作品,一定是骨肉筋兼備的書法作品,這是書法重要的美學指導思想。在書法領域,一直有著“顏筋柳骨”的說法,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筋骨的重要性。在米芾的行書作品中,米芾通過精心的安排,讓作品中的每一個字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呈現,而這每一個字都力圖骨肉均勻,這是他筆力深厚的表現,也是米芾審美理想的一個重要表現。
綜上所述,米芾的行書作品之所以取得較高的美學成就,一是得益于他長年累月的“刷字”,二是得益于宋代文學藝術領域“尚意”“尚趣”的美學風尚。在米芾的行書作品中,有著米芾對自己書論的嚴格踐行,而他的書論也正是得益于他長久的書法實踐。縱觀米芾的行書作品,總能看到其中飽含的思想感情,肆意揮毫的每一個漢字之間,是米芾對書法意趣的追求和體現。米芾在自己的書論中,總是強調書法是為了娛樂自己,他將書法看作一場游戲,這種不帶任何功利性的想法,讓其行書作品更純粹、更動人,也擁有了更高的審美價值和更好的藝術表現力,大大增強了其行書作品的美學效果。
參考文獻:
[1]米芾.米芾集[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彭吉象.藝術學概論[M].5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3]李福順.蘇軾論書畫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作者簡介:
金子鈺,中國計量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哲學、宗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