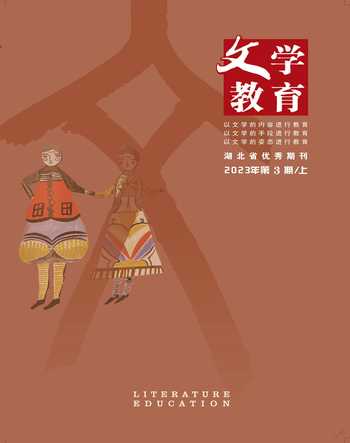魯迅《藥》的數(shù)字修辭及其主題意蘊
劉麗星
內(nèi)容摘要:短篇小說《藥》中的出現(xiàn)了187個數(shù)字,數(shù)字在小說中承擔敘事功能,參與文本建構(gòu)。在環(huán)境描寫中“一”的重復使用,強化了魯迅小說特有的絕望的孤獨;“一”與人物動作相結(jié)合,是對愚昧無知民眾的審視;不同數(shù)字間的對比,以數(shù)字命名人物,則象征著個體與群眾聯(lián)結(jié)的斷裂。而數(shù)字的背后是國民劣根性的解剖,與民族傳統(tǒng)中追求“天人合一”的人格結(jié)構(gòu)相悖,滲透著魯迅悲天憫人的情懷。
關(guān)鍵詞:魯迅 《藥》 數(shù)字修辭 主題意蘊
現(xiàn)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在魯迅手中成熟,對于魯迅的各類研究可謂浩瀚如海。但是目前,國內(nèi)外魯迅小說的數(shù)字敘事研究仍處于萌芽階段,除少量論文外,有分量的學術(shù)專著還沒有出現(xiàn),可以說該研究領(lǐng)域至今存在著大量的空白。目前學術(shù)界所界定的數(shù)字敘事是數(shù)字技術(shù)進入敘事領(lǐng)域,作為一種在線敘事,具有人機交互的性質(zhì),超文本小說、互動影視作品和人工智能寫作等是目前數(shù)字敘事的主要類型。[1]而筆者這里回歸文本內(nèi)部,數(shù)字成為小說的一個敘事元素,用數(shù)字講故事,承擔敘事功能,進而參與文本建構(gòu)。
根據(jù)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難看出,魯迅小說與數(shù)字研究出現(xiàn)了三種路徑。其一,數(shù)字與經(jīng)濟。如《經(jīng)濟敘事與魯迅小說的文本建構(gòu)》一文中指出“魯迅小說對經(jīng)濟的書寫具體呈現(xiàn)為商品經(jīng)濟意識、相應(yīng)的經(jīng)濟行為和具體精確的‘數(shù)字以及事件與情節(jié)的具細處理等等”。[2]其中經(jīng)濟數(shù)字對深入研究清末民初中國民間經(jīng)濟生活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其二,數(shù)字與敘事。杜貴晨教授在《“三而一成”與魯迅小說的敘事藝術(shù)——兼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數(shù)理批評》中認為,魯迅小說運用數(shù)字最突出的特征是“三而一成”,且存在于它敘述與描寫中或明或暗大量運用數(shù)字以為度數(shù)的總體表現(xiàn)之中,具體體現(xiàn)為:三事話語、三復情節(jié)、三變節(jié)律、三極建構(gòu)[3]。除此之外,豐競在《魯迅文學作品中數(shù)字的修辭分析》中通過對魯迅小說中數(shù)字的擬實、描摹、表演與凸現(xiàn)的修辭分析,進一步探究作品中背后幽默與諷刺風格。其三,數(shù)字與文化。如唐帥在《魯迅小說中的數(shù)字觀念及其文化蘊涵》注意到魯迅的《吶喊》與《彷徨》不少作品愛用數(shù)字為人物命名,具體分析了《風波》中各類人物后認為“不幸與悲哀以及死亡與哀悼,總和七字系結(jié)在一起”[4]。同時通過對《孔乙己》十九文錢的反復出現(xiàn)的分析,組成跳躍結(jié)構(gòu),揭示數(shù)字的文化意蘊。而集中分析《祝福》中祥林嫂的人物形象后,指出“一”背后是孤獨心理的刻畫,是“國民靈魂”的解剖。除此之外,魏耕原《數(shù)字十九實虛反復轉(zhuǎn)化的意義——兼論魯迅小說中的數(shù)字內(nèi)涵》一文也通過追溯極數(shù)十九所經(jīng)歷了實虛反復轉(zhuǎn)化的演變過程,用以分析孔乙己所欠的十九文錢,數(shù)字背后是下層知識分子淪為封建制度受害者和犧牲者的悲劇命運。
現(xiàn)有研究以魯迅小說創(chuàng)作為整體,對數(shù)字與小說做了一定分析,提供一個全新的解讀視角,但遠遠不夠。除了上述已系統(tǒng)論述過的小說外(《阿Q正傳》、《孔乙己》、《風波》、《祝福》等),值得注意的是短篇小說《藥》,4523字中就出現(xiàn)了187個數(shù)字,其中由“一” 組成的詞匯更是高達138組。其中有的數(shù)字是固定詞組,如“好一會”、“一無所有”、“十世單傳”;有的數(shù)字和量詞結(jié)合,作為普通敘事元素,并不具備特殊的意蘊,刪掉也不會影響文意,“簇成一個半圓”和“簇成個半圓”,“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和“印成個陽文的‘八字”等可以說并沒有差別;但更多的數(shù)字,在小說中承擔敘事功能,參與文本建構(gòu)。在渲染環(huán)境和人物刻畫中“一”的反復使用,赤裸裸袒露魯迅小說特有的絕望的孤獨。在對國民劣根性的解剖中滲透著魯迅的生命體驗,充斥著悲憫、絕望乃至恐懼。而不同數(shù)字間的對比,以數(shù)字命名人物,營造出一種象征的氛圍,即啟蒙者被被啟蒙者所吃,個體與群眾之間的聯(lián)結(jié)斷裂。而數(shù)字的背后是國民劣根性的解剖,與民族傳統(tǒng)中追求“萬物與我為一”的人格結(jié)構(gòu)相悖,滲透著魯迅悲天憫人的情懷。
一.數(shù)字“一”的重復
唐帥《魯迅小說中的數(shù)字觀念及其文化蘊涵》中專門提及“一”字的使用,主要集中對《祝福》中祥林嫂的論述,其認為:“《祝福》中無論是‘一個活物等相關(guān)數(shù)字‘一的表述,還是‘一件事等相關(guān)數(shù)字‘一的表述,并非所有的‘一字都帶有這種特殊的文化內(nèi)涵。魯迅先生慣于將有傳統(tǒng)寓意的數(shù)字‘一和普通敘事的數(shù)字‘一雜糅在一起,形成帶有節(jié)奏感的數(shù)字串,無形中強調(diào)人物的孤獨和無助。”[5]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祝福》以外,《藥》小說共4523字中,由“一”組成的詞組就出現(xiàn)了138組。通過文本細讀,“一”出現(xiàn)最多的地方有兩處,一處與環(huán)境相聯(lián),另一處則與人物的行為動作結(jié)合。從數(shù)理學角度來看,“‘一跟名量詞(包括某些借用名詞、動詞作‘量詞)結(jié)合,可用于寫人,刻畫情貌、心理、精神、品質(zhì)等,具有很輕的修辭色彩。”[6]
1.“一”與環(huán)境
自然環(huán)境描寫在文本中主要出現(xiàn)了三處,且這三處都采用了“一”字進行架構(gòu),每一處呈現(xiàn)出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且看以下三處。(序號為筆者所加)
(A)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游的東西,什么都睡著。
(B)街上黑沉沉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著他的兩腳,一前一后的走。有時也遇到幾只狗,可是一只也沒有叫。天氣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覺爽快,仿佛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lǐng)似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C)他四面一看,只見一只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微風早經(jīng)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fā)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jīng)]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里,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站著。[7]
胡亞敏在《敘事學》中指出“環(huán)境是一個時空綜合體……隨著情節(jié)的發(fā)展、人物的行動形成一個連續(xù)活動體,因此,環(huán)境不僅包括空間因素,也包括時間因素。”[8]A處環(huán)境出現(xiàn)在開頭,交代故事發(fā)生的時間和空間。短短一句話展觀出觀察的過程,月亮、天空逐一出現(xiàn)。電影般的鏡頭拉長,狹長的一道天浮現(xiàn),而“一片”相對于刪去“一”后更具有整體的空間感。“只剩下片烏藍的天”可以是華老栓抬頭目光所及之處,也可以是劊子手此時此刻所看到的天。而“一片烏藍的天”體現(xiàn)出某種審視感,這就像電影中的場面調(diào)度,鏡頭廣角形成整體。B處空間感仍舊存在,但不同的是從剛開始的空間擴大到華老栓出門走在路上空間聚焦,或者可以說空間縮小,從整體空間到聚焦于當前街道的局部空間。米克·巴爾也在《敘事學導論》中對空間感有相關(guān)分析,他認為“形成空間感知中特別包括三種感覺:視覺、聽覺和觸覺”。[9]視覺上漆黑街道、灰白路、狗遛街;聽覺上狗未叫,寂靜無聲;觸覺上,腳踩地,爽快走。這一切正是通過富有節(jié)奏感的數(shù)字“一”串聯(lián)其中,使得空間轉(zhuǎn)移得以順利進行。其中,在觸覺上敘述者寫到華老栓的腳步輕快,數(shù)字串再次出現(xiàn)。敘述者通過“一前一后”的動態(tài)過程,與緊接著“老栓倒覺爽快”呼應(yīng)。人物的心理意識流變過程,悄然發(fā)生。可以看到華老栓想到小栓有藥可救,腳步不由得輕快起來。C處出現(xiàn)在結(jié)尾,環(huán)境描寫中后半段的三個“一般”是普通敘事,固定搭配。但前半段的三個“一”卻有著話語蘊藉,充盈著一種絕望的、無垠的孤獨感。而且“一”本身就有“獨”、“單”的含義,更是強化了魯迅小說中特有的孤獨和無助。清明墳場,一只烏鴉,一株沒有葉子的光禿禿的樹,偌大的空間只有兩位老人上墳。短短十幾個字,簡單的白描,畫面感極強,仿佛世界在此定格,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啟蒙者已死,被啟蒙者不自知,何其悲哀!一股沉重的失落感涌上讀者的心頭,但這絕望中又帶有反抗的色彩,樹是筆直的,烏鴉是“鐵鑄一般站著”,給人以希望。這種反抗絕望的意蘊與《秋夜》中開頭異曲同工:“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外一株也是棗樹。”[10]有學者指出:“閱讀者在期待著,期待棗樹這樣高大挺拔、直刺天空、清醒而又堅強的‘戰(zhàn)斗者在秋夜里多多益善。然而,‘也是棗樹的結(jié)果使這一期待完全落空。”[11]一株棗樹的重復牽動著讀者的心緒,在閱讀的過程中打破心理上既成的思維指向,造成失落感。同時,棗樹“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也流露出一種“執(zhí)拗的反抗絕望的完全性和倔強感”[12]。
2.“一”與人物
讀魯迅的小說常有一種觀看戲劇的感覺,若把小說某一段拿去當劇本,甚至不需要修改。魯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說:“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qū)⒁馑紓鹘o別人了,就寧可什么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xiàn)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13]可見魯迅在小說中自覺借鑒戲劇藝術(shù),淡化背景,以“人”為核心推動敘事。
《藥》共四節(jié),像是標準的四幕劇。華老栓、康大叔是唱戲者,其他人既是戲中人也是看戲者。《藥》中用四個場景敘寫了華家的掙扎求生:華老栓夜晚偷偷買藥——華小栓服藥——茶客們談藥——華大媽清明上墳。前三節(jié)通過數(shù)字“一”的重復與人物動作在三個斷面展開,第四節(jié)場景轉(zhuǎn)換來到第二年的清明。第三節(jié)到第四節(jié)中文本時間幾乎為零,故事時間無窮大。熱奈特在《敘述話語》中首次提出了“故事時間”和“文本時間”的概念,其中當故事的某些事件沒有在敘述中出現(xiàn),便會造成省略。而受戲劇舞臺表演的限制,戲劇作品中也相應(yīng)存在省略。
動作大于語言是戲劇表演的關(guān)鍵,“運用數(shù)字在次數(shù)和頻率上對動作進行規(guī)定,使動作有 ‘數(shù)可依”[14]。其中《藥》中最代表性的人物莫過于華老栓和康大叔。
華老栓出門前“一面聽,一面應(yīng),一面扣上衣服”;路過一簇人小心翼翼地“按一按衣袋,硬硬的還在”;買完饅頭后匆匆忙忙回到家后,滿懷希望地“一面整頓了灶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灶里;一陣紅黑的火焰過去時,店屋里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店里人來人往,老栓忙忙碌碌“提著大銅壺,一趟一趟的給客人沖茶”,盡管“兩個眼眶,都圍著一圈黑線”;康大叔講話時,唯唯諾諾、卑躬屈膝地伺候著“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垂著”。通過有節(jié)奏感的數(shù)字串“一”的重復,對人物行為動作的刻畫,無形中增加了藝術(shù)的真實性,華老栓的一舉一動仿佛就在眼前上演,這一點是別的修辭手法無法替代的。魯迅關(guān)注的是病態(tài)社會中的病態(tài)人生,華老栓不僅僅只是一位為救兒子的普通老父親,更是國民劣根性根深蒂固的代表,概括了封建末世整整一代貧民的生活命運。作為底層民眾,他勤勞、善良、吃苦耐勞,但又有著深信人血饅頭能治病的麻木無知、愚昧,自甘被掠奪、被剝削。一切真誠的努力都毫無意義,在他身上,魯迅傾注了其悲天憫人的情懷。
數(shù)字“一”與動作結(jié)合的獨特手法在康大叔形象塑造中也同樣呈現(xiàn)。隨著一次怒吼康大叔第一次出場:“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康大叔作為職業(yè)劊子手,在出場時讀者不知其姓名,而是連著兩次寫到“黑色的人”。黑色意象本身隱喻著等級地位的尊貴和威嚴,可以看作是“封建舊勢力善用黑色的精神壓力效果以此恫嚇、威懾被統(tǒng)治階級的一種手段”[15]。對當權(quán)者的恐懼、卑微使華老栓立刻“縮了一半”。交換時,康大叔“一只大手,向他攤著;一只手卻撮著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緊張、密集的動作與數(shù)字“一”搭配充滿戲劇表演性質(zhì),康大叔冷漠、殘酷、威嚴的形象躍然紙上。
二.“一”與其他數(shù)字的對比
《藥》中數(shù)字“一”除了大量出現(xiàn)在主要人物華老栓、康大叔身上外,次要人物描寫中也出現(xiàn)了不少數(shù)字,在不動聲色的敘述中形成個體與庸眾的對立。我們可以看以華老栓是“一個人”,“他的兩腳,是一前一后的走”;看客是“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里徘徊”,“一眨眼,已經(jīng)擁過了一大簇人”;革命者夏瑜“家中只有一個老娘”,“榨不出一點油水”,最后只留下“一座墳”。華老栓只關(guān)心自己的生活,看客是爭先恐后去賞玩苦難,啟蒙者是孤身一人的奮戰(zhàn)。在魯迅有意識的設(shè)置中,個體與群眾之間的聯(lián)結(jié)斷裂,這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當時革命黨人脫離群眾的缺點。
除此之外,在魯迅的小說中以數(shù)字命名人物的情況也有不少。《風波》中有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趙七爺?shù)龋弧睹魈臁防镉袉嗡纳┳印⑺{皮阿五;《離婚》中的八三、莊木三、七大人等。具體到《藥》中,這些看客們同樣也沒有具體名字,駝背五少爺、夏三爺、二十多歲的青年人等。可以說,他們是看客的集合體,是庸眾的代表。五少爺家中排行第五,“少爺”稱呼可推知其出生于封建舊大家族,而駝背這一特征正是家道中落的象征。在他的身上明顯殘留著紈绔子弟的生活習氣,“每天總在茶館里過日”。而二十多歲青年人的存在魯迅特意點出其大致年齡,背后也別有深意。正處于朝氣噴薄、熱血的年紀,理應(yīng)當更快接受新事物,有目標,有理想,對于革命有自己的判斷,但他卻在茶館里游手好閑,虛度光陰。當聽到夏瑜“關(guān)在牢里,還要勸牢頭造反”時,則表現(xiàn)出氣憤的模樣,麻木滑稽,顯示出人性的冷漠與殘忍。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藥》中也出現(xiàn)了兩次有關(guān)于錢的表述。第一次是華老栓一家準備買藥的“一包洋錢”,第二次則出現(xiàn)在康大叔與眾人閑聊提及“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一包洋錢”是數(shù)字的模糊,具體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包”字我們又可揣摩出分量絕對不少。在《孔乙己》中,“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出到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16],“至于孔乙己所欠的‘十九個錢,則顯然借用虛數(shù)所蘊含極數(shù)的意義”[17],十九文錢是虛數(shù)中的大數(shù),壓垮了孔乙己最后生存的希望。而華老栓只是開著陳設(shè)簡陋茶館,他起早貪黑、勤勤懇懇,這一包洋錢也許是他一生的積蓄。華老栓家一床“滿幅補釘?shù)膴A被”,買藥的路上謹慎小心,“又在外面按了兩下”,“按一按衣袋”等細節(jié)描寫又暗示了華老栓一家生活上的困頓與窘迫。而諷刺的是,夏三爺?shù)母婷芫洼p松獲得了二十五兩白銀。在這里,數(shù)字不再模糊,而是明晃晃的、雪白的實在之物。夏三爺是夏瑜的親戚,銅錢到白銀的跨越式轉(zhuǎn)變,身邊人為了利益不惜出賣革命者,夏瑜最后只剩下“一座墳”就顯得無比落寞。
三.數(shù)字背后的文化內(nèi)蘊
“一”是《藥》中使用得最多的數(shù)字,而“一”的背后更多的是國民劣根性的暴露,這顯然與民族傳統(tǒng)中追求“萬物與我為一”的人格結(jié)構(gòu)相悖。早在春秋時期,《道德經(jīng)》便蘊含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哲學內(nèi)核,而《莊子》也有“泰出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行,物得以生,謂之德”。“一”是萬物之始,開啟了從無到有、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一”是最小的自然數(shù),卻又是最大之數(shù)。而“醫(yī)道相同”,中醫(yī)也循天時之變,追求“天人合一”。在《藥》里,“人血饅頭”治病法是對“道”的消解,帶進了魯迅對中醫(yī)的消極感受。魯迅的一生也和各種疾病糾纏著:童年的牙痛,父親的病與死,青年時赴日學醫(yī),中年以后飽受胃病、肺病的折磨,最后死于肺病。在《父親的病》中,所謂名醫(yī)們荒唐的藥引“蘆根和經(jīng)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對”[18]何嘗不是“人血饅頭”的變形?“一”所隱含的和諧、包容的內(nèi)核在華老栓身上轉(zhuǎn)為了愚昧落后、麻木冷漠,在康大叔的血紅刀子下聚合成兇暴殘忍。人血來自治病的“醫(yī)生”,而華小栓一聲聲的咳嗽也是飽受病痛折磨魯迅的切身體驗。“人血饅頭”治病顛覆著“醫(yī)/患”關(guān)系,用以審視著孱弱的國民。
而“三生萬物”背后蘊藉著“天、地、人”三級之道,正如魯迅在小說敘事中的“三級建構(gòu)”。[19]《藥》中的中心人物自然是華老栓,而與之對立的是以暗線形式出現(xiàn)的革命者夏瑜,康大叔、駝背五少爺、花白胡子老頭等酒客們,便構(gòu)成三級,推動故事的發(fā)展。其他數(shù)字,華老栓的“一包洋錢”與夏三爺告密所得的“二十五兩”白銀形成強烈的反諷。社會底層農(nóng)民傾家蕩產(chǎn),在生存的邊緣苦苦掙扎。而極端自私的夏三爺,為了保全自己和錢財,親人的命在他眼里視如草芥。更具普遍性的看客們“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青年的熱情,如此而已,看看殺人尋熱鬧。魯迅不止一次在作品中提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20]青年尚是如此,他人何嘗不是這般無知?魯迅赤裸裸地控訴封建思想觀念對民眾身心的戕害,而在這物質(zhì)和精神極度窘迫的狀態(tài)下,魯迅所發(fā)出的啟蒙之音又如何能夠漫延開來。同時文中的人物不配擁有名字,他們是一類人,是“吃人”的民眾,更是被吃的對象。至于夏三爺、夏四奶奶這兩個人物的年齡排行,細細揣摩也含有言外之意。《中國古代的神秘數(shù)字》一書中對于數(shù)字“四”有這樣一番解讀:“四”的大寫字“肆”卻不僅在語音上同“死”有巧合關(guān)系,而且在意義上也同“死”的觀念有著不解之緣……《說文解字》釋“肆”為殺死后陳尸。[21]可見夏四奶奶排行第四,而非第三,隱喻著兒子夏瑜的死。而“三”在《說文解字·三部》中釋“三,天、地、人之道也”,夏三爺?shù)臒o恥告密正是對道的違背。同時,《藥》共四節(jié),第四節(jié)華小栓、夏瑜已死,而清明上墳所各擺的四碟菜何嘗不是對農(nóng)民、革命者“死”的祭奠。
四.《藥》的主題意蘊
魯迅在談到《藥》的創(chuàng)作意圖時曾說:“《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斗而犧牲,愚昧的群眾并不知道這犧牲為的誰,卻還要因為愚昧的見解,以為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某一私人的福利”。[22]這也可以看做是對《藥》主題最直接的概括。《狂人日記》中是“吃人”更多是一種隱喻,而到了《藥》中“吃人”成為血淋淋的事實,《示眾》中“看 /被看”模式進一步發(fā)展為“被吃/吃”模式。
康大叔手起刀落,個人在他的世界里毫無差別,他是人性的野蠻、愚妄殘忍的象征。華老栓固執(zhí)地相信“人血饅頭”能治病,而這人血背后是革命者的犧牲,苦難是底層民眾的生活常態(tài),“生”的掙扎要以革命者“死”為代價。他努力求生,只想救救自己的孩子,但這一點合情合理的、微小的希望都得不到滿足。在吃人的舊社會,似乎全社會都要從他這樣的勞苦大眾身上榨取血汗?jié)M足自己的欲望。此外,《藥》中那些潮一般涌向看殺革命者的人,茶館里無所事事的看客,他們是精神荒原的流亡者,賞玩著苦難,不自知。花白胡子老頭,理應(yīng)該是年齡大,見識多。而他卻處處討好迎合,稱夏瑜為“這個東西”,被打也不可憐;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聽到夏瑜被打后反說阿義可憐時,他恍然大悟的說“發(fā)了瘋了”,其實什么也沒有悟到。而夏瑜是小說中塑造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者形象,雖在小說中沒有過多篇幅的正面描寫,但可以看到夏瑜始終存在,即使被捕后也在獄中熱忱地宣傳革命活動。而他做所的一切努力都毫無疑義,死后成為茶客們閑聊的談資。他是孤軍奮戰(zhàn),他所面對的是專封建制等級制度下制造的、早已麻木的順民和奴才,夏瑜的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了革命者不為群眾所理解的悲哀。”[23]
看客的精神實質(zhì)是自欺欺人、冷漠無知、殘忍自私,幾千年的封建思想觀念、封建倫理道德是其形成的社會歷史根源。看客形象中蘊含著魯迅悲憫的情懷和真誠的“立人”使命,魯迅正是借助“看客”形象顯示他徹底的反封建意識和呼喚啟蒙的現(xiàn)代性品格。而故事的最后,夏瑜的墳上憑空出現(xiàn)了“一圈紅白的花”,烏鴉箭一般向天空飛去,這是對黑暗現(xiàn)實的絕望反抗,給予那些縫隙中苦苦掙扎的人們一絲絲希望。
參考文獻
[1][荷]米克·巴爾.敘事學導論[M].譚君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2]張德鑫.數(shù)里乾坤[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孫玉.現(xiàn)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4]吳中杰.吳中杰評點魯迅小說[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5]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6]吳秀明.多維視野中的百部經(jīng)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7]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8]葉舒憲、田大憲.中國古代的神秘數(shù)字[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9]杜貴晨.“三而一成”與魯迅小說的敘事藝術(shù)——兼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數(shù)理批評[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02).
[10]豐競.魯迅文學作品中數(shù)字的修辭分析[J].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9(03).
[11]壽永明,鄒賢堯.經(jīng)濟敘事與魯迅小說的文本建構(gòu)[J].文學評論,2010(04).
[12]孫淑芳.論魯迅小說中色彩語碼的隱喻內(nèi)涵[J].魯迅研究月刊,2014(09).
[13]魏耕原.數(shù)字十九實虛反復轉(zhuǎn)化的意義——兼論魯迅小說中的數(shù)字內(nèi)涵[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1(02)
[14]唐帥.魯迅小說中的數(shù)字觀念及其文化蘊涵[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5).
[15]胡亞敏.數(shù)字時代的敘事學重構(gòu)[J].江西社會科學,2022,42(01).
注 釋
[1]胡亞敏:《數(shù)字時代的敘事學重構(gòu)》,《江西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
[2]壽永明、鄒賢堯:《經(jīng)濟敘事與魯迅小說的文本建構(gòu)》,《文學評論》,2010年第4期。
[3]杜貴晨:《“三而一成”與魯迅小說的敘事藝術(shù)——兼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數(shù)理批評》,《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4]唐帥:《魯迅小說中的數(shù)字觀念及其文化蘊涵》,《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05期。
[5]唐帥:《魯迅小說中的數(shù)字觀念及其文化蘊涵》,《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05期。
[6]張德鑫:《數(shù)里乾坤》,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頁。
[7]魯迅:《藥》,《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472頁。
[8]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頁。
[9][荷]米克·巴爾:《敘事學導論》,譚君強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頁。
[10]魯迅:《秋夜》,《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頁。
[11]吳秀明主編:《多維視野中的百部經(jīng)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頁。
[12]孫玉:《現(xiàn)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頁。
[13]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頁。
[14]豐競:《魯迅文學作品中數(shù)字的修辭分析》,《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15]孫淑芳:《論魯迅小說中色彩語碼的隱喻內(nèi)涵》,《魯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9期。
[16]魯迅:《孔乙己》,《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頁。
[17]魏耕原:《數(shù)字十九實虛反復轉(zhuǎn)化的意義——兼論魯迅小說中的數(shù)字內(nèi)涵》,《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18]魯迅:《父親的病》,《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頁。
[19]杜貴晨:《“三而一成”與魯迅小說的敘事藝術(shù)——兼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數(shù)理批評》,《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20]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頁。
[21]葉舒憲、田大憲: 《中國古代的神秘數(shù)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105頁。
[22]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藥》,轉(zhuǎn)引自靳邦杰、王世家:《中學語文課本魯迅作品詳解》(高中冊),北京工業(yè)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頁。
[23]吳中杰:《吳中杰評點魯迅小說》,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頁。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