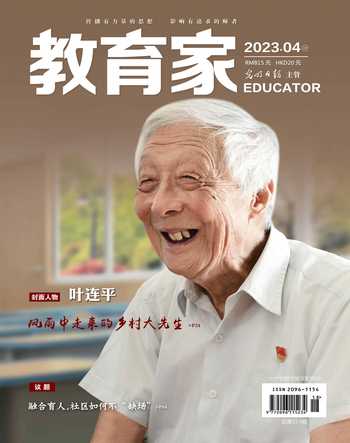家校社合作中社區“缺場”的根源分析
戚務念

家庭、學校和社區三者均是相對獨立的組織,各自的立場、利益和行動邊界在傳統意義上相對獨立。而為了一項共同的事業,需要協同起來跨界行動,這就意味著各自都在做著‘分外的事。要把‘分外的事做好,‘行動者,行動和組織結構,意義和價值均須超出傳統立場和行動邊界。
家校社合作是“學校、家庭和社區伙伴關系”這一問題域的簡稱。然而,學校、家庭和社區三者之間并不必然形成伙伴關系。在我國,與家庭和學校之間的互動頻率、質量相比,社區參與不足的現象的確普遍存在,尤其表現在機構(組織)層面的家校社合作行動中。
社區有著豐富的教育資源,但社區和學校共同開展的活動很少,且大多處于自發狀態,充當著被動支持者的身份。據江西省一項大型調研發現,在家校社合作的“當好家長、相互交流、志愿服務、在家學習、參與決策、與社區合作”六大任務類型中,家長和老師在“與社區合作”中的參與率均最低(分別為8.1%和7.9%),與家長“在家學習”的參與率(68.2%)、教師“志愿服務”的參與率(68.5%)相比極為懸殊。社區合作參與的不足,與家庭和學校對社區資源的需求渴望是不匹配的。2021年針對江蘇省某高中學校的調研顯示,78%的家長和74%的教師最需要社區(社會)給學生(孩子)提供社會實踐、志愿服務的場所和機會,41%的家長表示從未收到家庭教育指導培訓或講座的邀請,38%的家長很少收到。對癥方能下藥,解決問題的前提是找到問題的根源。
社區“缺場”的本質根源
所謂本質根源,是指不論在怎樣的時空條件和社會情境下都會發生,由于組織協同、社會治理本身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而產生的運行困難。這一困境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成熟社區還是不成熟社區,只要涉及多元主體協作,都必須正視和面對。
本質而言,家校社合作是一項組織之間的跨界行動。家庭、學校和社區三者均是相對獨立的組織,各自的立場、利益和行動邊界在傳統意義上相對獨立。而為了一項共同的事業,需要協同起來跨界行動,這就意味著各自都在做著“分外的事”。要把“分外的事”做好,“行動者,行動和組織結構,意義和價值”均須超出傳統立場和行動邊界。三者除了自身原有的主職主業之外,在現實的參與行動中,大多基于各自的立場,關注的是各自的利益,即他們在職責、社會功能、利益訴求和行動期望上具有異質性,這也是三者合作中存在阻礙的本質根源。
從現實情況來看,家庭和學校之間的立場沖突表現為,家庭更關注自家孩子的學習和成長,而學校老師則關注全體學生;家長對發生在家庭(生活地)的行動參與度較高,而老師更注重在學校(工作地)開展的活動;家長參與度高的活動為當好家長、在家學習等主導權高的活動,老師參與度高的活動則為參與決策和志愿服務等活動。又如,當前學校教育系統普遍反映,由政府各部門主導的各種活動進校園干擾了教師的正常教育教學工作,這種現象也主要因為各自的立場和行動邊界不同所致。在當前的職能設定中,社區主要承擔著政府部門賦予的管理和便民服務職能等,教育職能并未占據核心位序,即使在教育職能中,青少年的教育也只是眾多教育、培訓和文體活動中的其中之一而已。
社區“缺場”的機制根源
我國家校社合作中的社區“缺場”在機制建設根源上可作下述分析。我國的家校社合作主要由教育部門自上而下推廣普及,目前主要包括家校社合作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兩部分工作,歸屬于德育科室。在管理權限上,教育行政部門對學校有著明確的管理權限,在督查或評價機制上對中小學家校社合作共育也有具體要求。但在合作層面,教育部門只對家庭和學校的合作提出要求,并沒有強調與社區的合作,對社區相關工作更無管理權限。如有教師表示“家長可以配合學校工作這是沒有問題的,關鍵社區憑什么配合學校,這之中需要建立機制”。又如,學校系統雖較普遍存在家長委員會,但這一組織中并沒有社區工作人員的參與,監督和評價學校管理的社區工作人員更少。
在社區系統,家校社合作共育工作的地位很高,系黨建工作的一部分,與此有關的工作主要由社區黨支部副書記分管,但組織架構受重視度卻不夠,如尚無具體的合作共育機構和負責人,在家長學校、家庭教育指導站、家庭教育指導師的建設上缺乏,更談不上具體的工作計劃和任務。在活動開展上,主要通過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的老同志來組織青少年學生到社區開展教育活動,如平時開展節日主題活動,暑期舉辦傳承地方傳統文化和普法活動等。在實際工作中由市、鎮兩級的關工委進行督查和評估,但這方面工作的評價分值在綜合評估中所占比例很少。
在婦聯系統,由家兒部專門負責家庭教育工作,該部門有專門的負責人,負責布置下屬婦聯開展家庭教育等相關工作。同樣,由于沒有一個具體的共育組織機構,教育部門和婦聯系統掌握的資源又各自不同,調用統籌資源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所以在協調相關工作時比較麻煩。教育部門和婦聯在開展相關工作時有聯系,但只是暫時性的聯系,缺乏固定的聯系機制。在鎮婦聯和街道婦聯不再下設專門部門,而由婦聯主席負責全面工作。因為科層隸屬關系不同,街道或鎮婦聯與學校開展共育活動時,一般先要征得鎮、街道教育主管領導的同意,然后再與街道、鎮教育科橫向部門之間協作開展相關活動。一位婦聯系統的家兒部部長曾為家長學校的問題感到有心無力,“我們不知道如何在社區層面開展家長學校工作,因為學校系統有了家長學校,如果我們同質化地開展這項工作既沒有必要也沒有號召力”。
社區“缺場”的社會根源
《教育部關于加強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導意見》頒布以前,我國一直沒有具體政策文件要求社區承擔家校社合作共育的義務和責任。但通過對社區人員的訪談可以了解到,不少社區對于家校社合作中的缺場并非本意,而且也為此努力過,“其實每個社區基本都有青少年學校、家長學校”,但實際作用并不大,一些所謂的協作活動也是形式大于內容,“為了拍個照片,發條新聞,說明干過這項工作”。據社區工作人員反映,兒童青少年教育方面,社區一直沒有深入的社會性根源可以歸納為教育內卷,即總體而言青少年學生的學業負擔依然過重,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在學習之中,這種現象在城市社區更加明顯。“平時要上學,周末還要上各種輔導班,學各種特長。”不少家長表示,在教育焦慮的催使下,父母在孩子放學后要么自己監管子女寫作業,要么將子女送往各種輔導機構,學生們的時間和空間依然被片面的兒童發展觀掌控著,投身于社區才更可能獲得的軟技能(領導力、團隊合作能力、溝通能力、決策能力等)以及幸福感等則被排在次要的位置被不斷忽視。
找出家校社合作中社區缺場的根源,并不是為了停滯不前尋找借口,而是為了通過根源分析來尋找解決的路徑進而更好前行。在現實的協同育人情境中,家庭、學校和社區三者之間交疊影響的面積可大可小,可能出現如柏拉圖所設計的那樣高度重疊,合為一體,也可能出現相互分離,導致毫無交集等極端情況。兩個極端都是不可行的,歷史與實踐表明兩個極端的做法也是不可持續的。社區中蘊藏著豐富的教育資源,校社協作雙向互利,家校社合作意義重大。家校社合作正成為當今世界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教育變革的重大課題。不少學者和實際工作者分別從學校立場探索了學校和社區協作的路徑,筆者認為,我們同樣需要從整體上把握家庭、學校和社區三者在協同育人上的邊界與定位,國家需要有頂層設計和國際視野,也需要學界從廣闊的社區實踐中挖掘成功案例,并提煉機制和條件以使案例發揮輻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