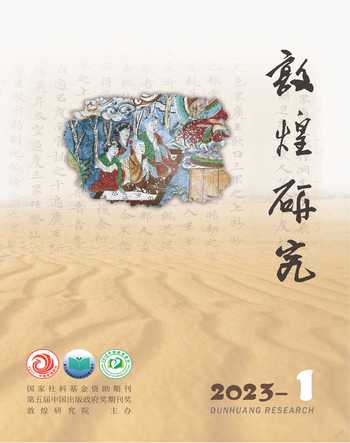帝后禮佛圖:大唐石刻線畫與敦煌紙墨畫稿



內(nèi)容摘要:利用近年新見《大唐皇帝皇后供養(yǎng)圖》線刻畫與敦煌莫高窟《帝后供養(yǎng)禮佛圖》粉本草圖,進行對比研究,結(jié)合在敦煌壁畫中多次出現(xiàn)的帝王形象,揭示了皇權(quán)統(tǒng)治者的形象對宗教藝術(shù)表現(xiàn)的深刻影響,指出經(jīng)幢石刻線圖與墨線紙本草圖,雖然均沒有真正轉(zhuǎn)換生成大型石窟壁畫新圖像,但是不僅可見中古時期佛教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的帝王政治庇護因素,也可見唐代皇帝、皇后形象作為“夫妻家庭與政治藝術(shù)”的圖像流傳,在宗教文化諸領(lǐng)域中不僅成為教化民間信徒的理想粉本,也成為國泰民安與積攢功德的祈求心愿。
關(guān)鍵詞:唐代;帝后供養(yǎng)線刻圖;敦煌;帝后禮佛粉本圖
中圖分類號:K87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3)01-0001-13
Scenes of the Emperor and Queen Worshipping the Buddha:Great Tang Line Drawings of Stone Inscriptions and the Ink Paintings of Dunhuang
GE Chengyo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items newly discovered at the Mogao Grottoes in Dunhuang:a line drawing taken from a stone inscription entitled“The Emperor and Queen of the Great Tang Presenting Offerings to the Buddha,” and draft paintings of a scene depicting “The Emperor and Queen Worshiping the Buddha.” By comparing these items with the images of emperors in Dunhuang mural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that images of imperial rulers had on Buddhist artistic expression. Although neither the line drawing nor the draft paintings were ever used as the basis for a large-scale cave temple painting, they do indicate that artists incorporated political themes in their creation of Buddhist artwork, particularly the idea of imperial political figures finding asylum in religious observance. Th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iconographical spread of “husband-wife, family and political art” in Tang dynasty China was not only ideal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lay practitioners, but also expressed the wish of the people for a prosperous mother country, peaceful life, and deities that would answer their prayers.
Keywords:Tang dynasty; ling drawing of the Emperor and Queen presenting offerings to the Buddha; Dunhuang; draft painting of the Emperor and Queen worshipping the Buddha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在唐朝皇權(quán)統(tǒng)治的國家里,皇權(quán)就是一張面孔,但是皇帝長得什么樣子,老百姓并不知道,絕大多數(shù)官員也不知道,在中國人的想象中,皇帝“龍顏”應該是雍容大度,皇后“容貌”應該是端莊鳳儀,歷史記憶中的皇權(quán)人格化因而成為畫匠描摹的對象。本文以近年新出的大唐帝后禮佛供養(yǎng)線刻畫和斯坦因劫走的敦煌晚唐帝后禮佛紙墨畫稿,進行對比研究。
一 青齊間新出佛座石刻呈現(xiàn)的皇帝、皇后拜佛形象
在雕像藝術(shù)和寫實繪畫傳統(tǒng)盛行的大唐世界,皇權(quán)的符號不僅通過人格化而廣為認知,更經(jīng)由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而可視化,皇帝的形象作為一幅幅圖像流傳在政治領(lǐng)域、宗教領(lǐng)域和文化領(lǐng)域之中,不僅成為教化民間大眾的理想粉本,也是廣大百姓祈求福祉的護身符。
在敦煌石窟經(jīng)變畫中,莫高窟第220窟唐貞觀十六年(642)前后繪制的一幅帝王問疾圖,另一幅是第103窟盛唐時期描繪的帝王問疾圖,都是維摩詰經(jīng)變畫“方便品”中的代表作[1]。畫面重點描繪了帝王率領(lǐng)眾臣前往問候身體有疾病的維摩詰。皇帝廣額豐頤,隆鼻美髯,頭戴冕旒,身著袞服,在穿著白練襦袍群臣侍從的簇擁下昂首闊步前行,整個畫面均是為了襯托出帝王儀表堂堂的威儀(圖1、圖2)。至于這兩幅帝王形象圖畫究竟是以閻立本《歷代帝王圖》為底本還是依據(jù)吳道子“吳家樣”勾畫,目前還未有定論。但是,藝術(shù)工匠們所刻畫帝王的形象,無疑為表現(xiàn)君主、貴族和官員提供了標準模板,隨后帝王的面容和皇后的容貌交相出現(xiàn),為王朝或皇權(quán)統(tǒng)治者戴上了合法性的面紗。
翻閱中國畫史,可見所有對帝王的繪畫都注重容貌的正襟危坐,眼神慈祥,從不會暴露帝王的面貌缺陷,反而利用帝王瑞像收服民心,宣示天命。我們看到歷史上的古代皇帝畫像多是老頭的形象,長須的神采風度向世人展示,給人的感覺差不多。如果沒有相應的備注,根本無法分清到底是誰。畫師并不依靠真實的畫像來流傳后世,而都畫差不多一樣的形象來維護“圣貌”的樣子。
萬幸的是,陜西漢唐石刻博物館收藏的唐代皇帝、皇后形象石刻線畫,原是佛像經(jīng)幢底座構(gòu)件上的祈福求平安圖像(圖3A、圖3B),據(jù)說出自山東淄博一個原是佛寺遺址的建筑工地里,后輾轉(zhuǎn)數(shù)地被陜西收藏家展出。保存下來的石刻線畫皇帝、皇后禮佛圖,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對比的圖像。按照畫面布局分為左右對稱的空間{1}。
石刻線畫右邊鐫刻“大唐皇帝供養(yǎng)“幾個字,畫面上皇帝頭戴冕旒長冠,身穿袞袍,手持笏板,一副中年“圣貌”的樣子,特別是他跽跪在空壸造型的榻上,袍邊下垂拖長,顯示出帝王的氣勢。在身后,站著六個穿袍服的文武官員,其中兩個戴幞頭、手持葆羽扇的侍從站立。接下來就是身穿官服的各個供養(yǎng)人依次排列的形象,上刻幢主供養(yǎng)姓名(圖4)。
石刻線畫左邊鐫刻“大唐皇后供養(yǎng)”字樣,皇后頭戴華釵蓮冠,身披霞帔,手捧拈香桃形盒,后隨兩個束發(fā)髻穿半臂的侍女,分別手舉圓蓋陽傘為皇后遮陽。皇后跪坐在空懸壸形床榻上,六個宮女頭梳雙環(huán)髻、雙束髻、飛髻諸樣,簇擁在她的后面,有的執(zhí)撐翣傘,有的手舉葆羽扇,有的捧物盒,題款也刻有女性供養(yǎng)名字(圖5)。
線刻禮佛圖中人物密集重疊,顧盼照應,既渾然一體,又有豐富變化。正面三層蓮花造型的高聳香爐下,有兩個飾瓔珞打扮的天女,紗巾繞臂下垂,都是單腿胡跪于蓮花座上,一個手托供奉物,一個作出吉祥掌動作。特別注意的是,按照當時常用的以形體高低大小來區(qū)分人物等級的手法,在男女兩組禮佛人物形象前面分別有一個戴幞頭的男性小人物和束雙環(huán)髻的女性小人物,以顯著的大小之別及人物的位置相互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風度威儀間的微妙差別,突出作為帝后禮佛圖全景中心的皇帝、皇后的高貴與尊嚴,頭戴介幘掌傘侍從與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皇帝問疾圖掌傘人非常相似,當然也體現(xiàn)出各地藝術(shù)工匠白描粉本的相同手法。
整幅線刻畫采取橫向構(gòu)圖圍繞石座一圈(圖6),人形處理因此顯得頎長,并略帶向前的傾斜感,既保留了禮佛盛典中的帝王生活氣派,又帶有飄然如仙的宗教意味和凝然靜謐的心境。同時,宮女們含睇若笑、駐步前視的姿態(tài),與整個虔敬肅穆的氛圍形成了含蓄的對照,流露出藝術(shù)工匠溝通人世和天界的欲求。趙力光等先生推測這幅禮佛圖可能創(chuàng)作于唐中宗、韋皇后神龍年間(705—707){2}。
禮佛圖也稱供養(yǎng)人像,是我國古代石窟藝術(shù)中常見的一種題材。從新疆庫車克孜爾石窟、甘肅天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岡石窟到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的禮佛浮雕和佛龕都展現(xiàn)了佛教入華后的造型藝術(shù),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間無疑是最具規(guī)模和最為優(yōu)秀的。然而,藝術(shù)工匠們描摹的皇帝、皇后肖像中心的焦點,不僅有皇帝、皇后端莊嚴肅的容貌,而且還有他們拜佛虔誠的姿態(tài),全都通過圖像延伸出神圣的王權(quán),傳達信息一目了然。這些翔實描述佛教宗教題材的藝術(shù)作品,代表了中國線刻畫藝術(shù)的新高峰。
北魏“皇帝即如來”的佛教觀念曾經(jīng)風行中國北方[2],不僅百姓要崇拜帝王,佛寺沙門也應禮拜帝王,從而調(diào)和佛教出世精神與儒教君臣理念的矛盾,即使正史中描述的統(tǒng)治者的殘暴荒淫形象,可在佛教史描述中卻往往又是一位虔誠的禮佛者。帝王禮佛雖不匍匐于地,但跪坐于榻臺上,塑造自己佛教轉(zhuǎn)輪王的身份,從信仰和政治的雙重維度加強統(tǒng)治的神圣性[3]。皇帝帶頭禮佛,使僧侶百官禮拜如來佛就定義為皇帝,確立北朝胡族皇帝專制統(tǒng)治下的佛教,可與儒家“孝”道結(jié)合,從而成為推動全國各個階層造像活動的原動力。
但皇帝與皇后共同禮佛的圖像究竟出現(xiàn)于隋唐什么時期,還有待新資料的出現(xiàn)與確認,這無疑是漢傳佛教在中土綻放出的新的華麗花朵,男女并列同出一幅畫面,很可能是藝術(shù)上吸收了西魏帝釋天、帝釋天妃畫像,敦煌莫高窟第249窟窟頂有帝釋天乘龍車、帝釋天妃乘鳳輦在天空云游的壁畫,也是新出現(xiàn)的藝術(shù)造型。但唐代帝后禮佛同時出現(xiàn)在佛教經(jīng)幢底座石刻上,這是第一次看到,堪稱珍稀。
二 敦煌晚唐五代畫稿上皇帝、皇后拜佛的形象
在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出土的65件白描圖中,最引人注目的墨線勾畫“帝后禮佛圖”(圖7—圖9),是學界關(guān)注已久的粉本,它是斯坦因與伯希和分別從藏經(jīng)洞帶回英國和法國的一組畫稿,編號為S. painting 83、P.3998,原定名為《禮拜者圖》{1},后依據(jù)唐義凈譯《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被確定為《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變稿》。整體三幅紙本畫稿連在一起,先用橫線畫出天頭地額,中間有淡色的烏絲欄豎線,線條畫出屏風式結(jié)構(gòu),布局和諧,很有可能是畫工對寺窟主墻上關(guān)鍵人物形象的深入研習,應該是畫史上難得的一幅草稿線圖,或是起稿粉本。
在敦煌現(xiàn)存白描畫稿中,墨線勾畫最有特色,雖然有的畫稿內(nèi)容具有較大的任意性,但它不是繪畫練習的涂鴉之作,而是準備上墻階段“起稿”的畫稿,構(gòu)圖簡練,嫻熟的寥寥幾筆,畫作就躍然紙上。白畫作品作為當時壁畫創(chuàng)作的過程性粉本,可以管窺白畫與壁畫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沙武田教授專門細致研究過這三幅白描畫,他認為畫稿的圖本來源是在沒有任何參照情況下的大膽創(chuàng)新{2}[4]。現(xiàn)在隨著唐前期石刻線畫的出現(xiàn),看來它們也不是敦煌畫匠的獨創(chuàng),表明在中晚唐以前佛教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曾廣泛流行過“帝后禮佛圖”的模式。
S. painting 83(a)左面一幅畫面(圖7)將帝王形象榜題為“梵王”,畫出了皇帝頭戴長板冠冕,冠帶垂至前胸,其臉龐豐滿,一腿屈膝著地,一腿盤跪地上,雙手合十,寬衣大袍長袖拖地,一群大臣模樣的人在后面站立合十,錯列其間簇擁著最前面的皇帝形象人物,大臣們也都戴三梁冠、三戟冠等,他們雙膝跪地與皇帝單膝胡跪著地不一樣,但不是一般的侍從護衛(wèi)或主仆關(guān)系。畫匠粉本的帝王坐姿與跪坐、跽坐相比,頗有點違禮自由的色彩。
S. painting 83(a)右面一幅畫(圖7)榜題為“中心第四,爾時復有彩女等”,第一排為首的盛裝貴婦,體型端正,神情安詳,雖沒有畫出蛾眉櫻唇,按照左右對稱來看,應是與皇帝對應的皇后像。最左邊鳳冠頭飾高聳、插滿大釵笄的皇后,正帶領(lǐng)一群被題榜為“天女”的女性,雙手合十陪侍跪拜,她們分別梳著與眾不同的發(fā)型,頭戴蓮花冠、螺旋冠、雞頭冠等,禮佛神態(tài)十分虔誠,這正符合女性崇佛信仰的心態(tài)。
我們無法確定敦煌這三幅白描畫具體的年代,無法找出系列皇帝形象的圖譜來確定某位皇帝是誰,只知專家們推斷這是9—10世紀晚唐五代草畫樣稿{3},但是藏經(jīng)洞遺存的白畫,可能是零散的小樣粉本,為洞窟或寺院壁畫服務,工匠可能因為雇主定做太多,要求快速,為了加快成畫效率,粗略勾圈,在畫稿創(chuàng)作中并不那么追求精益求精,但它絕不是即興揮毫寫意,流暢的筆觸和對人物神態(tài)的瞬間表現(xiàn),反倒讓畫作更具表現(xiàn)力,迸發(fā)活力,有著獨特生動的藝術(shù)效果。這幾幅畫稿為我們提供了極佳的觀察角度,放大后可以描繪到洞窟墻壁上的壁畫,盡管畫稿不是壁畫布局的全部,一幅完整的壁畫要首尾相貫呈現(xiàn)皇帝、皇后的神圣禮拜的歷史。然而,唐代皇帝、皇后禮佛圖的出現(xiàn),揭示了皇權(quán)統(tǒng)治者的形象對宗教藝術(shù)表現(xiàn)的深刻影響,結(jié)合在敦煌壁畫中多次出現(xiàn)皇帝形象{1},可以看到皇帝的面孔不僅出現(xiàn)在佛教石刻畫中,它們還從敦煌存留的畫稿中凝視著后人。
與云岡石窟的浮雕相比,帝后禮佛圖已經(jīng)開始擺脫古印度的犍陀羅風格,加強了本土的藝術(shù)語言色彩。然而,敦煌畫稿草圖作品變得單薄平淺,畫稿圓潤光影不復存在,線條成了藝術(shù)形式表現(xiàn)上舉足輕重的角色。人與人的空間、人體的曲折起伏都用線勾勒,特別是衣紋的處理,格外舒展流暢、疏密有致,頗有漢代畫像以線求形的神韻,表現(xiàn)出中國民族文化與外來佛教藝術(shù)的很好融合。
此外,從禮佛圖中人物的衣冠發(fā)式和傘蓋、羽葆等儀仗制度看,佛教漢化的政策已經(jīng)滲透到藝術(shù)中,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因此,青齊出現(xiàn)的帝后禮佛線刻畫和敦煌帝后禮佛畫稿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所以,無論從藝術(shù)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還是從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去估量,這些都是當之無愧的優(yōu)秀珍寶。
從社會心理分析的角度來講,從眾跟風是一個社會常有的現(xiàn)象。眾多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無緣的信徒和民眾,從下層官吏到家眷奴仆,都對他們所看到的皇帝圖像感到印象深刻。所關(guān)注的不僅是帝王本身或再現(xiàn)他們的諸位陪侍,還有無數(shù)注視著這些供養(yǎng)佛陀的一般人。對大眾平民來說,代表皇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面孔長期存在于藝術(shù)中,他們帶來的權(quán)威視覺體驗,都會影響藝術(shù),充分表現(xiàn)了傳統(tǒng)文化中對權(quán)力的崇拜。
在封建專制社會里只要政治和權(quán)力現(xiàn)象是永恒的,那么以皇帝作為至高無上權(quán)力面孔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也將永不停息,而皇帝的形象發(fā)揮的作用,通過寺院石窟推廣到各地,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方權(quán)力關(guān)系提供了自我表達的語言與資源。
我們疑惑的是,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這幅“帝后禮佛圖”粉本草圖并沒有轉(zhuǎn)換成敦煌石窟里的大型壁畫,并沒有如同其他畫坊粉本一樣真正轉(zhuǎn)換生成新圖像。畫工對這些草圖沒有再次重繪組合到或配置到洞窟壁畫里。這需要我們重新認識粉本之外圖像生成的原因。
三 帝后禮佛圖的圖像表征與粉本意涵
皇帝的形象在中古時期出現(xiàn)應該是一個普遍現(xiàn)象,5世紀后半葉平城云岡曇曜五窟首開為帝王造像的先河,奠定了崇佛與崇拜皇帝融合的禮敬思想。唐朝更是一個推波助瀾的年代。有關(guān)唐朝皇帝的故事或是傳說一直蔓延到社會的不同階層想象之中,如唐太宗接見吐蕃使臣、武則天接見番臣、唐玄宗接見異邦貢使等皇帝出面的故事。這些流傳至今的故事并不一定具備真實性,但完全可以是人們用以描繪那個鼎盛時代圖景的素材。
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帝王畫像來源于唐朝閻立本所繪的《歷代帝王圖》,里面畫了13位帝王形象:前漢昭帝劉弗陵、漢光武帝劉秀、魏文帝曹丕、吳主孫權(quán)、蜀主劉備、晉武帝司馬炎、陳文帝陳蒨、陳廢帝陳伯宗、陳宣帝陳頊、陳后主陳叔寶、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加上侍人共46人。
畫師根據(jù)封建帝王的共同特性和氣質(zhì)儀容,繪畫出來的人物多有相似之處,多為中老年的形象,長胡須、眼神深邃、肩寬胸廣,有些慈祥的老頭形象,很少有青壯年模樣。古人蓄胡子較早,如果不刮胡子或留須就分不清具體的年齡,所以難免會千篇一律,而不是百人百態(tài)。故畫像相對之前的朝代辨識度并不見得高。
我們從歷史記憶的圖畫而非歷史事實的角度,探討唐朝最高統(tǒng)治者們形象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而不是皇帝的實際樣態(tài)面貌。無論是青齊間石刻線畫還是敦煌白描畫底稿,皇帝都身穿登冕冠服,頭戴桂冠端坐中央,冕鎏下垂,即使雙膝下跪,也擺出正經(jīng)虔誠的樣貌,宛如佛祖委托的代理人,彰顯著君主至上的地位。透過畫工創(chuàng)作的畫樣,可以看出皇家對全國寺院的影響與傳播,這為我們思考藝術(shù)與權(quán)力、宗教的關(guān)系,以及藝術(shù)工匠作為參與者的使命或旁觀者的責任,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他們不是為了敬獻給亡靈,而是為生者祈求保佑。
中古時期以來尤其是隋唐王朝非常注重外在形態(tài)的大力崇佛,不惜財力修建舍利塔、經(jīng)幢、石窟等,筆者曾研究過西安碑林收藏的盛唐開元廿九年(741)《燃燈石臺贊》{1}[5],其上刻著來自供奉藝人的祈福文字:“奉為開元圣文神武皇帝、皇太子、諸王、文武百僚、幽冥六道爰及兆庶同獲斯福”;石臺上線刻畫用樂舞胡人、繁茂花卉和神獸圖案組合描繪了舉辦燈會的場面,既為皇帝歌功頌德、施恩納福,又借佛教保佑庶民、祈求國泰,與唐五代敦煌逢年過節(jié)時的佛事燃燈供養(yǎng)活動一模一樣。事實上,流風所及,唐代各個寺院道場都“復制”壁畫、造像,粉本的流傳肯定要成為藝術(shù)工匠的必修課,線描更是作畫的主要手段,起著骨骼作用 [6],帝王體貌雄偉、隆鼻美髯的形象也被一再復制,將帝王塑造成普天下的佛祖,表現(xiàn)帝王尊崇佛教,以此給信眾洗腦和教化民眾。
毋庸諱言,帝后的禮佛圖像會不斷激起人們強烈的崇拜感情。帝后們爭相聲稱自己是佛祖的慈善代言人,所以皇權(quán)是合理合法的繼承權(quán)力,臣民的視線也被從那些實施苛政暴政的君主身上轉(zhuǎn)移,只能感受到“政治與家庭的夫妻同體”統(tǒng)治的合法性。帝后在菩薩盡善盡美的塑像面前時,似乎也具有了宗教的魔力。當觀者無論從哪個方向看到帝后禮佛畫作時,他們都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皇權(quán)的本質(zhì)和威力。
四 帝后禮佛圖的真實性與虛構(gòu)性
追溯畫樣的歷史線索,隋唐以前帝后的代表性石刻浮雕畫,位于北魏時期龍門石窟賓陽中洞東壁,原是兩組大型浮雕,分別為《皇帝禮佛圖》和《皇后禮佛圖》,描繪了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禮佛的盛大場面,20世紀30年代被盜后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shù)博物館。北魏皇帝和皇后的禮佛圖開始了中國佛教美術(shù)史上的新造型,再現(xiàn)了皇家禮拜佛祖的場景(圖10、圖11)。
我們觀察到一個手持蓮花花蕾的男子,頭戴通天冠,身著北魏流行的褒衣博帶,身后有身材矮小的侍從為他托著長長的衣擺,還有人為他舉著華蓋,身份似乎非常尊貴。男子身后是一位妙齡女子,頭戴雙角冠,同樣衣著華美。這兩個人物的前面是一位雍容華貴的中年婦人,她也頭戴通天冠,并有隨從舉著羽葆和華蓋。有學者認為這位婦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宣武靈太后胡氏,那些身份尊貴的青年男女,則是她的兒子和兒媳——孝明帝元詡和皇后胡氏。整個皇家貴族出動禮佛的盛大場面[7-8]。
值得對比思考的是,在雕像藝術(shù)和寫實繪畫傳統(tǒng)深厚的西方世界,古羅馬皇帝形象與權(quán)力的符號,不僅通過人格化而廣為認知,更經(jīng)由藝術(shù)創(chuàng)作出可視化的一幅幅圖像廣為流傳,亞歷山大大帝等羅馬皇帝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般貴族肖像畫。在希臘化和羅馬化過去約五百年的時間里,這些皇帝和他們的妻子、母親及子女,被無數(shù)次再現(xiàn)于繪畫、掛毯、青銅器、銀器、陶瓷、大理石等藝術(shù)品之中。在基督教定為國教后,除了耶穌、圣母瑪利亞和一部分圣徒,皇帝、皇后的形象要比任何其他人物形象都更加頻繁地出現(xiàn)在西方藝術(shù)中。作為位居權(quán)力圖像系統(tǒng)中心的羅馬皇帝,包括那些荒誕殘暴的獨裁者,都會以登上權(quán)力寶座而在西方世界歷史中赫赫有名,甚至引起共鳴,在千年后文藝復興創(chuàng)作中仍在被描繪{1}。
眾所周知,與中古中國同時期的拜占庭美術(shù)首先是宗教美術(shù)。拜占庭建筑是基督教教會的建筑,繪畫作品多取材于《圣經(jīng)》,其形式和人物表情處理都須遵循具有神學意義的傳統(tǒng)模式。但拜占庭作為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藝術(shù),它炫耀王朝的強大和帝王的威嚴,把帝王表現(xiàn)為基督在塵世的代理人。從圣索菲亞大教堂南廊馬賽克畫來看,拜占庭女皇佐伊(978—1050)與其丈夫君士坦丁九世向基督貢獻時,都是筆直站立的(圖12—圖14),這幾乎是絕大多數(shù)拜占庭帝王圖像的基本形象。描繪一位皇帝在基督登基前張開雙手跪拜的場景在帝國肖像畫中極為罕見。圣索菲亞大教堂的另一幅9世紀鑲嵌畫,畫中的利奧六世正在匍匐向基督致敬(圖15),這種致敬禮拜方式是順服崇敬還是屈辱跪拜一直有爭論,或許帝王像融合了東西方的藝術(shù),更注重傳達皇帝的正統(tǒng)觀念,在基督面前順服被視為正義和必要的,而不是可恥和軟弱的[9-10]。大理石鑲嵌畫、壁畫,以及其他藝術(shù)品中的女皇、皇帝和基督的官方圣像均以色彩華貴的圖像宣示了視覺神學的崇拜。
中國與拜占庭帝國位于歐亞大陸的遠端,彼此之間聯(lián)系并不直接,但是具有同樣的政治結(jié)構(gòu)和文化特征,文化的趨同在歌頌帝王、王后上卻是一致的,關(guān)鍵是他們都會塑造帝王的至高無上,采用繪畫這種藝術(shù)特殊方式來表達對皇權(quán)的敬畏。有趣的是,有人認為14世紀伊朗帝王坐姿傳承于薩珊波斯帝王盤腿端坐的圖式,也有一條腿盤起觸地、另一條腿立起的坐姿[11]。實際上因為波斯薩珊藝術(shù)中沒有類似中國的帝后禮拜圖像,拜占庭有過皇帝、皇后禮拜基督或圣母,但大多是站姿,僅有一例是皇帝獨自跪拜。至于薩珊波斯是否有國王、王后同時出現(xiàn)的禮拜圖像,有待于學術(shù)界進一步探討。
西方近代一些藝術(shù)家譏諷中國畫家描繪的帝王容貌均是腫脹的大臉,他們認為那種巨臉胖得驚人,與身材不成比例,從形象透視上看身體不穩(wěn),不僅需要旁邊的壯漢搭手扶持,而且是健康不佳的表現(xiàn)。畫家筆下的帝王頭顱與身材必須連為一體考量,這影響到帝王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涉及福相還是苦相的面相問題。
肖像畫屬于人物畫的一個分支,原屬于西方繪畫藝術(shù)的專業(yè)術(shù)語之一。中國古代稱其為“寫照”“寫真”或“傳神”,這類作品特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為描摹對象,以精致細膩的手法將人物面貌鋪陳于紙面。有時還會對像主的容貌稍加美化甚至虛構(gòu),以符合審美傳神需求。據(jù)《歷代名畫記》卷6記載,六朝時畫家就擅長《天女白圖》《東晉高僧白圖》《馬勢白畫》及“無名真貌”等白描畫[12],官本、私本均不少,唐玄宗時用于典禮的帝王御容尤為興盛。敦煌五代曹氏畫院就有肖像畫師,描繪出了大量瓜沙曹氏家族的肖像,一家一族,如敘家譜[13]。
中古時期以來帝后和皇族成員的肖像畫逐漸成為主流,但“一主二侍從”圖式也開始變化,其中帝王御容多身著朝服,以正面威嚴的形象為主,有時還會出現(xiàn)同一帝王在同一時期內(nèi)諸多不同版本的肖像畫。越到后來人物畫的面貌越變得更為豐富,藝術(shù)畫家常借助多種底稿粉本的畫境氛圍去塑造“像主”的形象(圖16)。
帝王畫像的繪制一般都會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篡改,使得君主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長,面如滿月,須不盈尺,保證相貌不能丑化,至于正面形象的圓臉俊像是否接近其真實面貌,則不予追究。有意思的是,古代宮廷畫家作此類畫像多不落款,眾多帝王像作品中,兼具寫實、寫意的較少,也很少署名。敦煌莫高窟中所描繪的唐代帝釋天帝王形象一般都是凈面垂須,隆鼻細眼,頭戴遠游冠,后有光環(huán),身著寬袖深衣,腰圍革帶,長拖下裳,露出云頭高舄,畫家專門畫出全身,排在扈從侍衛(wèi)行列之前,突出天神般的帝王式造型。
古人對帝王肖像畫有著較為苛刻的要求,多以線條細勁、設色妍麗、筆墨流動、揮灑自如而自持,并將人物形象、身份地位與自身性格等相結(jié)合,以達到一種特殊且獨有的“情與境”。南朝齊明帝時畫家袁倩“善圖畫,畫人面與真無別,乃令畫王形象,并圖王平生所寵姬”[12]462。畫家水平很高,不僅將君王畫得栩栩如生與真貌無別,而且還畫出君王寵愛的姬妾。宮廷御用的畫師們所推崇的是將帝王神態(tài)、英勇身姿等傳神地表現(xiàn)出來,既注重外表的刻畫,也將細節(jié)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出來,至于表示服從拱手恭謹?shù)某剂艂兓蚱渌糠郑瑒t留下空白交給了觀者心領(lǐng)神會去補充。
莫高窟第98窟著名的于闐國王供養(yǎng)像及于闐皇后、公主供養(yǎng)像,雖與中原王朝帝王畫像有所不同,但時代屬于五代宋初供養(yǎng)像,于闐國王李圣天頭戴冕旒,冠頂裝飾有北斗七星、走龍、寶珠等,穿著袞袍,腰圍蔽膝,衣冠威儀如同中國。皇后曹氏頭戴著超大蓮花鳳冠,金釵三層,兩鬢作抱臉髻,帔帛禮服垂身。帝后身后都有男女侍從。畫像人物都是站姿為主,沒有跪拜伏地動作,顯示出高大威猛挺拔的形象。
晚唐五代時敦煌當時審美觀念已經(jīng)逐漸發(fā)生變化,畫像所表現(xiàn)的每個人神態(tài)需求也不一樣。畫家在作畫的時候不再追求形似,而是注重形態(tài)和面部的變化,皇帝的胡須、面相、體態(tài)等均與以前不一樣了,帝后的女性形象也不相同于以前隋唐前期風格。不同時期的帝王、帝后畫像,突出了當時畫師的心理狀態(tài),表現(xiàn)的藝術(shù)形態(tài)不一樣而已。在筆者看來,與其去想象心中完美的畫像,不如“起稿”時就留下最真實的畫像,因為最真實的畫像才是最貼近生活的。
一千多年過去了,唐代長安城、洛陽城等國家大寺與私人小寺中的壁畫都無一幸存,但是敦煌壁畫以其卓然的水平和地域特色,成為研究中古時期500年間壁畫史最好的參考,而出土的石刻線畫恰好是繪畫的主要補充形式。遺忘在藏經(jīng)洞里那些保存完好的畫稿,不僅與莫高窟現(xiàn)存的大量壁畫有聯(lián)系,而且這些畫稿和壁畫一起有益于我們對唐代藝術(shù)的認知。德國海德堡大學胡素馨教授指出:唐代數(shù)以千計的寺廟中進行著壁畫創(chuàng)作,因此粉本的創(chuàng)作越來越多,畫家在室外用墨線勾勒大致輪廓的習慣應運而生。這種景象似乎帶動了對白畫和底稿的欣賞,甚至在唐代當時就很受歡迎[14-15]。
歷史上朝拜禮佛的人們,無論是否留下名字,他們都會以對國家安定與皇帝庇護為目標,將給佛、菩薩獻上自己的供奉,寄予了國泰民安和積攢功德的祈盼心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從官吏到民眾在宗教活動中的精神狀態(tài)和狂熱崇佛風尚。對比山東青齊間出土的帝后禮佛圖線畫和敦煌莫高窟的帝后禮佛圖白畫,它們均帶有崇佛象征性的意義,背后的歷史語境是出資雕刻畫像的供養(yǎng)贊助人,其普世性會給我們理解唐朝畫樣粉本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以及畫像源流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論文修訂時得到陳文彬博士提供資料的幫助,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1]敦煌研究院. 敦煌藝術(shù)大辭典: 經(jīng)變畫[M].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223.
[2]巖井共二. 中國北朝的“皇帝即如來”和佛教美術(shù)[J]. 顧紅,譯. 敦煌研究院信息資料中心. 信息與參考,2009,11:120-126.
[3]孫英剛. 布發(fā)掩泥的北齊皇帝:中古燃燈佛授記的政治意涵[J]. 歷史研究,2019(6):30-44.
[4]沙武田. SP.83、P.3998《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變稿》初探:敦煌壁畫粉本系列研究之一[J]. 敦煌研究,1998(4):19-28.
[5]葛承雍. 燃燈祈福胡伎樂:西安碑林藏盛唐佛教燃燈石臺贊的藝術(shù)新知[M]// 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藝術(shù)卷.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249.
[6]周晉. 寫照傳神:晉唐肖像畫研究[M]. 北京:中國美術(shù)學院出版社,2008:134-135.
[7]焦琳. 帝后禮佛圖研究[D]. 北京:中央美術(shù)學院,2015.
[8]陳開穎. 北魏帝后禮佛儀仗規(guī)制及場景復原推想:以鞏縣第1窟為中心的考察[J]. 敦煌研究,2014(5):1-9.
[9]Cormack,Robin. Interpreting the Mosaics of Saint Sophia at Istanbul[J]. Art History, 1981, 4:131-149.
[10]Oikonomides,Nicolas. The Mosaic Panel of Constantine IX and Zoe in Saint Sophia[J]. 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1978,36:219-232.
[11]潘桑柔. 古史的形象:拉施特《史集·中國史》帝王插圖來源考[M]//李軍. 跨文化美術(shù)史年鑒:古史的形象:第3集. 濟南:山東美術(shù)出版社,2022:126.
[12]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校箋:卷6[M]. 許逸民,校箋. 北京:中華書局,2021:462.
[13]胡同慶. 敦煌佛教石窟藝術(shù)圖像解析[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31.
[14]Sarah E. Fraser. Performing the Visual: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618-960.
[15] 胡素馨. 視覺展演: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qū)的繪畫與粉本[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