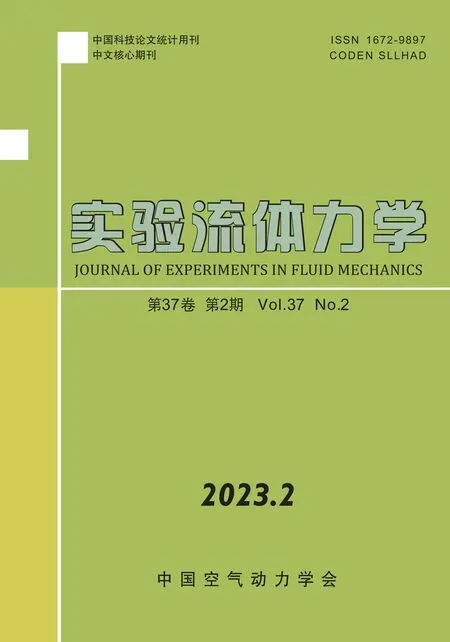迎角對翼型邊界層影響的實驗研究
郝東震,姜楠, 2, *,唐湛棋,馬興宇
1. 天津大學 機械工程學院,天津 300354 2. 天津市現代工程力學重點實驗室,天津 300354
0 引 言
近年來,隨著微型飛行器、無人機、風力機的發展,翼型在低雷諾數(即雷諾數在104~105量級,上限一般不超過5 × 105)下的氣動性能[1]日益受到關注。低雷諾數翼型在軍用、民用領域都有著廣泛的應用[2-3]。低雷諾數下翼型表面通常為層流狀態,抗逆壓梯度能力差,受到擾動后容易發生邊界層分離、轉捩、湍渦再附等現象,進而導致翼型升力系數急劇下降、阻力系數急劇增大的失速現象產生,嚴重影響翼型的氣動性能及飛行安全。
研究發現,在低雷諾數下,翼型表面往往會有非定常的分離泡存在。 Horton[4]最先提出了經典的層流分離泡模型,Alam 等[5]對分離泡進行了三維數值模擬,Liebeck 用實驗方法研究了低雷諾數下翼型的分離泡并進行了翼型設計。大量的風洞實驗[6-7]和數值模擬研究[8-9]發現,翼型層流分離流動存在顯著的非定常特征和非線性效應。周穎等[10]提出了一種負反饋機制,認為翼型尾緣的聲學信號為流動分離提供了原始能量,分離泡內的小尺度結構會引起邊界層分離后湍渦結構的破裂,進而形成向上游移動的小尺度渦結構。
Burgmann 與Brücker 等[11]通過粒子圖像測速(PIV)發現,分離泡內向下游發展的低速運動渦流作為一個整體結構圍繞轉捩點旋轉,導致了類似于噴射事件的渦流爆發現象,起到了局部流動的擾動作用。Burgmann 與Dannemann 等[12]采用立體掃描PIV 裝置研究了分離泡下游渦流的時空結構,證明了準周期渦結構的發展。Ol 等[13]通過PIV 實驗對比了3 種實驗設備(風洞、水洞和水槽)測量的SD7003 翼型的平均速度場、層流分離泡的形態、雷諾切應力和渦量分布。朱志斌等[14-15]采用大渦模擬方法研究了雷諾數對翼型邊界層的影響。
周穎等[16]通過數值模擬發現,在翼型前緣添加特定參數的粗糙凸塊可以減少或避免分離泡的產生,從而延緩邊界層分離,提高翼型在大迎角下的氣動性能。Kamari 等[17]研究了吹、吸控制對SD7003翼型性能的影響,發現吹、吸控制均能減小分離區域,提高翼型性能。朱玉杰等[18]研究發現反向控制能通過抽吸低能流體使邊界層變薄,增強翼型的抗逆壓梯度能力,提高翼型的氣動性能。
盡管上述研究工作已對翼型低雷諾數下層流分離現象及其氣動特性獲得了一定的認識,但都是基于數值模擬和實驗測量結果的時均特性,并未對流場進行精細化測量,流場中特征結構及其時頻特性隨迎角的演化規律還不明確。本文以SD7003 翼型為研究對象,采用PIV 實驗手段對其繞流流場進行高精度測量,分析迎角對流場特征結構及其時頻特性的影響規律。
1 實驗介紹
實驗在天津大學低湍流度回流風洞(圖1)中進行,實驗段長2300 mm,有效截面為1000 mm(寬)×1000 mm(高)的矩形。風洞實驗段的風速在2~60 m/s 范圍內連續可調,背景湍流度小于0.2%。實驗模型為SD7003 翼型,其弦長L 為150 mm,展向長度為1000 mm。翼型沿展向豎直固定在風洞實驗段底部的轉盤上,可通過風洞控制臺改變翼型迎角。實驗自由來流速度為5 m/s,溫度為20 ℃,空氣密度為1.205 kg/m3,運動黏度為1.513 × 10–5m2/s,來流雷諾數均為49570。翼型迎角取值為4°、6°、8°。如圖2所示,實驗測量區域為翼型的0.2~1.0 倍弦長,為保證高速相機的分辨率足夠高,將實驗測量區域劃分為視場1(FOV1)和視場2(FOV2)兩個部分分別進行測量,視場1 對應翼型的0.2~0.6 倍弦長區域,視場2 對應翼型的0.6~1.0 倍弦長區域。

圖1 天津大學低湍流度回流風洞Fig. 1 Low turbulence backflow wind tunnel of Tianjin University

圖2 標定靶Fig. 2 Calibration target
實驗采用的示蹤粒子為橄欖油,通過加壓型粒子發生器產生直徑為5 μm 的均勻粒子,在空氣中該粒子能較長時間處于均勻穩定狀態。DANTEC SpeedSense 高速相機分辨率為1280 像素×800 像素,采樣頻率為700 Hz。激光為NewWave Pegasus 雙脈沖激光器。采用雙幀模式采集圖像,相鄰兩幀的脈沖時間間隔為20 μs。
每個視場拍攝4107 對圖像,拍攝時長為5.897 s,圖像視野實際尺寸為64 mm × 40 mm。采用自適應互相關算法計算速度場,查詢窗口大小為24 像素×12 像素,窗口重疊率為50%。每個視場共得到4107個瞬時速度場,每個瞬時速度場包括105 × 132 個速度矢量,流向和法向相鄰矢量間的實際距離分別為0.604、0.301 mm。
2 實驗結果分析
本征正交分解最早由Lumley 等[19-20]提出并用于提取流場中的大尺度渦結構,后經Sirovich[21]改進并發展為Snapshot–POD(快照POD)方法,被廣泛用于復雜流場的降階及結構提取。
用N 個時間節點的速度場信息構建矩陣U:
計算速度場協方差矩陣的特征值矩陣λ和特征向量矩陣A為:
用所得特征值與對應的特征向量構建POD 模態,其中第i 階模態?i為:
式中:ψ為模態矩陣。
圖3 給出了Re =49570,α= 4°、6°、8°等3 個工況下分離泡附近的流線及流向平均速度云圖,橫軸(x 軸)、縱軸(y 軸)均為視場的實際長度。本文中正速度與流向相同,負速度與來流方向相反。可以看到,3 個工況都出現了典型的層流分離泡(值得注意的是,分離泡是一系列分離渦的時均結果,并非穩定存在于所有瞬時場中)。3 個工況下分離泡末端都有密集的流向速度分層,說明該位置有較大的流向速度梯度,且該速度梯度隨迎角增大而增大。

圖3 流線與流向平均速度Fig. 3 Streamline and horizontal average speed
表1 給出了不同迎角下,分離泡最大厚度(δmax)、雷諾切應力最大值(τmax)、最大雷諾切應力位置(xτ,max)及再附點位置(xr)對比。對比圖3 與表1 可以發現,隨著迎角的增大,再附點位置由0.7257L向翼型前緣移動到0.4017L;分離泡的最大厚度也由2.9579 mm 增大到3.7173 mm;分離泡的形狀由扁長型變為厚短型。分離泡位置前移及其厚度增大導致邊界層抬升,進而使邊界層厚度增大。迎角由4°增大到6°時,高速區域(> 6 m/s,低壓區)擴大;當迎角繼續增大到8°時,分離泡位置前移限制了低壓區向后延長,低壓區減小,這也是分離泡會降低翼型氣動性能的原因。

表1 不同迎角下分離泡最大厚度、雷諾切應力最大值、最大雷諾切應力位置及再附點位置對比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maximum thickness of bubbles, the maximum and locations of Reynolds shear stress, and reattachment points against angles of attack
圖4 給出了3 個工況(α= 4°、6°、8°)下雷諾切應力τ分布云圖,橫軸、縱軸以翼型弦長L 進行了無量綱化。可以看到,隨著迎角增大,雷諾切應力分布區域逐漸向翼型前緣移動,且其法向厚度也有所增大。雷諾切應力分布區域的起始位置在分離泡內,在再附點附近雷諾切應力達到最大值。對比圖4 和表1 中各工況下的最大雷諾切應力(絕對值)及其位置可發現:迎角由4°增大到8°,最大雷諾切應力由0.5595 N/m2增大到0.8461 N/m2,這表明邊界層中流體的剪切運動也隨迎角增大而增強;最大雷諾切應力的位置都在再附點附近。對比圖3 和4 可發現:分離泡末端區域(即再附點附近)的流向速度梯度和雷諾切應力都比較大,這說明再附點附近可能存在較強的脈動及能量交換,再結合Burgmann 等[11]發現的分離泡末端的低速渦流作為一個整體結構圍繞轉捩點旋轉的類似于噴射事件的渦流爆發現象,可推斷出再附點處于轉捩區域。
圖5 給出了3 個工況(α= 4°、6°、8°)下POD 分解的各階模態對湍動能的累積貢獻率。α= 4°工況下,視場1 中為層流狀態,因此只對包含主要流動結構的視場2 進行了POD 分析。α= 4°工況下,POD分解的前4 階模態對湍動能的貢獻率達到32.03%;α= 6°工況下,視場1 的前4 階模態能量占比為49.87%,視場2 的前4 階模態能量占比為24.15%;α= 8°工況下,視場1 前4 階模態能量占比為29.44%,視場2 的前4 階模態能量占比為28.03%。各工況的前4 階模態能量都較高,且隨著模態數量的增加,各階模態的特征值迅速衰減。當模態數量超過20 后,各階模態所攜帶的能量都比較低,說明高階模態中表征的是流場中的小尺度、低能量的流動結構,流場中大尺度、高能量的主要流動結構都集中在前幾階模態中。

圖5 POD 模態累積貢獻率Fig. 5 Cumulative mode energy of POD modes
圖6 為3 個工況(α= 4°、6°、8°)下前4 階(mode 1~4)模態含脈動速度矢量的流向脈動速度u′云圖。圖7 給出了3 個工況(α= 4°、6°、8°)下POD 分解的前4 階模態的時間系數功率譜,橫軸為頻率f,縱軸為能量密度(即功率)。


圖6 α = 4°、6°、8°工況下POD 分解前4 階模態Fig. 6 First four POD modes at α = 4°、6°、8°

圖7 前4 階POD 模態功率譜Fig. 7 Power spectrum of the first four POD modes
在α= 4°工況下(圖6),mode 1、2 中的流場結構基本相同,僅在流向上有空間位移;mode 3 中壁面附近有明顯的正速度波動區域,說明流場中有強烈的流向振蕩;mode 4 中出現正、負兩個方向的流向波動結構。在翼型同一流向位置上的紅色和藍色區域為一個渦結構,前2 階模態中均含有多個交替出現的正、反向渦結構,且隨著渦結構向下游發展,其尺度也逐漸變大。mode 3、4 中流向波動結構附近的速度矢量分布與 mode 1、2 中渦結構附近的速度矢量分布相似,由于邊界層限制,渦結構尺度始終小于邊界層厚度,因此可以認為mode 3、4 中的流向波動結構是尺度大于邊界層厚度但未產生的一部分渦結構。從前4 階模態包含的流動結構可以發現,流場結構主要是渦結構和流向波動結構的疊加。由圖7(a)可以看出,mode 1、2 的頻譜曲線幾乎重疊,在183.53、201.95 Hz 出現2 個明顯峰值;mode 3、4 中各種頻率的能量密度值都遠小于mode 1、2,其能量主要分布在低頻部分(<100 Hz)。mode 3、4 中流動結構的尺度比mode 1、2 大,但mode 3、4 的能量卻低于mode 1、2,這說明該工況(α= 4°)下mode 1、2 中的較小尺度結構比mode 3、4 中的較大尺度結構攜帶了更多的能量。由此可見,POD 模態能量大小不僅與其包含的結構尺度有關,也與模態頻率有關。
由圖6 和圖7(b)、(c)可以看到,在α= 6°工況下的視場1 中,前2 階模態與α= 4°工況相似,也包含多個交替出現的正、反向渦結構,也僅在流向空間位置上有區別;mode 1、2 的頻譜曲線也幾乎重疊,在201.95 Hz 出現明顯峰值;mode 3、4 中的流場為渦結構與流向波動結構的疊加,其所包含的大尺度波動結構出現在0.5L 處,能量分布主要集中在60 Hz以下的低頻區域。在α= 6°工況下的視場2 中,mode 1、2、4 包含的流動結構相似,都含有多個流向波動結構;mode 3 中含有一個更大尺度的正速度波動區域;mode 2、4 中左側的流向波動結構和與其方向相反(在上方)的小流向波動結構組成了一個渦旋,這也證實了前文對流向波動結構產生原因的推測。對比α= 6°工況下視場1 與視場2 中的流動結構和能量分布可以發現,視場2 中的流動結構尺度明顯大于視場1,視場1 中流場能量的頻域分布集中在200 Hz 附近,而視場2 中集中在100 Hz 以下。由此可見,隨著邊界層向下游發展,流場中渦結構尺度變大,流場中能量的頻域分布由高頻向低頻移動。
由圖6 和圖7(d)、(e) 可知,在α= 8°工況下,視場1 中流場與α= 4°、6°工況下再附點后的流場有明顯不同:能量最大的mode 1 中包含頻率較低的大尺度流向波動結構,mode 2、3、4 均為渦結構與流向波動結構的疊加,mode 4 中依然可看到交替出現的正、反向渦結構。mode 4 中峰值頻率為202.63 Hz,與α= 4°工況下mode 1 中的峰值頻率基本一致,說明該渦結構產生的頻率受翼型迎角變化影響不大。在視場2 的 mode 1、2 中均含有一個大尺度流向波動結構;mode 3、4 中含有由正負交替的渦結構衍生出的多個正負交替的流向波動結構。視場2 中前4 階模態能量的大小與各階模態所包含結構的尺度成正比。對比α= 8°工況下視場1 和2 的功率譜可以發現,與視場1 相比,視場2 中流場能量頻域分布整體向低頻區域移動,其分布范圍由0~260 Hz 壓縮到0~140 Hz。
綜上所述,本征正交分解實質上是對流場中流動結構的能量大小進行排序,各階模態的能量與其所包含的流動結構尺度、特征頻率密切相關。各工況在層流分離泡下游、再附點之前發生轉捩,轉捩后的流場中交替形成正、反兩個方向的渦結構。隨著湍流邊界層向下游逐漸發展變厚,流場中所包含的渦結構也逐漸發展變大,但是隨著渦結構與周圍的流體不斷發生剪切、卷積和能量交換,其自身能量不斷耗散,渦結構逐漸破碎分解成大尺度的流向振蕩結構和低能量的小尺度結構。
在α= 4°、6°工況下的視場1 流場中,流場的能量主要來自頻率為180~210 Hz 范圍內的較小尺度渦結構。在α= 8°工況下的視場1 流場中,由于轉捩點靠近翼型前緣,導致邊界層發展距離變長,湍流邊界層變厚,大尺度結構攜帶的能量明顯增強,進而使大尺度的流向波動結構與較小尺度的渦結構對流場的能量貢獻相差不多。與α= 4°相比,在α= 6°、8°工況下的視場2 流場中,流動結構尺度明顯增大,低頻大尺度波動結構比較小尺度的渦結構攜帶的能量更多;流場能量的頻域分布由0~240 Hz 壓縮至0~160 Hz 范圍。由上述分析可知,隨著翼型迎角增大,流場中的流動結構尺度增大,流場的能量頻域分布逐漸向低頻區域移動。
3 結 論
通過TR–PIV 實驗分兩段精細測量了翼型吸力面的瞬時流場,對比了3 個工況下的分離泡及雷諾切應力分布,并基于POD 方法分析了轉捩后流場的流動特性,結論如下:
1)隨著翼型迎角的增大,分離泡位置向翼型前緣移動,分離泡的厚度也有所增大。
2)流體在分離泡下游和再附點附近存在較強的剪切運動。隨著迎角增大,翼型吸力面上雷諾切應力分布區域前移,雷諾切應力的最大值及其法向分布范圍均有所增大,說明流場中流體的剪切作用隨迎角增大而增強。
3)POD 分析結果表明,翼型吸力面流場中的流動結構主要是由渦旋和流向振蕩疊加而成;流體在層流分離泡下游轉捩后形成交替出現的正、反方向渦結構,這些渦結構隨著邊界層厚度增大而發展變大;POD 分解的各階模態能量不僅與其所包含結構的尺度有關,還與各階模態的頻率有關。
4)隨著翼型迎角的增大,翼型吸力面流場中流動結構的尺度增大,流場中能量的頻域分布由高頻向低頻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