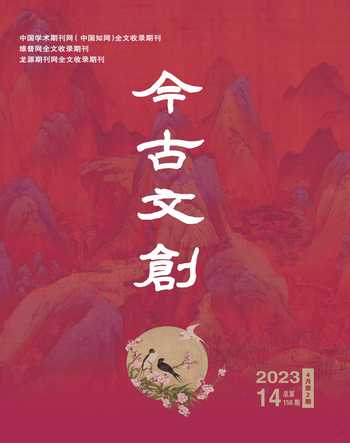淺析“知人論世”在文藝作品鑒賞中應(yīng)用
韋青玥
【摘要】 “知人論世”是由孟子提出的鑒賞文學(xué)作品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文藝作品鑒賞中,對“人”“世”的了解能幫助人們體味作品所承載的情感,把握作品傳達出的內(nèi)蘊以及構(gòu)建一個全面的、立體的作者形象。但“知人論世”亦有其局限性,不恰當(dāng)?shù)亍⑵娴剡\用會使評鑒步入誤區(qū)。
【關(guān)鍵詞】 知人論世;文學(xué)批評;文學(xué)作品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biāo)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4-003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4.009
一、“知人論世”的內(nèi)涵
作為中國古代文學(xué)理論中的一種重要的文學(xué)批評的原則和方法,“知人論世”最初由孟子提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雖然原意在于闡發(fā)一種尚友之道,但這其中也暗示了一種適用于閱讀和解讀詩歌的方法。因為談?wù)摰健爸淙恕薄罢撈涫馈迸c讀書、論詩的關(guān)系,后世的文藝批評者把它當(dāng)作一種解讀詩文的方式,并在逐漸發(fā)展中成了詩文批評的原則和方法。而后來的這一種含義,其輻射程度甚至超越了原意,“知人論世”也滲透進了中國的文學(xué)批評傳統(tǒng),并成為以后形成的諸多批評方式中的源頭。
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作者自身的思想、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所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guān),因此,要真正識其人、論其世,也就是要認識其人生理念、創(chuàng)作所處的年代,從而客觀、正確地理解和掌握其精神內(nèi)涵。“知人”指的是通過對作者的生活經(jīng)驗和觀念的認識,從而掌握作者的寫作風(fēng)格、精神品質(zhì)和審美情操,從而使作者能夠從作者的角度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從而更好地領(lǐng)會作者的寫作目的和思想內(nèi)涵。而“論其世”,即探討其所生活的年代,以全面認識其創(chuàng)作的內(nèi)涵和思想感情。
自漢代以后,“知人論世”的解讀方法一直延續(xù)到了魏晉之際,及至南北朝時期,“知人論世”說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專門列有《體性》一章,探討了“性”與“形”,也就是體貌與性情之間的聯(lián)系。他由“賈生秀發(fā),文潔體清;長卿狂妄,所以言盡于言。”等作者的具體情況,揭示詩人的個性特征、詩文風(fēng)格以及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此外,他還試圖從理論上進行總結(jié),將這上升為一種普遍性規(guī)律。
魯迅的“論詩三顧及”觀點是基于“知人論世”的認識同時結(jié)合實踐中的體驗提出的,“我總以為倘若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這一看法是對“知人論世”說的一個較為嚴(yán)密的詮釋,從中亦能看出,孟子的“知人論世”思想對后人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這種原則使人們在鑒賞古人詩詞時,能夠依憑文本而又超越文本,通過文字來認識一個全面的、立體的作家,并從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出發(fā)更加全面的理解作品反映的內(nèi)容,使人們在把握作品的內(nèi)蘊時更加深刻透徹。
二、“知人論世”在文學(xué)鑒賞中的作用
(一)對作家所處的時代生活的理解,可以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內(nèi)涵。文學(xué)作品作為時代、社會發(fā)展的產(chǎn)物,通常能夠不同程度地反映時代與社會,因此,要真正領(lǐng)悟其意義,就不能不了解作家所處的時代。一個時代的社會和經(jīng)濟狀況決定了塑造了一個時代的人,而當(dāng)時的文學(xué)作品當(dāng)然也是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這些作品中的角色和思維,即便是虛構(gòu)的,也是這個時間長河中最真實的結(jié)果。
如菲茨杰拉德于20世紀(jì)20年代寫就的《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是美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喧囂年代”,即一戰(zhàn)結(jié)束后的1919年到美國經(jīng)濟崩潰前的1929年之間這十年。在他的作品中,菲茨杰拉德詳細地描繪了爵士時代美國社會的生活狀態(tài):“那是一個神奇的年代,一個藝術(shù)的年代,一個奢侈的年代,一個充滿了嘲弄的年代。”那是美國最繁華最輝煌的時代,繁榮的氣息飄散在空氣中,奢侈的消費和享樂主義的炫耀廣為盛行。而菲茨杰拉德本人身處當(dāng)時的上層社會,作為一個作家,他所處所見的燈紅酒綠夜夜笙歌、歡歌與縱飲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都不乏表現(xiàn)。只有在了解那個年代的情況下,大家才能理解作品中“美國夢”的破碎,當(dāng)金錢是萬物的象征,美國夢中最初的美好元素早已蕩然無存。
亦如中國古代的“李杜”兩位詩人,一位身處盛唐,一位經(jīng)歷“國破山河在”。他們的作品風(fēng)格與內(nèi)容之迥異,在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不同社會環(huán)境對于文學(xué)作品的影響。“歌謠文理,與世推移。”盛唐文化的繁盛和社會的興旺,使得盛唐文人的人生態(tài)度大都是積極、活躍、自信的,李白本人的山川詩詞中也充滿了為人的自豪,他的詩歌也以豪放俊逸的浪漫主義表達方式體現(xiàn)了他的人格追求。《清平調(diào)》中的“解釋春風(fēng)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將進酒》中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fù)來。”、《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的“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等詩句,都鮮明地展現(xiàn)了其詩豪邁奔放又浪漫飄逸的特點。
與李白相比較,可以說杜甫是苦難的詩人。當(dāng)時唐朝政局日趨腐朽,杜甫雖有“致君、堯上、先讓民風(fēng)純”的政治理念,然而他的仕道卻并不順利,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處處藏著悲苦”的生活。杜甫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見證大唐的由盛轉(zhuǎn)衰,亦親眼看見民間百姓流亡的慘狀,作品中充滿了沉郁與凝重。“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窮年憂黎元, 嘆息腸內(nèi)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些詩歌不僅真實地再現(xiàn)了當(dāng)時人民的苦難,也表現(xiàn)出了那個時代的苦難和痛楚。杜甫本人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思和愴然淚下的悲切之感,在那個時代下振聾發(fā)聵。時代造就的人總是屬于那個時代,也正是唐代的繁榮與衰落,造就了李白與杜甫。從宏觀上對時代的把握入手,才能對文學(xué)作品的深層含義有更深刻的認識。
(二)了解作者的家庭背景、生活經(jīng)歷與人生軌跡,有助于理解作者和理解作品的情感。不同的家世會塑造出人不同的性情, 而不同的人生經(jīng)歷則會使人原有的精神繼續(xù)發(fā)展。因此,在對文學(xué)作品進行鑒賞的過程中,一個作家的身世和他的人生軌跡通常是不可忽略的。
例如,《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出生于包衣世家。其祖父曹寅擔(dān)任江寧織造期間,曹家進入鼎盛階段,論財力在江南地區(qū)無人能及,日用排場亦極盡奢華。同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喜好文學(xué),喜愛收藏書典,對詩詞、戲曲、書法都頗有研究,其深厚的文化教養(yǎng)和廣泛的文化活動,營造了家族中濃厚的文化與藝術(shù)氣氛。
曹雪芹《紅樓夢》的創(chuàng)作,與曹家包衣世家、旗籍包衣漢人的特殊社會身份、博大精深的漢文化修養(yǎng)和家庭文化、藝術(shù)氣氛的熏染密不可分。曹家因虧空沒落前,曹雪芹早年曾親歷了一段“錦衣紈绔,飫甘饜肥”的生活。也正是由于曹曾親身經(jīng)歷過這種生活,《紅樓夢》才得以向讀者呈現(xiàn)“鐘鳴鼎食”之家、“詩書簪纓”之族的百象。如其中名目繁多的飲食種類,有學(xué)者對《紅樓夢》中的食品數(shù)目進行統(tǒng)計,多達兩百余種。其中第四十一回寫到的菜肴“茄鲞”,需要用精致昂貴的材料配合,經(jīng)過繁復(fù)瑣碎工序才能制成,劉姥姥吃過之后說:“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樣的味兒來了。”“我的佛祖,到得十幾只雞兒來配他,怪道好吃。”也說明這道菜極其奢華講究,非尋常人家能見過吃過。雍正六年,曹家因虧空獲罪被抄家,自此一蹶不振、日漸衰微。大量紅學(xué)研究的觀點也認為,《紅樓夢》所體現(xiàn)的廣泛而深刻的悲劇精神與作品的悲劇性,來源于曹雪芹本人生命歷程中的親身經(jīng)歷。作家自身的悲劇經(jīng)歷常常是其作品中悲劇的根源,當(dāng)他的人生經(jīng)歷豐富、曲折、不如意的時候,他常常會產(chǎn)生一種悲觀的情緒,而作者的抑郁與壓抑也總是文學(xué)作品中悲劇風(fēng)格形成的原因。
不同時期、不同環(huán)境下,同一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也會因其境遇和情感的不同而呈現(xiàn)出不同的意境。如宋代婉約派詞人李清照,她出身于文人世家,同樣從小就過著錦衣玉食的日子,她的詞作以南渡為界,鮮明地分為早期與晚期兩個完全不同的階段。其早期的作品,文風(fēng)清麗細膩,后期則是憂郁滄桑,沉郁凄涼,感情基調(diào)大都轉(zhuǎn)變,內(nèi)容上也有了明顯的區(qū)別。李清照早年生活于汴京,生活環(huán)境幽雅,而京都的繁榮,更是激起了她的創(chuàng)作激情。但“靖康之變”后,北宋朝廷崩潰,李清照亦流徙至浙東一帶,開始了流亡生活。其作品風(fēng)格的重大轉(zhuǎn)變,與時代變遷、人生變故的軌跡大致是一致的,早年生活安定、優(yōu)裕時,詞作多寫相思之情;晚年漂泊、顛沛流離,詞句多作感嘆身世飄零。
準(zhǔn)確地把握作家的情感脈絡(luò),是理解、鑒賞作品的關(guān)鍵。要深入了解作家的人生歷程,構(gòu)建一個全方位的、立體的作者的形象,以“知人論世”的方式細致地揣摩作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境遇與狀態(tài),依憑文本而又超越文本,更加準(zhǔn)確地體會到作品的意義和感情。
(三)幫助理解人物的思想行為、情節(jié)設(shè)置與作品總體的價值取向。在不同的時代,人們的價值取向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在對文學(xué)作品進行賞析的過程中,如果僅僅以現(xiàn)代視角去凝視,作品中的部分內(nèi)容會使人費解、疑惑,而許多作品所推崇的價值觀在今天看來實際上也弊病頗多。脫離作品所屬的“人”與“世”,可能會導(dǎo)致對作品的評價不恰當(dāng),無法觸及作品在當(dāng)時真正的意義與價值。
19世紀(jì)五十年代的美國現(xiàn)實主義作品《湯姆叔叔的小屋》,以南北戰(zhàn)爭為背景,用尖銳的主題和引人入勝的表達方式,借主人公湯姆的經(jīng)歷,呈現(xiàn)了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奴隸制社會。這本書一直被視為“重要的反奴隸制工具”,是美國反蓄奴制運動里最偉大的宣言,但近半個世紀(jì),作品中湯姆的堅忍、對主人的忠心以及對基督教虔誠的信仰都開始為人們所質(zhì)疑。
有觀點認為,盡管該書是對南部奴隸制度的真實刻畫,也是對其陰暗與反動的深刻揭示,但書中黑人奴隸的刻畫,以湯姆為典型代表,大部分是自愿服從主人、沒有反抗性的。湯姆沒有意識到痛苦的根本原因,也沒有反抗的意志。隨著奴隸制度的完全廢止和社會的發(fā)展,小說里的故事與現(xiàn)實生活的距離越來越遠,所以時至今日,對該書重視程度已遠不及19世紀(jì)中期。但除了不可能要求主人公湯姆有超出時代的遠見,具有反抗性外還能認識到苦難的根源、自主地擺脫在白人的殘酷“馴化”下成長起來的“奴性”,也應(yīng)認識到,作家本人斯托夫人也是處于時代之中的。無論是作品中主人公湯姆的人物塑造的缺憾或是大量的宗教內(nèi)容,以及其中暗含的“他救”思想——黑人依靠白人的幫助來實現(xiàn)本民族的解放與進步,這些都表明了作家自身的缺陷。當(dāng)以現(xiàn)代視角去回望這部作品,它所蘊含的價值觀念,很有可能會被一些人所唾棄。但如果客觀評價作品的價值,其在發(fā)表當(dāng)時對社會歷史產(chǎn)生的重大意義與影響也應(yīng)當(dāng)適當(dāng)?shù)丶{入考慮的范疇內(nèi)。但若是對一部著作進行客觀的價值評估,它在出版當(dāng)時對社會歷史產(chǎn)生的重大意義與影響,也應(yīng)該被恰當(dāng)?shù)亓腥氡豢剂康姆懂犉渲小!稖肥迨宓男∥荨吩谀莻€時代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曾被評價為“在歷史上只有少數(shù)其他的小說能夠企及”。盡管對于作品內(nèi)容上、思想上文學(xué)價值的評價應(yīng)當(dāng)與時俱進,但“知人論世”某種程度上有助于大家了解它的歷史意義。
三、局限
雖然“知人論世”在現(xiàn)代文學(xué)理論中仍有支撐其合理性的基礎(chǔ), 也尚可在現(xiàn)代批評中找到與這一原則密切相關(guān)的理論,但“知人論世”說理論上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且無可規(guī)避的。
首先, 文學(xué)作品作為一個審美自足體, 是充斥著想象與虛構(gòu)的,其邏輯與現(xiàn)實生活的理性大相徑庭。因此,“知人論世”在文學(xué)批評中的可靠性如何,是大家在實踐中必須要考慮的問題。與作者本人的生活相比,文學(xué)作品始終存在著相對的獨立性、片面性、片斷性,在文本和評論中,若不能恰當(dāng)?shù)剡\用“知人論世”,就有可能有所偏廢。忽略文本本身的審美特質(zhì)和藝術(shù)特點,而文本與審美作為文學(xué)中最基本的兩個要素,這樣的忽略會造成批評中審美感悟和對作品理解的匱乏。
問題核心在于是從文本出發(fā)以“人”“世”作為延伸, 還是從作家個人和時代背景出發(fā)到文本。依照雷納·韋勒克的文學(xué)批判理論,“知人論世”實際上是一種作品的外在研究,它能拓寬內(nèi)部研究的視野,提供借鑒,提供參考, 但它不能、也不應(yīng)該凌駕于內(nèi)部研究之上。就如知人論世應(yīng)當(dāng)先知還是后知的命題一樣,知人論世未學(xué)先知還是應(yīng)時后補之所以區(qū)別的根本問題也在于文本與“人”“世”的先后次序,這種次序的排序區(qū)別也代表著對兩者不同的持重。
盡管“知人論世”說在中國文學(xué)批評實踐中曾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但隨著新的文學(xué)理論和文學(xué)觀的不斷興起,這一文藝觀點也被不斷地沖擊著。特別是在20世紀(jì),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zhì)疑和挑戰(zhàn)。例如羅蘭·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這一觀點。作品出版后,作者不再是一個深層的個體,而是無生平、無歷史背景的一個人,一個在某個界定范圍將作品所有構(gòu)造匯集在一起的人,這一概念區(qū)別于古典主義范疇上的作者。相比古典主義批評從不關(guān)心讀者,只承認作者全然的統(tǒng)治地位,巴特批駁性地指出:“讀者的誕生應(yīng)該以作者之死為代價。”這一觀點反對在作品發(fā)表后作者占據(jù)著被認可、被歌頌或者被崇拜的位置,消解了以往幾千年作者一直占據(jù)的主體位置,顛覆了作者與讀者的關(guān)系,把后者從邊緣提升到中心。它賦予了讀者極大的閱讀權(quán)威,同時也是現(xiàn)代主義批評、結(jié)構(gòu)主義的重大結(jié)果之一。他們不相信作家具有外來功能,他們認為,作品文本的交互才是推動文章運轉(zhuǎn)的驅(qū)動力。
雖然“知人論世”頗受現(xiàn)代文學(xué)理論和批評觀的擯斥,也被人從多種局限質(zhì)疑與詬病,但文學(xué)批評只取一端大都是不好的,每種重要的批評觀都有其片面重要性。“知人論世”說在文學(xué)批評中的有限性也不必掩飾,任何鑒賞方法都應(yīng)視作品、適情況而采。
四、結(jié)語
綜述可見,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往往與其自身的境遇和所處的時代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因此,要避免孤立、主觀地去附會作家創(chuàng)作意圖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就需要考察作者的思想和經(jīng)歷,了解時代的特點并探究其對作品的影響,做到“知其人”“論其世”。
“知人論世”在相當(dāng)長的時期里,都被視作文學(xué)鑒賞的前提,現(xiàn)在它的地位雖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但仍發(fā)揮著極大的影響力,以“知人論世”為依據(jù)進行鑒賞是有相當(dāng)意義的。但本文也已對這一方法存在的局限進行了探討,所以,在進行作品鑒賞時,應(yīng)當(dāng)把“知人論世”與其他的鑒賞方法、批評觀進行結(jié)合。形成互補,對各種觀點加以綜合運用,實現(xiàn)感性與理性的結(jié)合,作者與讀者的兩者角色的不缺席,這樣才能夠更好地、從多個層面觸及其本質(zhì)與精髓,充分且深刻地品味作品之美。
參考文獻:
[1]邵瀅.“知人論世”與文學(xué)批評[J].贛南師范學(xué)院報,2010,31(04):78-81.
[2]王英娜.淺談文學(xué)鑒賞中的“知人論世”[J].科教文匯(上旬刊),2008,(04):178.
[3]于蘭.淺論曹雪芹人生悲劇與《紅樓夢》作品悲劇的關(guān)系[D].首都師范大學(xué),2009.
[4]光輝.羅蘭·巴特作者消亡思想述評[D].華東師范大學(xué),2006.
[5]魯迅.魯迅文集[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6.
[6]饒翔.知人論世與自我抒情[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7.
[7]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