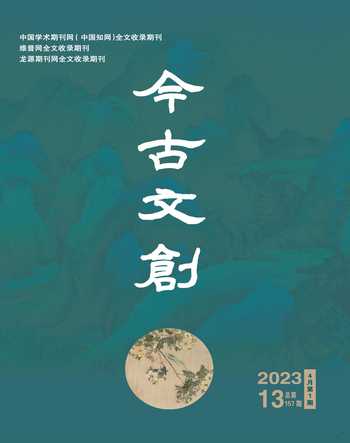譯者主體性視角下《女媧補天》英譯本對比分析
胡子月 冉玉體
【摘要】 譯者主體性是進行翻譯研究時值得關注的切入點,不同譯者的主觀選擇使得原文呈現出不同的翻譯效果。本文從譯者主體性視角入手,對丁往道和約翰·梅杰兩位譯者的《女媧補天》英譯本進行研究,分析譯者主體性在原文理解、翻譯策略方法兩個方面的具體體現。通過對比兩個版本的異同,為后續其他中國文化典籍的英譯本研究提供一定借鑒。
【關鍵詞】譯者主體性;女媧補天;對比分析
【中圖分類號】H315?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3-01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3.037
一、引言
神話是人類童年幻想的文明表達,中國神話故事英譯對于向外部世界傳遞中國先民遠古哲思、研究中華文明起源、促進文化交流與碰撞具有重要意義。作為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翻譯家,丁往道先生翻譯的《女媧補天》備受學界肯定。而對于外文譯者而言,直到2010年,才在美國專家約翰·梅杰及其他翻譯人員的共同努力下,推出了第一本英文全譯本The Huainanzi,且其海外發行、讀者接受程度等情況較好。(丁立福,2019:4)因其代表性,本文選擇丁、梅兩譯本進行比較研究,以探究譯者主體性對其產生的影響。
二、譯者主體性
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為達到翻譯目的而在翻譯過程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能動性、受動性和為我性是譯者主體性的主要特征。受動性指譯者翻譯時要尊重原文,不能隨心所欲進行翻譯。能動性是指在尊重原文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為我性指的是主觀能動性發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查明建,田雨,2003:22)本文將通過《女媧補天》英譯本的對比,從原文理解、翻譯策略與方法兩個方面對譯者主體性進行分析。
三、《女媧補天》英譯本實例對比分析
(一)對原文的理解
理解原文是進行翻譯的第一步,然而受到自身所處時代、知識儲備、文化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響,不同譯者對于原文的理解會有不同,進而在譯文中體現出其譯者主體性。本文通過具有代表性的實例,從詞匯選擇、句子理解、文化理解三方面對《女媧補天》不同譯本進行分析。
1.詞匯的選擇
例(1)
原文:
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
丁譯:
Then Nuwa melted rocks of five colors and used them to mend the cracks in the sky.
梅譯:
Thereupon Nüwa, smelted together five-colored stones in order to patch up the azure sky.
在這一例中,“煉”和“補”兩位譯者分別選擇了不同的詞匯進行表達。對于“煉”,丁譯本中的melt 通常指任何固體的熔化過程,而梅譯本中的smelt更多指的是金屬的熔煉。對于“補”,丁譯本選用mend一詞,側重于用針線對開裂之處進行縫補。梅譯本使用patch一詞,更傾向于“為天空打補丁將其修復”之意。對于“蒼天”,丁往道先生譯為the sky, 約翰·梅杰先生譯為the azure sky, azure指的是天青色,即將“蒼”字也譯了出來。兩譯本雖有不同,但都在尊重原文的基礎上進行翻譯,體現了譯者主體性中的受動性。而譯者選擇不同的詞匯進行表達,又體現出其能動性。
例(2)
原文:
火爁焱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
丁譯:
A great fire raged and could not die out; a fierce flood raced about and could not be checked.
梅譯:
Fires blazed out of control and could not be extinguished; water flooded in great expanses and would not recede.
在這一例中,“爁焱”指大火燃燒,“浩洋”指大水泛濫。丁譯本中rage指突然而猛烈發作的暴怒,race用作不及物動詞指的是全速前進。用rage形容大火熊熊燃燒的狀態,用race形容洪水泛濫的狀態,顯然是采用了擬人手法,更具畫面感,讓讀者感受到當時環境的惡劣,進而襯托出女媧功績之偉大。梅譯本中blaze out of control指火焰猛烈噴發,難以控制,flood in great expanses指洪水泛濫成災,這些詞匯幾乎沒有感情色彩。相比之下,丁譯本更側重于生動性,而梅譯本更加強調情況的客觀性。對于同樣的詞匯,不同的譯者因其想達到的翻譯效果不同而選擇不同的英文詞匯,體現了譯者主體性中的為我性。
例(3)
原文:
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
丁譯:
Savage beasts devoured innocent people; vicious birds preyed on the weak and old.
梅譯:
Ferocious animals ate blameless people; predatory birds snatched the elderly and the weak.
在這一例中,“顓民”指善良的人民,“鷙鳥”指兇猛的鳥,“食”即“吃”,“攫”指用爪取物。兩譯本進行對比,savavge意為“野蠻的殘酷的”,側重于未經開化,粗魯野蠻。Ferocious更強調兇猛和殘忍之意。beast 指野獸,而anminal則所指范圍更大,即區別于植物和礦物的動物總稱。丁譯本中savage 譯出了原文中的“猛”,beasts譯出了原文中的“獸”。梅譯本中雖然沒有“獸”的直接體現,但“殘忍的動物”也完全能夠傳達“猛獸”之意。對于“食”的翻譯,丁譯本中的devour相較于梅譯本中的eat,強調狼吞虎咽地吃,更能體現出猛獸的殘暴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兩譯本中innocent 和blameless都指無罪的、清白的,含義相近又有些許不同。innocent含有“無辜”之意,老百姓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卻難逃被野獸吃掉的悲慘命運,可見世間毫無正義可言,亟須女媧拯救百姓于水火;blameless含有“無可責備、無可非議”之意,傾向于針對某件事情來說當事人不應該受到責備。對于“鷙鳥”的翻譯,丁譯本中vicious指邪惡的、狠毒的,梅譯本中的predatory指食肉的。丁譯本中vicious birds強調鳥的兇殘,與前文“猛獸”相呼應。梅譯本中predatory birds強調是食肉性鳥類,自然順承后文“攫老弱”的句子邏輯。對于“攫”的翻譯,丁先生概括性地譯為“捕食”prey on,并未強調其動作。約翰·梅杰先生將其譯為“抓取”snatch,直接描繪出了“用爪取物”的動作。對于“老弱”的翻譯,二者都采用了定冠詞加形容詞的類似表達,只是old只強調年齡大,而elderly包含有對老人的尊重意味。中存在大量一詞多義和多詞一義的情況,不同譯者對原文和譯入語詞匯的感知和理解程度不同,就造成了譯文的不同,同樣體現了譯者的能動性。
2.句子的理解
例(4)
原文:
天不兼覆,地不周載。
丁譯:
The sky could not cover all the things under it nor could the earth carry all the things on it.
梅譯:
Heaven did not completely cover the earth, earth did not hold up heaven all the way around its circumference.
在這一例中,丁譯本中理解“天”所不能“覆”的是天下萬物,“地”所不能“載”的是地上萬物,天之下地之上正是萬物生存的空間,體現出中國傳統宇宙觀。將“周”譯為all, 表達全部、周全之意。梅譯本中將原文句子理解為“天”不能覆蓋“地”,“地”不能支撐“天”,且將“周”理解為地的圓周,與丁譯本的理解存在很大不同。丁譯本體現了中國傳統宇宙觀,梅譯本體現了非中文母語譯者對于中國“天”與“地”的理解。受限于原文卻又有自己的理解方式,這便是譯者主體性中受動性和能動性在句子翻譯層面的體現。
3.文化的理解
例(5)
原文:
四極廢,九州裂。
丁譯:
The four conors of the sky collapsed and the world with its nine regins split open.
梅譯:
The four pillars were broken; the nine provinces were in tatters.
在這一例中,涉及中國古代文化中“天圓地方”這一理念。在還未意識到我們生存在地球之上,而天空其實是浩瀚宇宙之時,古人認為,地為方形,天為圓形,地之四角之上的四根巨大柱子支撐著天空。丁譯本中the four conors of the sky指的是天被四根柱子支撐起來的四角,collapse即崩塌,天的四角塌陷,即四柱折斷。譯文不僅緊貼原文,而且形象地勾勒出中國古代先民心中天地之間的空間結構。梅譯本中the four pillars意為四根柱子,對原文進行直譯,但the four pillars并未揭示出 “四極”與“天”和 “地”之間的關系。這便體現出文化背景對譯者主體性的影響。“九州”指古代中國劃分為九州。但在古代先民還未看到外部世界之時,“中國”實際指的是整個世界,因此丁譯本the world with its nine regions準確傳達了原文含義。梅譯本中the nine provinces將“九州”理解為九個省份,仍限定在“中國”范圍內。如同漢語讀者在讀西方神話故事時,會想象故事發生在西方世界而沒有覆蓋中國,自然也就不會把西方世界理解為整個世界。對于“裂”的翻譯,丁往道先生采用with復合結構,split 含有裂開、切斷之意,能夠讓讀者想象出天崩地裂的災難場景。約翰·梅杰先生則是使用了介詞短語in tatters, 多形容衣服破破爛爛或人衣衫襤褸,也可形容抽象事物,如事業、名譽、計劃等的毀壞,此處形容九州的混亂狀況。 由此可見,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會影響譯者對原文的理解,從而形成不同的譯文,也正體現了譯者的能動性。
(二)翻譯的策略與方法
除了對原文的理解不同,由于譯者主體性,不同的譯者也可能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與方法,從而呈現出不同的譯文。
1.歸化與異化
歸化法是“把原作者帶入譯入語文化”,而異化法則是“接受外語文本的語言及文化差異,把讀者帶入外國情景”。(Venuti,1995:20)文中對于“女媧”的翻譯,丁譯本和梅譯本都采取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分別譯為Nuwa和Nüwa。作為中國古代神話中極為重要的代表人物,女媧有補天造人之能,承載著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意義。“女媧”與西方“上帝”的形象有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不同,因此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更能保留中國古代神話的特色,有助于譯入語讀者了解中華文化。對于“殺黑龍以濟冀州”的翻譯,丁譯本為She killed the black deagon to save the people of Jizhou,梅譯本為Killed the black dragon to provide relief for Ji province。“冀州”為中國古代九州之一,與上文“四極廢,九州裂”相呼應。丁譯本將“冀州”作為地名進行英譯,側重于“異化”。梅譯將冀州譯為Ji province,與其上文the nine provinces相呼應,側重于“歸化”。由此可見,翻譯策略不同,最終的譯文也就不同,這同樣是譯者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的體現。
2.直譯與意譯
例(6)
原文:
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
丁譯:
Nuwas deeds benefited the heavens above and the earth below.
梅譯:
Examining into these glorious achievements, we find that they reach up to the ninefold Heaven; they extend down to the Yellow Clods.
在這一例中,“九天”指古人認為天有九重,“黃壚”指的是黃泉下的黑土。丁譯本采用了意譯的翻譯方法,“九天”和“黃壚”分別用天heaven和地earth來表示。梅譯本采用了直譯的翻譯方法,“九天”譯為the ninefold Heaven,“黃壚”譯為the Yellow Clods。丁譯本側重于原文整體內涵的傳達,即女媧的功業福澤天地,簡潔明了;梅譯本則更加具體,注重對原文中意象的描述,更能讓讀者想象出“九天”與“黃壚”的形象。不同翻譯方法的采取體現了譯者主體性中的能動性和為我性。
四、結論
由以上例證可知,不同譯者在受到原文客觀條件制約的前提下,仍然會由于其能動性和為我性,在原文理解、翻譯策略與方法方面進行不同的選擇,進而形成不同的譯文。因此,譯者主體性是在進行翻譯研究時應該予以充分關注的重要因素。中國文化典籍內涵之豐富從《女媧補天》神話故事中可見一斑。而在研究典籍英譯的過程中,譯者主體性或許能為學者品鑒不同版本的譯文提供新的思路。希望本文能夠為后續其他中國文化典籍的英譯研究提供一定借鑒。
參考文獻:
[1]丁立福.論中國典籍譯介之“門檻”——以《淮南子》英譯為例[J].北京社會科學,2019,(6):4-14.
[2]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J].中國翻譯,2003,(1):19-24.
[3]L.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
作者簡介:
胡子月,女,漢族,河北懷來人,河南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語筆譯。
冉玉體,女,漢族,河南溫縣人,河南理工大學教授,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和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