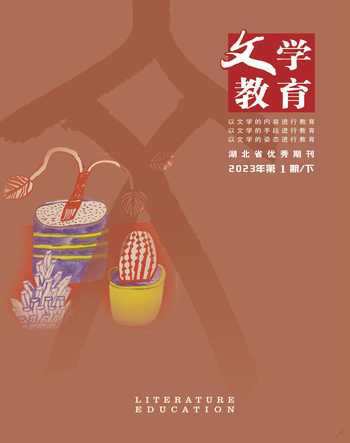論“霸史”和“偽史”的差異
孟欣晴
內容摘要:“偽史部”的設立最早出現在南朝梁《七錄》,“霸史”類的設立最早出現在唐初《隋書·經籍志》。“霸史”雖脫胎于“偽史”,但并不等同于“偽史”,其一,《隋書·經籍志》的“霸史”類所包含對象的范圍比《七錄》的“偽史部”小;其二,“霸史”和“偽史”的概念義基本一致,但是色彩義中的感情色彩存在差異,“偽史”具有明顯的貶義色彩,“霸史”的感情色彩比“偽史”更加積極。
關鍵詞:目錄 “霸史” “偽史” 差異
受南朝梁阮孝緒《七錄》中“偽史部”的分類標準影響,“霸史”和“偽史”的詞義通常被認為是完全一致的。唐以后的《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等沿用《隋志》立“霸史”類,《舊唐書·藝文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遂初堂書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沿用《七錄》立“偽史”類,對于當時所認為的非正統政權的史書,一直都沒有固定使用“霸史”或者固定使用“偽史”命名,甚至《文獻通考·經籍考》的分類目錄直接使用“偽史霸史”這一名稱。“霸史”和“偽史”一直都是混用的。但實際上,《隋志》使用新詞“霸史”,而不是照搬《七錄》中的“偽史”,這本身就已經表明“霸史”與“偽史”是不同的。現當代有個別研究者注意到了“霸史”和“偽史”的不同①,但并未進行深入和詳細的探討,因此本文擬對“霸史”和“偽史”的概念和對象等進行梳理和比較,結合魏晉南北朝和唐初的正統觀和民族觀,深入探討《隋志》中的“霸史”和《七錄》中的“偽史”的差異。
一.“霸史”的概念及對象和“偽史”的概念及對象
西漢班固所撰《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目錄學文獻,“六藝略”的“春秋”類記史書。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從《漢志》所記“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1],增加到《隋志》所記“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2]992,史學發展迅速,史書脫離了“春秋”,別為一部。南朝梁阮孝緒《七錄》的“記傳錄”記史傳,有“國史部”和“偽史部”等12個小類。發展到《隋志》,目錄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史部下有13個小類,分別是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目錄文獻中第一次出現“霸史”這個詞。
《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十三個小類中,地位最尊貴的應當是排在第一位的“正史”。通過對《隋書·經籍志》所列史書的分析,《隋志》中的“正史”應當指以帝王本紀為綱的紀傳體史書,同時《隋志》也將為這些紀傳體國史進行注解的書列入了“正史”類。“正史”的“正”當有兩層意義:第一是體裁正,依照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的紀傳體體例編寫而成的史書;第二是本紀所記對象正,正史中本紀所列的政權,其正統性在后世基本上能夠得到廣泛承認[3]。
《隋志》對“霸史”的描述是:“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后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爾朱之亂,并皆散亡。今舉其見在,謂之霸史。”[2]964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霸史”是指獨立于合法政權以外的割據政權的歷史,它們“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不管使用何種名號何種方式稱霸,終究不是正統。這段話對“霸史”的對象也作了明確說明,即永嘉之亂之后各地的割據政權。具體來說,“霸史”包含的對象是永嘉之亂后除被唐初史官認為包含在“正史”中的東晉、宋、齊、梁、陳、北魏、西魏、北齊、東魏、北周史書之外的所有割據政權的史書,其所指政權不僅有《十六國春秋》記載的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后秦、成漢、前涼、西涼、北涼、后涼、后燕、南涼、南燕、西秦、北燕、夏,還有不在十六國之列的吐谷渾、翟魏等割據政權,比如《趙書》《二石傳》《二石偽治時事》記載后趙史事,《漢之書》記成漢史事,《燕書》記前、后燕史事,《南燕錄》五卷、《南燕錄》六卷、《南燕書》七卷記南燕史事,《燕志》記北燕史事,《秦書》記前秦史事,《秦紀》記后秦史事,《涼記》八卷、《涼書》十卷(記張軌事)、《西河記》記前涼史事,《涼記》十卷記后涼史事,《涼書》十卷(高道讓撰)、《涼書》十卷(沮渠國史)記北涼史事,《拓跋涼錄》記南涼史事,《敦煌實錄》記西涼史事,《漢趙記》記前趙史事,《吐谷渾記》應為記吐谷渾政權史事,此條下還記載有“梁有《翟遼書》二卷……亡”,《翟遼書》應為記載翟魏史事。
何為“偽史”?最早的解釋出自唐代劉知幾的《史通·因習》:“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創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還依阮《錄》。”[4]對比《七錄》被保存下來的目錄②和《隋志》的目錄,《隋志》霸史類與《七錄》的偽史部相對應。按照劉知幾的解釋,“偽史”記載的是非正統的僭偽政權,《七錄》偽史部包含的對象應是東晉南北朝時期東晉、南朝的宋、齊、梁之外的所有政權的史書,前趙、后趙、前秦、后秦等政權都是“僭盜”。“偽史”帶有強烈的批判色彩。至唐,《隋志》對書籍的分類還依照流傳下來的《七錄》,這是對前人史書分類技巧和經驗的繼承,并不是對情感和態度的繼承,因為隋唐時期,以前在這片土地上的各個國家統一成了一個國家,沒有你我之分、偏愛和憎惡之分。
從《隋志》“霸史”和《七錄》“偽史”所包含的具體對象可以看出,“偽史”所包含的對象,范圍(這里比較的是對象的范圍,而不是對象的數量,因為《七錄》和《隋志》撰寫的時間不同,梁以后朝代的史書《七錄》都不可能記錄)比“霸史”更大,至少“偽史”比“霸史”多包含了北朝政權的史書。
二.“霸史”和“偽史”的詞義
詞匯意義可分為概念義和色彩義。概念義的作用在于給詞所聯系的事物劃一個范圍,凡是該詞所指事物都包括在內,凡不是該詞所指事物都不包括在內。色彩義附著在詞的概念義之上,表達人或語境所賦予的特定感受,可分為感情色彩、語體色彩、形象色彩。[5]感情色彩指詞義中所反映的主體對客觀對象的情感傾向、態度、評價等內容。
由第一部分可知,“偽史”和“霸史”的概念義是一致的,都是獨立于合法政權以外不被承認正統性的割據政權的史書,合法政權的認定是史書著者本人或史書著者所在國站在自身的角度衡量后判定的。在色彩義中的感情色彩方面,“偽史”含有明顯的貶義色彩,是“僭盜”即非分竊取政權的賊子創建的非法國家的歷史。而最開始使用“霸史”這一分類的《隋志》并沒有表現出對這些獨立于合法政權以外的割據政權強烈的斥責和蔑視,對這些政權“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的評價可證,認為它們也有君臣忠義的氣節,致力于治理國家養育百姓。
《隋志》開篇的大序,有對《七錄》的概括和評價:“有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2]903說明唐初《七錄》還未散佚,魏征等人看到了完整的《七錄》,才能對其題目和內容進行概括和評價。沒有沿用《七錄》中“偽史”這一詞語,而是改用了“霸史”,可見唐初史官并不認同阮孝緒“偽史”類史書的命名,對“偽史”類包含的對象也重新進行了劃定。改用“霸史”及重新劃定此類史書所包含的對象,也從側面體現出唐初史官對此類史書不同于南朝梁阮孝緒的評判。
三.從正統觀和民族觀看“霸史”和“偽史”感情色彩的差異
《隋書》是唐初官方所修撰的一部史書,在政權正統的政治問題上,其所持立場當和初唐時期的官方態度一致。結合唐初官方對于各割據政權所持的態度,能幫助我們理解“霸史”的感情色彩以及唐初史官用“霸史”而不用“偽史”的原因。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東晉及宋齊梁陳只能偏居江南,被迫離開中原,這對有“大一統”儒家思想的漢族是難以接受的,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自身實力不足以抵抗夷狄入侵的戰亂時期,正閏問題與民族關系往往混為一談,漢族尤為強調“夷夏之辨”和政權的“正統性”,并以此為武器抨擊其他少數民族政權③。夷夏之間矛盾越尖銳,對抗越激烈,漢族的民族意識也就越強烈。從曹魏時期開始,因東漢末天下大亂,少數民族介入兵亂者不在少數,故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隨之加深,“夷夏之別”和“正統性”意識也隨之強化。各少數民族政權受儒家“受天命”思想的影響,各政權統治者都聲稱自己是“受天命”的正朔所在,其他割據勢力則是“僭偽”。南北朝時期,各政權爭“正統”的論戰更為激烈,都極力蔑視對方以抬高己方的地位,表現在史書中就是這一時期編成的史書都以本朝帝王為本紀對象,放在最高的地位,以及使用大量侮辱性的詞語稱呼其他政權,比如南北朝時期編成的《魏書》在對南方政權的稱呼上侮辱性表現地尤為明顯。“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6],阮孝緒雖不入仕,但這并不妨礙他受這種正統思想和民族思想的影響,反映在《七錄》里,是劃分出“國史部”和“偽史部”,以“國史部”的命名強調南朝政權的正統地位,以“偽史部”的命名表示對北方各割據政權的斥責和蔑視。
與政權林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同,初唐時李氏政權是一個南北大一統的政權,沒有其他強有力的政權和自己爭“正統”,李唐的“正統”地位已經得到確立。疆域的統一需要民族的統一,用以鞏固政權、穩定社會。而民族的統一,除了武力的震懾,還需要正確的民族思想來處理民族關系,“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成為處理民族關系的思想基礎。因此對于正統問題和民族問題,唐初統治者保持了一種包容的態度,唐初史家也能把政權正閏與民族關系區分開來加以討論。在正統問題上,唐高祖李淵下達的《修魏周隋梁齊陳史詔》明確表明了對東晉南北朝時期的南北政權的態度,詔書說:“自有晉南徙,魏乘機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于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于時。”[7]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北魏至周、隋的北朝政權還是東晉、宋、齊、梁、陳的南朝政權,對他們政治上的功績,唐高祖都從大一統的政治局勢出發給予了肯定,這篇對歷史上的政權問題作了相對客觀認識的詔書,成為唐初諸史修撰的指導思想,并在其中得到具體的反映,對唐代史學影響深遠。在《隋志》中的反映就是把東晉、宋、齊、梁、陳的國史與北魏、北周的國史都列在了“正史”類,以這種做法顯示南北政權的平等地位。在民族問題上,唐高祖曾說:“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8]唐太宗更提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9]的觀點。
從李唐對正統問題和民族問題開放包容的態度,看“霸史”和“偽史”的不同。《隋志》的“霸史”類小序指出,永嘉之亂后那些據有中原的政權“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一一查看“霸史”中列舉的史書,“推奉正朔”的政權指的應當是向東晉上表稱臣的前涼和西涼政權,這兩個政權表面上尊奉東晉,實際上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割據勢力,向東晉稱臣只是一種外交手段。“假名竊號”的政權指的應當是除了“正史”里的政權和向東晉稱臣的前涼、西涼以外的所有割據政權。雖然這些割據政權“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但是唐初史官并不認為他們是篡逆,只是因為特殊局勢而只能以稱霸一方的方式保持自己,《隋志》對這些政權的評價是:“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認為這些割據政權有君臣忠義之節,也有治理國家管理百姓的功勞,從這句話看,唐初史官在肯定各政權的政治功績、“中華與夷狄同”的思想上與唐初統治者是保持一致的。盡管由于時代的局限,唐初的史學家還不能完全消除偏見,對所有政權一視同仁,但此時的史學觀相比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進步和開闊了許多。“霸史”一詞是在唐朝初期這個特定時代,在比較開放包容的正統觀和民族觀的思想下發展而來的,這個詞盡管不含褒義色彩,但在唐初也不是貶義的,并不等同于“偽史”。“霸史”是特定時代發展的產物,是對正統政權歷史以外的各割據政權歷史客觀評價的詞語。
另外還可以從《隋志》“霸史”類的記載來看二者。“霸史”類有這樣6條記載:“《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記石勒事。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南燕錄》五卷 記慕容德事。偽燕尚書郎張詮撰”“《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偽燕中書郎王景暉撰”“《涼記》八卷 記張軌事。偽燕右仆射張諮撰”“《涼書》十卷 記張軌事。偽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涼記》十卷 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這6條記載,凡是屬于“霸史”類所包含的政權國家的史書作者,其所屬國家前都冠有“偽”字。而“霸史”類下還有這樣3條記載:“《燕志》十卷 記馮跋事。魏侍中高閭撰。”“《秦記》十卷 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都和撰”和“《十六國春秋》一百卷 魏崔鴻撰。”[2]964同屬于霸史類,前面6條記載的史書作者所屬國前冠有“偽”字,后面3條記載的史書作者所屬國前未冠“偽”字,這說明在撰寫《隋志》時,前面6條記載中的“偽”字是直接抄錄《七錄》而來,因為如果不是直接抄錄《七錄》而來,身為南朝梁人的阮孝緒,應該也對北魏的作者高閭、崔鴻的所屬國家前冠以“偽”字。《隋志》在目錄分類中使用“霸”史,不會在本目錄下記載具體書目時,又使用“偽”字這種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后面3條記載中,“魏”前的“偽”字被刪去。可以推測出,《七錄》記載“偽史”類時,凡是屬于東晉、南朝之外的國家,阮孝緒都在其所屬國家前冠以“偽”字,以示南朝的正統性。《隋志》“霸史”類將史書作者所屬國屬于《隋志》“正史”類的國家前的“偽”字刪去,“正史”類政權之外的國家前的“偽”字照抄了下來。一方面,或許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唐初史官還受中國傳統的正統、非正統思想的影響,或許是為尊重前人及不妄改著作內容的習慣,《隋志》在記載具體書目時,照抄了《七錄》具體書目前的“偽”字;另一方面,史部分類時,改用“霸史”命名而不沿用“偽史”及重新劃定此類史書所包含的對象,可見唐初史官并不認同《七錄》用“偽史”這個明顯帶有貶義的詞語命名此類史書及對此類史書劃分范圍的不認同,才會改用“霸史”客觀的歸納此類史書。
《隋志》的“霸史”所包含對象的范圍比《七錄》的“偽史”小。“霸史”和“偽史”的概念義是一致的,都是獨立于合法政權以外不被承認正統性的割據政權的史書,合法政權的認定是史書著者本人或史書著者所在國站在自身的角度衡量后判定的,但是它們色彩義中的感情色彩有差異。“偽史”含有強烈的貶義色彩,所指政權均為“僭盜”,“霸史”的感情色彩比“偽史”要更加積極,所指政權并沒有被指責為篡逆,甚至它們有君臣忠義的氣節,治理國家養育百姓的功勞。霸史是唐初由分裂走向統一、動蕩走向穩定的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相對于前代,初唐對各割據政權的看法更加客觀。從南朝帶著強烈貶斥情感的“偽史”到初唐客觀的“霸史”再到宋代混用的“偽史霸史”,最后到《四庫全書總目》中清代史官改用弱化情感色彩的“載記”,時代的意識會反映在文獻中,反過來,從文獻中也能看出時代意識的變化。“霸史”和“偽史”都是特定時代下產生的特色目錄名稱,對于研究目錄學、正統觀和民族觀都具有重要意義。
注 釋
①相關研究可參見馬鐵浩:《<史通>與先唐典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196頁;王強:《論霸府與霸史》《寧德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②《七錄序》,《廣弘明集》卷三,四部叢刊本。
③關于唐初正統觀和民族觀,李珍:《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民族史觀的演變》,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1月第27卷第1期;許殿才:《魏晉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整合》,求是學刊2012年3月第39卷第2期,作了較全面的闡述。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M].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4:1781.
[2]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3]王強.論霸府與霸史[J].寧德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1):40-44.
[4]劉知幾.史通[M].北京:中華書局,2014:223.
[5]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第一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19.
[6]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3342.
[7]董誥.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32.
[8]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18.
[9]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6247.